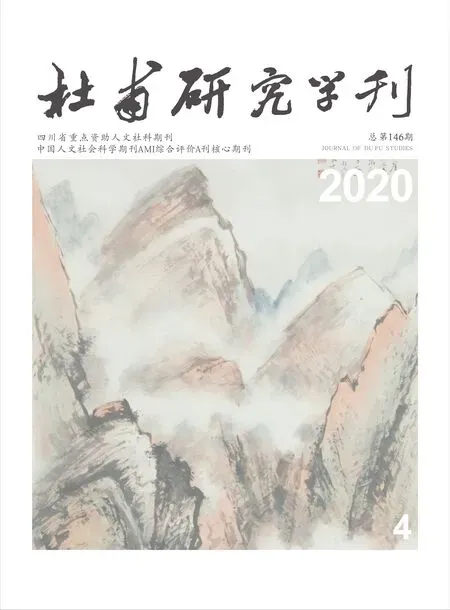论缪钺先生的杜诗研究
张 月
缪钺(1904-1995),字彦威,江苏溧阳人,著名文史学家、教育家,历任河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广州学海书院教授兼编纂、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华西协合大学中文系教授、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作为一位文史兼通的学术大家,先生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成就斐然,如《诗词散论》《杜牧年谱》《灵谿词说》(合著)皆为不刊之论。先生将中国古典文学作为早年和晚年的治学重点,对中国文学史和古典诗词剖析入微,尤对唐宋诗词致力颇深,对重要作家如屈原、曹植、陶渊明、陈子昂、杜甫、杜牧、李商隐等人都有专文论述。对于“开启后世法门”的杜甫,先生尤为推崇。在先生七十年的教学和治学生涯中,开设过杜甫、杜诗相关课程①,出版有专著《杜甫》,并撰写了《曹植杜甫诞生纪念》《杜诗中含蓄之法》《杜甫的生平及其诗歌创作》《陆游与杜甫》《杜甫如何改诗》《略论对杜诗遗产的全面继承》《成都杜甫草堂》等一大批关于杜甫和成都杜甫草堂的学术论文和介绍性文字。刘明华在回顾现当代杜甫研究时指出:以萧涤非、程千帆、缪钺、罗宗强等为代表的学者“既有深厚的旧学基础,又不乏现代学术理念”,“是他们奠定了百年杜甫研究的基础,推进了杜甫研究的深入”②。此论甚允。
然而目前学界对于缪钺先生学术成就的关注多在其史学研究、古典文学研究、治学方法等方面③,对其杜诗研究关注甚少,笔者不揣谫陋,拟对先生的杜诗研究进行梳理总结,以重新认识先生在古典文学研究以及整个杜甫研究史上的成就。
一、论诗:以“质形用”论杜诗之集大成
1932 年,时值杜甫诞辰一千二百二十周年,缪先生在《大公报》上专门撰文,对杜甫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发表了精到见解:“至杜甫出,于五七言律诗则以人巧夺天工,发神明于规矩,开阖变化,广启法门;于七古则纵横盘曲,惟意所之,长短奇偶,无不兼备;即于五古,亦不为六朝所囿,而叙论时事,长近千言,开前人未有之体。……大之忧时伤乱、倦念民生,小之一已所经、亲友离合以及山水灵光、鸡虫得失,莫不行之吟咏,发为篇章。”④他认为杜甫生于集大成的时代而又有集大成的容量,故能成为集大成之诗人,他既注意到杜诗内容的博大广阔与艺术成就的精益完美;又从道德层面赞颂杜甫继承了孔子、屈原锲而不舍的救世精神⑤,无愧“诗圣”之名。其实早在1929 年《学衡》第69期的《诠诗》一文中,缪先生就对杜诗的地位和价值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通过对杜诗的诠释、品评,他认为杜诗在“质形用”三方面都完美符合“诗”的最高标准。在他看来,凡物之成,有形有质,故杜诗作为“质形用”之集大成者,其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都值得后世学习探究。
(一)杜诗之“质”,涵盖三类
缪先生将诗之质分为三类:灵锐之感、深远之思、温厚之情,“灵锐之感,本之禀赋;深远之思,俟诸学识。至于温厚之情,则固为天生,亦赖涵养”⑥。他认为杜诗深闳广大,兼备三类。首先,灵锐之感乃人之禀赋,是诗人触物生情、睹物生思之能力,如《春望》诗中所写“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其次,杜诗中的温厚之情,在明清便得到极大推崇,“明人之论诗者,推杜为诗圣,谓其立言忠厚,可以垂教万世也”⑦。清人朱一新言:“杜诗原本忠孝,其性情之纯摯,随处涌见。虽许身稷、契,未知如何,然于温柔敦厚之旨,则深有契矣。”⑧清人卢德水云:“杜诗温柔敦厚,其慈祥恺悌之衷,往往溢于言表,人所固有。”⑨先生先举《寒峡》一诗,指出杜甫由自身处境想及百姓,居穷不怨且能自慰,饱含温厚之情;更以《除架》《废畦》为例,认为其“敦厚之情,不但能藏诸己,感乎人而已。兼能推其情以化万物,蠢然冥然之物,自诗人视之,皆有温柔敦厚之情焉”⑩。然而他人纵有温厚之情,却未必能有深远之思,杜诗则兼而有之,“杜甫诗中不但思弟妹,惜妻孥,于君则一饭不忘,于友则千里相慕而已。且悯万民之震愆,伤禽鱼之所失,是其情之广也。……如曹植、阮籍、陶潜、杜甫,莫不有深远之思”⑪。无论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⑫中抒发对家人的思念;或是“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中寄托的对李白才情的赞赏、对友谊的珍视;抑或是“幸结白花了,宁辞青蔓除” 的代物揣分,“岂敢惜凋残”的代物安命,都流露出对世间万物一视同仁的温柔敦厚之情。
(二)杜诗之“形”,“四尚”兼备
缪先生所言诗之形专指诗歌发表之方法,格调、音律不论在内。诗质想要达到深远、温厚、灵锐,诗形必与之相辅相成,如此诗歌才能臻为上境。先生总结诗形有“四忌”“四尚”:“四忌”指“质、直、拙、滞”,“四尚”曰“文、婉、灵、浑”。杜甫之所以取得如此“丰功伟绩”,除其自身天才卓越外,更因其“忠实于艺术”,不论是“新诗改罢自长吟”,抑或是“老去渐于诗律细”,又或是“语不惊人死不休”,都强调对诗艺的研磨、追求。在先生看来,杜诗“四尚”兼备,浑然一体,这其中委婉含蓄之法最为突出,故此处以之为例。
先生认为杜诗表达“含蓄”的方式有“空灵蕴藉”与“沉郁顿挫”,二者皆可达到“言近旨远”“兴寄深微”。他赞同杜甫自叙“新诗改罢自长吟”,“作诗造句贵婉折而忌平直,贵含蓄而忌浅露”⑬,并采用对比的手法将《江南逢李龟年》与《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一同审视,同样是表达抚今追昔之感、家国动荡之乱,前者空灵蕴藉,后者沉郁顿挫;前者是“子美之逢龟年,百感交集,而括以四言”,后者是“简括浑融之笔,以唱叹出之”,杜甫用七言绝句和七言古体,将复杂曲折的情事,辅以简要融贯之笔,使诗歌“如聆雅奏,余音绕梁,如饮佳茗,回甘满颊”,充满含蓄之美。⑭再如《兵车行》、“三吏”“三别”皆为讽刺现实的叙事性诗歌,极具战斗力,诗人却写得相当含蓄,“言有尽而意无穷” 更能引发读者深思。
(三)杜诗之“用”,三训俱备
缪先生认为匡正时弊、言志抒怀乃诗之根本,如《毛诗序》所言:“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⑮因此在《诠诗》的文末他驳斥了那些认为诗歌徒有其表、空无一物的错误观点——“(诗歌)既有顺美匡恶化民淑世之功,复为言志抒怀传世行远之具,世有谓诗为空华无实玩物丧志者,亦所谓蔽于一曲,暗于大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者矣”⑯,明确指出诗之抒情、言志与教化的功能。
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阐释 “诗有三训”(即承、志、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为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坠,故一名而三训也。”⑰先生将此“三训”谓为诗之“用”,即诗歌的教化作用,并作进一步解释:“诗歌与政通,语出一己而情周百姓,同时者可以观国,易代者可以论世,此所谓承。有情进而感思,思满而作,此所谓志也。诗歌化其感情,礼法导其理智,诗之温柔敦厚谓之持。”⑱杜甫出生于一个“奉儒守官”的传统世家大族,胡可先曾总结杜甫家学的特点“首先表现在儒学世家,其次表现在文学世家”⑲,受家族家风影响,杜甫一生都怀着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因此杜诗中常见对时事的关注、对百姓的关心,以诗歌记录时事,针砭时弊,这正是先生所言杜诗之“用”的具体表现。对此先生极为推崇并在诗歌创作中实践这一观点,下文将详细论述。
二、创作:崇杜与学杜
缪先生少时即开始旧体诗词创作,自十四岁创作第一首《蟋蟀》诗始,在此后八十余年中,吟咏不断。先生曾言“夫真知出于实践,评议古人诗词者,如不能自作,则无从谙悉其中甘苦,亦难以探索古人作品之深情远旨、精思妙诣”⑳。故其诗词皆出肺腑、真情实感。先生现存诗词400余首,纵观其诗词无论是古体还是近体,小令或是长调,均能得唐宋人神韵理致。其诗多伤忧国事、哀悯民生之作,反映了以先生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的关注与期盼,这与杜诗中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情怀一致,故有学者称其诗词“上继风骚轨辙,为现代诗史”㉑。翻检先生与友人的通信,无论是战乱时期写给郭斌龢信中提到的“惟以杜诗遣日”,或是解放后以“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表达与友人胡厚宣阔别廿载重逢的喜悦,又或是与吉川幸次郎的信中以“文章千古,得失寸心”来形容因杜甫而结缘的中日学者间的友谊,都能从中寻见杜诗的痕迹,可见先生对杜诗的熟稔达到了信手拈来的程度。先生在创作中主动学习杜诗,从杜诗内容和精神等方面汲取养分,创作了多首仿杜之作。通读先生诗词,可从中窥见他对杜甫其人其诗的推崇以及在创作上的师法。
(一)崇杜
1、对杜甫“诗史”精神的继承
自晚唐孟棨《本事诗》最早记载杜诗:“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㉒此后“诗史”说至宋代被广泛接受,宋祁、王得臣、陈岩肖、胡宗愈等都袭用这一观点㉓,以“诗史”指称杜诗,其指向的是其所具有的史的特质。杜诗所代表的“诗史”精神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每当中华民族劫难之时,仁人志士无不奉杜诗为圭臬,言志抒怀。缪先生继承杜甫“诗史精神”,其诗作深刻反映了社会现实,为国家民族危难而忧。战乱时节缪先生自保定南下开封,困居巴蜀,后到贵州,终留成都,一生辗转四方、离家万里,历经抗战播乱之苦。自身经历的波折坎坷与国难时期的爱国之心两相交织,使先生产生了与杜甫异代同时之感,能够自觉从思想上亲近杜甫。故在国家动荡、民不聊生这一特定时期,先生在诗歌创作中将杜甫忠君爱国之心置于首位,并以杜诗作为穷愁之中宽慰己心的一剂良药。先生有《寒夜感怀》一诗:
三年时命秋荼苦,千里关河战伐新。子路有亲思负米,少陵伤乱每沾巾。寒风簌簌偏侵袂,明月娟娟肯向人。此夜何堪怜病弟,万端愁绪入孤颦。㉔
此诗作于1927 年,是年国民革命以及国共内战的爆发,使得国家时局陷入动荡之中,先生胞弟缪锺也身患肺结核,命悬一线。在如此凄凉寒夜,先生身处动乱时局,又想到家中重病的胞弟,不免“万端愁绪”涌上心头却无处消解,诗中借“子路负米思亲”来寄托对亲人的思念,用“少陵伤乱沾巾”表达对时局的担忧,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将先生的思念与忧虑的复杂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
写于1932 年的《吴碧柳挽诗》是哀悼友人逝世之作:
……中间曹与杜,日月照百世……悲悯热中肠,长歌多涕泪。如读少陵作,相见天宝岁。远合诗教宏,岂矜雕虫艺。木铎天使鸣,大声振聋聩。方期老成时,弥见诗律细……
吴芳吉,字碧柳,民国时期重要的教育家、爱国诗人,其独创的“白屋诗”以忧国忧民为基调,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先生听闻吴芳吉病逝,遂作此诗以志哀恸,他与吴芳吉虽未有面交之缘,却因故友吴宓的介绍早已对其钦佩欣赏,盛赞其为人“不偭规矩”,为诗“天骨开张”。值得一提的是,吴芳吉本人对杜甫甚为推崇,不仅从思想上高度认同杜甫忠君爱国思想,更在诗歌创作上学习模仿杜诗。㉕挽诗中缪先生多处化用杜诗词语,如“悲悯热中肠”乃化用杜诗“惊呼热中肠”;“方期老成时,弥见诗律细”乃由杜诗“庾信文章老更成”“晚节渐于诗律细”二句诗绾合而成。另外先生将吴诗比作杜诗,“如读少陵作,想见天宝岁”,将吴芳吉与杜甫并举,较为贴切,可见先生对吴芳吉做人为诗的高度评价。尤可注意的是,此时中国正处于全民抗战的国难时期,先生把对友人逝世的哀痛放置在雅废国微的大背景之中,用“多难国陵夷,久战民憔悴”之语细述疮痍现实,同杜甫一样将国家伤痕诉诸诗笔,从中可见先生对时局的关注,对战争的批判。
诸如此类之作还有1935 年至1937 年间创作的《自题〈元遗山年谱汇纂〉后》《遣愤》《四君咏》等诗。自1931 年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国家祸乱频仍,百姓民不聊生;1937 年卢沟桥事变,北平、天津相继沦陷,8月先生携家自保定南下开封,暂居友人薛声震宅;10 月经其介绍,应聘至河南信阳师范学校教授“国文”,“以后行止恐将随时局之变化而定”㉖,这一年先生多方奔走、生活动荡,故多借杜甫其人其诗抒发对时局的担忧、以及自身漂泊无依的喟叹:
白傅乐章多讽世,杜陵诗句最哀时。(《自题〈元遗山年谱汇纂〉后》其四)
史公牛马走,杜甫凤凰饥。(《遣愤》)
杜公热肠人,期君尧舜上。丧乱哀生民,升平责诸将。(《四君咏》其四)
与战乱时期不同,抗战胜利后缪先生诗作中较少对现实的直接揭露而多为抚今追昔之感慨。如1946 年先生得吴宓推荐,结束在浙江大学近7年的教学,应聘至华西协合大学,担任中文系教授兼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同年先生联想到与蜀地有密切关系的司马相如、扬雄、杜甫、韦庄、范成大等五人,写下《成都怀古五首》,其四“讥弹时政成诗史,卓尔江干有草堂。自古骚人论气节,杜公日月同争光”,应为游成都草堂后感怀杜甫而作,将杜甫的诗史实录精神,以及高标气节高度凝练于这首七绝之中。
2、对杜甫交友重情之赞许
缪先生崇杜还表现在对杜甫为人重情的赞许,将杜甫以志交友自我比况,抒发对友情的珍视。杜甫被梁启超称为“情圣”,“因为他的情感的内容,是极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㉗,杜诗中随处可见其对亲人、友朋的咏叹和热爱。因此先生择取杜甫交友事典,化入与友人酬唱诗中,如“共居未谂离群苦,小别相思情转亲。过岁况逢华胜日,寄诗肯负草堂人”(《人日寄怀李子㧑、许君远》)、“孤客逢人日,题诗寄草堂。当窗喜种竹,经雪可成行”(《人日寄怀张效直先生》),诗中用杜甫与高适人日寄诗相赠的典故与自己和李子㧑、许君远、张效直之间的友谊相比,表达“佳节倍思亲” 之感。另外先生还借用杜甫与李白的友情形容其与吴宓、叶嘉莹的情谊,如“晦庵尊子静,杜甫梦青莲”(《赠吴雨僧》),“少陵怀太白,永契夙心亲”(《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日,初识叶嘉莹教授于草堂。十月二十日,倏已半载矣,赋此见怀》)。先生与吴宓的友情长达半个世纪,从20年代经友人李濂堂介绍与之始有神交,到1929年夏在北京清华园首次见面,二人讲学论文,甚为投机,至此成为一生挚友。先生与叶嘉莹则是因诗圣杜甫而相识,二人初次见面于1981 年4 月下旬成都草堂举办的杜甫研究学会第一届年会上,初逢即如旧识,“别后经常通函论学……与叶君相互勉励,计划合作有所撰著”㉘,此后十余年间二人合撰《灵谿词说》及其续编《词学古今谈》,就平日读词心得,自创体例成书,二人的友谊也成为学界佳话。此外先生与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先生也因杜甫而结缘,1979年先生在杜甫草堂接待吉川幸次郎率领的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者访华团”,与吉川先生相谈甚欢,以诗相赠,“蓬海嘉宾到草堂,杜公祠宇更辉煌。扶疏古木侵云上,迤逦清江绕寺长。能为生民歌病苦,应同皎日竞光芒。晁衡高谊垂千载,文化交流继盛唐”(《日本吉川幸次郎教授研精杜诗,士林宗仰,一九七九年四月,率日本学者访华团远来成都,拜谒诗圣草堂欢聚,欣聆清论,奉贻长句,以志景慕》)。全诗用唐代晁衡的典故追溯盛唐以来中日文化交流研究的源远流长,并展望了新时期以吉川先生为代表的域外杜甫研究新前景。8月先生又作“草堂寻胜迹,讲舍挹清芬。慰我新诗简,飘如出岫云。月明生海上,此际最思君”(《吉川幸次郎教授自日本京都寄诗见怀,赋此奉酬》),表达了自成都一别后对吉川先生的思念。
(二)学杜
1、诗教观的效法
诗歌的教化作用被视为诗歌好坏的重要评判标准,中国传统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缪先生少读儒书,受其浸染,重视诗歌“温柔敦厚”的教化作用,认为“《诗经》三百,义归无邪,尼父之旨,盖贵中正,哀乐不陷于伤淫,讽刺能归于敦厚”㉙,他更进一步指出“诗教”还应包括孔子所谓“兴观群怨”。他在《与梁鹤铨论诗》《吴碧柳挽诗》《吴雨僧寄赠黄晦闻先生〈蒹葭楼诗〉》三首诗作中,对自己所持诗教观有不同程度的论述:
诗思重无邪,偏激非所尊。风雅久坠地,万士恣淫昏。宿儒囿封域,小生噪蝇蚊。孰为高蹈才,邈然凌秋云。温厚培本教,吐辞亦自文。阮陶耀奇采,宁以字句论。努力千载业,攻错古所敦。(《与梁鹤铨论诗》)
礼亡国为戎,诗教久衰敝。何堪丧斯人,南望独流涕。……歌咏自生民,风骚最温丽。逶迤二千年,作者纷变异。句别五七言,体殊古今制。末分源则同,一本无邪思。中间曹与杜,日月照百世。汉唐世运昌,声诗何雄厉。(《吴碧柳挽诗》)
盖棺诗百首,姑射神人姿。峥嵘经世志,岂料空文垂。早树攘夷论,功成弃若遗。故人满廊庙,穷居惟说诗。欲持敦厚教,力挽风俗衰……(《吴雨僧寄赠黄晦闻先生〈蒹葭楼诗〉》)
由上可知,先生“诗教”观包含两方面,即“温柔敦厚”与 “兴观群怨”。他认为诗歌不光是具有形式美的艺术,也是内容与情感共鸣的载体,应重视诗歌对政治、社会、文化、人生的作用和影响。他推崇杜甫、阮籍、陶渊明,认为他们诗歌文采四溢、高情远韵,尤其杜诗“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符合“温柔敦厚”之旨,如杜诗《又呈吴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被清人认为极具“温柔敦厚”之味㉚;且“《三百篇》兴、观、群、怨,事父、事君、鸟兽、草木之义,惟杜诗备”㉛,因此被历代文人不断推崇直至成为集大成,正是先生最好的效法对象。
缪先生以敏悟博学之资,发温柔敦厚之教,阐兴观群怨之旨,重视诗歌对社会政治的教化作用。他于1932 年所写《吴碧柳挽诗》陈述了诗歌衍变与国运兴衰间的紧密关系,通过梳理诗体发展史,指出五言诗与五七言律诗分别因曹杜二人得以成立和成熟;同时又着眼于诗教,将“歌咏自生民,风骚最温丽”“汉唐世运昌,声诗何雄厉”与今日“礼亡国为戎,诗教久衰敝”相比,突出了如今国运不昌,诗教不存的现状。《吴雨僧寄赠黄晦闻先生〈蒹葭楼诗〉》更是以诗言志、针砭时事的典范,1935年近代著名学者、诗人黄晦闻先生辞世,缪先生观其《蒹葭楼诗》一书,睹物思人,因作此诗。在近世诗人中缪先生对黄先生诗作甚为喜爱,在讲学中常以《蒹葭楼诗》中名篇为例讲述古典诗歌艺术之美㉜,同时对黄先生之民族气节也多加钦佩,高度肯定其于动荡离乱中仍“欲持敦厚教,力挽风俗衰”。黄先生晚年目睹国运衰败,常将满腔爱国热情移于诗词之中,此诗所提“晚遘猾夏祸,讲席多苦词。心契亭林翁,大任天所归”是指“九一八”事变后黄先生在北京大学讲顾亭林诗一事,“他常常是讲完字面意思之后,用一些话阐明顾亭林的感愤和用心,也就是亡国之痛和忧民之心”㉝。顾亭林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他累拒仕清,是民族忠烈之士的代表,缪先生对顾亭林也极为敬佩,曾自述“我们三人(指缪钺、吴宓、郭斌龢)慷慨论天下事,认为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培养了民族气节及抗敌御侮的精神,我们都以顾亭林的民族气节相勉励”㉞。后来他在76岁高龄时,承成都大学中文系白敦仁先生、钟树梁先生之邀,到成都大学讲学,内容为“顾亭林治学的精神与方法”㉟,可见黄顾二人的为人、治学都给予了先生很大教益。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后,缪先生携家眷自保定南下暂避开封,致函郭斌龢:
自卢案发生,保定即风鹤频惊……弟不得已,亦于仓卒中携家南下,甫抵豫中,而淞沪告警,全家老弱困滞汴郑,幸遇故人薛效宽,慨然以居宅相假,异乡漂泊,暂得安居,可谓“穷途仗友生”矣。……弟穷愁之中,惟以杜诗遣日,亦略有所作,容后抄寄。……杜诗云“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愿与兄共勉之。㊱
此时正是国难当头之日,先生于动乱中颠沛流离,穷愁中嗜读老杜诗,从中汲取力量,正如其信中所说“惟于古人忧时悯乱之诗词领略较为深透”㊲,在如此环境中引杜诗为同调,以此激励自我与友人。
作为一名教育家,缪先生不光在自我创作中追求“敦厚”之情,更重视学生们“敦厚”诗教的养成,其在1929 年所作《送培德中学第二班诸生卒业》一诗中提到“论学忆寒舍,含情伤路歧。勉持敦厚教,长与古人期”㊳,先生时任保定培德中学教员,面对学生毕业分离,难免生出伤感之意,然而离别乃为人生常态,他勉励学生将来唯有秉持敦厚之教,才能与贤人心志相接,可以说“温柔敦厚” 贯穿其整个治学生涯。
2、语典的引用
缪先生诗作中多引用杜诗语词,主要有两类:一是承其语:截取杜诗词语,沿用其原意;二是变其意:对杜诗的化用。前者如《初至信阳苦雨》诗中有“山城初远客,夷狄正相侵”,联系诗歌写作背景显然从杜诗《登楼》“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句中化出。又如《哭六弟季湘》,有“烽烟遍九州,骨肉各异县”一句,其中“骨肉”在杜诗《前出塞九首》其二、《杜鹃行》、《得舍弟消息》、《戏赠阌乡秦少府短歌》中多次出现;而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杜甫有“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之语,先生将两处词语绾合为一句中,将国家丧乱之痛与骨肉死别之悲表现得淋漓尽致,沉痛笔墨仿若老杜天宝诗史再现。
相对于杜诗词语的截取,先生对杜诗的借鉴化用更为广泛深入。有化用杜诗,意境相类者,如《一九七九年十月,余以事至京,志岳兄南游沪杭将返哈尔滨,道出京华,相逢话故,并出新诗见示,归后赋此奉寄》中“十年桑海惊多变,七字诗篇更老成”㊴化用杜诗“老去诗篇浑漫与”“庾信文章老更成”二句而成,并沿用杜诗原意;《读古诗》“歌者心徒苦,知音不可求”与杜诗“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相类;《梁鹤铨寄函相勖,赋此代柬》中“野草舒新碧,群莺弄好音”与杜诗“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营造相同氛围;再如《春望》“桃绽春舒眼,楼高客怆心”一诗,不仅与杜诗《春望》同题,更用“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情景交融手法,且化用《登楼》“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表达国难之时登楼望远所生出的与杜甫异代同悲之感。此外另有借鉴杜诗,翻出新意者,如《清华园小住,赋呈吴雨僧、郭洽周四首》其三“振敝起衰豪俊事,人间何幸又逢君”明显化用杜诗《江南逢李龟年》之“落花时节又逢君”一句,然与杜诗所表达的国家丧乱、人生飘零之感不同,先生庆幸在这“举世沉醉,唯君独醒”的世态中能再与郭君重逢,突出的是对友人的思念与欣赏。再如《论词绝句》其三“骚雅清空尊白石,无妨转益更多师”化用杜诗《戏为六绝句》“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前者论词,指出张炎词之“骚雅清空”;后者论诗,总结自身创作经验。先生用杜诗诗法评价张炎词法,可见诗词本同源,都需熔古今于一炉而自铸伟辞。
3、事典的模仿
历代文人墨客作诗多称引扬雄,其中杜甫是称引扬雄最多的唐代诗人㊵,缪先生亦承其风流余韵,于诗句中多有称引。如同用扬雄“草《玄》”之典表达对他人才华与著书立业的肯定。杜诗《酬高使君相赠》中有“草玄吾岂敢,赋或似相如”一语,从中可看出其对扬雄及其著述的推崇;先生也有“牖世情何苦,草玄力已勤。文章千载业,此意独期君”一诗(《寄怀吴雨僧北京》),赞赏吴宓先生潜心著述、用力甚勤的治学态度㊶。另外扬雄清净自守、淡泊名利的文士风骨素为后世推重,如杜诗“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堂成》)似意在懒于自解、不与扬雄作比,实则是向扬雄看齐、期盼清静淡泊的生活环境。而缪诗“百卷藏山司马记,一厂墨守黑子云亭”(《呈张效直先生》)、“寂寞扬雄宅,相过许赋诗”(《夏历九月初七,张效直先生招饮寓庐,谨呈一律》)同用“子云亭”“扬雄宅”事表达了对张效直先生禀性耿介、不妄交游的敬仰。
对于陶渊明,二人诗中也多有称引。此处仅举一例,杜甫有诗“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官定后戏赠》),正用靖节“不为五斗米折腰”一事自表心迹;先生反用此典,“读书尚复爱三馀,折腰久已轻五斗”(《别刘愚忱四年矣,来保定不数日,又复归去,怅然有作》)写下对自己前程颠沛的自嘲。先生平日嗜杜,用典自然深受杜甫影响,上述事典虽未能笃定先生必乃模仿杜诗用典,但不可否认有借鉴杜诗的可能。
4、诗风的承袭
缪先生诗作学杜更集中在对杜诗精神与具体词句上的学习,对于情感风格之借鉴属于少数,其诗之总体风格更接近于晚唐与宋诗,如其所言“拟取阮籍、陶渊明之寄兴深微,李商隐之情韵绵邈,黄庭坚、陈与义之笔致峭折,而熔于一炉,自创新境,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㊷。这或许与先生的为人性格有关,叶嘉莹先生曾对缪先生诗风形成渊源分析到:先生天性敏感深情,使其情韵深长绵邈,近于晚唐李义山;另一方面为人有耿介气骨,喜江西诗派峭折之风格。㊸然有学者注意到先生古体诗风受到杜甫影响,景蜀慧指出先生古体诗“更多受到陶渊明、杜甫那种深挚真淳、直抒胸臆的诗风影响,工拙皆忘,朴质无华”㊹,如《一九三九年岁除之夜,王星贤招饮,戏为长句,时栖泊都匀》。其实先生不少古体诗作更似杜诗般沉郁顿挫、兴寄遥深,如1937 年哀北平沦陷而作的五古《京阙篇》,全诗三十六韵,共三百六十字,为先生五言诗篇幅最长者,前半部分吸取了汉赋的写法,以铺排手法叙述北平自古至今作为都城的盛世景象,但全篇宗旨绝非仅此而已,结句“灵均《哀郢》作,莫漫拟张衡”点出诗人沉痛有如屈原哀郢,非泛泛颂美之作;后半部分在写法上明显借鉴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从亲身见闻出发,以冷静笔触将东北、北平沦陷等祸事娓娓道出,将盛衰之感层层推进,今夕强烈对比,如杜诗般回肠荡气、兴寄遥深:
……自昔当全盛,神州尽俊英。百藩朝贡入,四海泰阶平。曜日明峣阙,连云抗翠甍。绿槐夹道直,红药及时荣。灵沼金鳌丽,觚棱彩凤轻。开场多贝玉,列第半簪缨。广陌红尘合,春游乐事并。……游学当初冠,观光托上京。闳规犹未泯,戎祸已频惊。商邑初移毫,齐师竟入郕。十年伤巨变,万古发幽情。自有荆三户,能兴夏一成。灵均《哀郢》作,莫漫拟张衡。
1982 年先生为纪念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七十周年及杜甫研究学会第二届年会召开所作的长篇七古,豪迈雄劲、沉郁顿挫,颇得杜诗遗风:
去年群贤聚草堂,论诗谭艺神飞扬。青莲故乡访遗迹,诗坛双璧同辉光。今年春韶更明媚,鹃花红艳松楠翠。一千二百七十年,诗圣诞生满此岁。诗圣生当开元间,海内殷实多欣欢。……华夏立国万载传,贵有诗教相绵延。远承杜工继骚雅,汉家新数中兴年。(《一九八二年四月,在成都草堂集会,纪念诗圣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七十周年,并举行杜甫研究学会第二届年会,爰赋歌行,以志欢庆》)
古往今来,凡卓有成就之诗词者,无不取古人之长为己所用,先生亦如此,在“转益多师是汝师” 的基础上终成自己独特诗风。
三、建设:推动新时代杜甫研究队伍的建立
1979 年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同志参观成都草堂时指出:在成都应当成立杜甫研究学会,草堂也应当大力开展杜甫研究工作,因此省委市委开始筹备创建杜甫学会和学刊,并将成都杜甫草堂确定为杜甫学会开展研究工作的基地。㊺1980 年成都杜甫草堂纪念馆(现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联合川内高校成立了杜甫研究学会(现为四川省杜甫学会),翌年创办了《草堂》(现为《杜甫研究学刊》),先生积极推动了学会学刊的成立创办,并担任学会首届会长、学刊首任主编,将杜甫研究推向新的进程。在杜甫学会首届年会上,先生作诗表达了对新时代杜甫学会的成立、杜甫专刊的创办、杜甫研究蔚为大观的欣慰喜悦:
十年惊见海生桑,今日群贤聚此堂。庭馆清华犹昔日,松楠苍翠度严霜。高名照世终无损,公论常存岂可伤。灿烂红霞映天半,喜看探索写新章。(《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日,成都杜甫研究学会在草堂举行年会,赋此志喜》)
此后,他不遗余力地关心学会学刊的发展,参与学会学刊相关工作,时常出席学会理事会,讨论筹备“杜甫夔州诗学术讨论会”“庆祝杜甫草堂建馆三十周年”等年会事宜;参加学刊编委会、审定每期刊发稿件等。他还积极向名家约稿,如在与友人张志岳先生的二十八封通信中,几乎每封信件都提及学会学刊的近况,并代学刊向其多次约稿。㊻对于学会学刊日常事务性工作也多有关心,时常听取草堂方汇报学会学刊近期工作;还多次赴草堂为工作人员讲授杜诗,以提升杜甫研究水平。
四、杜学研究的方法与启示
缪先生早年以中国古典文学开启学术之路,在执教浙江大学以后,他的研究方向开始扩大至史学领域,至此先生治学重心由文学转向为文史并重。尽管先生自1952 年起就一直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但他仍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纳入治学范围,同时积极关注新时期古典文学研究动向,在1982年首届全国唐诗讨论会上,先生因眼疾未能与会,作诗两首代柬,第一首“文章得失寸心知” 化用杜诗“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表明文章学问个中甘苦唯人自知,勉励科研人员保持勤思苦学之态度;第二首借“起衰振弊英豪事,李杜重辉日月光”发出咏叹,表达了对唐代文学研究从深度和广度都将取得新突破的期许。先生文史结合的治学风格给予后人诸多启示。吴光兴将先生在古典文学研究的成就概括为“一本经典(《诗词散论》)、两个‘专家之学’(元好问、杜牧)以及晚年的‘灵谿词学’”㊼,较为全面总结了先生在古典文学领域的主要成就,杜诗学研究虽未成为先生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之“显学”,但其杜学研究所呈现的方法与启示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质形并重,从接受史角度强调杜诗思想性与艺术性
杜诗因其思想内涵和艺术形式方面的典范意义,自唐代以来成为文人写作取法的对象,沾溉深广,宋人孙仅有言“孟郊得其气焰,张籍得其简丽,姚合得其清雅,贾岛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陆龟蒙得其赡博,皆出公之奇偏尔,尚轩轩然自号一家,赫世烜俗。后人师拟不暇,矧合之乎。风骚而下,唐而上,一人而已”㊽,概述了后人取法杜诗并得其一体之长。因此对杜诗的研究应是全面动态的,质与形、思想与艺术不可偏颇。然而20 世纪50 年代后期,在古典诗词评论中,盛行重视思想性忽视艺术性的研究方法,杜诗研究领域同样如此。在当时的背景之下,先生敢于发声持批评态度,“我们论诗时,必须记住所论的是‘诗’,不是散文论著,尽管思想性在诗中是很重要的,但是仍然不能只阐发它的思想性,不能只说明作者思想与意图的价值,而必须结合它的艺术性,说明诗的意境、风格、韵味,甚至于技巧方面的种种特点。”㊾改革开放以后,针对杜诗研究,先生再一次明确指出“今后研究杜诗,在注意其思想性的同时,也要注意它的艺术性”㊿。在《论李义山诗》《陆游与杜甫》两文中,先生分别从诗歌艺术、思想人格两个角度探究李、陆二人对杜甫的接受,表达了先生对诗歌本体研究的重视,即杜诗中的艺术性是其为诗的前提,不应忽视杜诗本体特质,这对我们当前的杜诗研究仍有启示作用。
(二)继承革新,从文体通变角度评价杜诗之集大成
自刘勰将“通变”引入文论后,“文体通变”便作为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成为贯穿中国美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重要范畴。先生对“通变”观中强调的文体嬗变间的继承与革新多有推崇,他认为“凡一种文学体裁之演变,大抵起初多浑成自然,生新活泼,其后渐重技术,渐重雕琢,以人巧掩天机,遂流为匠气,趋于衰敝”,“新体代兴,时有变革,然每一种新体之成就,皆能于旧传统中汲取营养,其精神意脉亦有相通之处,夕秀虽振,不忘朝华”,从起源、发展、继承、革新揭示了诗歌文体通变的脉络。而杜甫正是在继承前贤的基础上,转益多师、自铸伟辞,终成集大成者,其“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的“文体通变”观为先生所赞同。
(三)融通文史,用“知人论世”之法对杜甫生平进行考证
缪先生善于采用“文史结合”从历史背景、个人际遇以及与时代的关系作为考察杜诗的必要条件,同时运用史料丰富杜甫形象,最终将其人其诗结合起来赏析,互为比观。文史结合是先生鲜明的学术风格,在治学方法上,他最为服膺陈寅恪先生所提倡的文史互证法,并将之作为文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先生自述“我读王国维、陈寅恪两位先生之著作,尤为敬佩。王、陈两先生学识精博、融贯中西,能开拓新领域,运用新方法,在许多学术范畴中均有显著的创获,使我深受教益,在我的文史著作中,常会看到王、陈两家的影响”,如《诗词散论》《冰茧庵丛稿》《杜牧年谱》《杜甫》等都是文史结合的产物。《杜甫》一书,行文流畅且思清句洁,兼具通识性与文学性,先生结合杜诗及相关史实,对其生平进行考证,做到知人论世、以史证诗。在《论宋诗》中将杜诗作为唐诗代表与宋诗相对照,融历史背景与时人心声于其中,探究唐宋人作诗背后的心理情趣,如其所言“研究古代某一作家的作品与生平,必须熟习当时的历史背景才能深入,此即所谓知人论世;而研究历史,如能联系文学作品,探索当时人的心声,则对于问题往往能有深刻而新颖的看法”。
(四)古今结合,用“通古今之变”的眼光审视杜诗价值
中国传统文学自古以来具有实事求是和经世致用两重性,前者要求文学来源于生活、还原事物本身,后者追求学术当下价值意义,并对现实起指导作用。故遇兵戈兴起、时运厄难之际,仁人志士希冀能从杜诗中得到慰藉与信心,杜诗中忠君爱国思想就成为时人研究重点。而当国运安泰、民生安享之时,如何让杜诗精神在当下社会发挥最大价值更值得学人深思。先生认为“研究古典文学,注重理解其发展情况及优秀传统,古代作家的高情卓识,精湛艺术,尤其是古典诗词中生生不息的感发作用”㉟,因此在教学中他重视阐发古代贤人志士的嘉言懿行、高风亮节,时常以杜甫之高情卓识、忧国忧民激励学生,培养他们远大志向与高尚情操。
缪先生一生涉及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文学等多个学术领域,其在深受清代诸位“朴学”大家及近代陈寅恪、王国维学术思想沾溉基础上而拓展的会通文史的学术观念与考证、批评、创作为一体的研究方法,给予后人以新的启示。具体到先生的杜学研究所呈现出的独特性,首先表现为他将杜诗诗法与自身创作结合,认为杜诗从“质形用”三方面都符合诗歌最高标准;其次在诗教观念上推崇杜诗的“温柔敦厚”,并将其自觉运用于诗歌创作中;最后运用融通文史、古今结合等方法研究杜诗,重申杜诗的当代价值。上述浅见,尚祈方家教正。
注释:
①1927 年先生任教于保定私立培德中学,与梁鹤铨常论杜诗,二人“比屋而居,夜灯静室,共读杜诗,札记所得,集为两册”;1930年被河南大学校长张广舆破格聘为该校中文系教授时,自编讲义,讲授“六朝文”“六朝诗”“杜诗”诸课;1981年在与叶嘉莹先生通信中写道“在古代诗人中最推重陶渊明、杜甫、李商隐”。可以说先生一生都将杜甫作为自己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点。
②刘明华:《现代学术视野下的杜甫研究——杜甫研究百年回顾与前瞻》,《文学评论》2004 年第5 期。文中将杜甫研究百年进程分为三个时期,而这三个时期又有对应的三代杜甫研究者,第一代有梁启超、闻一多、郭沫若等;第二代有萧涤非、程千帆、罗宗强、陈贻焮、朱东润、裴斐、叶嘉莹、王运熙、曹慕樊、金启华、傅庚生、廖仲安、缪钺、苏渊雷、许永璋、陈友琴、刘开扬、钟来茵、钟树梁等;第三代有杨义、莫砺锋、张志烈、陈尚君、邓小军等。
③目前学界关于缪钺先生古典文学研究主要有钱鸿瑛:《缪钺与中国古典诗词研究》,《社会科学》1993 年第8期;吴光兴:《缪钺:回翔文史、通变发微的古典文学研究述论》,《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 期;林振园:《会通文史:缪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述论》,安徽师范大学2017 年硕士学位论文;刘梦芙:《灵光腾彩笔,青史照丹心——论缪钺先生〈冰茧庵诗词〉》,《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八届年会暨缪钺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7月。涉及治学方法的主要有方北辰、吕一飞:《一脉灵溪映学林——回忆缪钺恩师的治学教诲》,《许昌学院学报》2005 年第4 期;王东杰:《由文入史:从缪钺先生的学术看文辞修养对现代史学研究的“支援作用”》,《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 期;顾农:《缪钺先生成才经历的启示》,《中华读书报》2016年2月24日第8版。
④缪钺:《曹植、杜甫诞生纪念》,缪钺著:《缪钺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二卷,第35页。
⑤缪钺:《纪念诗圣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七十周年》,缪钺著:《缪钺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二卷,第110页。
⑥⑩⑪⑯⑱㉙缪钺:《诠诗》,缪钺著:《缪钺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年版,第二卷,第6页、第5页、第6页、第10页、第9页、第6页。
⑦⑨⑫(唐)杜甫著,(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原序》,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页、第1763页、第320页。文中所引杜诗均出自此书,不再一一出注。
⑧(清)朱一新撰,吕鸿儒、张长法点校:《无邪堂答问》,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75页。
⑬参见缪钺:《杜甫如何改诗》,缪钺著:《缪钺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七卷,第190页。
⑭缪钺:《杜诗中含蓄之法》,缪钺著:《缪钺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七卷,第192—194页。
⑮(清)方玉润撰,李先耕点校:《诗经原始·卷首下》,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5页。
⑰(清)阮元校刻:《十三注疏·毛诗正义·序》,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54页。
⑲胡可先:《杜甫的家世、家学与家风》,《杜甫研究学刊》2018年第4期,第8页。
㉑刘梦芙:《灵光腾彩笔,青史照丹青——论缪钺先生〈冰茧庵诗词稿〉》,《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八届年会暨缪钺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7月,第11页。
㉒(唐)孟棨:《本事诗》,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页。
㉓《新唐书·杜甫传》《麈史》《庚溪诗话》《成都草堂诗碑序》均称杜诗为“诗史”。
㉔缪钺:《冰茧庵诗词稿》,缪钺著:《缪钺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年版,第八卷,第6 页。文中所引缪钺诗篇均出自此书,不再一一出注。
㉕可参考彭超:《传统诗歌对中国新诗发展之影响——“白屋诗体”对杜诗的接受》,《杜甫研究学刊》2013 年第1期;马旭:《新旧诗歌视阈下的杜诗学嬗变——以吴芳吉杜诗学研究为中心》,《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㉖据《缪钺先生编年事辑》,1938 年先生在与吴宓通信中曾说“以后行止恐将随时局之变化而定”,后于7月抵达重庆,8 月赴四川省江安县江安中学讲学,10 月任浙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㉗梁启超:《情圣杜甫》,梁启超著:《饮冰室文集之三十八》,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8页。
㉘缪钺、叶嘉莹:《灵谿词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93页。
㉚清人卢世㴶评《又呈吴郎》:“杜诗温柔敦厚,其慈祥恺悌之衷,往往溢於言表。”(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 年版,第1763 页;何焯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迂回顿挫,极温柔敦厚之味,所以异于鄙儒之大言也。”(清)何焯著,崔高维点校:《义门读书记》卷五十一,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01页。
㉛(清)张溍著,聂巧平点校:《读书堂杜工部诗文集注解》,齐鲁书社2014年版,第3页。
㉜㊷㊸缪元朗编:《缪钺先生学记》,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0页、第37—38页、第61页。
㉝张中行:《负暄琐话》,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页。
㉞缪钺:《回忆吴宓先生》,缪钺著:《缪钺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七卷,第122页。
㉟㊱㊲㊳㊴缪元朗撰:《缪钺先生编年事辑》,中华书局2014 年版,第288 页、第29 页、第33 页、第16 页、第282页。
㊵张朝富:《李杜与扬马关联论》,《杜甫研究学刊》2020年第2期,第1页。
㊶先生此时已从北京大学辍学,任保定私立培德中学国文教员,与时任保定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教师的李濂堂时相往还,通过其向吴宓转达了倾慕之意,并经李先生之手,将自己所作诗文相示,据笔者推测此诗应该就是其中之一。缪钺:《回忆吴宓先生》,缪钺著《缪钺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七卷,第121页。
㊹缪元朗、景蜀慧:《缪钺先生七十年学术生涯述略》,缪元朗编:《缪钺先生学记》,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83页。
㊺曾亚兰:《缪钺先生与四川杜甫学会和〈杜甫研究学刊〉》2004年第3期,第85页。
㊻张志岳先生是当代有名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家,主要研究汉魏六朝文学和古典诗词,1980 年缪先生收到志岳先生《诗词论析续集》一书,其间有论杜之文数篇,先生在回信中写道“希望吾兄赐寄新作,以光篇幅”。参见缪钺著,缪元朗整理:《冰茧庵论学书札(上)》,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03页。
㊼吴光兴:《缪钺回翔文史、通变发微的古典文学研究述论》,《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9月第29卷第5期,第78页。
㊽(清)仇兆鳌:《杜诗详注·附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238页。
㊾缪钺:《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第162 期,1957 年6月23日。
㊿缪钺:《略论对杜诗遗产的全面继承》,缪钺著:《缪钺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二卷,第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