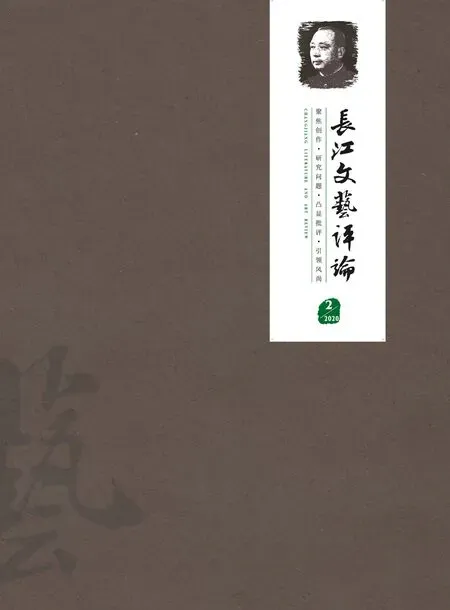发明“新中国风景”
——电影《白毛女》与社会主义电影范式的探索
◆朴 婕
1945年歌剧《白毛女》公演后大获成功,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电影局提议将这部引起轰动的作品搬上银幕,以便进一步传播。[1]电影自1951年上映后取得了不俗成绩,截至1956年,全国6亿人中有5亿人观看过该片,[2]“不满百户”村子也可观看到《白毛女》[3],它尤其深受工矿农村的群众欢迎,每次放映都座无虚席。孟悦将电影《白毛女》的成功解读为“以市井流行文艺中富于悲欢离合的娱乐性形式翻译并转换了歌剧所表现的乡土伦理原则”来为自己赢得了城市观众[4],电影能在工矿和偏远乡村放映并获得巨大反响,显然不仅是市井流行文化的作用。《白毛女》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意味着它必定找到了一种更容易为底层民众所理解的形式。
长久以来对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讨论都以上海电影产业为中心,但电影作为一种现代艺术,需要观看者对现代文化有一定理解,张硕果对建国初期上海电影改造的研究中便提到“由于工人和农民观众受教育程度一般比较低,又很少看电影,不习惯电影的表现手法,所以普遍反映看不懂电影。”[5]这尚且是发生在上海周边的状况。上海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还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市民群体,他们有着较为良好的教育背景,可以为电影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观影群体,上海以外的情况只会更为严重。所以当代社会主义文艺要求“为工农兵服务”时,本就有意改造上海电影的形式,当时的电影工作者也明确提出电影“要用新的手法,不要用过去上海那一套”。[6]《白毛女》由东北电影制片厂(即后来的长春电影制片厂,下文简称东影)而非上海电影人云集的北京电影厂,或者已经解放的上海电影公司制作,本就暗含当时中国想要走出上海电影范式的意图,而其呈现出的样式,也反映了当代电影形式改造的目的。
另一方面,电影形式改造又有其特殊性。自延安时期以来,我们在文艺改造上就形成了一套经验,即吸收民间旧有形式来改造新文艺,但电影伴随着现代工业而来,在现代都市流行,没有传统文化作为依托,且电影是一种工业生产,不能像文学等只靠作者一人的创新就能转换形式,所以其它文艺改造的经验很难应用于电影。在这一方面,东影对其前身“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下文简称满映)技术和形式的吸收值得关注,它创造性地转化了日本占领时期的电影呈现,为当代电影形式转换提供了参考。因此电影《白毛女》提供了一个切口,可以反思当代中国如何既继承自身电影传统,又吸收并改造日本电影资源,形成一种全新的、自主的电影新范式。
一
“白毛女”叙述起源于1930年代在解放区流传的“白毛仙姑”传说。[7]该传说讲述了晋察冀边区某个偏僻的山村中,村民具有“白毛仙姑”信仰,认为若不敬奉仙姑便会招致大灾大难。这个迷信阻碍了革命工作的展开,区干部认为事有蹊跷,于是到藏身仙姑的奶奶庙中一探究竟。不想到了夜里,真有个通体白色的“物件”进来。“物件”看到干部受惊之后迅速逃走,干部追着它进了山中,发现所谓的“仙姑”原来是遭到地主迫害的贫民之女,被地主欺凌,不得已逃入山中。干部将她带出山,让她重获新生。后来这个传说流传到了延安,文艺工作者对其进行改编,创作出了歌剧《白毛女》[8],讲述地主黄世仁逼贫农杨白劳以自己的女儿喜儿抵租,杨白劳无奈画押后懊悔不已,喝卤水自杀的故事。喜儿被带到黄家后被逼迫当牛做马,还遭到黄世仁强暴,怀上身孕。而后黄世仁要娶亲时觉得喜儿是个累赘,打算暗中害死她。喜儿逃出虎穴后藏身山洞,以野果为食,导致营养不良,自己和生下来的孩子都全身发白。她在奶奶庙觅食时被村人发现,村民因为她的形象而误把她当成神仙,兴起了“白毛仙姑”信仰。喜儿家的邻居大春在成为八路军回到村中后,听到“白毛仙姑”传说,认为可能是地主的阴谋,于是暗中藏身庙中一探究竟,发现了喜儿。他带喜儿回家,发动土改斗争,打倒了黄世仁。
电影在情节上基本延续歌剧,但值得注意的是它增加了大量农业劳作的情节与场景。相对于歌剧始于大年夜,影片从秋收开始,首先讲述贫农杨白劳与女儿喜儿相依为命,他们与隔壁的邻居王大春一家共同劳作,结下深厚情谊,两家还为喜儿与大春定下在大年初一成婚的亲事。而后进入原版歌剧的情节,即黄世仁看上了喜儿并设下奸计让杨白劳以喜儿抵债,大春欲救喜儿不得后参加八路军,喜儿在杨家遭到强暴逃到山中成了“白毛仙姑”,归来的大春救出喜儿并组织土改打倒了黄家。而在歌剧版土改这一结尾之后,电影又增加了人们回到田野上劳动的场景,此刻喜儿也恢复了黑发,和大春共同收获丰收的果实。这些场景让电影在继承歌剧的经典故事之余,将乡村的明丽风景以及劳动场面也纳入表现对象。
影片先是以山林一角为背景进片头字幕,随着字幕淡去,画面切入全景的山川,再大全景俯拍华北平原广袤的农田和远方的层峦叠嶂。随后两个定点全景镜头沿着河流而上,切入在山上放羊的赵大爷的全景。赵大爷从镜头深处穿过羊群进入前景,环视周边景象,开始歌唱“清清的流水蓝蓝的天,山下一片米粮川,高粱谷子望不到边”,镜头就随着他的歌声进入麦田,俯拍饱满得低头的成片麦穗,仰拍笔挺坚实的高粱。紧接着一句“黄家的土地数不完”,镜头再次遥拍一望无际的原野。随着“东家在高楼,佃户们来收秋,流血流汗当马牛”的歌声,镜头转向黄家在豪宅中作威作福,而农民在田间辛苦劳动。尾声几句“老人折断腰,儿孙筋骨瘦,这样的苦罪没有个头”,镜头进入杨白劳的特写,他在田间呼唤喜儿,至此女主人公喜儿才正式登场。这些镜头交代了故事发生的大致地理位置——华北平原,主要人物的生活空间——田园村庄,生活方式和劳动对象——农业劳作和农畜牧生产等信息,但镜头数量如此之多、时间如此之长的空间呈现显然不只是为了做场景交代,它有意将乡村打造成一个景观,带来审美感受。
完成开场并进入情节叙述后,乡村风景仍在镜头中占据很大比例。王大春的母亲带着午饭来到田间,杨、王两家人坐到树下一起吃饭。除了部分特写镜头之外,人物常常只占到画面的二分之一,更大的画面被自然环境等占据。吃饭的场景中,画面表现为人物被树丛包裹、树丛之外有农田、农田之外还有远山的景观,透过前景对话的人物,还可以清楚地看到远处的山峦田园和劳作的人们。而后大春和喜儿又跑到田间劳作,麦浪几乎可以将两人淹没,在最后远景拍摄时,几乎无法从画面中找到两人。到此为止,影片已进行了十分钟,它让人感到不仅喜儿等人物是影片的主角,乡村风景本身也是影片强调的重点。影片尝试建构一个空间的视觉镜像,将理想的中国形态以直观的画面传递给观众。
地主的罪恶,也表现为对这种美丽风景的蚕食。赵大叔的唱词:“清清的流水蓝蓝的天,山下一片米粮川”却都属于黄家,在这片土地上人们只能“流血流汗当马牛”,体现出地主对农民、对农业以及对乡村美景的欺凌。且随着喜儿被带到黄家、又从黄家逃到山里,风景就越来越狭小,最后就局限在山洞之中。与之相对,大春寻找红军的一路都可以看到风景,可见红军能够保卫风景留存。而后,随着大春打马归来,风景才回到了杨家庄。到了影片最后,镜头穿过开满鲜花的树丛再次来到华北平原之上,喜儿和大春以及无以数计的农民重新回到这里进行劳作。恢复黑发的喜儿解下头巾为大春擦汗,大春扛起两垛粮食先行离开,而后喜儿扎起头巾,抱起一垛粮食,饱满的麦穗映衬着喜儿重新丰润起来的脸颊。这时呈现出来的清澈的天、丰收且错落有致的田园,让人感到中国共产党不仅解救了喜儿以及千千万万“变成鬼”的穷苦人,同时也解救了被蚕食的乡村风景。而以喜儿、大春为代表的新中国农民形象,也是在这种空间景观的映衬下,彰显出他们的精神与活力。
这样的乡村景观呈现具有多重意义。它首先颠覆了乡村在此前的黯淡形象。自“五四”运动以来,乡村在主流叙述中就作为压抑晦暗的形象出现,它或者是扭曲的封建礼教的代表,或者是底层人民疾苦的集中体现。电影中更是如此,上海电影从制作主体、表现对象到主要服务对象都处在现代都市语境中,多数观众对乡村的了解较少、兴趣较低,再加上乡村拍摄需要支付更多的成本,[9]所以当时影片对于乡村的重视程度和表现力度都不大。纯粹的娱乐电影自不待言,左翼电影中也只有少量表现封建制度压迫或底层农民疾苦的影片,它们中的绝大多数还是将注意力放到城市底层,或者已经来到城市的农民身上。即便是少有的几部拍摄乡村的影片,如《春蚕》《小玩意》《渔光曲》等,其场景也多在城市近郊拍摄完成,所以建国之前的乡村影像主要是一些南方小村落。当下提到中国乡村时会联想起的千里沃野之类的景观,在当时是不可见的。因此以《白毛女》为代表的当代电影是有意于“发明”出一种新的乡村风景,重构中国的城乡形态和关系,传递新的意识形态。著名编剧羽山对电影《白毛女》的评论中有句话值得注意:“当电影的最初几个镜头显现出来的时候,使人深深地感到:由勤劳勇敢的劳动人民所开辟的祖国田园是多么秀丽、丰沃啊!”[10]此处的关键不是看到了怎样具体的景色,而是祖国被作为一种风景建立起来了,电影建构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
二
大量凸显空间景观与此前上海电影的表现形式构成了对照。1920年代末,以格里菲斯和苏联蒙太奇学派为代表的电影人发现了通过剪辑,可以让简单的几幅画面传达出完整的信息,自此电影不必全面呈现人物所处的环境,就能让观众理解大概的时间、地点、人物。这种技术促使好莱坞式情节剧走向成熟,在情节剧的普遍范式中,空间性的表达收缩到一些抽象象征之中,并入线性的故事叙述。深受好莱坞情节剧和苏联蒙太奇学派影响的上海电影,也因袭了这样的特征,以情节发展为轴心,对空间的表现大而化之:先大全景拍摄故事发生地点,再切入具体场景的全景,通常三四个镜头就结束了交代,而后集中于情节叙述。有声电影的出现更加剧了空间的收缩,因为无声电影还需要通过画面来展现各种环境信息等,有声电影发展起来后,声音与对话便可以交代环境,空间镜头进一步减少了。
但是蒙太奇毕竟是一种现代表意方法,它对观众的现代教育程度有一定要求。现代电影主要为城市知识分子群体所消费,他们接受这种技法没有太大阻碍,但当文艺要以教育程度较低下的“工农兵”群体为服务对象时,这样的技法就过于晦涩。《白毛女》将人物融入到所在的背景之中,使之整体构成一幅年画式的简明易懂的景观图,便是对上海电影手法的反拨。
可以选择一个具体的例子进行对比说明。《白毛女》的摄影指导吴蔚云在1947年指导的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中,讲述上海某纱厂女工素芬在夜校中认识了进步教师张忠良,两人相知相爱,结为夫妻。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忠良参加救护队离开上海,素芬带着孩子和婆婆一起到张家乡下的老家避难。自此电影以双线交错展开:张忠良一线展现他跟随部队颠沛流离,终被俘虏,逃脱后流亡到重庆,在重庆的纸醉金迷中日渐堕落;另一边,素芬等人回到的乡下张家也未能逃脱日军魔爪,在日军的压迫、奴役之下被动劳作,张父在要求减租时被日军杀害,张忠良的弟弟张忠民加入抗日游击队而离开家乡,素芬与张母生活无以为继,又回到上海。在这里,张忠良有着从上海一路到大后方的流亡过程,如果影片有心展现,大可呈现出沿途风景。但影片只是通过拍摄标有地名的符号,如断壁残垣上书写的“南京”、运送伤员处墙壁涂着“武汉”、火车站头挂着“南昌”的标识,以及被俘后押解途中界碑上写着“宜昌”等等。在这样的表现中,影片相当于是划定了一个故事发展的范围,人物和情节都在特定的故事舞台范围内发展,并不强调与周边的世界发生对话。在素芬所在的乡村部分,也只是八个镜头简单交代了他们被迫劳动的情况,这八个镜头还以人物特写为主,乡村到底是什么情景并没有得到充分展现。《白毛女》中的乡村风景则别有意味,同样是人物的移动,大春寻找红军的路上,沿途都充满着自然和乡村的实景。它直接呈现出中国的大好山河,以及人物如何与自然发生关系。
在《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呈现中,人物是超越空间的存在,风景是为了衬托画面的层次感来凸显人物形象,电影的着重点也在于打造人的故事,讲出人的觉醒和堕落。在画面呈现上,也多凸显人身上的光影。而《白毛女》中融于风景的人物,则是参与进时代画卷的整体描绘,人身上的光影大幅缩减,可见比起呈现一个立体的、大写的人,影片的重点更在于呈现群体。即使影片最后以喜儿的特写结束,它也让人感到故事中的所有人、乃至观看故事的观众也被收进画框中,成为这道乡村风景的一部分。
同时需要考虑的背景是“人民电影”的一个主要传播途径是放映队的露天放映,李道新研究指出:“跟影院电影不同,露天电影往往没有固定的场所和座位,观众的视域可以自由调整;观众分布虽然以银幕为中心,却几乎没有边界,能够将银幕上的活动影像、银幕下的各色人等以及大自然的多变夜空同收眼底;声音环境也是丰富而驳杂的,除了自然界的风声、雷声或雨声外,发电机的轰鸣、放映机的运转以及观众的交谈和嬉闹,跟影片本身的声音系统交互作用。”[11]所以电影的图层和现实生活交融在一起,电影不再是个凝视的对象,而仿佛生活的一部分。银幕内外的界限仿佛已然消解,人总是作为群体存在,而观看者也是在分享中进行观看。这已然改变了现代艺术基于凝视而使观看者产生自身是孤立个体的感受,促生了群体的视点,从观看方式上颠覆了上海电影乃至现代艺术的特质。
三
这种群体的视点需要综合考虑中国传统视点的群体性,以及当代“人民电影”对日本电影技术的吸收。由于东影建立初期,资源和人员匮乏[12],所以东影大量征用了满映的物力与人力资源[13],包括留用了大量原满映人员:东影在兴山安顿下来时,共计278个工作人员中有二百余人出身满映,其中日本人员也占到八十余人,他们参与了东影初期的电影制作,并帮助中国培养了一批电影人才。《白毛女》的剪辑师安芙梅便是满映的岸富美子,她主持了当代中国第一部长电影《桥》、第一部反特片《无形的战线》等多部重要影片的剪辑。她和《白毛女》的导演之一王滨因《桥》而认识,按照岸富美子的回忆,王滨虽然在上海有过拍摄经验,但上海的拍摄并不关注剪辑,也就是对电影成片没有很好的把握能力。王滨又有十年左右没有参与到拍摄一线上,所以也有些生疏。再加上满映采用同期录音这种先进技术,王滨此前并不了解,在经过合作之后,王滨才明白了这种拍摄方法。[14]因而可以推定,延安出身的电影人很多是通过与满映人员的接触来掌握或加强电影制作技术。反过来,满映的工作人员对于东影的工作也十分热心。当时剪辑助手祖述志对岸富美子的回忆中,提到在《无形的战线》制作时,岸富美子主动对拍摄女特务的方法提供了建议。[15]东影员工将在满映时期习得的成果应用到中国电影之中,从导演朱文顺、于彦夫,到摄影王启民,演员浦克、方化等等,都积极投身中国电影建设,在当代中国电影中大放异彩。
除了技术性的传承关系之外,满映对东北文化和审美塑造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影响常常是潜移默化的,既然东影的创作需要以东北人民的审美和理解能力为基准,就必须要有针对性的反思和修正满映时期对中国的叙述。鉴于这样的背景,东影尝试建立新的表意方式时,不可避免地要对话满映时期建立的表达,并对其中有益的部分进行吸收。诺埃尔·伯奇《抵抗的电影?》指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电影的一大特征是“电影导演较少依赖蒙太奇或者特写之类的手法”,“追求每个镜头的长度、以及空间的广大”。[16]这原本是电影初兴之时的普遍特征,但随着蒙太奇技术的发明,这种表现方式在其它国家逐渐衰退。伯奇认为由于东方艺术原本是“非线性、反现实”的,它是面向群体来进行展现的形式,不像西方现代艺术那样是为某个特定点的人物展开、让观众认为整个作品都是针对他的视点来服务,所以日本电影在发展过程中保留了全景记录式的表现,使之与自身传统的审美习惯结合,因此形成了日本特色的表意方式。在“娱民电影”(即故事片)中,满映1938年制作的《东游记》,也是以乡村风景开场:开头八个镜头分别表现河流融化、冰块解冻时滴在水面上的涟漪、雪水濡湿的泥土、冒出新芽的枝条在晴空摇曳、广袤的田野和村庄俯瞰、牛群在山坡吃草、鸭群在河中嬉戏,以及最后全景展现农庄一角的农家院景象,随后主人公登场。
这种简明的表达正与“人民电影”的需求相契合,所以“人民电影”可以既利用满映本身简明直观的拍摄方法,来辅助建立适宜工农兵理解的视觉形象。不难发现上述《东游记》与《白毛女》在构图、剪辑节奏上的相似性。而《白毛女》的海外传播在日本尤其成绩斐然,到1955年已有超过200万人次观影,且口碑绝佳,从知识分子、工人到农民都深受感动,表示“从影片中得到了什么力量”,[17]乃至受此影响创作了芭蕾舞《白毛女》,这种成绩想必和观众对这种画面的熟悉和认同感也是分不开的。
当然,满映人员参与到《白毛女》以及东影建设和影片生产工作并不能意味着文本中所有的形式相似就必定来源于日本,它们同样可能是巧合,或者是为了某种相似的目的而采用了相似的处理手法。但满映、日本电影对于“人民”视点的形成却是有着启发作用的,它可以提醒“人民电影”的奠基者们,他们想要尝试的便于“工农兵”群体理解的视觉可以通过一种分散聚焦的方式来实现。
无论是建立不同于上海电影的电影语言还是征用并改造满映的电影技术,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探索出“人民文艺”独特的表现,以便传达社会主义的思想理念。《白毛女》以及以它为代表的一系列人民电影通过让延安文艺理念、满映电影风格与上海电影传统发生碰撞,使某种不同于现代凝视的、带有传统色彩的视角进入到电影之中,“人民电影”得以开启了新的视界。所以乡村风景并不只是形成一种景观,它还引导人们形成了一种观看世界的方法,教会民众何为“真实”、何为“新中国”的“乡村”以及何为“新中国”。并且观者将自己与这一景观中的人物形象画上等号,明白自己会怎样“被看”,因而形成了自我规训,让自己逐步成为景观中的人物。
注释:
[1]据电影《白毛女》场记的宋杰回忆:“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之后,电影局局长袁牧之和艺术处处长陈波儿决定把舞台歌剧《白毛女》拍成电影。”参见宋杰:《导演王滨与电影〈白毛女〉》,《电影艺术》,2004年第6期。
[2]段宝林:《〈白毛女〉与民间文艺》,《民间文化论坛》,2012年第5期。
[3]夏阳湖:《〈白毛女〉在周江村》,《大众电影》,1952年第3期。
[4]孟悦:《〈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载唐小兵主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2-63页。
[5]张硕果:《论上海的社会主义电影文化(1949-196 6)》,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第49-50页。
[6]转引自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1949-1965)》,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年版,第18-19页。
[7]《白毛女》起源于民间传说是目前的普遍说法,因歌剧创作者之一贺敬之采用此说法而被广泛接受,但从该传说中描述存在“白毛仙姑”信仰且它能够影响到革命工作这一点来看,在这个传说之前应还有一个宣传成仙的“白毛仙姑”传说。参见孟远:《歌剧〈白毛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第32页。也采集到一些传说是“白毛仙姑爬山越岭,如走平路,像仙家一样,腾云驾雾”。由这一点来看,这个传说便可以上溯到上古“毛女”传说。关于“毛女”传说与《白毛女》的关系,详见姚圣良:《汉代毛女传说及其渊源流变论略》,《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王立、孟丽娟:《染及俗气难为仙——毛女传说的历史演变及其性别文化内蕴》《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发现“白毛仙姑是受苦乡村女”的传说本身便很可能是经过改造过的传说了。但因相关证据仍不足以还原出最初的传说是什么,本文在此仍采用普遍说法。
[8]歌剧公演后进行过多次改编,有很多修改版本,这里取通行本的内容进行陈述。歌剧版改编的具体情况可参考孟远:《歌剧〈白毛女〉的叙事变迁史》,《学术研究》,2008年第12期。
[9]侯曜:《影戏剧本作法》,《当代电影》,1986年第 1期。
[10]羽山:《电影“白毛女”的成就》,《人民日报》,1951年9月17日。
[11]李道新:《露天电影的政治经济学》,《当代电影》,2006年第3期。
[12]陈波儿:《故事片从无到有的编导工作》,载吴迪主编:《中国电影研究资料1949-1979·上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59页。
[13]钱筱璋:《最初的甘苦》,《电影艺术》,1961年第 3期。
[14]岸富美子:《満映·新中国·『白毛女』―岸富美子インタビュー》,载四方田犬彦、晏妮編:《ポスト満洲映画論―日中映画往還》,人文書院2010年版,第66-68頁。
[15]参见《祖述志访谈录》,载陈默、启之主编《长春影事:东北卷》,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第256-257页。
[16]ノエル?バーチ:《抵抗する映画?》,千葉文夫訳,载《日本映画の展望》,岩波書店1988年版,第33-44頁。
[17]山田晃三:《〈白毛女〉在日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