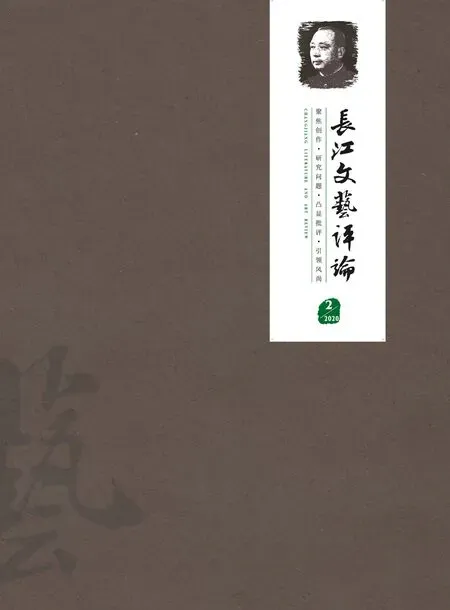理解当下文学制度
——以2019江苏短篇小说为例
◆黄明姝 何 平
“江苏文学”不单是地域文化造成的,但“江苏文学”在2019年短篇小说上呈现出来的繁盛态势,却是地域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地域文化不仅涉及传统意义上的非物质性精神遗产,也涉及期刊、高校、书店等物质性文化空间及其产品,涉及江苏相关的文艺政策以及市场经济影响下的那些为群体所共同承认的价值观念、所共同遵从的规范。2019年的江苏短篇小说相较于“江苏文学”或“江苏传统”是非常小的单位,越细小也就越具体。所谓的年度观察,其基础是对生于兹长于兹或长期供职于兹的江苏作家年产总和与分布的统计。有很多角度可以观察2019年江苏短篇小说这个样本,近几年江苏为当下文学发展,尤其是青年作家的成长提供了很多人才计划和扶持项目,在文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理解当下文学制度,观照的是制度和一个规定性时间和空间里文学之间相互塑造的微妙关系。
一
当下文学制度客观上存在作协体制下的专业作家和非作协的作家。如果专业作家的专业体现在作家的创作实力和文学品质,其实无可厚非。事实上,江苏专业作家的文学“专业性”一向有目共睹。当然,专业作家制度因为没有相应的退出机制,江苏目前在岗的专业作家,除了1983年出生的孙频,其他都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如果存在一个编制问题的话,年轻作家很难补员到专业作家队伍,尤其是江苏这样的文学大省,青年作家人口基数庞大。如何进行制度创新?值得思考。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专业作家队伍为例,2019年范小青的《现在几点了》《邀请函》《旧事一大堆》《到代》《你在通话我未接》、叶兆言的《吴菲和吴芳姨妈》《红灯记》、王大进的《蜡人》《独奏》《变线的命数》《向上生长》、朱辉的《岁枯荣》《如梦令》、荆歌的《亲爱的病人》、罗望子的《容易记》部分地体现了江苏专业作家的创作实绩。
观察这些小说,对现实问题的关切,是它们的不约而同之处,即便是《如梦令》这类充盈着雾气与恍惚的篇什,也透露出个人生活的隐秘底色,这往往是这些作家的“代际”特点。同一个“代际”的非专业作家,如韩东的《夏日霓虹》、王啸峰的《劫持》《地震》《路口》《一次约谈》、陈武的《小千》《和乔卫民有关的那些事》《三里屯的下午》、葛安荣的《风中的轮笛》、徐循华的《通扬河畔的男人》、裴文的《改名》等都是不错的作品。可读性应该是“50后”“60后”作家的另一个共同之处。王大进的《蜡人》和徐循华的《通扬河畔的男人》不约而同地取用了“黄老邪”“黄药师”这样的人物符号,而像荆歌的《亲爱的病人》这样的短篇,其可读性则在于窝踞于其中的戏剧性尺度,以及只有在这种尺度之下才能看清的原本遮遮掩掩的时代寓言真身。精神病或疯狂本就是现代性的典型标识,《亲爱的病人》中拯救蕾蕾的是一场彻底的意外,或许从现代精神病学来看,蕾蕾的好转完全得益于科学且严谨的暴露疗法,即将洁癖严重的蕾蕾突然暴露在脏恶的垃圾堆旁边。患有强迫症的蕾蕾,既无法用人类理性解释与控制,亦不受人与人关系的约束(以丈夫潘亮和心理医生为代表)的人格形态,似乎正指向生活背后某种无所不在的庞然大物。这种庞然大物感在许久不见短篇小说的韩东新作《夏日霓虹》中亦有显现。此外,王啸峰的可读性正在于其作品中若隐若现的某种悬疑色彩。《劫持》本身就是充斥着悬疑的故事,而更大的悬疑恐怕在于“劫持”本身所蕴含的现实隐喻,这一点似乎与苏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现实观念隐秘对接。《地震》则是王啸峰此前创作中所使用的少年视角的延续,王啸峰所经营的具有颗粒质感的弄堂影像,注定不会过于清晰。《路口》和《一次约谈》都是主人公出发前往同城的某地并在各自的目的地得到真相或自我和解的故事,流转着物理时间与精神时间的博弈:“在路上”或是“到达”所产生的物理时间与物理距离是有限的,但叙事中不断闪现的往昔记忆与主人公的心灵臆语,却造就了无法估量的精神时间与精神位移。王啸峰是2019年江苏短篇创作中为数不多的尝试处理与自己成长等量的时代的作家之一,《劫持》与《地震》都以诸如BP机和486电脑、四环素牙等细微之处兑现着八九十年代于今日恍如隔世的陌生感。或许可读性不单单属于某一“代际”,而是当下小说的症候。“80后”的翟之悦和“90后”的秦汝璧,她们刊载于《钟山》的《流逝》与《华灯》,也打磨出了流畅而有余味的故事性。《流逝》与《华灯》都有着明显的示旧成分,但在《钟山》的年度短篇小说语境中,它们与其它作品一样富有一种难以平复的“重”量——密集的乡镇知识经验,以及仅凭个人的良善、浪漫式的想象无法抵抗失范的时代这一沉重的预设。《钟山》一直是先锋文学的重镇,曾经发表过许多类似《褐色鸟群》这样的先锋经典,但从1980年代参与策划“新写实”“新状态”到“联网四重奏”,《钟山》在现实主义和可读性上也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审美规范和刊物传统。
“代际”视角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运用得最多的视角和范式,某种程度上,可能已经制度化了。顺着“代际”的思路,2019年的短篇小说年产量最大的是“70后”作家,这其中包括曹寇的《龙》《对食》《高铁怪客》《我们的身高》《月夜》《高先生》《年轻时候的事》《没花钱》《引娣》《赵老师》、黄孝阳的《深夜去动物园》、朱文颖的《生命伴侣》、汤成难的《奔跑的稻田》《金光闪烁》《失语者》《海上升明月》《追风筝的人》《共和路的冬天》《老胡记》、房伟的《阳明山》《小陶然》《苏门答腊的夏天》、宋世明的《兔子快跑》《大桥照相馆》《如梦之梦》、李云的《地下室》《晚秋》、杨莎妮的《D大调卡农》《烈焰蓝金》《树杈间的黑洞》、李新勇的《谁都认识苟富贵》《去往野山的路途》、葛芳的《安放》。而“80后”和“90后”作家中的李黎、朱婧、焦窈瑶、庞羽等亦极具实力和努力的青年作家,在2019年的短篇小说领域也交出了相当满意的答卷。相比2018年的15个短篇,庞羽2019年的《羚羊小姐》《金鱼》《花灯》《年轻人的好运气》《黄桃》《白猫一闪》依旧显示了她写作的可持续性。
以发表江苏作家的作品量而言,《作家》的“金短篇”值得一提。王啸峰的《地震》为小说的“轻”提供了一个美学意义的范例。朱婧的《水中的奥菲莉亚》是张怡微心中的“典雅的欲望”。朱文颖的《生命伴侣》利用讲故事和听故事的结构对业已成为故事的本事进行了缝补和修正,冒险和死亡被调离了叙事的中心。黄孝阳的《深夜去动物园》懂得如何利用先锋元素为自己的写作增加难度。然而,任何一场招魂术其实都是非自然的,在先锋文学业已落潮的今天如何“再先锋”值得思考。
就全国范围来看,《作家》和《钟山》似乎是同等量级的杂志,然而对于江苏这样一个省域单位来说,它们的位置却不尽相同。不同的位置意味着回馈不同的期待。《钟山》作为江苏省作家协会直接主管的大型文学刊物,不仅要对江苏省作协和各基层作协负责,也要对向全国输出与文学期刊“四大名旦”同等分量的作品负责。而《作家》作为外省刊物,在编排来自江苏的短篇小说时更注重对江苏文学写作品格的提炼,那些以灵动、精致、梦幻为底色且“善于发现人的卑微、人的小聪明、小志气、小情趣、小龌龊”的作品或许正应和着《作家》对整个“江苏文学”的想象。[1]然而,无论是“位置论”还是“重”与“轻”,都是笼统而具有惰性的归纳,一份杂志的文学品格需要有历史眼光和制度上的深层考量。但有一点却是明确的,即2019年的江苏短篇小说能够为各类不同的文学期刊提供所需,说明江苏的短篇小说在这一年提供了远超我们想象的体量。
二
2016年,江苏在北京向全国集中推出“文学苏军领军人物”后,又于隔年提出“文学苏军新方阵”。同年,江苏省作家协会与南京师范大学“江苏当代作家研究基地”共同开启一项名为“江苏文学新秀双月谈”的活动。围绕遴选的“文学新秀”“双月谈”采取两位青年作家、一位主持人和五位青年批评家的对谈模式,旨在为江苏文学的后继发展培养新生力量,截至2019年,该活动已在《雨花》上刊载了九期现场实录。参与对谈的庞羽、杨莎妮、汤成难、朱婧、焦窈瑶等在2019年皆有短篇作品刊出。2019年在短篇发表数量上领跑的汤成难亦是《雨花》杂志“绽放“栏目大力扶植的青年作家。由南京市委宣传部、南京市文联和南京出版传媒集团共同资助,南京市作协和《青春》杂志社共同实施的“青春文学人才计划”,每期三年,自2017年启动以来已举办至第二期,而2019年正是“青春文学人才计划”第二期的元年。本期“人才计划”共签约31位作家和在校大学生写作者。他们不仅依托《青春》进行组织推介活动,其部分成果也依托《青春》发表。
从“青春文学人才计划”签约作家2019年度作品发表、获奖、转载情况来看,九位作家涉及短篇小说,一期的曹寇、二期的房伟和朱婧三位都是江苏作家。房伟、曹寇和朱婧还同时入选江苏文艺“名师带徒”计划,分别师从叶兆言、王尧和汪政,其中,房伟和朱婧都在综合性大学文学院担任教职。从2018年“回归”写作的朱婧持续发力,2019年的四个短篇《那般良夜》《危险的妻子》《影》《水中的奥菲莉亚》分别发表于《青春》《雨花》和《作家》杂志,其中三篇被《小说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思南文学选刊》《中华文学选刊》转载。
2019年的短篇小说集《譬若檐滴》是朱婧继2005年《关于爱,关于药》时隔14年后的第四个短篇小说集。小说集首篇即是《水中的奥菲莉亚》。小说家的语言并不是天生的,对比2003年的处女作《N自由》,朱婧的文学语言具有明显的生长性。湿漉漉而不愿妥协的《水中的奥菲莉亚》,其间也隐现着谷崎润一郎《西湖之月》的倒影(白净的雕刻,以及鳞片般的银色光辉),这或许与朱婧多年亲近日本文学和艺术相关,但朱婧的成长却远不止这些。
2019年,曹寇除了有《龙》《对食》和散落在《第一财经》杂志的短篇小说专栏上的诸篇,也有中篇小说《鸭镇疑云》发表在《十月》,以及剧本《片警宝音》。在曹寇的《对食》和朱婧的《水中的奥菲莉亚》中,所谓“忘年”或曰“代际”都是极不稳定的因素。与曹寇同样是1970年代出生的房伟,2019年除了《小陶然》《苏门答腊的夏天》《阳明山》外,也有中短篇小说集《猎舌师》出版且荣获同年的“第三届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奖”。房伟迷恋着对话,《阳明山》模仿汉大赋的主客问答,本身就是一场盛大的对话;《苏门答腊的夏天》则在一遍又一遍的求索无果后选择萨满的木古茨为已故的郁达夫和章谦招魂。传统的公案小说常有托梦以致沉冤昭雪的场景,然而无论是借助灵异形式抚摸历史真相,还是通过问答方式探讨语言问题,抑或是《小陶然》中不断覆辙的相亲故事,流窜于那些足以对抗形式主义的“形式”之间的,却是能够轻易被捕捉到的主观预设。
如前所述,作家的非职业化倾向更多地体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及以后出生的江苏作家身上,这是制度使然,也是时代使然。而在江苏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中,专业作家仍是一支劲旅。“文学苏军领军人物”除了鲁敏,其他都是“50后”“60后”作家,而10人中除毕飞宇和叶弥,赵本夫、范小青、黄蓓佳、苏童、叶兆言、周梅森、储福金、鲁敏皆为江苏省作协的专业作家,或者供职作协。而“文学苏军新方阵”除了生于1983年的孙频,朱文颖、王一梅、戴来、韩青辰、李凤群、黄孝阳、育邦、曹寇、张羊羊都是“70后”。而除孙频外,其余九人都是清一色的非作协建制的专业作家。“代际”是一整套系统,它松散地整合新旧价值、意义以及鲜活的经验。而“文学苏军”的这样一种梯队构型,连同江苏文艺“名师带徒计划”,实际上提供了一种承诺——“代际”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正是“代际”与地域的双重际遇,才使得诸如从陆文夫、范小青、苏童到叶弥、王啸峰、朱文颖、戴来,或是从韩东、鲁羊、朱文、顾前、赵刚到曹寇、朱庆和、李樯的这类文学线索变得生动。
观察2019年的江苏短篇小说实绩,文学资源越来越集中在南京、苏州这样的中心城市,尽管有苏州周边吴江的荆歌、昆山的翟之悦,以及扬州的汤成难、泰州的刘仁前、南通的李新勇、金坛的葛安荣、海安的罗望子等等,这个文学格局大致不会有大的变动。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不仅是文学资源的分配不均,也是文学研究的分配不均。在对整个2019年度短篇小说考察中,我们所关注的更多的是大型文学期刊或重要省级刊物所提供的典型样本,典型亦是一种遮蔽,许多基层文学期刊和基层文学生产机制并没有被照顾到。虽然我们可以说,从大体上看县级市作家提供了更多的关乎乡村和城乡结合部的文学样本,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种说法本身是有问题的,它以价值评判模糊了文学质量,以文学生态平衡的名义逃避了直面更复杂的地方性写作。
而与此相辩证的,是熟谙地方知识与叙事知识的短篇小说作家,如何将标识着自己出生地或常住地的地域文学经验转化为文学地标,一如刘仁前之于“香河”(泰州里下河),焦窈瑶之于“芦镇”(以南京大厂为原型)。刘仁前在2019年继续着《香河纪事》的系列短篇创作,而焦窈瑶也在《与男孩三木重逢的夜晚》《鹤舞》《左轮造型》中继续着主人公与“芦镇”之间的同构,“芦镇”就像是一块海绵,“吸汲着这些不断涌流的记忆的潮水,并随之膨胀”。[2]事实上,无论是“代际”还是地域,只有切实与文学发生关系而不只是社会关系中的一种先赋地位,才能变成文学的语法。
三
青年作家的非职业化程度所标识的亦是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消费与生产的日常化程度。非职业化不只是现象,也是一种结构,只有将作家尤其是年轻作家的非职业化看作一种新型社会结构,才能更好地理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大量针对青年作家的扶植项目,以及作家非职业化本身对省域文学再造的意义。
随着年轻作家非职业化而来的是文学期刊在某种意义上承担起个人与市场之间的缓冲地带。年轻作家在刚刚涉足严肃文学时往往都从短篇小说起步,而像李黎、朱婧等这样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几乎只创作短篇小说的青年作家如今恐怕也不在少数。写作的日常化潜在内涵之一就是写作越来越个人化,这里的“个人”不是与公共相对的私人,而是指现代社会及其现代性所造就的“个体”。就像市场经济将努力与回报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样,写作的日常化也将赌注全部压在了作家个人身上。而此时文学期刊协同学术界的其他力量因子的救济力量就能发生作用,如2019年由《雨花》杂志所主持的“李黎作品研讨会”和“汤成难小说研讨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讨论并不只是为了评判好坏,也是为了即时地分散责任,为一系列的文学活动也为作家本人的创作情况“兜底”。正是在这样的保障下,有潜力的新人作家才能快速成长。
李黎和汤成难都是《雨花》“绽放”栏目在2019年度力推的青年作家。《雨花》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便与《钟山》一起构成了江苏集结和孕育文学力量的重要平台。2019年的《雨花》继“雨花催发”“雨花写作营”“毕飞宇工作室”之后,推出“绽放”专栏,以双月一期并举办作家作品研讨会的形式,力求为优秀的省内青年作家搭建面向全国的高层次平台。2019年作为“绽放”的元年,其首选的往往是现阶段已经具备一定创作实力或拥有一定创作成果的青年作家,其中包括江苏的汤成难、宋世明、李黎、朱婧和重木。
汤成难的《奔跑的稻田》《金光闪烁》之间隐约透露着延续性,好像要从地里拔出来的父亲和要把自己种到地里去的婆婆,都将对自己仿若无足轻重的事情过成了他人命运之中的转折。同为“70后”的宋世明在《大桥照相馆》和《如梦之梦》中打造出不掺杂质的童话结构,然而无论是有关长江大桥的集体记忆、“南京大萝卜”的市民群像,还是问题少年的成长,都是极难处理的主题,日常生活里的美好和奇迹,却不一定是文学语境里能够成为对抗遗忘的方式。李黎的《逃逸》发生在全民抗疫的“非典时期”,内里透露着青春期迟来的少年冷酷和无所适从。此外,李黎也在2019年为其之前持续创作的“水浒系列”画上了句号,正式出版了小说集《水浒群星闪耀时》。愈是年轻的作家往往愈有一种明确的为时代立传的迫切感,不管是业已从江苏“出走”的赵志明,还是作为2019年“绽放”栏目中唯一的“90后”的重木。重木的《近黄昏》试图打捞晚清民初那些传统士人的心灵史。《近黄昏》中建立在传统帝王史观之上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咏叹,或许并不成熟,但也不失为一次警醒。
“绽放”每一期除了刊载其扶植作家的一至两篇作品之外,亦同期刊出创作谈、专业评论和作家创作年表。于汤成难,有创作谈《先试着写令自己满意的小说》和陈进武的评论《倾诉与孤独的双重悖论——汤成难〈奔跑的稻田〉〈金光闪烁〉读札》,于宋世明,有创作谈《对抗“存在的被遗忘”》和贺仲明的评论《关怀生命中的日常和卑微——读宋世明两篇小说》,于重木,有创作谈《失败者的历史》和邵风华的评论《重现鼎革时期的彷徨与张望——评重木〈近黄昏〉》,李黎和朱婧只有评论,分别是李伟长的《好汉李黎》和何平的《致无尽的,致永在的,致难以归咎的——读朱婧两篇小说》和何燕婷的《家,当代人的战场——朱婧小说责编手记》,而这样集中且具有爆发性的专栏体式在“联网四重奏”前后到现在即有诸多先例,证明在推动年轻作家成长上行之有效。
这样的期刊行为所应对的不仅是对自身文学新人资源的优化,也对其所支持作家的自我塑造提出了一种技术性规范,即每一位从事实际写作的新人作家都被当作一种复合型文学写作者来培养,他们都必须同时是自己的理论家和方法论专家,并且依靠同行评议来不断更新自己的位置与责任。在新媒体、自媒体疯狂生长的时代,严肃文学本身是普遍难以融入到网络语境中的,短篇小说之短、之快并不意味着可以像公号文章或微博头条一样被碎片化地阅读。由媒介革命引发的中国新文学如今再次面对新的媒介。或许恰是文学期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2019年的江苏短篇小说乃至“江苏文学”“江苏传统”承担一部分基础性的注解工作。这不仅因为现代短篇小说与文学期刊紧密相关,通过策划与选择相互塑造,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短篇小说就是一种期刊文学,刊物所偏好、所选择的篇目,以及它们和“江苏文学”的关联性,其内在逻辑通常是能够自洽的。对于某一个省份的文学期刊,尤其是作家协会和文联系统的文学期刊,即便它有全国乃至世界视野,也不影响它去想象一个行政区划的地理空间如何成为一个有着共同文学精神的文学空间。
或许,技术的革新正需要用技术来应付。事实上,随着各类作家班、写作营的开展和创意写作专业的设立,专门的写作培训逐渐成为常识和入圈门槛,我们的文学时代正从年轻一代悄然改变。然而,写作培训至多只能是一种狭义的技术,因为技术不仅是叙事技巧,也是观念的转变和长久的经营,不仅是作家个人的文学观念,也是文学期刊乃至整个文学“江湖”的文学观念及其所沉淀的形制,文学乃是一种活动甚至运动。而对于一份过于简单又不乏偏见的短篇小说年度观察来说,恐怕最好的结果或许是三五年甚至更长时间以后,我们现在所困惑并提出的那些问题,已经被留在了过去,而我们如今所提及或品评的那些短篇,依旧在未来被置于它的现在和未来的脉络之中。
注释:
[1]郜元宝:《卑污者说——韩东、朱文与江苏作家群》,《小说评论》,2006年第 6期。
[2]王一梅:《“虚构的圣殿”和最初的宇宙》,《西湖》,201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