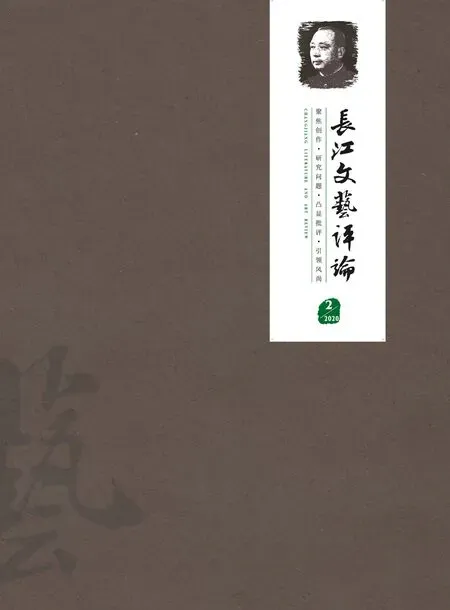“日常”如何“诗意”
◆卢 桢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日常生活逐渐进入诗人和评论家的理论视野。他们有意识地摒弃与意识形态勾连颇深的“大诗”写作和“英雄”情结,转向更为贴近生活本真的个人化叙事方式,着力强化诗歌与日常生活的关联,将西方美学话语的日常生活理论与跨世纪的新诗观念相互化合,从各自殊异的运思角度出发,抒写主体生存体验与生命感悟。一种沉潜于日常生活的先锋性诗学得以确立,并形成带有普遍性姿态的诗歌向度。
对于新时期以来诗歌中的日常美学,大多数写作者都没有从资本全球化的视域介入其中,也较少视之为反思现代性的基础。他们多将日常看作个体生存不可避免的现实,把它作为艺术和科学等非日常生活形式存在和发展的起点(在某些程度上和卢卡契的观念达成一致)。在对基于日常生活体验的诗歌话语的发现和重估中,写作者发现了蕴含其间的颠覆一元文化之无限可能,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也逐渐构成新时期以来诗歌的主要想象空间。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本真书写和审美再现,当代诗人建构起关于日常生活的叙事诗学,在民间立场上确立了日常生活的价值和意义。
于坚曾在给刘春的邮件中如此表述:“我强调日常生活,就是将日常生活神圣化。……重建常识、重建日常生活的尊严就是在今天也非常重要……我其实是把我那些朋友当作仙人来写,他们在我心目中决不是小人物,而是我生活世界中的天才朋友。我调侃的恰恰是那时代把天才视为庸人。这种神化日常生活,李白在酒中八仙歌中就做过了,只是时代风气不同,他的时代殷实,所以他喜欢夸张。而我是在20世纪为了掩盖真相而夸张成性的时代中回到事实。世俗化可以用于我之后的那些诗人,我并不世俗,我其实是升华了日常生活,将日常生活神圣化了。”正如诗人所说,作为朦胧诗的反拨性因素,日常生活美学最初以“生活流”的姿态升华了平民的普通生活,同时在技术上将口语元素频繁纳入诗歌的意义生产。很多诗人采取一种有别于朦胧诗的平民视角,把抒情重心从彼时曾经流行的家国经验拉回到凡夫俗子的喜怒哀乐中,给予读者一种贴近现实的亲切感。如韩东的《大雁塔》、伊沙的《车过黄河》、于坚的《尚义街六号》等早已被文学史经典化的篇章,既是消解沉重文化意义的解构之作,又是各臻其妙的个体美学发现之作。这些文本语言浅近,内容生活化,呈现出许多极富幽默感的细节,人们从中既可感受到文学的魅力,也能察觉日常生活的诗意,因而深入人心。
文学“个体”在生活中的重新发现,影响到1990年代乃至新世纪诗学中的“个人化写作”“口语诗”“底层写作”等观念的萌发与成长,特别是诸多诗人和评论者早已视“日常诗学”为首要的诗学维度,其为诗为论,均不离日常之左右。当日常已成为一个显在的诗歌元素后,它将如何引导诗歌审美建构,它自身是否存在泛化等问题,它是否还具有相对可延伸的发展空间,这些问题依然值得讨论。
一、日常生活与诗学的互喻
与传统诗歌相比,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典型意象与特定心理的对应关系,诗人们意在通过口语贯通日常生活气息,以“个人化的象征”联络外在世界与内在心灵,从而抵达情感的真实。“第三代”诗人文本中的抒情主人公再也不是北岛作品中那种“第一千零一名的挑战者”,也不是顾城诗歌中寻找光明的“黑眼睛”,而是个人日常生活的体验者。大批诗人重新开始思考诗歌与现实的关系,并认为“诗歌的语言也就是生活的语言”。[1]
日常生活与诗学的联姻,在语言上首先表现为从口语中挖掘诗意。在第三代诗人笔下,日常审美集中由平民生活审美所呈现,他们对语言作了凡俗化的艺术处理,以摆脱宏大观念对思想的钳制。于坚的《下午,一位在阴影中走过的同事》《尚义街六号》便以俯瞰生活现场的方式,不断堆积大量的“物性词语”,表达对现实生活,特别是市井生活的贴近,正切合了其“拒绝隐喻”的诗学主张。在口语般的絮叨中,诗人与城市(昆明)拥有同样的观察视野,他不会比城市看到的更多。抒情者处于一个纯粹由冷叙述积聚而成的内焦点,用絮叨的口语不断印证着:诗歌中的“现实生活”本就是对日常经验的复制。
同样立于“平民”的观察视角,伊沙的视点较之同代诗人显得更为独特。在《下午的主场》中,他消解着自己对坐在球迷中间的妓女产生的某种诗意联想,并赋予“她”和自己同样的身份——球迷。都市文化的繁复性使现代人的角色与身份的边界不断漂移,角色转换与身份倒置使诗人无法把自己从城市诸多欲望交织的网中疏离,他们只能以“肉身”的知觉方式去感受日常生活。在球场中,抒情者与妓女的身份并无不同,诗人以“牛粪”式的自嘲,传达出“直面当下”的一代人对“底层”生存价值的平行式认同。
吴思敬先生说过:“九十年代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生存问题,诗人喜欢从身边的平凡事物上取材,从而折射我们这个时代普通人的生存处境,以及面临生存危机的疑惧与焦虑。”[2]从“第三代”诗人群开始,写作者在日常文化与生命殊相的融合中,便已把日常化的审美意识纳入创作实践。日常生活美学为诗歌引入一种“平民化”的价值理念,这与20世纪末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转型密不可分。诗人们意识到,诗歌精神不再需要通过塑造英雄传奇来实现,它更依托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理性原则和现世主义观念使他们珍视自身的日常体验,在浩瀚的生活之海中打捞属于自己的主体独立意识。“诗人们自觉到个人生命存在的意义,内心历程的探险开始了。”[3]于坚的话正是将日常生活的诗性视为生命与灵魂的象征,在外部世界和群体经验愈发不可信任的时代,惟有自我的生命意识才具备超然之力,它可以使精神主体摆脱文化伦理与历史意识的困束,以及物质对人的感觉、记忆和下意识的侵占与控制,使其在内部世界中保持完整的自我形象。这也就印证了崔卫平的话:“日常生活就是这样一种既不粘不稠、又像磁粒般吸咐、吸引的东西,要想摆脱已不可能。”[4]
价值观念上的“平民化”与诗歌语言上的“口语化”,以及美学生成方式上的“叙述化”共同构成了新诗日常生活美学的三重维度。“第三代”诗人提出“诗歌以语言为目的,诗到语言为止”[5]的口号,他们取消了将语言作为营造意象的手段,不再把语言本体的自足性奉若圭臬。针对朦胧诗以来将意象崇高化、所指陷入单一的意义危机,他们力图使意象与“具体化的感觉”建立距离,“象外之意”亦被取消了特定的喻指关系,大量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片段开始以口语形式进入诗歌。看于坚的《我生活在人群中》:“穿着一双皮鞋/我生活在人群中/有时欢天喜地/有时沉默忧伤/我的房间很小/我的朋友很多……我生活在人群中/穿普通的衣裳/吃普通的米饭/爱着每一个日子/无论它阴雨绵绵/无论它阳光灿烂”。人群中的“我”是一个小写之“我”,在诗人的娓娓叙述中,俗常个体本真的生活经验流动而出。
对日常生活而言,针对它的表达既可以由词的组接实现,也可以通过一个个小事件组成的句关系展露,以事态意象取代物态意象曾经占有的主导地位。事态句组的活跃,直接增强了诗歌的叙述性,诗人的写作与生活就此形成互文。在成员多散居在消费城市的“他们”诗派那里,核心成员韩东和于坚均喜好采撷都市的凡俗事态片段入诗,特别是于坚,他的诗以“在结构现代城市社区形态史和心理史上表现的材料意识与情节性的叙述特征”最为显著,“具有与机智空灵相反的从容与大度,并含有特殊的小说因素”。[6]在《远方的朋友》《罗家生》等早期作品中,于坚在日常生活经验里发现了语言的运动和它自身的能动魅力,90年代完成的《○档案》和“事件”系列更是以语言作为言说体制的工具,形成一种“生活流”的事态语象。这样的技法,正可使读者触碰到日常原色生活中的语感脉动。其诗性叙事凸显出诗人切入生活的独特角度,带有与生活平滑的对接感,叙述性的强化成为诗人完成虚构事件的活力来源,而零度的姿态又昭示出他们的抒情策略。
生活叙事成分的介入,似乎成为诗歌自身发展的新动能。日常叙事手法直达诗歌本体和人类的心灵结构,如敬文东所说:“人是叙事的自行展开,叙事状态是人生活的常态。只有叙事才真正配得上人的日常生活。”[7]多彩的现实世界化生为一个个段落式的生活情节,诗歌的叙事成分和戏剧化因子得以滋长。这些事态意象参与诗美构成,必然要求取自民间的、不需形而上淘洗便可直接使用的日常生活素材,这使得现代抒情个体的日常经验既要拥有整体上的凡俗特征,又要具备个体的复杂与独特性,正所谓“凡俗之中的诗意”。从诗歌形式角度观之,这样的诗性叙事将日常生活语言纳入诗歌语言,呈现出生长在城市文化之中的当代口语特征。蕴涵在日常口语中的平易与亲切、诙谐与反讽等诸多要素,进一步拓展了当代诗歌的语感空间。以口语语感承载诗歌抒写的叙述性脉动,表达对恢复“日常生活合法性”的情感诉求,逐渐成为诸多文学实践者积极倡导的诗歌美学新向度。
读那些深蕴日常生活诗意的文本,总能感到由口语的字句节奏所衍生的、舒卷自如的情绪节奏。于坚强调过日常语言节奏与诗歌语感之间的联系。他要建立的应该是能够“拒绝隐喻”或“回到隐喻之前”的,具有“流动的语感”的新语言,即回到诗歌作为日常生命形式的本真,能与同时代人进行最熟悉、最亲密交谈的话语形式,凡俗日常生活的口语正与他的要求两相吻合。韩东也说:“‘诗到语言为止’中的‘语言’,不是指某种与诗人无关的语法、单词和行文特点。真正好的语言就是那种内在世界与语言的高度合一。”[8]在“回归语言”的过程中,得到强化的“口语”表现出诗人对“回归生活”的渴望,以及他们在共时的时间结构中对主体“存在感”的瞬间领悟。对生活在商业化时代的诗人来说,口语句式既是他们的叙事策略,同时也已影响到其文本整体结构的构成。丁当、王小龙等人便擅于用口语化的语言,描绘追求个人日常生命价值的“新型”自我形象,其诗学主题便是:要获得真正的自我就必须承认普通的日常生命。进入新世纪,运用并改造口语以增强诗歌语言的叙述性,依然是多数诗人在日常生活中寻觅诗意的首要途径。唐欣的《北京组诗》便发挥其一贯的对日常视觉素材的捕捉力,文本通篇采用漫谈式的口语,联络着诸多现实与历史杂糅而生的印象片段。同时,诗人对“零度”的情感姿态进行了调整,他采用大量“诉说式”的口语,并与叙事性内容实现珠联璧合。通过口语而完成的叙述,以其一次性、现时性和不可替代性应和了日常生活的“非诗意”以及“瞬间化”的情感特点。从表达系统层面言之,口语表达系统隐含着对书面语言(精英文化意识)的反叛,同时也是诗人谋求回归民众的有效方式,其美学基础是日常凡俗性的审美追求,而生活“此在”的种种荒诞与矛盾,则是构成其文本话语张力的主要来源。
二、诗人在日常中的自我超越
先锋诗歌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为契机实现的历史转变,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商业化转型关联密切。欧阳江河曾说:“对我们这一代诗人的写作来说,1989年并非从头开始,但似乎比从头开始还要困难。一个主要的结果是,我们已经写出的和正在写的作品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中断。”[9]他的《傍晚穿过广场》可以看作是对1980年代的正式告别,同时也可以看作是知识分子庙堂情结裂变的标志。作为政治活动载体的传统意义上的广场,此时却成为日常商业符号的广告牌,它悄无声息地记录着1980年代、1990年代中国发生的现代性变异。在杨克的《天河城广场》中,凝聚一代人国家想象的、政治意义上的“广场”被物态实体的商业建筑取代,诗歌也开始从构筑神性世界向以追求即时愉悦性的、以商业化为推动力的大众日常生活审美进行转移。“广场”的意义经历了一个由上而下的意义衍变,从中或可窥见1990年代诗歌较之前代的观念新变。自1980年代出现的一系列“PASS”“超越”等口号理念,正是对崇高、理想、价值等宏大命题的诗学拆解。而1990年代诗学则注重捕捉感性印象,在世俗精神中强化生活的偶然和无限的可能性,文化的负载感已无足轻重。诗人开始以轻松的姿态与日常生活对话甚至调侃,在对日常生活的“冥想”中直接进入文本,与日常文化保持着共谋的姿态,弥散出现代人消解历史的“当下性”气息。
曾几何时,远离具体的生活语境,专心修缮自己的心灵孤岛,从而与高逸孤绝的思想境界相通,成为诸多诗人苦心孤诣的企慕情境。但是,完全脱离具体生活的哲思即使能够触及人类某些共性的经验,也因其意象过于诡谲、语言偏向晦涩而难以进入阅读者的视野,从而影响其生命力的延续。诗歌是个人化的艺术,一些抒情者往往乐于在心灵的孤岛专心耕耘,甚至沉浸于“自我的时空”而疏远现实生活,这种抒情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世俗经验对内心的干扰。不过,在理想中飞翔固然充满快意,却也容易受到个体经验的限制,沉入凌空虚蹈的自闭状态。
新世纪以来,诸多诗人寻求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对话的渠道,对自身所处的心灵“高度”进行调整,其文本也表现出“及物”的烟火气息,这彰显出诗人主动与时代语境建立对话联系、并积极介入周遭日常生活的努力,以及日常生活美学对诗人物质观念的解放。例如,惯于抒写心灵“痛感”经验的李轻松写下了《煎鱼》《一道汤》《一顿早餐》《你好,亲爱的厨房》等一系列作品,从这些诗题便可看出,诗人以一个完整的生命本体姿态进入琐碎的生活,进而发现日常经验中所拥有的审美性质。在《来杯茶》一诗中,这种“及物”的转变表达得直截了当:“让我收起那些锐器吧/让我学会喝茶/用清水洗脸/学会跟自己说话/炒菜、煲汤/避过一些危险的瞬间/那些平淡的事物/正渐渐地显出它的力量”。身处日常生活却又与之拉开距离,透过“清淡的物质”,诗人学会以微笑面对时代的病症,为痛感找到新的栖息之所。再看蓝蓝的《让我接受平庸的生活》:“让我接受平庸的生活/接受并爱上它肮脏的街道/它每日的平淡和争吵/让我弯腰时撞见/墙根下的几棵青草/让我领略无奈叹息的美妙”。诗人的精神意向对物质文化彻底敞开,其自我意识的倾注焦点完全转向物化对象或现实,由此触碰到生存的可感性。可见,诗人所及之“物”已经失去了国家主义的意识支撑,它们蔓延在个体生活之中,为标注个体存在提供了想象的抒情样式,正如王小妮的《喝点什么呢》《活着》等文本,诗人轻松地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美的元素,仿佛他们对日常物质代码的亲近是天然的,对这种经验现实唯有接受,无法割舍。杨克有一首诗题为《在物质的洪水中努力接近诗歌》,虽然诗行里始终演绎着超越物质的精神“终极”幻想,不过诗人能够将物质社会作为“美”的基点,仍然值得注目。抒情者“及物”的目的,正是为了强化诗歌写作与日常生活的联系,同时也恢复了“物质”欲望的合法性,使其成为汇合或释放所有感受力的渊源。在这些抒情者看来,当代的生存首先便是欲望化的人之生存,对物质欲望的本真认同便是对世俗化表层生活的体认。
走进生活,认识日常之美,这是诗人重新定位诗歌写作与现实生活关系的实践,他们在艺术的自主性、独立性与艺术反映现实、干预现实之间寻找着平衡。通过“及物”的努力,诗人们不断寻求在日常生活的“此岸”和诗歌的“意义生产”之间建立经验联系,使其人文精神与公共精神实现统一,新世纪诗歌言说现实的能力也由此得到了增强。在重大事件如地震灾难面前,诸多诗人表现出令人欣慰的承担意识,他们认识到,面对现实世界,诗歌难以充当万能的武器,因为时代的外表坚硬无比。更重要的是,诗人永远无法穷尽灵魂与语言之间的表达,它的有限性决定了诗人失败的宿命。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灾难面前,朵渔会以《今夜,写诗是轻浮的……》作为诗题,在灾难的黑暗之上进行抒写,无异于对黑暗的掩藏与逃避。诗人要想名实相副,就必须时刻怀有对周遭环境的洞察力,既能承担现实中的种种痛感,又能在道德良知的督导下进行独立判断,正所谓“以心及物”。这体现出新世纪诗歌的一个热点,即诗人的观念尽管存有差异,但介入现实抒写生活的兴趣却在不断增强,其诗意表达也更富有当下性和时效性。他们中的很多人拒绝单纯形而上意义的写作,也警惕那种充满幻觉意味的精神自恋,如欧阳江河曾说的要“追求一种诗歌的痛感和真实性”,不作情感的过度表演与软绵绵的私密经验暴露。因此,新世纪以来的写作者大都能从存在实际出发,有效勾连诗歌文本与生活现实,将“及物”与“及心”统一在一起,凭借其艺术直觉力捕捉到那些易于从指缝之间匆匆滑过的、凡俗中的瞬间之美,也从人们对日常生活的种种经验预设和先在判断中抽离而出,找到专属自身的心灵节奏。一个个极其凡俗的日常生活片段,神秘无声地滑入抒情者的诗歌视阈,通过对动态细节的诗意还原,现代生活的情感经验在诗人心中神秘化地完成。
在精神求索的过程中,诗人的情绪逐步恢复常态、回到人间,诗情特质也由滞涩向澄明转移。这种澄明,既是感性的显现,也是本体的敞亮,广远、自由而充满诗意。通过身处凡俗生活,抒写日常点滴,诗人们找到了安置自我的一个途径,同时也发现了一种锻造语感的方式。为了追求经验的澄明,很多诗人还特意调整了抒情的“速度”,减缓了行走的步伐,即身处日常生活之中却又与之拉开距离,透过专属自身的语言中介,诸多诗人找到了发现自我的二次途径。他们希望借此突破语词的限制,获得反身的能力。在抒写日常生活片段时,一些写作者注重将情感作“内敛”化的处理,使用简净的字词和素朴的意象,以使每一寸的抒写都能落到心灵实处。当然,这里的“内敛”并非源指某种诗学技巧,而是诗人真实地、与世界展开对话的方式:恬淡、平静、偶露锋芒、进而速归本真的朴实之境,品读这类文本,可以感受到抒情者隐显适度的情感表达。如大解的《个人史》,诗人在细小事物中发现了时间的秘密,并以“时间”诗化了他的想象。时间的惯性无法回避,而诗人的主体性反而得以生长。他在世俗的主流时间速度之外独辟蹊径,专心经营属于“个体”的时间,从而在建构个体心灵史的过程中使时间也变得“个人化”了。借助“时间”与“书”的象征脉络,诗人随心所欲地自由压缩或是延展属于心灵记忆的那部分时间,令凡俗生活的琐碎瞬间竟也产生丰沛的诗意。
艾略特曾将历史意识作为诗人的要义之一,在很多诗人的文本中,历史不是他所经历的线性生活时间的总和,而是经其心灵运思之后着意拣选出来的、重述之后的“发光”片段。时间既涵盖着诗人已知记忆中的吉光片羽,同时也指向他的未知经验,维系着诗人对存在感的承担与言说,以及他对生命的热爱和敬畏。这种对日常时间经验的反拨,正如海德格尔所认为的,日常生活并非自足的价值和意义的根源,它甚至“是一个全面异化的领域,一种非本真的存在状态。”[10]无差别的日常生活消弭了人类的自我时空感,他们被裹挟进千篇一律的大众主流速度和时间中难以超脱,个人的“此在”消融于他人的存在方式中,难觅个性与锐气。而诗人所要做的则是对日常生活保持足够的反思,如波德莱尔式的,既能深入他所经历的时代,又能顺滑地从人群中抽身而出,成为“人群中的人”,于此方可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挖掘出独特的、被隐藏的事实,让诗歌真正抵达意义。胡弦的《钟表店》正是一首关于自我意义如何生成的诗。金属盘、珐琅壳、筋疲力尽的发条和电池……每一个钟表原件都代表着矛盾而驳杂的时间碎片,隐喻着这个时代总体性破碎的事实,而人们也难以在机械复制的世界里觅得完整的自我形象。对诗人而言,这时恐怕就得借助修辞的转换之力,尽可能地“学一只停摆的钟”,以主动寻求“减速”的方式,发现缓慢乃至停滞的时间感觉。经历了生命的轮转,作者找到了高于生存的东西,他可以在最纯粹的感性经验中发掘属于个体的时间,由经验抵达经验,为自己的精神存在找到合适的栖所,甚至可以借此静默观察那些微小的细节与可爱的事物,由此获得重新指认世界的机遇。现实主流速度与个体心灵速度所形成的悖论,成为诗意产生的重要契机。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加速的飞翔,还是减速的写作,都是在现实的平面时间之外,拓展富有独特心灵体验的时间纵深感。人类共性体验着的时间也是日常生活经验的象征,借助对这类经验的超越性抒写,诗人们获得了重新认识自我的机会,其心灵探秘的深度与情感表现的浓度也得到了相应的提升与增强。
三、问题与展望
在西方的美学话语体系中,“日常生活”概念经由卢卡契、胡塞尔、海德格尔、列斐伏尔、鲍德里亚、费瑟斯通等理论家的持续讨论与充分发酵,已成为西方学术界的一个显词。自20世纪90年代始,主体主义得到了恢复与强化,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了超越主体性思维的生存逻辑,探索出反权威的行为方式。“日常生活诗学”逐渐进入诗歌写作与评论者的话语范畴,诗人以此为契机,纷纷从自我的生命意识出发,将日常生活的诗性视为生命与灵魂的象征,不断为适合自身的写作打造“合适的鞋子”,借助与日常生活同步的语感节奏,让温情与痛感缓缓流出。在处理具体的情感信息过程中,很多写作者能够熟稔地使用简净的字词和素朴的意象,以使每一寸的抒写都能落到心灵实处,这是诗人真实地与世界展开对话的方式,但有时情感过于平实化的展现,也或多或少使得诗意“显在”的成分过多,而“隐秘”的成分不足。一些诗人在最大限度逼近生活本真的同时,某些“口水式”白话的泛滥,仍然需要引起我们的警觉。诗歌语言毕竟不能照搬生活语库,它应该是从粗砺的日常口语中提炼出的具有表现力的文学语言,是文字化的灵魂。如果落入口语的快意放纵与无深度的意义陷阱,便会在取消形式的过程中,再次受控于新的话语暴力,沦落为形式神话的囚徒。即使是用日常口语营造出诸多貌似无序的意义片段,其诗歌内里也应保有一定的逻辑性,以在相对闭合的语言空间中形成对日常生活的集中隐喻。口语化的“日常”经验应与“知性”经验再次化合,这是关乎诗歌生命内核的重要品格。
如上所述,将日常生活简单化理解和使用,片面认为它就是用口语写日常生活,而忽视了对日常经验进行反思与提纯,缺乏价值层面的二次加工,导致的问题就是诗歌的崇高精神和典雅形态被日常琐碎事物和形而下的庸俗经验所遮蔽,最终很可能会导致话语资源的枯竭、审美的泛化与抒情的失效。在当今的消费语境下,社会同质性的消解使政治、经济、文化三者之间呈现出清晰的分裂状态,难以相互阐释与支持。在物质浪潮中,诸多诗人秉持一种通俗实用的、迎合感性现代性的审美倾向,强调个体的感官经验和物质欲望的合理性,从日常的层面进入诗歌现场。不过,在具体操作中,有些诗人过度消解了“深度”,非常容易滑入审美的粗俗化。日常生活和文本影像之间的差别消失之后,诗歌的“经验中介”作用反而陷入了尴尬。同样,对叙事等技巧的过分沉迷也使他们长久处于非理性的无根状态,空有语言快感和形式新意,却又因强调“体验的当下性”而忽视了生存的历史根基,在丧失历史与未来的纬度之后,难以形成超越意识。诗歌的意义在于发现“新奇”,但问题是这样的“新奇”应该具有对历史的回溯力和对未来的前瞻性,就像于坚十几年前的旧作《飞行》一样,岁月飞逝,文字中的预言竟然一一兑现,仿佛具有先知书般的魔性。遗憾的是,大多数诗歌在日常生活所具有的消解性面前都很难形成指向未来的尺度,诗歌走进生产线,迈向一个个“秀场”,在经历无数次“一次性”的消费之后,仅能为受众带来瞬间的话语快感,难以沉淀出持久的意义,这同样是新世纪诗歌存在的普遍问题。
昆德拉说过:诗歌的使命不是用一种出人意料的思想来迷惑我们,而是使生存的某一瞬间成为永恒,并且值得成为难以承受的思念之痛。任何形式的创新和实验、思想的扬弃与升华,目标都是为了捕捉定格在这“唯一”瞬间的意义永恒。今天,日常生活的当下现场仍然是这种“永恒”之美的源发之地。大众群体多元的生活状态触发了诗人的诗情,使他们注重挖掘隐含在日常生活之中的事态化文本,将其作为整体性的诗歌意象进行诗意沉潜和智性加工,并以口语的方式动态呈现出日常生活的现代脉搏,实现戏剧化的效果。这既是诗人在美学探踪过程中的必经阶段,同时也是中国进入城市时代的内在要求。日常生活的缤纷物象、周遭人物的市井百态、活动空间的经纬方圆……都要借助诗人的捕捉,进而透过抒情者智慧的想象力,从瞬间物象被点染为诗歌意象,成为具有意味的客观中介物。对诗人而言,他需要在对日常生活的惯常性思考之外,透过潜藏于心灵中的另一双“眼睛”去发现超越日常经验之外的世界,探索隐藏在生活表象之下的潜在风景,从琐碎而非常规的细节中重构总体,为日常美学浸染下的当代诗歌寻求经典化之可能。
注释:
[1]孙文波:《我理解的九十年代:个人写作、叙事及其他》,载王家新、孙文波编:《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0页。
[2]李复威主编、吴思敬编选:《九十年代文学潮流大系:主潮诗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序言。
[3]于坚:《诗歌精神的重建——一份提纲》,载陈旭光主编:《快餐馆里的冷风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0页。
[4]崔卫平:《诗歌与日常生活——对先锋诗的沉思》,《文艺争鸣》,1995年第4期。
[5]韩东:《自传与诗见》,《诗歌报》,1988年7月 6日。
[6]燎原:《东方智慧的“口语诗”冲和》,《星星》,1998年第3期。
[7]敬文东:《诗歌:在生活和虚构之间》,《诗歌在解构的日子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8]万夏、潇潇主编:《后朦胧诗全集》(下册),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39页。
[9]欧阳江河:《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和知识分子身份》,《今天》,1993年第3期。
[10]【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