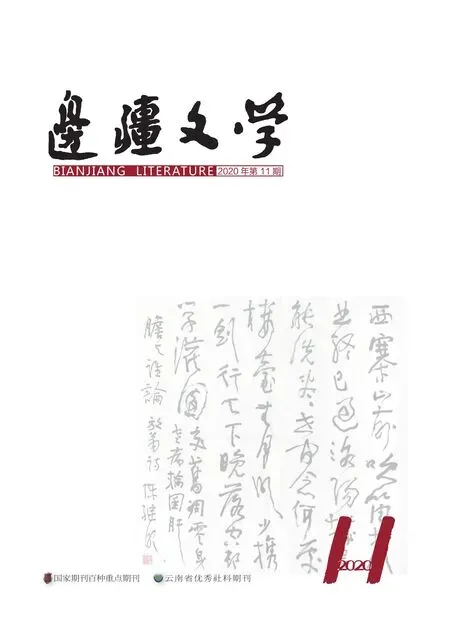扫把客
徐晓华 土家族
高大浓密的竹荫罩住了扫把客。
弯刀挥起,雪白的弧光划过,竹枝嚓嚓的断裂声,竹叶沙沙的叫声,蹦进他怀里。
竹枝剔得差不多了,他靠住一蔸腰杆粗的楠竹,坐在疏软的竹叶上,双腿夹住捋顺的竹枝,一枝压一枝,到虎口握不住时,不用数,一定有二十四枝了。竖起来笃齐整,拿蒸熟后的慈竹篾打三道箍,翻来翻去看几眼,才扔到扫把垛上。
有四十几把了。这一天他只干得了这么多活儿。拖着一瘸一拐的腿跨过七十九岁的门槛,再进山,发觉手脚慢了,眼睛雾了。原来一天扎六十多把,下坡时太阳还不得落土。长一岁就翻一道门槛,看来吃八十岁的饭,不简单。
他想得开。村里好多一起长大的伴,骨头早就打得鼓了,剩的几个,也是药罐子煨着的病秧子,走平路都喘气,哪还能在山上梭上梭下。
楸木园的竹林望不到边。得趁天光赶回家做晚饭。儿子也有乖的时候,吵着要帮他做饭。他相信儿子煮得熟。等他进屋,看到儿子坐在灶门口,扎好的扫把当了柴禾,竹枝在灶膛里爆出的火光,照着儿子一脸憨憨的笑。火光里,儿子脸上的胡茬,白了好多。
锅里的米香了。扎了半天的扫把却成了粉白的灶灰。
他没有责骂儿子。他舍不得骂,卖扫把养大儿子不容易。儿子不是为了挨骂才到人世投胎的。养了儿子就要疼。快五十岁的儿子,还跟五六岁的小娃差不多,不懂事哦。那又如何?总归是他这根竹蔸发的笋子,是他周和举的后人。别人说儿子傻,他不服气,我儿子会扎扫把呢。这是实话。堆得小山样的竹扫把,最后一道装把儿的活路,是儿子做的。裁一样长的竹棍,插进箍好把的竹枝,留一尺二寸长的柄,然后十把一排,一百把一摞,好生生地码着。儿子也没读过书,数得一把不差,那是傻家伙会做的事么?
他固执地认为,儿子识数,是跟他卖扫把时学会的。儿子八岁那年,娘亲没了。他去城里卖扫把,只好带上儿子。从楸木园进城,要走过去挑盐的西大路,两尺宽三寸厚的青石板,嵌在红砂石山间。石头缝里蓬了青草,挠得脚背发痒,也不晓得好多挑盐的把铺路石磨光了,赤脚走过,不扎脚板。下再大的雨水,也不打滑。他不晓得刀背一样陡峭的山,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丹霞山,一座挨一座,一直长到城边上。沿路有一层层绕山的茶园,也有一片片亮亮扫扫的竹林。伏天,竹下躲荫;雨大,竹丛挡雨。累了,竹叶比铺盖软和,倒下就睡得着。要在桃花天,会遇到挖笋子的人,老远喊他,扫把客,挑了好多,挑的是一担钱呢,要不要笋子?拿几节回去炒肉吃。他连忙摆手,不要不要,吃不惯那个东西。白送你,又不要钱,客套么子。
哪是吃不惯?笋子炒腊肉,香香脆脆的,吃得饱吃不厌。平日里带儿子出门吃酒,席面上要么有新笋炒肉,要么是干笋炖鸡汤,都是恩施人爱吃的家常菜。儿子一双筷子,恨不得时刻伸进笋子做的菜中。问过儿子多少回,笋子好不好吃。儿子指着竹林含混地说,竹子——好,笋子——好。
他舍不得吃笋子。扎扫把的人,全家的衣禄饭碗,长在竹林里。老竹发新笋,新笋长新竹,新竹发枝叶,到了伐竹时节,竹林的主家拿竹杆派了大用场,竹尖子丢在竹林里,等干枯了,做引火柴。可在扫把客这里,竹尖却是个宝。竹枝多长在竹尖上,又韧又柔,剔下来扎竹扫把,哪个都喜欢用。乡里人家,扎了扫院坝,软和的竹枝,不伤泥巴夯的地皮;城里人,买去扫大街小巷,一扫把过去,半边街就干净了。若贪心、好吃,笋子挖绝了,竹林就败得快。好比一个家族,只剩老的,不添丁加口,那要绝后,哪有个盼头。再说,竹子败了,拿什么扎扫把呢?有时去街上赶场,看到菜摊上堆着又粗又壮的笋子,剥得只剩一圈白花花的笋肉,他不敢多看。看久了,觉得那就是竹摇篮里粉嫩的月娃娃。
他万没想到,一夜高烧,让新笋样活鲜鲜的儿子变得痴痴呆呆。本来就体弱的妻,成天面对痴呆的娃儿,落下个心痛病,没过几年,丢下他们父子走了。
扫把客赶急下城里,把半堵墙高的竹扫把卖了,买口黑漆棺材,把妻葬在南河岸边最大的竹林里。那地方向阳,一坡竹子长得密,画眉儿从早到晚在林子里蹿,好多股山泉水冒出石缝,汇入溪沟,像一匹白绸子挂在南河的悬崖上。到了秋天,河里捉鱼儿的白鹭拖儿带崽,歇在起伏的竹梢,啄几下羽毛,抖几下翅膀,一家子就驮着清亮的阳光,飞向另一片竹林。睡在凉悠悠的竹林中,妻有福气呢。
他经常带上儿子,去那片竹林。他坐在坟前扎扫把,儿子捡一把竹枝,爬上坟堆,把坟上的枯竹叶扫得满天飞。枯干的竹叶,纸钱样飘下来,有的粘在他头上,有的钻进他怀里。落雨天,早已成年的儿子换了玩法,抱住竹子使劲摇,竹梢像一条长辫子,摆过去摆过来。枝叶上亮晶晶的水珠洒下来,儿子迎着水珠张大嘴巴,接到一滴两滴入口,就大笑着喊,妈啊,起来喝糖水水,糖水水,甜蜜蜜。听到儿子喊叫,他就抬起手中的竹枝,挡住了眼睛。他不能当儿子的面流泪。太伤心,会让好人都变傻。
当年,竹枝上的露水救了他的命。十二岁那年吧,右腿割草沾了瘴气,长一腿的恶疮。家里穷得舀水不上锅,哪有钱去大医院看病。找草医讨的草药敷了几个月,并不见好,躺在屋里半死不活。大人也想不到方,只好出工前,支张木床,把他放在门口的竹林里。那里有雀儿闹,有花蛾子飞,有松鼠跳,看它们时,腿就不那么疼了。吹大风的时候,他更是喜欢,几百上千根竹子嘶叫着冲前冲后,冲上冲下。竹叶上许多露珠抖下来,落在火烧火燎的腿上,清清凉凉的,蛮舒服。嘴巴干了,就望着竹尖,挪动着头,等一滴两滴露水润口。那露水不像井水,也不像河水,浆一样的黏糊,进口一股清甜味,吞下肚子,又像南河里的土虾子,游进了浑身的血管里。那以后,他每天都要大人把他抱进竹林,一进竹林,他就忘了痛。没风的日子,他使劲摇晃竹子,盼着露从天降。一天熬一天,四年过去,腿上发臭的恶疮竟然收了水汽,长了新肌。腿,残了。命,却捡了回来。怪的是,他站起来的那年冬天,一园竹子却回了头,一根根枯干了。第二年春,再也不发新笋,几年过后,那片竹园就成了长着乱草的荒地。有个老篾匠说,露是竹子的保命水,掉光了,竹子怎么活得下去?
到每年十月,他会问人家讨几根竹母子,栽在妻的坟前。原来那竹林,只长楠竹,他要栽上慈竹。慈竹梢子长、竹性柔韧,竹尖在风里摆来摆去,就像妻摆来摆去的长辫子。慈竹最肯发笋子,一蔸竹母子,不上三年,就挤挤满满一大丛。虽然他只读过一年级,却懂得慈的意思。上慈下孝,慈母慈爱,村里一代一代人都是这么传下来的。妻在世时,不算能干人,心地却好,不论手头多么紧,扎的扫把先送周围团转的人家用,再扎的才会去卖。儿子也喜欢慈竹,砍一节下来,剖一个口子,衔嘴里吹,嘟嘟的哨声整个楸木园都听得到。有了慈竹哨子,儿子成天吹,不在他身边时,找起来就容易,哨声在哪儿子就在哪。他扎扫把做箍篾的,也是慈竹篾。扫把不打箍,是散的。好比一家人,没得妈,就少了箍力,终会七零八落。妻走了,他靠什么箍住一家人呢?他每天就望着楸木园的竹林,望着发的新笋,望着新笋长粗,长壮。竹子多了,竹林密了,有人砍竹,他才有竹尖子扎扫把。有了竹扫把,父子俩的日子就有了指靠。
比不得腿脚利索的人,从楸木园到恩施城四十里山路,挑百多把竹扫把,清早出门,进南门城门洞,天就要黑了。去的年代多了,城门洞下摆摊的都成了熟人。炸油馨的胡妈嘴巴快,给他编了个谚子:扫把客挑担子,一头高一头低。嘴里说笑,心里却疼着父子俩。夜饭,照例是胡妈请客。没什么好吃的,锅里的油渣用漏瓢捞起来,一人舀半盘子。卖散装包谷酒的蒲老三,会打半碗酒端过来,陪他喝几口。有酒有菜,一路的劳累就在日白夸海中消解了。
他还在喝酒,儿子早跑去看扫街的人了。抓住人家手里的竹扫把不松手,喊,爹吔,是我屋里的扫把。扫街的就逗儿子,是我路上捡的呢。儿子就把扫把抢过来,指着扫把箍上的篾,重复着说,是我的,我的。儿子真没搞错。他扎扫把用蒸熟的慈竹篾打箍,扎得紧,竹枝轻易不掉,用得久。别人扎扫把,用的生篾,几个太阳晒,几场大雨淋,篾箍会变形,用不了几天扫把就散架了。胡妈经常笑他,扎一辈子扫把,也不晓得取个巧,一把扫把用几个月,扎新的卖哪个去?他就反问道,你的油馨哪门不少放点米浆,三个当做四个炸,挣的钱不多些么。胡妈就正儿八经地说,几代人的老摊子了,做吃的东西,搞得假么,哪比得你扎扫把,好歹都是扫地。他就不搭话了。心里却说,未必看不到通城用的都是我的扫把么,不经用,哪个还要。
夜间父子俩就在胡妈屋里打地铺睡。次日天不亮起来,留三把竹扫把算是答谢,也不告辞,就往恩施师专去。他一直叫三孔桥那学校为恩施师专,后来也知道改了名字,叫湖北民院。怎么改,他并不关心,改了,那里的人还是叫他扫把客。学校用的还是他的扫把。只是送扫把的时间,越来越密了,每次要的量,也加了几十把,一年算下来,得一千五百多把。想想也是,当初进校门有个球场坝,栽的一圈梧桐树,只得手杆粗,如今树枝比手臂还粗,树皮也起了一块块的斑点,跟他脸上的老年斑差不几。树大落叶多,人多灰尘大,扫把是得多要些。他并不知道,他慢慢变老时,校园大了好几倍。
每学期开学,第一次去送扫把,门卫上戴红袖标的值日生会拦下他。免不了一番口舌,才进得去。以前,值日的都是本地口音,往后说普通话的多了,得仔细听,才晓得个大概意思。硬是进不去时,就报出管后勤的小王的名字。小王该叫老王了,在他手里买扫把,也有了三十好几年了。价钱从一毛钱一把,涨到了五块钱一把。走进校园,他不看那些高房子,只低着头看路上,看广场。四处干干净净,脸上就泛了光,好像是他的功劳。看到扫地的学生,要走过去问一声,竹扫把好不好用,掉不掉苗子。有些学生拿扫把姿势不对,还手把手地教。有回路过教室边上,儿子不肯走了,站在窗户下,直勾勾望着讲台上的老师。老师讲什么,他是一句都听不懂,儿子能听懂什么呢。
儿子爱听,他就放下扫把担子,歇在教室外的走道上,安安心心等。看了这座学校几十年,哪里有根树,哪里有花草,哪里的路宽,哪里的路边有块牌子,闭上眼睛也清楚。那时候,他心里又快活又闷得慌。恩施最好的学堂,从建校来一直都用他扎的扫把,那些教书匠、读书郎能走得利利索索,没得枯叶占路,没得灰尘糊鞋,他心里高兴呢。看到儿子傻傻站那里不动,就想,要是儿子或是有孙娃在教室里读几句书,多好啊。儿子没指望了,孙娃只怕也盼不到了。扎扫把的手艺传给谁呢。恁大一个校园,没得竹扫把,冷冰冰的塑料扫把扫不干净的。
等结账的时候,他就带上儿子,走出校门,在土桥坝一带的市场上看,铺子里卖的扫把都是塑料疙瘩。硬杵杵直戳戳的,扫过的地是花脸呢。一所学校不干不净,学生哪门读得好书。还有,城里扫街的扫把,环卫所在他手里定做了四十多年,他总会有一天扎不得扫把了,恩施城不晓得会脏成哪个样子。街上脏了,会埋怨他没有送扫把来么。一把扫把,让他心里挂念着一座城,挂念着城里最大的一所学校。
他把这挂念说给胡妈听。胡妈没好气地说,你倒是担心一哈你的儿,你要百年了,他哪门生活哦,饭也到不手吃。他就叹气,我这辈子就是一把扫把,说有用就有用,说没得用,反正用处就那么大一点。你见过竹子砍了,竹枝还能活么。胡妈到底是城里人,马上口气就换了,说,竹子死了扫把在,天无绝人之路,你也莫想多了,把扫把生意做好,多攒几个钱吧。
晚年,他还真不为钱发愁。父子俩每月有六百元的低保,加上残疾人的生活补助金,卖扫把的钱贴补一点,过日子宽裕。只是,安居房在山下坝子里,隔坡上的竹园远了。一天不扎扫把,心里发慌。住了小半月,他又跑上山,在半山腰的竹林里,竹子做柱头,竹块做瓦片,竹篾编窗框,搭了一个竹棚。把儿子托付给邻居们看,一个人还往山上去,天气好,就在竹棚住几天。那条上山的小路,被他踩成了两半,一边平,一边凹。扫把扎多了,倒是不用肩挑背驮弄进城。老屋坎下的谢家媳妇开网店,生意火爆得很,帮他带货,“土家艳子”的抖音号上,周大爷的竹扫把蛮走俏。也不需要自己弄进城了,山上通了旅游公路,隔个把月拖一车出去。联系扫把的人,再不用漫山遍野钻竹林找他,打电话就行。
他的老年机上,存了一个人、一个单位的号码。一个是恩施师专小王的,一个是环卫所的。扫把客的扫把,先卖这两个单位。有多的,才卖别人。
正是六月天气,竹林的新笋,早已脱去笋衣,一竿竿冲进了半天云,青绿的枝叶上,无数颗露水在阳光下闪。
风过竹叶响。扫把客剔竹枝的嚓嚓声,经久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