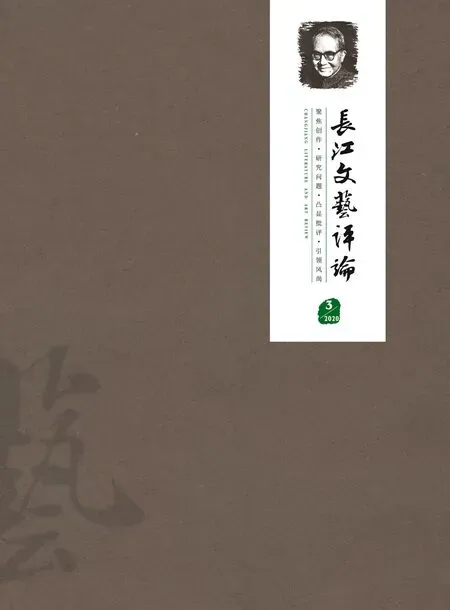“主持人化”恐怕难以拯救批评
◆牛学智
一
对于文学批评,本人有过一些年月的跟踪、梳理和审视。既然在这个方面投入过不少时间与精力,研究得怎样,是水平问题。但只要长时间关注过,无论如何不能说陌生了,这是态度问题。我先后有四本书较系统、分层次地讨论过文学批评,自然也触及到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家。有时候,范围还会扩展到文化、思想领域。尽管是秋鸡娃打鸣——一尽腔子撸,那也没办法,因为近几十年来的一般社会文化思潮,恐怕都被批评家作为背景压缩到文学批评里了。这一点,相信不用太多说明,关心的人是不难意会的。
在《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2012年)中,盘查了有代表性的18位批评家,从老一辈“40后”的刘再复到“70后”青年学人。重点凝聚了他们的“经验”,也粗略勾勒了他们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引进的各种理论的消化、处理和转化程度,算是有名有姓的18宗批评经验“个案”。“个案”也者,留有余地之谓也。这余地就是与“普遍性”勾连对比后的空白地带,还包括“个案”自身原因所招致的局限。因此,由“众神”折射出的问题遂成了《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2014年)一书的主要研究对象,可简称“本土话语”问题。既是“审视”,必然首先要搭建一个基本的话语语境,这便是主体性话语、民间民俗文化话语、日常生活话语、身体性话语等四种典型而突出的批评话语分化的由来。它们差不多都是“启蒙”或“新启蒙”话语及价值认同被消解以后的“类型化”批评产物,属于阶层分化乃至趣味被肢解因而价值碎片化的反映。该书为了使问题更清晰,当然也是为了在批评类型化中探讨理论的彻底,一个技术性选择是让批评“文体化”。“文体化”程度越高,价值便越深入。反之,就会越来越笼统、漫涣乃至于肤浅。《当代社会分层与流行文学价值批判》(2017年)一书着力解决前两部书探讨的剩下部分。在社会结构内部,分析文学批评价值选择、审美趣味圈子化与阶层化原因,可以防止批评思想的空疏,至少能在“个体”为单元的批评视野中衡量出如今中国文学批评触及“普遍性”的水平。探讨的结果:一是仍然照搬“五四”价值模式与话语方式,连语气也模仿得很像;二是彻底否定或者有意绕过“启蒙”俩字,主张就事论事、有一说一,不漫溢边界。看起来这两种批评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它们产生于同一个知识胚胎,即高度认同“传统”。区別只在角度上,前者“照搬”,目的是逃避“现实”,后者“心无旁骛”为的是绕开“现实”。社会中的“个体”一进入文学批评,都成了超脱具体阶层之上的全知全能的上帝,这种知识或理论本身就是问题的本质所在。我们通常说的脱离现实生活,此之谓也。《文化现代性批评视野》(2015年)一书则是对前三者研究结论的再度聚焦,属于批评实践建构。简而言之,文化现代性是对社会现代性、审美现代性批评的进一步审视,突出人的现代化程度。因而,从总体上批判了文学创作及其理论批评的虚无主义倾向,把文学的视角拽回到了新型城镇化这一社会现实中。丈量了审美的分裂,指出了传统的虚伪,通过传统人性与现代人性的对比分析,我认为,当前炒得很热的文学叙事和镶嵌在版面重要位置的文学批评,是现代性个体意识太稀薄了,而不是太过剩以至于像有些人说的,到了反现代性,甚至思考现代性危机的阶段。极端一点看,当前文学批评中的现代性思想,恐怕真是太少了,少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地步。
总而言之,因为做了些跟踪与研究,应该说也有些心得。但看到有如此多的人在谈批评问题,且或多或少以“我们”“中国当代”作为复数,我自觉渺小,不敢打肿脸充胖子,只能以自己的切身体验和发现的具体问题来说说“我感知”到的现象。我认为最突出的批评现象是批评刊物的“主持人化”。
二
“主持人化”是近几年批评界发生的一个新变化,肇始于重要批评刊物,但实际却直接影响到整个批评趣味、价值选择和批评姿态。当然,一直以来习惯于从主体性、价值、思想、审美等惯性思维来研究批评的人,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批评格局隐性然而具有颠覆性的“剧变”,毫不含糊,主要由重要批评刊物栏目的“主持人化”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几乎均由此而来。
其一,极端专题化。当批评刊物让出宝贵版面,聘请刊物认可的教授、学者来担纲主持,通常以收编零散自由评论为旨归,以预先定制的专题或选定的论评对象为对象。批评写作旁征博引却三纸无驴,看起来处处有高度实际上自说自话,四平八稳。专题化后的批评,形式上好像更加规范了,论题也更有学理性了,但一张一弛几乎遵循无一字无来处和有一说一的规矩,其实要达到的目的是把毛毛草草、旁逸斜出的触角一一剪除,进而使批评变得更加规整、圆滑。如此一打扮,奉献于市场的就不外乎两种产品:一是最大限度去除作者溢出规范的思想与未经过滤的主体性体验;二是任何留连忘返或心理抵触,都必须建立在文本细读的阐释之上,文本外视野被迫退于次要甚至末位。毋宁说,这是批评的终结。因为局外人或普通读者一看就明白,学院课堂教案或文学史经验衍生而来的知识,即文献化经验,不是以直接感知体验的形式参与到日常疑难的呈现。非但如此,它还进一步排斥社会一般知识、信仰、思想对文学理论惯例的冲击、冲突。之所以这样,不是编辑与主持人不了解批评背景,相反,是太了解太熟悉的后果。推理而论,把散乱批评加以拾掇,直接动机无疑为着打断“接着说”至少是“跟着说”的链条而来。不幸的是,这两种方向,究其实质,始作俑者是学院的量化考核制度,并非零散化批评所致。在量化甚至数字化考核流程中,不“接着说”或不“跟着说”实际上等于学术不规范,也就不是既定学科规定性的“有效”知识生产”和“有益”学术增长。无论哪方面都不在“专家主宰”范围,因而不属于“合法化”成果,岂容乱来?事实证明:一个阶段比较活跃的“作协派”“自由评论”都已基本式微。当然,倘若专题化批评仅限于学院的四堵墙之内活动,即使鼓荡得尘土飞扬,那也没什么了不起,毕竟不影响墙外继续吆喝、呐喊、嚎叫、苦闷、彷徨、焦虑、困惑。可现在的问题是,这种专题化思维已经排除万难、隔山驾岭,来到了各大批评刊物要冲,俨然一副排兵布阵、起灶搭锅的架势。自由选稿也就被压缩了,这也意味着批评的“偏味”开始上升,“杂味”骤然下沉。教案与文学史预案正式启动,而类似当年“地下写作”式批评潜流口子被扎死。更极端化的表现是把学术仓库里陈年积压的学位论文翻晒出来,交付相关批评栏目去消化。未经阅读市场检验、未经第三方考验的学位论文,不能说全站不住脚,但从定选题到生产制作再到答辩过关,整个流程中起关键作用的仍是执掌文学史旧知识的评委说了算,那就只能说作业及格了。但知识生产线上及格的作业肯定不都等同于有价值的思想。
至于专题化批评的积极意义,我想不用去多说,人们早已心知肚明。最直观一点便是增加了处理库存的机会。“去库存”自然是在“供给侧”与“互联网+”的平台完成。这就像一盘普通醋溜白菜,被新概念一包装,营养虽然没增加,但吃起来仿佛不一样了。
其二,片面专业化。先是一条线,继而一个点,直至“去政治化”乃至“去社会化”为止,片面专业化批评追求正是如此。盖因批评的期待读者并不在民间社会,而在某个学术委员会,或某个期刊的相关栏目主持人那里。如果专业化还有点意思的话,便在其主张及执行该主张时事无巨细的细节阐释、图解上。放置若干年后再读,或许真有“历史化”意味,然而就像今天读民国张爱玲、胡兰成小说与相关评论的感觉,那些提笼驾鸟的烦恼、喝下午茶品咖啡的感觉与亭子间里你来我去的风波,的确不是多数人的体验,那意思也就在一层一层接近原子化赋形中,越来越走向了无聊。技术主义是片面专业化批评的典型呈现形式,批评中几乎不再追问“写什么”“为什么这样写”,而是直扑“怎么写”而去。研究诗歌只关注修辞技巧,研究小说只关注既有文学史上的人物谱系,甚至研究审美不问社会文化现实,这属于典型的“鬼打墙”式低层次循环写作,连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都算不上。因为见树,总会牵扯到树周围的杂草、土壤,也就能推知一片树林生长的大概环境。片面专业化批评的全部心思在急作家之所急,想作家之所想,终极目的是为了挖作家“腹笥”。之所以十分讨好相关栏目,是因为它正符合专业主义胃口,而专业主义正是当代文学经典化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作家花很大篇幅写“自我阉割”,写古人轶事,写一条河流的前世今生,写一群流氓的为非作歹,写某个山头的草虫物种,甚至写一泡尿的来龙去脉,都能给其赋予一种美学形式或隐喻意义。因为封闭的专业主义做得比作家的描写还精细,也就理应笼罩某种神秘的色彩。有神秘性等于说不清道不明,但符合感觉眷顾的“文学性”,而发现所谓独特“文学性”,基本就能坐实作品的“经典”品质。
其三,急切经典化。经典化本是一个历史沉淀过程,可是要给今天,甚至期刊刚发单行本就来一通经典化赋形与预告,恐怕难以说是真正的批评与研究,只能算贴广告或发海报。这其中可能有“秘密”,但无论如何猜测,“秘密”不会是批评家不懂艺术而胡乱瞎诌,最大的可能性只怕是市场的需要。学区楼盘飙价,不是房子一定用了什么特殊建材;“流浪大师”沈巍用脏兮兮的双手捡垃圾几十年,好读书,颇有口才,能信手拈来一二句典故、文词,千里迢迢赶来的“粉丝”肯定不是为了现场聆听讲座增长知识。即使当前墨迹未干的文学,真是了不起的杰作,那也不是一两个所谓的评论家能一锤定音的,最起码还得等上几十年后,看有没有读者重读与评说来定。不幸的是,现在这些常识都被弄反了,这不是因为人们不知道常识,而是因为反常识、拧巴常识才能引起关注与点赞。那些不惜自家羽毛,乃至于胡乱堆砌高大上形容词的批评者,心里很明白,名家新作不会差破底线。即便话说得过了头,只表明是语言能力问题,而不是鉴赏力问题,更不是立场问题。
忽忽悠悠,飘飘乎乎,久而久之,整个批评界围着一两个作家、一两部作品瞎起哄,反而成了“正宗”的中国文学经验的生产榜样;起承转合的指鹿为马,反而成了恪守学术规范的楷模。到此为止,当前文学就这样被一拨一拨的新晋学人提前送入“经典”的殿堂了;当前文学批评也就这样被一批一批墨迹未干的新作品抬举成了中国文论话语。
其四,批评界开始门阀化。单是重要批评刊物栏目“主持人化”,也许还不能代表什么,充其量算是“同仁办刊”,但当这一现象与核心期刊标准、学院考核机制结合,事情就没那么单纯了。说得好听点,周围集结的是一批“价值共同体”;不好听点说,“价值共同体”还有个优先权的问题,其中不可能没有学术身份、学术师承的考虑。有所考虑或者有一定影响,也还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问题的关键在于,看不到制约考虑与影响的相关机制。换句话说,即使有,如此个人趣味,认为不过是学术伦理问题,仍然享有学术豁免权,刊物仍在免除“风险”中被“专家”所主宰。毋宁说,这是经济利益集团化在学术上的一个次贷反映,其特点是表面上几乎拥有“民主”程序的所有可见形式,而实际上分蛋糕与切蛋糕的是同一个人。
更悲哀的还在于,从选稿的专题化、专业化、经典化一路走来,在各层相互补充、相互推动、遥相呼应中,美学原则实现了深度转化,由“庸人主义”终而“集体失联”。如果转换一下齐格蒙特·鲍曼关于“上层”与“下层”的论述,文学批评的“集体失联”则表现为:目光盯住当下社会文化现实,并以强烈的文化现代性感受、体验,表达批评的批判性意见的群体,他们的视角、言说方式、话语与价值发现连同他们的人,在地域上受到限制,只有在正统地形学的、世俗而“脚踏实地”的概念织成的网中才可觅得。长期寄居在这一生活空间的人,按鲍曼的说法属于“下层”。他们的批评可能欠规整,但因感受现实的直接,无疑更多质疑、解构、反叛、反讽意味,文化现代性诉求也就更加强烈。然而他们处江湖之远,只能“冒泡”于公众号,至多散兵游勇式出现在并不出名的理论刊物或索性充当文学期刊的边角料。“上层”生活空间的人们可能只是肉体上“处于这个地方”,却并不“属于这个地方”。精神上当然如此,而且一旦他们有此希望,肉体也可以在任何时候离开这里。“‘上层’的人们并不属于他们居住的地方,因为他们的关注焦点(或者应该说漂浮)于其他地方。只要不受打扰,自由自在,可以全心投入自己的消遣之中。”[1]受困于脚下现实,因而笔下常常流露出深沉、凝重、焦虑、迷茫;精神自由、志得意满,因而热衷于个体精神世界的精妙感受、微微悸动与小小风波,研究路子变得微小、精致、琐碎、利己。凭借互联网乃至自媒体,生活于这两种空间的批评本来可以交流、互动得更加频繁、密切。但当栏目“主持人化”把隐而不发、蛰伏伺机的门阀、学阀猛力一推,在“集体失联”中,自由批评的消息被封锁,自由批评的渠道被堵死。不消说,强塞给读者的,好像只能是“主持人化”后的批评,人们也就只是在此基础上抱怨批评。岂不知,这是多么的天真!多么的错位!
三
当然,栏目“主持人化”以来,批评刊物的确不是没有收获。一是不再为在海量自由投稿中选稿煞费苦心、头疼脑热;二是不再纠缠于飘飘乎乎的人情而周旋平衡、痛苦煎熬;三是不再为某些不具体、莫须有的敏感思想、言论而举棋不定、左右为难。一句话,围绕在批评刊物周围的批评界,主题明确,层次清晰,目标专一。再引申一下便是,冲和淡定,周正平稳,安详喜庆。不过,这样一来,毋宁说是对批评的背叛,对批评的亵渎。
“专家主宰的世界”是很“安全”,可以最大限度避免风险。文学批评不是可以精确化的科学技术,更不是实验室里通过千百次试验屡试不爽的一粒速效救心丸。几个白发苍苍的资深专家说就该如此专题化、就该如此专业化、就该如此经典化,说这才是文学批评该走的正途。于是正途就出现了?就算专家没有康德所讲的自身原因所招致的局限,事情也没那么简单。更何况没有局限只指语言文字的运用,根本不可能管理到不同甚至完全相左的思想、经验、价值取向。在这一层面,相对于未定型思维,既定思维模式也许正好是僵化的。作为思想表达题中应有之义的批评,它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击溃凝固的专题,不断解构程式化的专业,不断更新习以为常的经典。惟其如此,批评也许才有理由清理沉渣泛起的现象,甄别良莠混杂的价值,发掘偏僻边缘的经验,论证蛰伏潜隐的思想。也就是说,它强调在过程中工作,在过程中执行理性的制衡作用。而不是把精力预支给一个完全未知的文学史,并为之奔走相告,修订备选项目;批评家更不是占卜先生,用抽签卜卦和口气坚定来预测文学的命运。
邓晓芒致力于哲学研究,但他的《批判与启蒙》《新批判主义》等著作,却有相当篇幅的当代文学批评。刚开始不是冲着他的文学批评去读他的著作,但最后反而被他的批评所吸引,可谓“自否定”体批评,其“中西双重标准参照”令人醍醐灌顶。金雁的《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并不是文学研究著作,但吸引我的恰好是通常文学批评中没有的非文学性价值与眼光,“去魅”而不虚无,“结构”而不溢美。李建军的《重估俄苏文学》,当然是文学批评,但令人击节的又反而是对俄苏文学之所以是这样不是那样的刨根问底,在整个苏俄历史文化语境中折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及批评来龙去脉的本质主义气质,引人入胜、别开生面。李洁非、杨劼的《解读延安: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同样是研究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学,然而超越左右的视野,格外让人眼前一亮。毕飞宇《小说课》不过是小说家言,可是他贯通文学知识、政治经济学知识与个人感知性体验的表述,实在胜过多数深文周纳的学术论文与专著。
的确不排除批评刊物“主持人化”产生过一些主题凝练、归类清晰、论述精确的好论文,但学术刊物乃天下公器,不是自家后花园。它的社会影响力,只能以对整个批评界乃至知识分子群体养成的价值导向而论。栏目“主持人化”无疑是有意窄化批评的路子,有意纯化批评的思想,有意制造批评界的板结格局。
这一点看法,是否确当?诚待方家批评指正。但我如是说,并非冲某一刊物和具体编辑。只是把这种现象视为批评界一种新动向来看待,作为批评刊物的忠实消费者的感受,自然与栏目“主持人”、在岗编辑的体会不一样。尽管如此,我本人十分感激批评刊物,因为它们过去是将来仍然是我格外热爱的纸质读本之一。非为别的,只因为我把期刊始终看作最重要最直接的审美和思想窗口。一些重要批评刊物如此整齐地走向栏目“主持人化”,无疑是为着革新批评的格局、拯救批评的低迷,效果究竟怎样?将会怎样?我表示怀疑。
注释:
[1]【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时代:生活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谷蕾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