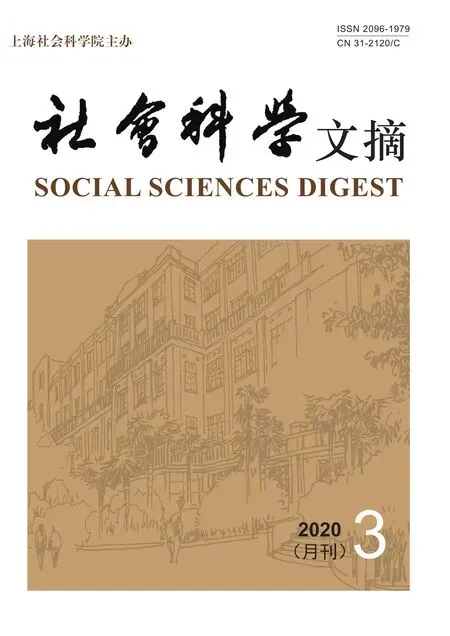焦虑与困顿:从《星形广场》看二战后犹太幸存者的生存意识
2014年瑞典文学院在授予法国犹太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写道:“用记忆的艺术,召唤最难把握的人类命运,揭露了占领时期的生活世界。”出生于1945年的莫迪亚诺并未亲历二战的残酷,但他的小说多以法国被占领时期为故事背景。其成名作《星形广场》(La Place de l’Etoile)发表于1968年。莫迪亚诺在这部小说中塑造了经历大屠杀并侥幸存活下来的犹太人形象,他们自大屠杀直至后大屠杀时代都在挣扎求生。充满了矛盾的主人公什勒米洛维奇是这类人的典型,他言语荒唐,行为怪异,焦虑与困顿构成其生存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压抑和扭曲:承继大屠杀创伤记忆的幸存者
美国学者谢尔曼认为“以第二代二战‘幸存者’的身份撰写小说,在伍尔夫、莫兰黛之外,还有法国的帕特里克·莫迪亚诺”。什么是“幸存者”?迄今为止,《大屠杀百科全书》尚未作出明确的定义。以色列学者丹·巴旺认为“任何在二战期间生活在纳粹占领区、受到最后解决政策的威胁、并且最终设法活了下来的人,都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二战中的大屠杀给犹太人留下了深重的心理创伤,大屠杀的幸存者是心理创伤的直接承受者。法国哲学家阿兰·芬凯尔克劳特提出了“想象的犹太人”,特指那些未曾经历过大屠杀,却在想象中将自身与亲历者等同起来,并在替代性的大屠杀中界定自己的犹太身份的个体。莫迪亚诺虽然并未直接经历大屠杀,但他承载了大屠杀的记忆与创伤。《星形广场》的主人公什勒米洛维奇与很多犹太作家塑造的善良、正直、坚忍不拔的形象不同,这个经历了大屠杀的幸存者具有很强的颠覆性以及突出的时代性和个人气质。莫迪亚诺为读者塑造了一个放荡、堕落的犹太青年形象。但莫迪亚诺作品的意义并不在于他塑造了这样一个癫狂的犹太青年形象,而在于通过这个形象,直面了承继大屠杀记忆的犹太幸存者压抑扭曲的状态,表达了他对后大屠杀时代犹太人的生存焦虑。
大屠杀是反犹主义的极致表现,是一场人为制造的灾难,不仅播下了巨大的毁灭种子,而且压抑了若干年后的自由回忆及反思。莫迪亚诺与奥斯维辛之间横亘着时空,但他以文学想象的方式间接经历了大屠杀,建立起自己与大屠杀之间的联系。莫迪亚诺在《星形广场》中虽然少有正面描写大屠杀的场景,但大屠杀的恐怖阴影无处不在,给犹太民族带来的噩梦挥之不去。莫迪亚诺在巴黎出生成长,巴黎是他最熟悉的城市。在书写大屠杀时,他已然把巴黎和实施大屠杀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看作是一体的存在,莫迪亚诺以浓墨重彩把大屠杀贯穿于《星形广场》写作的始终。因此要真正理解什勒米洛维奇的悖逆行为就必须把他与纳粹大屠杀联系起来进行解读。通过癫狂的什勒米洛维奇,莫迪亚诺展现了法国犹太人在二战中的遭遇,表现部分犹太人的分化和背叛,以“叛逆性认知”体现了他与犹太文化的联结。他在文中写道“唯独犹太人,才能真正理解他们当中的一员”,所以他深切关怀犹太人的现实处境,对犹太人在大屠杀之后失衡的生存焦虑感同身受。
分析小说的时间节点,参阅历史史实,我们可以梳理出小说发生的时间大概是在1940年到1950年之间,在此期间什勒米洛维奇作为犹太人经历了二战大屠杀,并侥幸存活了下来。他如何得以幸存?在战争胜利后,作为幸存者,他因何成为癫狂的被害妄想症患者?通过小说,我们可推测出什勒米洛维奇在二战中与纳粹政府合作并做了叛徒,或许借此逃过了大屠杀,幸免于难。不过作为犹太人,他背叛了自己的族人,作为法国人,他背叛了自己的国家,双重背叛者的身份使他陷入深深的耻辱之中。再加上幸存者普遍存在的内疚感,促使他以外在的癫狂来掩饰内心的不安与失落。二战后法国民众对在战争中与德国合作的叛国者无比痛恨,给予他们无情的批判和惩罚。而不仅作为大屠杀幸存者,而且作为通敌合作的犹太人,什勒米洛维奇战后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巨大的恐惧感、强烈的自责感以及无尽的孤独感,多重情感促使他陷入精神癫狂的状态。
除了什勒米洛维奇,他身边的亲朋好友也都深受大屠杀的折磨。什勒米洛维奇的父亲身为犹太人却对德国人很有好感,经常出入德国人聚集的酒店,与德国人做生意,但是,被“独裁者的警察追捕”的经历依然是他的噩梦。虽然他与儿子相处时并没有过多讲述自己如何逃脱纳粹的追捕,但这段不光彩的经历无疑带给了他痛苦的回忆,并无时无刻不折磨着他。经历过大屠杀迫害的人,无论承认与否,无论表现如何,潜意识里他总是对这一段经历感到恐惧,以致风声鹤唳。莫迪亚诺用寥寥数笔就塑造了一个大屠杀亲身经历者的形象,表现了大屠杀对幸存者带来的永远无法消除的创伤。
什勒米洛维奇的朋友达尼娅一直被集中营的噩梦折磨着,她最终不堪忍受而自杀,她的悲惨结局与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虐杀的犹太人前后呼应。莫迪亚诺通过达尼娅表现了大屠杀苦难的延续性——大屠杀的创伤与后大屠杀时代犹太人的窘境存在着因果关系。战争的结束只是在表面上掩盖了这种延续性,事实上大屠杀的阴影不仅具有共时性,而且是一种历时性的存在,深刻影响着战后犹太人的生活,是导致他们生存焦虑的原因之一。
无法融入:幸存者犹太意识觉醒后的生存窘境
20世纪纳粹势力在德国兴起后,反犹主义骤然升级为“最后解决”的“灭犹”行动,但这场大屠杀反而唤醒了犹太民族的犹太意识。美国犹太思想家欧文·豪说:“大屠杀的记忆深刻地嵌入了犹太人的意识中,所有或几乎所有一切均使他们感到,不管作为一个犹太人意味着什么,他都要求他们一定要尽量永久做犹太人。”张倩红指出:“大屠杀作为一场民族灾难与集体记忆,强化了不只是幸存者而且是整个民族的犹太意识。”曾桂娥也指出:“在后现代语境中,犹太身份认同往往直接建立在大屠杀记忆或后记忆的基础之上。”大屠杀以一种令人难以忘却的惨烈创伤渗入犹太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第二代、第三代幸存者来说,在想象中与大屠杀建立联系成为身份确立的关键。
通过什勒米洛维奇的所见所闻所思所行,莫迪亚诺描绘了大屠杀带给犹太人的创伤;在此基础之上,莫迪亚诺描写了大屠杀创伤记忆在促进犹太意识建构方面的影响。什勒米洛维奇自称盖世太保、通敌的犹太人,但翻遍全书,笔者并没有发现他对犹太同胞如何伤害。他反而要为“奥斯维辛集中营死者”祈祷。他还在臆想中对纳粹分子施以惩罚,把希特勒及其手下当作马戏团成员戏耍。后来他“横渡红海,抵达巴勒斯坦……从而走完从巴黎到耶路撒冷的行程”。《圣经》中记载,摩西带领族人从埃及出红海,历经磨难,回到圣地,他是民族英雄;什勒米洛维奇是一个反英雄形象,但这个犹太逆子依然要从巴黎回到圣地。什勒米洛维奇表面上行为癫狂,言语混乱,但事实上他对自己的犹太身份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且明白这一身份对自已在法国乃至欧洲社会中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才是支配他言行的深层原因。
在小说中,莫迪亚诺认识到大屠杀对于犹太人身份建构的重要作用,但他同时也注意到,正是由于对自己犹太身份的清醒认识,大屠杀幸存者才无法顺利融入法国社会,只能作为“他者”游离于这个社会之外。出生于法国的犹太人什勒米洛维奇一直尝试着融入法国社会,多方努力后发现,如果坚守自己的犹太身份,恪守犹太教的教义,他便很难适应法国社会的生活。起初他为了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故意高调行事,与反犹主义者在报纸上辩论,对自己的犹太身份供认不讳,并对德雷福斯事件大放厥词,以此哗众取宠。他创作剧本,试图通过痛骂犹太教中的异教徒来博取眼球,不料反响平平,因此只好“从此离开巴黎,一去不返”。“德雷福斯事件”是反犹主义者针对犹太人的一次攻击,这次事件使很多自认为已经融入法国并且抱持同化愿望的犹太人清醒过来,意识到法国社会对犹太人的偏见根深蒂固,其根源不仅仅限于宗教。法国民众或许自己也没有这样的认知:反犹主义已经作为一种集体潜意识在社会上生根发芽,德雷福斯事件不过是反犹主义这种潜意识在法国社会的外化罢了。莫迪亚诺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并在文中以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加以展现,他借用“德雷福斯事件”来说明什勒米洛维奇的行为是在法犹太人与法国反犹主义者的博弈。什勒米洛维奇的失败,表明了犹太意识在与反犹主义传统深厚的法国社会斗争中的失利。他的遭遇表明大屠杀促进了犹太人犹太意识的觉醒,但在后大屠杀时代犹太意识的强化反而阻碍了他们在寄居地的生存和发展。
离开了巴黎的什勒米洛维奇去到位于法国西南部的波尔多,决定考取巴黎高师,这是他尝试同化的努力。但在内心深处他仍然自觉维护犹太教,过于关注自己犹太人的身份,而无法与周围的人友好相处。他只能借助身体优势,以武力维护自己的独特性。没过多久,他就因为狂悖的行为被学校开除,这意味着他同化努力的失败。之后他带着罪恶的目的来到一个山区小镇,与试图感化他的神甫的侄女洛依佳相恋。但是,他发现自己无法与法国人感同身受,没有那种“法兰西的愤怒”,他情不自禁地维护犹太人的利益,无法接受非犹太教徒,最终他出卖了纯洁无辜的少女洛依佳。通过什勒米洛维奇的经历,莫迪亚诺进一步证明了囿于犹太意识是后大屠杀时代犹太人获取生存空间的一大阻碍,是促成犹太人生存焦虑的第二个重要原因。“长期在文化夹缝中生存的现实境遇使犹太移民产生了一种被世界排斥的感觉,这种对自身客民身份的自觉在犹太人身上常常体现为强烈的困惑感和边缘感,而反映在犹太作家的文学文本中就成了各种各样人性扭曲和精神异化现象。”《星形广场》的主人公在恍惚中分不清他自己生存的时代,他在现实与臆想之中跳跃、穿插,产生“昏迷狂乱的幻觉”,患上“犹太式的神经官能症”“犹太妄想症”。莫迪亚诺以一种貌似荒诞的戏剧手法,表现了犹太青年被排斥出主流社会的焦虑感、对自身模糊身份强烈的困惑感、自觉难以融入法国社会的边缘感。难以融入法国社会的什勒米洛维奇和大多数战后的犹太人一样,把目光投向以色列这块儿“应许之地”(Terre Promise)。战后成立的现代以色列国成为他们的救命稻草,他们期望在这里找到“根”。
难以回归:欧洲幸存者在现代以色列国的尴尬处境
“从犹太人的历程一开始,犹太人就没有泯灭回归迦南之地的梦想。”什勒米洛维奇在法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于是他自然地把目光投向了以色列。他拿着一名法国警官送给他的去往以色列的船票,从马赛港登上邮轮来到特拉维夫,“他的心脏平稳地跳动让他明显感到,阔别了两千年,他又踏上了祖先的土地”。但在以色列他能找到自己的理想家园吗?莫迪亚诺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小说的后半部分,作者用荒诞的笔法令时空扭曲,使什勒米洛维奇在战后的以色列和1942年的巴黎来回穿梭。在1942年的巴黎,什勒米洛维奇受到了惨无人道的肉体虐待,被毒打,被施以水刑,被刀子割开脚掌走在盐堆上。在以色列,他不仅遭受以色列军官的精神虐待,还被送到农场进行劳动改造。劳改农场里聚集了从欧洲各国前来寻根的犹太青年,“全是知识分子”。以色列军官要把他们改造成“游击队员”,他们被迫在烈日下砸石子儿,而且无端被枪杀。无论是在哪个时空,犹太人皆承受着反犹主义强加于他们的痛苦和折磨,甚至犹太人自己也异变为反犹主义者。作者似乎以此表明,战后犹太人在以色列所受到的虐待并不比被德军占领时期少,偏执的犹太复国主义走到极端便无异于纳粹主义,以色列犹太人似乎陷入了一种以暴制暴的误区,他们从受害者摇身一变而成了加害者。现代以色列建国(1948年5月)后开始在国际社会上发声,新成立的以色列国家强调奋斗精神,号召犹太人发扬坚韧不拔的精神建设新家园。“在以色列,自1948年建国到70年代以前,只有那些参加过犹太区起义或者反德游击队的抵抗者才是真正的‘正义之士’,才是‘为生存而战’的典范,除此之外的幸存者都被视为软弱与无能之辈。”他们对幸存者进行严苛的道德谴责,说他们如绵羊般任人宰割。在这样的背景下,犹太幸存者的个人情感被压缩至可以忽略不计,个人的怨言则被视为大逆不道。“以色列复国是几千年来犹太人的梦想,但建国后的以色列虽然以犹太之名行事,却使怀有美好理想的犹太人日益成为以色列国的政治牺牲品。”莫迪亚诺不仅仅指责了法西斯主义和反犹主义,锡安主义者也难逃他犀利的词锋。什勒米洛维奇因为来自欧洲而被以色列犹太人怀疑。以色列也不是他的心之归属,更有甚者在这个所有犹太人寄予厚望的神圣之地,他彻底沦为精神失常者。很明显,新建立的以色列国绝非莫迪亚诺心目中的伊甸园。他指出借复兴犹太国之名而行的狂热政治、极端思想只能使犹太民族自我毁灭。
莫迪亚诺塑造了一系列带有大屠杀创伤记忆的幸存者,他们既无法融入寄居地社会,又难以在以色列国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虽然侥幸逃过大屠杀,却沦为后大屠杀时代的弃儿。
结语
战后犹太人该如何摆脱生存困境,获得生存空间,如何在恐惧中找到希望,一直是困扰莫迪亚诺的难题。当时的临床医生较为普遍地使用弗洛伊德创立的修通观念来描述幸存者如何处理他们在大屠杀中遭受的创伤,以精神分析方法来治疗大屠杀后遗症,但莫迪亚诺认为“精神分析和精神疗法是很不相同的”。书中他虽然安排弗洛伊德医生为什勒米洛维奇进行治疗,但弗洛伊德医生自己也陷入崩溃,更不用说治疗什勒米洛维奇了,这说明莫迪亚诺并不赞同单纯的精神疗法。但他似乎并没有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法,似乎也乐于保持这种半隐半现的晦涩不明,因为那时的他不过是一个“愤怒的青年”。然而,我们可以从什勒米洛维奇的结局窥见莫迪亚诺思考的解决之道。他安排什勒米洛维奇返回欧洲,说明他不愿犹太人被狭隘的民族主义所束缚,被政治道德绑架,而是希望他们作为“人”而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什勒米洛维奇被纳粹处死的同时,却被同为犹太人的弗洛伊德医生所救,说明他希望犹太民族团结,希望犹太人保有自己的民族意识而具有凝聚力。莫迪亚诺为什勒米洛维奇安排的这种结局暗含“和而不同”的价值观,或许是他对处于困顿和焦虑中的幸存者指明的一条生存之道。作为莫迪亚诺处女作的《星形广场》已然体现出了日后被诺贝尔文学奖所赞赏的对“人类命运”的关注。
莫迪亚诺作为法国犹太作家对犹太人的处境进行了多维度思考,展示了他对后大屠杀时代法国犹太民族精神状态的担忧,同时也提醒犹太人要时刻警惕,既不要沉溺于受害人的角色无法自拔,也不能因为心理的不平衡由历史的受害者变成现代社会的施害者,表现出知识分子特有的历史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