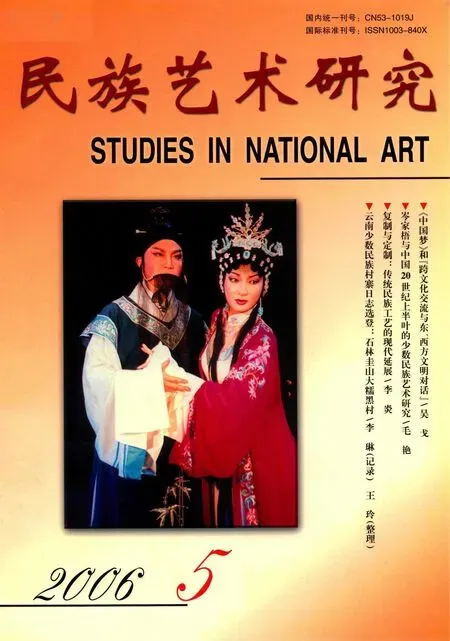商业献礼片:主流价值的“工业美学” 呈现
姚 睿,曾正一
近年来,随着电影产业结构日臻完善,电影工业美学理念的不断成熟,传统献礼片正在逐渐转变为携带电影工业美学印记的主流商业献礼片 (以下简称商业献礼片)。这类商业献礼片不仅令传统献礼片难以顺畅实现的意识形态表述获得了别开生面的呈现形式,还呈现出电影工业美学的特征:秉承电影产业观念与类型生产原则;在电影生产中弱化感性、私人、自我的体验,代之以理性、标准化、规范化的工作方式;游走于电影工业生产的体制之内,服膺于 “制片人中心制”,但又兼顾电影创作的艺术追求;最大程度地平衡电影艺术性/商业性、体制性/作者性的关系,追求电影美学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①陈旭光:《论 “电影工业美学” 的现实由来、理论资源与体系建构》, 《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9年1期,第33页。如果说传统献礼片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被政治宣传和教育目的驱动的政治宣传电影的话,那么商业献礼片就是在中国电影工业日臻完善的市场经济时代,被工业美学观念驱动的市场化商业电影。本文将从观念衍变、创作特征和营销路径等层面对工业美学视域下的商业献礼片展开分析,探索商业献礼片的美学特质、工业特征和未来发展路径。
一、商业献礼片的美学观念衍变
献礼片是指在重要节日上映,以献礼作为目标的主流价值/主旋律影片。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特的电影形态,献礼片源自1958年至1959年中央发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电影献礼活动。在此之后,每逢建党、建军、建国纪念日,革命领袖诞辰周年等重要日期都有献礼片上映。中国献礼片曾在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经历了三次高潮②参见唐榕、邵培仁:《电影经营管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4—246页。,不断将崭新的时代元素融入献礼片中。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从计划经济时代迈入市场经济时代,献礼片也开始逐渐呈现出叙事技法和展现形式的创新,但其时献礼片的制作主体和美学特征基本上还是延续了先前的献礼传统——制作主体仍以国营电影制片厂为主,倾向于表现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塑造英模人物,风格样式以正剧为主,着重于发挥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作用。
进入21世纪,伴随着国家多项电影政策的出台,电影产业化的脚步不断迈进,这激活了民营资本的活力。民营电影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带动了中国电影行业整体的类型化与商业化生产。在这种态势下,商业献礼片应运而生。与传统献礼片相比较,商业献礼片注重类型化的创作手段和市场化的营销手段,注重艺术性和娱乐性的结合,开始呈现出工业美学的特征。如果从影片的艺术风格、内容理念和制作方式机制等方面审视,可将21世纪商业献礼片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2009年的 《建国大业》为开端,开启了商业献礼片的 “1.0时代”,建立了献礼片的工业化制作模式。在这个阶段中,《建党伟业》《建军大业》等影片融合政治宣传功能与商业属性,扛起 “商业” 的大旗,完成 “献礼” 的重任,从创意策划、生产流程、营销手段到排片放映都采用了当时最新颖有效的市场化运作方式,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其中,以 《建国大业》 《风声》 《南京!南京!》为代表的商业献礼片甚至处在当年中国电影市场的票房领跑位置。《建国大业》《建党伟业》 《建军大业》为商业献礼片的工业化做出了有益探索,进行了许多载入史册的开拓。如:第一次采用 “全明星” 阵容参演献礼片,通过明星策略黏连粉丝受众来拓宽影片的目标受众群体;通过话题事件营销提升了该系列献礼片在公共领域的被认知度等。
除了工业生产上的与时俱进之外,这段时期商业献礼片开始发展出电影工业美学的萌芽,呈现出美学观念的转向。从艺术风格和美学呈现上来说,这段时期的影片展现出越来越开放、包容的艺术观念与文化建设意向,在美学上均衡各元素,追求电影艺术性和商业性、体制性和作者性的平衡统一。尽管这些影片仍然以政治宣传价值为底色,题材聚焦于英雄、模范、领袖和重大革命历史事件,但影片的类型、形式感和风格正在悄然变化,融入了爱情、青春、警匪、黑帮等多样化的类型电影元素。这种历时性变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逐渐完成的。如果说 《建国大业》和 《建党伟业》等影片仍在建构成熟稳健、充满英雄气概的国家形象的话,那么到 《建军大业》时,则另辟蹊径展现出似少年般鲜活奔放、热情阳光的年轻中国形象。《建军大业》所有主演的平均年龄不超过31岁,即契合了影片中历史人物的真实年龄,使得整部影片充满奋进的朝气。由于影片兼顾了历史、革命、故事的巧妙平衡与和谐共振,并由此掀起观影热情和爱国情绪①刘伟强、黄建新、谭政:《〈建军大业〉:新主流电影的类型叙事——刘伟强、黄建新访谈》,《电影艺术》2017年第5期,第52页。。这种“轻量化” 的呈现形式,使影片在 “献礼”与 “商业” 之间取得了较好的平衡。
商业献礼片发展的第二阶段由2019年的《我和我的祖国》开启。自此,献礼片开始在工业基础的保障下完善美学观念并进行美学转向。这种美学转向的最大特征体现在对普通人与献礼关联的重新认识。如果说 《建国大业》等 “1.0时代” 的商业献礼片仍在重大革命历史和英雄、模范人物的宏大叙事中进行探索的话,那么在 “2.0时代”,商业献礼片开始将叙事主体转向宏大叙事之外的普通人,展现普通人与国家民族历史的命运勾连,探索 “普通人” 的历史价值和 “小我”见证历史的情感体验。201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而创作的商业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攀登者》《中国机长》《烈火英雄》都明确显示出以普通人视角对历史的见证。《我和我的祖国》令每个人成为历史的参与者,在历史转折处以个体化的微观视角与历史迎头相撞。《攀登者》将具象化的个体拼搏与抽象化的国家形象相融合,通过爱情故事和团队协作完成了个体理想与家国情怀的结合。 《中国机长》 和 《烈火英雄》 两部作品则分别以民航机组工作者和消防员为切入点,塑造出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的基层工作者形象,表达出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工作者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奉献的力量。
陈旭光教授在多篇文章中提出工业美学的普遍特征是服膺于 “制片人中心制” 但又兼顾电影创作的艺术追求,最大程度地平衡电影艺术性/商业性、体制性/作者性的关系,追求电影美学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从而形成平均的美、世俗的美、均衡的美、生活的美和现实的美。①陈旭光:《新时代、新力量、新美学——当下 “新力量” 导演群体及其 “工业美学” 建构》,《当代电影》2018年第1期, 第38页。在商业献礼片的 “2.0时代”,无论是工业制作还是美学呈现,都符合上述界定。同时,“2.0时代” 的商业化献礼片在题材上突破了英模人物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局限,将镜头转向积极参与历史建设的每个值得尊敬的个体,这种美学观念的转向与 “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 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相契合,呈现出普通人的审美视角与美学价值,通过 “去宣教化” 发挥宣传教育功能,形成了工业、美学和献礼三者的有机统一。本文认为, “2.0时代” 的商业献礼片通过项目化、流程化、团队协作等生产手段,呈现出 “制片人中心制” 的前端规划保障、故事创作的类型化意识、制作环节的协同效应与营销的理念革新等工业美学特征。
二、“制片人中心制” 的前端规划保障
缔造标准化的工业流程是献礼片工业化生产的重要原则,也是对产品质量、票房和利润的稳固保障和维系品牌稳定发展的基础。市场定位、投资把握、剧本创作、演员选择、摄制等共同构成电影生产领域的主要环节,每个环节都有其自身特点。前端规划的系统化保障将这些环节有机统筹安排在一起,形成彼此合作、有条不紊的流程。这种规划保障主要通过 “制片人中心制” 实现。
献礼片的创作模式受到社会形态与生产制度的共同影响。在计划经济时代,献礼片的生产主要由制片厂厂长与导演共同负责。进入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之后,电影导演的话语权力逐渐突显,献礼片创作也开启了以导演为中心的创作时代,呈现出导演的个人风格特色。
进入21世纪,中国电影在产业化道路的摸索中,不断吸纳好莱坞电影的工业化优势,开启了 “制片人中心制” 的标准化运作模式。“制片人中心制”②在实际操作中,制片人有时会被署名为 “监制”。是商业献礼片得以成型的重要保障。作为电影制作的枢纽,制片人承担电影生产全部流程质量监督与把控的职责,同时,他还运用自己的艺术创作才能和产业营销经验与各部门进行沟通,确保稳定有序的制作输出和基本的艺术成色。因此,制片人既是电影生产的 “把关人”,又是 “导演身后的导演”,协助导演完成艺术创作中难以完成的任务。工业美学是作为物质的 “工业”和作为精神领域的 “美学” 的对立统一。其除了具有技术密集、分工细致、流程化和制度化等一般属性之外,更要强调在电影生产的每一道工序上发挥人的主体性,按照美的规律去创造。③陈旭光、李卉:《电影工业美学再阐释:现实、学理与可能拓展的空间》,《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第102—103页。这种创造性在制片人的引领下,呈现出个人才能与创作集体的调和以及电影生产过程中的包容性与和谐美。如 《我和我的祖国》是由7位年龄、风格特点各不同的导演联合执导的,但由于总制片人黄建新的整体把控,使得 《我和我的祖国》 不是一个风格迥异的短篇集锦,而是一部概念完整、风格统一的商业献礼片。黄建新本人就曾在2019年第3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学术论坛中详细阐释了 “历史瞬间、全民记忆、迎头相撞” 的美学理念,提出激活普通老百姓心灵深处的温存和理想主义是电影需要迈出的重要一步。在这个核心理念的贯穿下,才有了 《我和我的祖国》的实践形式: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70年历史中截取7个代表性历史事件,以时间切片的方式将个人记忆与国家记忆相连,由点及面,迸发出深切的爱国情怀。7个小故事中囊括了来自不同时代的一群普通人物:电动旗杆的设计师、隐姓埋名的原子弹研发者、钟表修理师、出租车司机、扶贫干部、飞行员……这种平民史观的银幕呈现沿用了 《阿甘正传》 的策略,让观众通过与这些普通人物共情,产生历史转折与时代洪流的想象。正如主题曲 《我和我的祖国》歌词中表现的人民和祖国的关系:“我” 是赤子,是浪花;祖国是母亲,是大海;“我” 的每一分喜怒哀乐都与祖国母亲息息相关。“我” 不再是集体化、阶级式的“我们”,而是情感充沛的 “我”①张慧瑜:《〈我和我的祖国〉:重新定义 “我” 和祖国的关系》,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345845431_790641? scm=1002.44003c.fe01650183.PC_ARTICLE_REC,2019-10-08。,通过真挚情感的表现进行对时代精神 “美” 的讴歌。可以说, 《我和我的祖国》 所产生的美,正是“制片人中心制” 带来的前端规划赋予的。
三、故事创作的类型化意识
在电影工业美学 “形式美、功能美、协同美” 的概念引领下,“2.0时代” 的商业献礼片通过类型化的故事创作模式实现了 “献礼” 的崇高价值,将政治教育宣传内化到饱含情感的电影故事中,使更多用户在情感共鸣的基础上产生对主流价值的认同。好莱坞类型电影的剧本创作模式是最具工业形式的故事生产流程。“美国电影之所以令人如此销魂,在于它既是生产 ‘公式化’ 又是生产‘艺术性’既生产成规的又生产现代主义的电影形态。”②[美]托马斯·沙兹:《旧好莱坞·新好莱坞:仪式、艺术与工业》,周传基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 第27页。在长期的观影过程中,观众已形成了对类型电影的一种观影默契。“生产和接受的每个过程,电影制作者与观众都是通过类型联系起来的。③[美]罗伯特·考克尔:《电影的形式与文化》,郭青春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页。” 这种观影默契是一种代表性的观众对电影的预期判断,也就决定了剧本必须依照定型化的模式结构进行创作生产。美国派拉蒙影业20世纪便开始采用 “绿灯委员会” 的规则,根据长期总结出的剧作规律对故事片生产进行规范化把控。这套体系被中国的阿里影业等公司借鉴吸纳,成为剧本开发阶段的必要流程。④白金蕾、张妍頔、程子姣、张彦君、沈畅、王浩然、梁馨:《阿里影业参投的 〈绿皮书〉拿下 “小金人” 中国电影的奥 斯卡资本局》,《新京报》2019年2月27日。虽然 “绿灯委员会” 的剧本创作模式曾被批评过于僵化,但这套模式却保障了工业化的故事片生产。
商业献礼片的类型化模式即是将中国范式的献礼片故事与成熟的类型模式进行融合,保障献礼片剧作在戏剧冲突、情感传递和主题呈现上的有效输出。类型化的创作模式已经成为商业献礼片故事创作的必备模式。在工作流程中采用多位编剧、文学策划和剧本医生共同对剧本进行写作润色,最终由制片人和导演对剧作进行整体把关。2019年的 《我和我的祖国》囊括了众多顶级编剧共同参加创作,为每个短片编制了独特的剧情。作为商业献礼片,以现实原型为基础进行改编创作的 《攀登者》 《中国机长》 《烈火英雄》剧作运用了惊险电影的类型特质,利用惊险电影的刺激、悬疑、焦虑和崩断神经的紧张感形成超越现实的假定性和虚构性。《攀登者》 用平行蒙太奇的方式表现登山队的登山险情与山下指挥部的焦灼; 《中国机长》 用交叉剪辑的方式记录了川航3U8633在万千关注中的顺利着陆;《烈火英雄》通过一触即发的爆炸与主角 “最后一分钟营救” 的场景交叠,营构类型化叙事中险象环生、一波三折的跌宕起伏。由此可见,类型化的剧本创作保证了商业献礼片在剧作生产环节的高质量及稳定性。
需要注意的是,电影工业美学的出发点是大众文化,因此在商业献礼片的生产过程中应呈现出兼顾作者性与类型化的 “中间层面” 的表达。陈旭光教授认为,电影工业美学是工业和美学的折中,不是一种超美学或者小众精英化、小圈子化的经典高雅的美学与文化,而是大众的, “平均的”,不那么鼓励和凸显个人风格的美学。⑤陈旭光:《论 “电影工业美学” 的现实由来、理论资源与体系建构》,《上海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第33页。在 《我和我的祖国》 中,陈凯歌导演的 《白昼流星》以抽象写意的方式将中国航天成就与脱贫攻坚关联,其脱缰的个人意识造成影片结尾的叙事不连贯和不 “接地气”,因此而颇具争议性。文牧野导演的 《护航》用大量升格镜头展现女兵戴墨镜的英姿飒爽,但这种视觉“炫技” 使用过多,破坏了观影的沉浸体验,违背了工业美学的 “均衡” 原则。尽管瑕不掩瑜,但若能够尊重工业美学原则,将作者性和商业性进行有机统一,便能形成影片更加普适性且被大众接纳的审美感受。
四、制作环节的协同效应
“2.0时代” 商业献礼片在制作生产领域通过明星和制作流程的优化来形成稳定可控的生产环节。其中,明星的联众优势和电影声音团队工作方式优化是近年来商业献礼片在制作环节取得的突出成就。
在注意力经济时代,电影明星采用是能够将注意力转化为经济价值的最有效手段。在预算可控的前提下,如何组建最合适的明星团队是电影工业化生产不可回避的问题。2019年同档期上映的两部商业献礼片 《攀登者》和 《中国机长》 类型相似、明星影响力相当。表1中列出了参演两部作品的明星演员的以往作品累计票房和先前的合作关系数。根据表中数据可以发现,《攀登者》主演明星的作品累计票房 (445.69亿元)比 《中国机长》 (405.86亿元)更占优势。可见 《攀登者》的明星影响力更大。但 《攀登者》 迄今为止获得的票房 (10.97亿元) 却明显要弱于 《中国机长》 (29.12亿元)。由此可见,主演明星之前所取得的个人成就 (以往作品累计票房)并不能对本次参演影片的票房收益形成绝对性影响。

表1 明星的合作关系与票房影响① 数据整理自猫眼专业版App。
相比明星演员个人对票房的贡献,参演明星之间先前的合作紧密度对电影票房的影响力更大。黄敏学等学者在 《何种明星团队有助于电影成功》 一文中对明星的联众效应展开量化研究。文章以明星合作的紧密性为自变量,电影的商业表现 (票房)为因变量,通过网络数据的模拟运算,推演出明星先前的合作次数与本次合作影片票房之间的关联。文章提出,若一部电影的参演明星为6人,在这6人之前合作7次的情况下,能够为本次合作制造最佳票房收益。同时,明星先前合作次数与本次票房收益呈现倒U形曲线分部。先前的合作次数越趋近于7次时,本次合作的票房愈佳,反之则愈差。②黄敏学、刁婷婷、郑仕勇、胡琴芳: 《何种明星团队有助于电影成功?——适度的合作紧密性研究》, 《珞珈管理评论》2018年第4期,第97—113页。从上图可以看出,《中国机长》中的6人明星团队在拍摄《中国机长》 之前曾合作6次 (趋向于最佳值7次),超过《攀登者》明星团队先前的3次合作 (远离于最佳值7)。而现实境况中,《中国机长》的票房也确实是 《攀登者》的3倍。这种反向验证巩固了该研究得出的结论:明星对影片票房的贡献不仅取决于单个明星的个体影响力,还取决于明星团队合作产生的联众优势。未曾合作或合作过多都会影响明星本次的合作效果,只有在彼此间有过一定合作基础的情况下,明星团队的配合才能获得最佳票房效果。由此可见,电影是合作的艺术形式,明星团队的联众优势对电影的票房收益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未来商业献礼片的明星团队打造上,要挖掘演员和团队的联众优势、注重 “实力派” 与 “偶像派”的明星混搭,促使明星之间形成最佳组合,从而更好撬动票房收益。
除了演员团队的协作外,制作团队的流程优化也是 “2.0时代” 商业献礼片的突出特色。艺术的灵感来源于技巧。技巧的实现仰仗于技术基础。商业献礼片 《我和我的祖国》将好莱坞高效的声音制作流程融入本土创作实践,形成了统一调性的声音美感。《我和我的祖国》是中国电影行业首次采用 “动效拟音监督 (Foley Supervisor)” 职位的影片。动效拟音 (FOLEY) 指各种动作的声音效果。细致的声音动效能创造出电影独特的气质。《我和我的祖国》由7部短片构成,为保证时间进度,这些短片在中影基地的两个录音棚中进行了同时录制。①王子威:《〈我和我的祖国〉后期动效声制作的技术分析与流程管理》,《现代电影技术》2019年第12期,第13页。按照以往的工作流程,在完成动效声音编辑之后,声音会直接输出给混录师。而在 《我和我的祖国》中,在传送声音素材给混录师之前,由动效拟音监督 (Foley Supervisor)先进行声音统筹和预前编辑,之后再输出给混录师。②王子威:《〈我和我的祖国〉后期动效声制作的技术分析与流程管理》,《现代电影技术》2019年第12期,第13页。这种协同创作方式流程缓解了终混压力,极大提升了声音制作的效率和质量。同时,在艺术创作与声音美学层面,动效拟音监督的编辑也解决了因录音棚与录制时间的不同而产生的声音差异,统一了全片的动效风格与声音调性,让 《我和我的祖国》呈现出整一化的声音美感。
五、营销领域的理念更新
宣传发行营销是最能体现电影工业化属性的环节。随着中国电影产业语境的变革,需要建立电影的大众文化定位和 “受众为王”观念,尊重大多数人的审美趣味。在互联网时代营销商业献礼片,需要实现营销理念的新媒体化、营销语境的现代化和营销手段的贯通性三者的和谐统一。
在商业献礼片的电影营销中,理念是手段和方法的 “指挥棒”。在市场营销学中,预期管理的意义在于通过有效的引导和协调对受众形成预先认知,从而降低不利因素并规避风险,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在献礼片萌生工业化意识的 “1.0时代”,《建国大业》等商业献礼片注重商业与教化并重,主要以海报、预告等先导方式传达影片承载的重大历史意义。由于当时并未形成受众的预期管理理念,因此对电影票房的预测方式主要仰赖业内资深人士对影片类型、团队组成、投入资金等前期变量估算判断。而在商业献礼片的 “2.0时代”, “渠道为王” 的互联网营销理念与预期管理理念的结合将为商业献礼片营销带来新契机。
新媒体语境带来的现代化手段为商业献礼片提供了更为准确直观的前期调研效果呈现。用户通过发帖、阅读、评论、转发等传播方式建立网络人际关系,进而自发形成有群体认同性的网络圈层。2019年上映的商业献礼片还运用了时下最受青年受众群体青睐的短视频形式进行话题营造。将献礼片特有的主流价值和宣传教育主题以现代化的方式呈现,有效对接了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青年受众群体,实现了主流价值的现代化表达。
商业献礼片通过互联网渠道的大规模推广,并不能完全实现影片票房和口碑的有效转化。因此,配合以线下的路演、点映活动将信息触及的最大人群范围逐步精确到目标核心受众,最后让活跃度最高的群体率先走进电影院,产生正向口碑放大效果。青年受众在文化消费中呈现出明显的 “主动性”“互动性”,这意味着,此类受众一旦接受了来自互联网给予的献礼片的相关先导信息,他们将不再满足于被动地接收,进而更愿意转向参与感强的线下活动。除此之外,线下与导演、明星面对面地交流互动,还能将粉丝效应与电影营销贯通,为献礼片的营销宣传进行新一轮助推。商业献礼片在完整的营销体系中,以适当的先后顺序、灵活贯通的线上/线下宣传发行手段形成期待感与参与感的双重体验。商业献礼片营销手段的同步推进相互贯通,提前为影片打造口碑、预热市场,以期唤起更多的观影期待。
结 语
在传统献礼片时期,献礼片旨在完成献礼的崇高任务;在商业献礼片的 “1.0时代”,献礼片开始逐渐实现商业和献礼的融合;在商业献礼片的 “2.0时代”,献礼片开始呈现出自觉的工业美学意识,进行商业、献礼和美学三者的有机结合,使得献礼的崇高性被包裹在美学呈现中,通过商业化的制作得以成型。陈旭光教授在 《论 “电影工业美学” 的现实由来、理论资源与体系建构》一文中,提出电影工业美学试图在理论层面上建构一个互补辩证、兼容并蓄且务实有效的理论体系,呼唤美学品格的坚守和艺术质量的提升。①陈旭光:《新时代、新力量、新美学——当下 “新力量” 导演群体及其 “工业美学” 建构》,《当代电影》2018年第1期, 第32页。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 “2.0时代” 的商业献礼片不仅呈现出工业美学的特征,而且在此基础上令传统献礼片的意识形态表述获得了别开生面的形式。
作为基于现实需求而建构的当代电影理论,电影工业美学旨在调和传统和艺术至上的电影艺术研究与专注市场和产业而忽视了电影艺术特性的产业研究,在工业/艺术这一看似二元对立的情境中,开辟理论建构的可能性。②陈旭光、李卉:《电影工业美学再阐释:现实、学理与可能拓展的空间》,《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第101页。在全球化时代,主流文化价值观的传达对国家形象塑造和国民身份认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工业化手段应当责无旁贷地担当起书写主流价值的责任。对创作生产而言,未来的中国商业献礼片要在VR、AR等影视技术革新的状况下,继续探索讲好中国故事的路径与框架;对宣传、发行、营销而言,未来的中国商业献礼片需要在电影营销的投资动机、运作方式和盈利模式等方面继续与时俱进地探索互联网时代的可能性。
真实事件的快速影像化使得献礼片的生产开始呈现出 “即时性” 的特点。 《中国机长》的原型事件发生于2018年5月,同年7月被引入电影改编阶段,2019年1月正式开机。这种即时性背后必须拥有完整、协调、系统的体系作为支撑。可以预见,随着商业献礼片工业化的进程,未来的商业献礼片必然体现出更加迅猛的 “中国速度”③陈旭光:《类型升级或本土化、工业品质与平民美学的融合》,《中国电影报》2019年11月6日。,在工业美学的体系引领下,为商业献礼片的生产营销继续提速。2020年1月起,中国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在疾病面前涌现出的平民英雄和事迹值得被铭记与颂扬。也许在不远的未来,献礼片中将会出现这些平民英雄的身影,通过迅捷的速度和过硬的品质保证,用电影抵抗遗忘,将更多英雄的事迹记录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