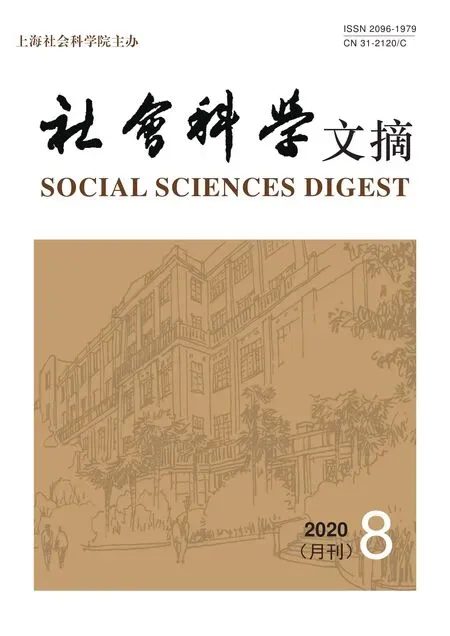赓续历史,重返原乡
——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小说的“历史叙事”
文/徐诗颖
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不少港人淡薄的历史意识其来有自。这源于英国人致力于培养港人的分离意识,以此逐渐使他们与民族意识对立起来,从而扩大他们同祖国的疏离感。香港大学周永新教授曾言:“我读书的时候,中国历史课本只记述到辛亥革命……课本用英文写,总不会常提中国事。孩子喜欢听故事、读寓言,今天我脑里载的还是爱丽斯梦游仙境、快乐王子等。这些寓言和故事是世界文学遗产,没有国界之分,但虽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对自己的传统和历史,却是这么的陌生……”这种尴尬的处境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回归过渡期,才让沉睡着的港人惊醒过来。他们惊觉对香港乃至中国历史的一无所知,港人成了被历史放逐的群体。与此同时,香港长期以来作为西方世界的东方主义产物,似乎城市百年的发展离不开他们的想象与实践。鉴于此,不少香港作家尝试借助小说赓续历史、重返原乡,希望借此解决英殖民统治时期留下的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去历史化”行为;另一个是刻画带有东方主义色彩的香港历史形象。寻根的意识在此彰显。
具体到叙事领域,不少作家聚焦百年香港殖民史,在城市史、家族史以及个人史书写范畴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产生以下四种代表性的叙事形态:双重颠覆性叙述声音;个人/集体口语体的叙述方式;充满象征意味的家族书写;多声部交错的空间叙述。他们试图治愈殖民时期留下的“无根症”,并逐渐改变西方世界的东方主义立场,在中西文化融合视角下重新思考“香港”的前世今生。鉴于此,本文立足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小说所呈现出的有代表性的历史叙事形态,从美学的层面探究作家背后的艺术追求和叙述用意。
双重颠覆性叙述声音
在西方殖民者的眼中,香港能走过“由小渔村发展为工商业大都会”的城市现代化历程,离不开港英政府实施的科学统治。因此,香港在他们眼中长期扮演着需要被拯救的弱者形象。这主要表现为香港常常以“妓女”的角色出现,其中有代表性作品《苏丝黄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和《大班》(Tai Pan)等。一百多年来,“妓女”作为香港这一空间的隐喻,无形中强化了其阴性化的形象。香港史的书写同样如此,回归前一直为英国殖民书写所垄断,本地的声音得不到有效彰显。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本地出现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历史书写。其中一种叙述策略就是颠覆这种阴性化的弱者形象,试图打破蕴藏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西方/男性”和“东方/女性”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对立架构。为此,有的小说突出双重颠覆性叙述声音,具体表现为叙述者并没有隐退在幕后,而是站出来,或成为小说里面的角色,或作为“说书人”的角色交待故事发生的缘由,让叙述者与主人公共同发出强有力的颠覆声音,借助对历史的重新赓续发掘更多被英殖民者有意遮蔽的历史以及蕴含在其中的复杂性,从而反思本地的历史叙事,重返精神原乡。对此,有两部重要代表作值得研究,一部是诞生于“九七”回归前的《香港三部曲》(施叔青,1997),另一部是写于21世纪初的《龙头凤尾》(马家辉,2016)。特别的是,两部作品虽然出版时间相隔近20年,但在颠覆“阴性化”的叙事策略上有相似之处,可以构成互文性阅读,并在反思历史叙述的层面上提供更多向度的思考。
虽然《香港三部曲》和《龙头凤尾》在选取书写百年香港史的时空点上有所不同,但在叙述策略上,当加入双重颠覆性的叙述声音后,都在辨析诸多暧昧复杂的现象里有力诠释被西方殖民书写遮蔽的地方历史。其中,性别关系与身份认同成为两部作品共同颠覆香港作为阴性化弱者形象的重要切入点,并以此作出相应的反省。与叙述者一起参与这种颠覆行为的主人公分别是《香港三部曲》的黄得云和《龙头凤尾》的陆南才。
两部作品在面对“西方/男性”和“东方/女性(男性)”以及“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二元权力对立架构层面均有着强烈的反省意识。殖民史本身潜藏的暧昧性与混杂性使得作家要颠覆固有架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他们并未放弃“赓续历史、重返原乡”的努力,当加入双重颠覆性叙述声音后,这种解构西方殖民历史书写的决心显得更为有力。
个人/集体口语体的叙述方式
如果将英殖民者在殖民时期书写的香港历史视为“大写”历史的话,那么对这种叙述方式进行拆解的行为可看作“小说”历史。关于这一点,黄碧云的“口述体”小说值得关注。黄碧云在两部小说《烈女图》(1999)和《烈佬传》(2012)里使用“口述体”的叙述方式来实践其“小写的历史”观。她曾在《后殖民志》里提过:“相对于书写历史而言,口述历史是一种颠覆。书写历史是国家的,口述历史是部落的、家族的、小的。”“口述体”的叙述方式分为“集体口语体”(《烈女图》)和“个人口语体”(《烈佬传》)两种。两部作品不仅替以“烈女和烈佬”为代表的弱势群体发声创造条件,还以此赓续一个群体的历史,为他们寻找重返精神原乡的路。
即便如此,在真正将“口述体”叙述方式融进“小说”历史前,黄碧云的创作也是经过反思和改进的。《烈女图》同样借女性弱势群体的叙述视角与香港殖民时期大事结合起来,即使没有如《香港三部曲》和《拾香纪》般结合得天衣无缝,也依旧无法摆脱“百年沧桑”的大历史叙事模式,仍受到“大写的历史”观的潜在影响,只是用妇女琐碎的语言包装,从弱势女性的角度切入。这种刻意处理历史的“不纯动机”,让黄碧云深感自己的创作已成为一件“解释历史的工具”,进而促使她思考如何才能真正追溯并赓续香港的历史。她曾公开作出自省:“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无法真真正正,揭示人内心的所有;我们无法完完全全,记下我们的时代,刻划时间,捕捉空间,追溯历史。”
经过4年与更生人士的深入对谈和资料搜集,毕业于香港大学犯罪学专业的黄碧云深谙人心,渐悟到她只能写“一个人的小历史”,那就是:或许因为他只是一个人,他自知的小人物,他对无论自己过去,还是其时所发生种种,说起来,“是这样”,没有更多,不怨不憎。愈到后来,黄碧云愈感受到如果不为这个群体写一段“小历史”,那么就不会再有人记得他们。书写这段“愈小至无”的历史,其实也是在反观我们自己的一生。到了创作《烈佬传》,她慢慢学会最大限度将自己代入角色的身份、视角与思维,叛逆大历史书写观,真正回归“小写”的姿态。在7年的创作里,她专注于写一个瘾君子(周未难)和一个鱼龙混杂的江湖之地(湾仔),实现“小说”历史的可能,以一己之力付诸实践,切实赋予这群被社会忽略的男性以身份和尊严。
《烈女图》和《烈佬传》采用的“口述体”叙述方式,与黄碧云后期形成有关历史书写的两大理念密不可分,那就是:自由的本质、小写的可能。这源于她对自己人生的重新思考和定位:“我想我的人生也从此进入省减时期:真的不需要那么多。我甚至不再需要一个姿势。”
充满象征意味的家族书写
在香港百年史的文学书写里,有一类小说涉及家族书写。作为具有血缘关系的社会群体,每一个家族的“小历史”,都是构成香港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呈现出香港历史的多元面貌,弥补西方殖民者的香港史书写中无法涵盖的领域。
对于家族书写,目前学界有“家族小说”和“家族叙事”两种称谓,而界定两者的区别主要集中于文学体裁和小说类型。本文探讨的“家族书写”集中在小说这一文学体裁,也与其他类型的小说有所区分。在“家族书写”体现出来的特征方面,除了具有特指性和历史性之外,还具备象征性。中国文学的家族书写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可以上溯至“神话与史传叙事”。香港小说在这一文学传统的传承上有着新的创造,与香港的社会发展和文学先锋实验探索有着极大关联。突出的“象征性”内涵,与“物”这一符号联系在一起,分别指代作为实存意义空间和构想意义空间的香港,进而钩沉由港人挥洒热血奋斗出来的百年香港史。有学者曾经将作家聚焦“时代与物”之间的关系所创设出来的符码称为“物符号学”。作家董启章也认为:“世界建构的关键其实就在于‘人’和‘物’的关系。”《飞毡》(西西,1996)、《拾香纪》(陈慧,1998)和《天工开物·栩栩如真》(董启章,2005),可以作为具有“象征性”的家族书写范本探究历史上“人与物(家族/城市)”的互动关系,在与家族史/城市史的对话中回归精神原乡并安顿自己的灵魂。
作为家族小说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在探索“人与物”的互动层面比前两者更进一步,实现了对家族史的想象与创造。相较于《飞毡》和《拾香纪》展现的单一世界(想象世界/现实世界),董启章笔下的香港及其相关物符同时指涉两个世界,具有两层含义:一是真实之物(真实空间/真实世界),二是虚拟之物(虚拟空间/可能世界)。二者齐头并进,形成“真实和虚拟(实然和或然)”两个声部(世界)的交错叙述(各12章)。
可见,香港小说的“家族书写”常与物符联系在一起,并尝试通过实存空间与想象空间的相互渗透探索人与物的互动关系,进而弥补以往西方殖民者在描画物化时代日常生活史时缺失的维度,对这个城市的“物理”展开“象征性”的想象,在赓续历史中重返精神的原乡。
多声部交错的空间叙述
在书写百年香港时,如果说大多数作家选择“向后看”的线性叙述模式,那么董启章的视野则受球状史观影响,并不仅仅局限在一城一时一地,而是放眼寰宇,将香港放置在更大的宇宙空间进行多维度思考。更为特别的是,他还把视野推向未来百年的香港,回顾并反思过去的历史,实现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跨界打通,从而开辟出实然、或然和应然的多声部交错空间叙事。这样一条错综复杂的叙述脉络暗示着董启章不断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地找到赓续历史、重返原乡的路。《地图集》(1997)《繁胜录》(1998)以及《时间繁史·哑瓷之光》(2007)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董启章将笔下的“香港”称为“V城”(维多利亚城),这包含作者对香港的历史与未来想象的指认。“以V代之,正是建构一层虚构的距离”和“此‘城’实是中西两种城市观的合体显像”,是作者中西文化融合视角下想象的产物。
21世纪以后,董启章对香港百年史有更深入的思考,缔造出宏大工程“自然史三部曲”,积极探索“实然、或然和应然”三重世界,让我们看到更多的未知与可能:既表达个人与香港的历史,也直指宇宙的历史,在历史叙事上迈向一个新阶段。其中,第二部《时间繁史·哑瓷之光》展示了多重时态的可能世界,是一部充满可能性的小说。它被看作“是一部未来史,也即是把未来当作可能的事件去体验,去想象的一种方式”。对于“未来史”一词是否成立的问题,董启章曾分析道:“过去”和“未来”并不是以一个(纵使是变动不居的)“现在”分隔开来的,两者是互为表里的。只有这样,“未来史”一词才说得过去。因此,如果说“自然史三部曲”的第一部《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偏重于讲述过去百年的香港,那么到了后两部曲则把时间推向未来百年的香港。
董启章在这部小说里创设核心词“婴儿宇宙”,把未来作为一种历史的可能性来想象、体验、珍重乃至反思。也就是说,他不把时间当作线性和因果性来看待,而是将其当作一个环状球形,也就是大多数物理学家所认可霍金提出的“宇宙有限而没有边际”的球体时空观,指向的是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无边无际的宇宙。随着未来史将小说的时间无限延伸至整个21世纪,创设“婴儿宇宙”的空间想象将超越V城时空的局限,直面人类生存本身,乃至整个宇宙。因此,该小说“不只是一部V城史,也不只是一部城市史,而同时是人类文明史,宇宙史,自然史”。
在众多作家纷纷把目光聚焦于叙述过去百年的香港时,董启章将视野推向未来,试图将香港史的叙事纳入球状史观,打破西方殖民者叙述香港历史的定论,让多种历史同时并存,在无边无际的球体时空里运行,从而实践小说发出的疑问:为什么不能有一种共时的历史,空间化的历史,并行的相悖或不相悖的多种历史?这是否也属于普鲁斯特克服时间、超越时间、复得时间的“隐喻”范畴?过多时间意义的加持让不少作家的历史叙事显得确定与唯一,以至于无法看清多重历史的真相,无法实现精神的返乡。空间不是历史的可有可无的要素,而是构成整个历史叙事的必不可少的基础。于是,董启章让时间与空间在历史叙事的维度展开多种互动的可能,用更贴近日常生活感受的方式,构筑立体分层的历史叙事空间。
学者叶维廉曾对香港文学发出如下感慨:香港文学不是摹仿大陆,就是摹仿台湾,很少有反省香港殖民经验的作品。香港还没有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文学,没有真正触及并反省一些内部本质的问题。作家陈映真也曾提醒香港的知识者:“在香港这样一个殖民地的时代,应该从殖民地香港这个本身开始反省,从清末香港所走过的路,香港文学的发展,香港社会的发展,以至香港中国人的身份的认同的问题,香港在历史当中,在社会发展当中,在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发展当中占一个怎样的位置,提出整个的反省。”他建议从整个香港的殖民地历史开始反省。然而,香港知识阶层对陈映真的回应可谓少之又少,“像陈映真那样具有强烈的反省意识、深刻的思考能力的文人(同时又有精彩的创作),则并不多见”。可见,审思殖民地经验进而实现去殖民化,仍任重道远。这令人不得不慨叹香港人在殖民时期留下的对地方历史经验一知半解的态度,使得不少有担当和情怀的作家拾笔思考如何赓续历史并重返精神原乡的问题。于是,“赓续历史”与“精神寻根”之间便存在复杂而微妙的对话关系。在“历史之中寻求重量”才能对英国殖民统治留下的历史问题作出有效反思,而不是把“历史事件”写进小说就会产生历史感。
要想真正在小说中做到“赓续历史、重返原乡”,需要聚焦具体事物在不同时期的变迁,展示人在历史洪流面前的各种姿态。也就是说,这一切需要放置在“历史叙事与精神寻根”的互动关系中展开并作出阐释。追溯作家重建历史向度的努力,既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叙事”提供新的视野和经验,也有利于巩固地方性精神凝聚力和历史文化认同感,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