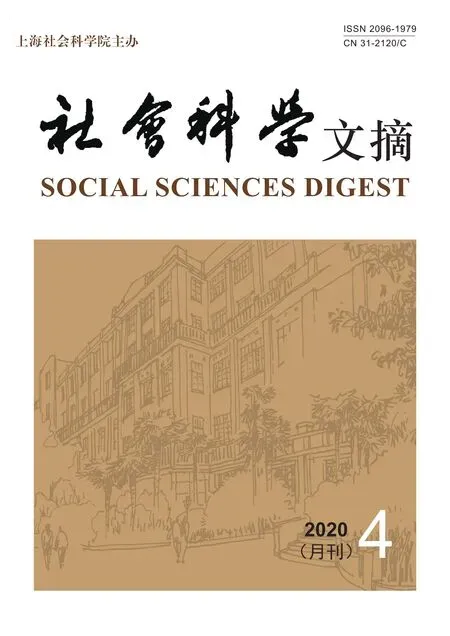社会学的理论危机与齐美尔的方法论基础
文/王赟
自然科学式的图景划分往往依赖生物学在近代广为采用的属加种差逻辑。
社会学也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但大多数时候表现为代价而非成就。在社会学内部出现了两种具有明显问题的研究倾向。第一种将社会看作社会科学之总和的地位,其他社会科学分支学科只是社会学的子学科。
第二种倾向首先将其他较易确定的对象交给诸如经济学、法学等学科,然后将“剩下的”称为社会学。社会成了现代人之规范化生存诸范畴的剩余;而社会学则成了现代人对其规范化生存诸范畴之剩余的规范化认识。
研究对象问题导致了“社会学的理论危机”。事实上,从社会学的古典时期开始,齐美尔对这个话题的思考就非常重要:限定了社会学的是对象和方法的联系。本文试图通过对对象、方式和心理设置三个方面及其相互联系来分析齐美尔方法论的基本设置。正是通过这三个因素及其相互间的联系,齐美尔将“社会化过程之形式”确定为社会学的独特对象;形式则同时意味着经验的重要性和人际层面的相互-行动的必要性。反过来,社会学也因此同时得以确立它的科学性和学科边界,来走出自身的理论危机。
对象、方法和心理因素设置
首先,齐美尔揭示了学科和对象间的不对称。从史学或美学目的出发,人们可以研究一幅画的价值。在此情况下,作品的史学或美学意义是我们的研究对象。但同时,一位自然科学家同样可以以别样的科学目的研究这幅画。如画的颜色会具有什么独特化学构成等等。对于社会学来说,从对象角度出发并不能得出关于学科门类的专属分类。
由于根本不存在不涉及经济、法律、宗教、历史等因素的社会,社会学所考察的现象或现实,同时就是经济学、法学、宗教科学或史学所考察的那些现象和现实。
在方法论角度上,他宣称,整体论观念下的社会无法在功能主义意涵之外提供社会存在的意义;而在方法论缺陷之外,社会无法成为真正外在于人及其行动的整体,任何被整体论评价为“社会”的因素同时也必然是关于个体人的因素。
因此,对象和方法的有机联系才能确定一个自成的社会学。它使社会观念与个体或自然得以互相区分,并在科学分类中给出社会学真正的角色。
社会学所观察之物因此处在两个层次上。首先,相较于其他科学,社会学所拥有的就是日常的那些内容;它建立在对社会生活的日常和内生因素的把握之上。其次,社会学的建立,在于用独特的方法论,使学科在认识层面与日常生活中的知识或其他社会科学的知识做出区别。
对象问题的核心因此实际上就是方法论问题,必须建立一种合适的视角来思考具有如下特征的社会:首先,社会并不真正与组成它的个体相割裂;其次,社会也从来不是零散分布的若干单位或个体的简单数量之和。构建了完整社会单位的,是处于相互和有机过程中的个体、他们的冲动和目标。齐美尔眼中的社会从经验意义出发,其中“完整单位”的提法已经潜在指向了“交互”意涵。社会的完整单位的提法潜在意味着组成部分间的交互性。
人的心理来源、冲动、旨趣和其他心理活动在齐美尔笔下是最根本的行动来源。一方面,它们是社会生活中人之存在的最根本单位;另一方面,它们通过对这些存在的表现进行观察而进入社会学。这些实践中可被观察的心理因素构成了社会和社会学最基本的内容。
必须同时强调,构成社会的这些心理因素也还并不是社会学直接和立刻的对象。这些心理因素仅在同步整合/对立的相互联系上才进入社会学研究。心理因素如果要构成通过经验可感知和观察的社会,就必须籍由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社会化过程。
作为纯粹社会学对象的社会化过程之形式
既出于个人本能也出于社会需求,人具有与他人交往的意愿和能力。那么,人就以理性和意愿的双重手段符合了先天提供的交往可能性,并因此向个体提供了无尽的共同生活的能力和可能。齐美尔将社会化过程之形式(以下简称形式)看成个体和社会整体之间的媒介。形式还是某项具体实践和关于它的抽象认识之间的媒介。
齐美尔的形式描述了一种人的独特范畴或者关于这个独特范畴的观念:通过形式,不同的个体在社会现象中相互-行动。一方面,个体并非某个整体社会的功能组成部分,因此相互-行动区别于共同行动,前者更为强调个体以各自意愿为出发点,并在“对于自我”和“对于他人”两个维度提供行动效果。另一方面,相互-行动强调了动态的社会化过程。人通过互动不停地对其所处的社会联系进行调节,形成了永恒的动态过程。其结果是,形式因此要么是社会联系本身,要么是个体处于其中的社会联系所发生的情境。归功于这些联系和情境,个体性不是个体的孤立状态,而是个体在社会场景中的联系状态。由于形式既是本体性的社会机制,又是认识对其的正确把握,因此,它提供了克服纯粹主体性而通向“相对客观的”和“相对群体的”的可能性。
齐美尔的形式观念因此指出了其方法论首要原则:人之经验是社会和社会学的来源。经验并不意味着纯粹个体维度的应激以及应激在认知中的储备,而是指向人的社会本能:人以共情或说共同经历的方式来理解他人。在实践中,个体那种并列摆放的潜在状态就通过形式被转化成相互关系上的向量。行动者之间因此总存在状态上的共生性和机制上的交互性。
基于实践,形式过程使复数意义的个体得以结成互动联系,社会从中生成。社会学因此通过对形式的研究来建立对社会现象和人的理解。由于形式通过旨趣等心理因素对行动中的个体和他们的共同活动进行了重组和联系,社会学并不陷入“局限于对心理因素进行主观描述”的心理主义和由纯粹主观性带来的唯名论陷阱。通过形式,社会学完成的是从主体认识达到存在之客观呈现的过程。
此外,对于社会学,必须通过对这个过程的研究来把握社会本身。对社会化过程的功能研究有助于理解其在社会中的运行机制,但这并不能否认如下事实:社会化过程在个体及他们之间是自生的。功能主义只是将社会化这个自生和自为的角色变成了一个纯粹的认识工具,用来满足某个外在并被假设为高于人的原因,这样的原因根本就不存在。
齐美尔社会学的独特对象就是形式本身。形式意味着实践和研究的联系,以及由实践中的形式所凝聚了的那些内容与社会表现出的整体模态和趋势之间的联系。
形式与普遍法则不具可比性。普遍法则意味着公式或模式与由它所揭示的事实间的普遍、先验、排他的关系。形式并不是某种力或某种实存,而更多的是一种有效联系了人的关系和方式。不对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环境和他们之间的联系网络进行把握,就不能把握形式。此外,将形式当作一个认识方式,又暗指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学方法。
齐美尔对实证主义的反对,还在于后者与功能主义思想的联系。人类社会中的个体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这确实作为效果产生了某些功能。但首先,个体行动的目的是每个个体自身的生活,而并非功能性的生存或社会维持。个体只间接地向社会提供其行动和与他人互动的影响;功能则只是他的行动和互动在后天意义上的效果。
社会学作为专门学科的独特性寓于对象到方法的联结上。虽然与其他门类共享来自于日常的直接内容,社会学的对象只能是社会化过程之形式,因为对象意味着直接内容和社会学独特的形式方法之间的内部联系。其最大特征因此在于与其他社会科学门类相比明显具有差异的对待直接内容的方法。
如此,才能把握齐美尔关于社会学的“社会科学之几何学”比喻。形式并不致力于普遍意义上的法则,形式本身就是一个正在演进社会中的过程。社会学致力于理解这个过程及其中因素的运作。至于个体,由于他直接关涉于生活中的多种形式,他本人也通过对这些形式的研究来部分得到揭示。对社会个体的理解只能通过形式研究来完成,形式联系了外部世界和个体所具有的社会联系。如此研究的重点在于最细致的和最根本的心理因素,因为正是这些因素在互动过程中反射回自身,在社会存在意义上的个体性之下塑造了心理存在意义上的个性。
作为形式驱动者的心理机制
齐美尔认为,每一个形式背后都有一个支撑它的心理机制,一个处在更深层次的旨趣、动机、理由等。把握一个形式因此意味着同时在作为行动内部冲动的心理机制上,和作为行动效果的人际互动上,把握个体的心理机制。所以,不考虑个体或个体间的心理机制就无法研究形式。形式又同时是个体间沟通和相遇的表现。个体同时具有独立和交往的二重状态,这构成了个体和他者间的关系,社会也得以可能。
必须避免将社会的构建建立在对个体心理机制的排斥之上。如果主体性意味着个体在其行动中的特殊性,那么社会化及其形式则是主客体联系的保证:社会的运行并非主体的直接产物,而是“伴随主体”的过程。
齐美尔也非常强调他者的角色。社会联系首先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互助联系本身。通过这些联系才形成了生活世界。同样,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联系处于人际这个维度,它使得客观性可以基于主体性而得出。
社会和历史因此就是社会化过程本身,通过这些过程,且归功于相互联系,个体成为个体“们”。
重提齐美尔在《社会如何可能》中指出的三大“先天形式”因此显得非常必要。这些形式是社会这个本体存在的基础。首先,人通过类型化的方式来了解其他个体。其次,人的生命/生活同时具有私密和公共意义。第三,社会一经人的意识把握,就现象学地展开。第一形式意味着,人只能通过预先习得的认识以类型化的方式形成预置模型,并在遇到新的对象时,由对象被主体把握了的相似性而将其纳入相应的已有认识类型。“类型化”因此是认识过程的普遍实践(而非实证)逻辑。这种认识的构建方式意味着与经验相关的双重运动。一方面,经验是人得以建立知识的唯一可能。另一方面,类型化内在地要求类型、概念,和通过共同点而将一定数量的个体联系在一起的形式。
第二形式意味着,通过无尽的创造过程,个体和社会同时成为可能:个体意味着社会性,就像社会同时意味着个体性一样。社会作为个体和生活世界之间的桥梁因此对个体和外部世界同时具有历史或社会意义。人通过在社会中接受知识和形成认识而是其所是。传统、习俗和信仰标志了一个人的特征。但同时,人在“此刻”的社会生活又通过对行为及其中的心理因素的接收反过来生产着新的知识和认识。这一过程又是对自我和社会进行重构的过程。
第三形式意味着,个体在其相互行动中生成社会,社会也同时向组成它的个体提供社会角色来占据。“每个个体看起来都完美地整合到某个社会位置上”这种感受在日常生活随处可被体会到,但这种所谓“完美”是现象而非某个法则给出的。
齐美尔因此特别反对通过某种自然科学式的规律来解释社会。整体论观念的主要问题就在于无法彻底如愿地在社会学分析中祛除个体心理因素:这是由个体和他们所组成的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所决定的。心理因素和情感冲动是社会构建不可分离的因素。事实上,正是这些因素解释了个体的社会性来源。这些因素也并不仅仅是可被阐释的;它们的运行首先是社会的必要条件。应该致力于展现作为存在的社会如何在一个动态过程中,通过形式同时联系了个体和生活世界。
作为方法论基础的形式与心理机制的重要性
社会学家的问题不仅仅是知晓社会如何构建,还必须指出社会为何以及在何种状况下是必不可少的。瓦蒂尔提出,用知识(savoir)视角取代旧有的功能主义的认识(knowledge)视角是紧迫而必要的。认识视角预设了行动者以包括他人在内的行动对象为工具来实现其行动这一功能,而这并非人的社会状态:人的社会行动当然包括某些策略和功能行为,但人在此之外首先是社会性地存在着的。两个观念的差距指向实践意图。实践中,人不仅接受外部社会和他人传递的信息并对他人做工具性的开发,而是首先期许着和他人沟通交流,用以传播信息、形成社群、维系交流,并在非目的性的意义上构建了社会。
因此,社会学首先将注意力放在心理知识在社会化过程之形式的构建过程中的状态,并将社会的构成本身当作目标。齐美尔并不将社会学设置在心理学之上。他强调的是,一方面,社会的构成处在个体、机构化和整体社会的相互行动过程之上;另一方面,这个过程如果没有作为催化剂的心理机制是不可能实现的。
心理因素对两个学科起到不同功能。心理学将眼光局限于个体层面,在个体心理运行机制中研究心理因素,致力于建立对心理状态的内生解释。社会学则通过对心理因素的研究,在人际因而是形式层面,研究作为“对象的部分内容”的心理因素。如果个体的理由和意志使其可以面向一个心理目的,社会学上,研究指向的则或多或少是另一个明确区别于自我心理构建的目的:一种人际的心理目的。社会目的只能存在于社会化过程中,由于心理因素在社会内容中体现,且这些因素首先被当作“心理上的”,我们才可以在其中提取出“社会学上”的目的。
由此笔者认为,两个学科的区别既在功能上又在方法论上。一方面,虽然都包括心理因素,社会学却是在人际层面考虑这些因素。如果心理学研究心理机制,社会学则利用这些心理机制建立社会学观点。另一方面,社会学的形式方法面向的是社会性的意义或价值,而非返回到个体上的病理心理学取向。
此外,心理学和社会学仅在个体范畴也不具有完全对等的对象。一个社会现象并不能被单纯理解为个体的心理机制及其结果,还同时包括了一些无意识因素及其影响。研究者必须意识到,1)复数意义上的个体心理机制塑造了社会联系;2)社会联系联系了个体;以及3)这两个层面间的永恒往复。
结论
将心理因素等同于主观,进而等同于前科学或非科学的范式在今天越来越受到质疑。客观主义无法回答社会学在祛除方法后造成的对象混杂的局面和相应的理论危机。与此同时,齐美尔的方法论基础既强调了方式到对象的联系,又强调对包括心理因素和心理机制在内的所有因素的广泛联系。
作为一门学科,社会学对象的独特性必须建立在与方法的联结之上。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分享来自于实践的同样内容,却要求考虑人际层面的互动及其影响。作为一门科学,社会学强调人在个体和人际层面的行动、动机、效果,因而与经验质料、心理因素保持亲密联系,却由于“形式”这一内在要求同时区别于心理学和自然科学式的实证主义或整体论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