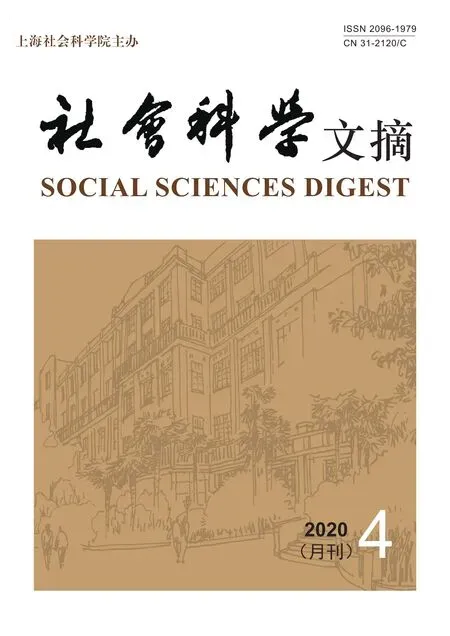外资进入自由化是否影响了中国制造业生产率
文/毛其淋 方森辉
自1995年中国商务部颁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以下简称《目录》)以来,《目录》先后历经大小8次修订,中国外资进入自由化进程不断推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外资企业设立实现由“逐案审批”向“负面清单”管理的重大变革,预示中国进一步放宽外资行业准入门槛,外资进入自由化迈上新台阶。伴随大量外资流入,外资与中国企业生产率的关系引起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但现有文献未能取得一致结论:一些文献支持外资进入对企业生产率具有正向的溢出效应(路江涌,2008;Lin等,2009;Du等,2014);而另一些研究则证实外资进入不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Liang,2017),甚至具有负向的溢出效应(蒋殿春和张宇,2008;Liu,2008;Lu等,2017)。现有文献一般直接采用行业外资占比或结合投入产出关系构造指标来衡量外资进入水平,难以有效处理外资进入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外资进入自由化对企业个体生产率与制造业总体生产率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如果是,导致二者差异性背后可能的作用渠道是什么?为此本文以中国外资管制放松为背景,利用1998—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在微观层面研究外资进入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因果效应及其作用渠道。本文的发现有助于客观准确地评估外资进入的经济效应,同时对发展中国家引资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目前,已有大量学者研究了外资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其中,一些文献考察了外资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及其影响方向,如Monastiriotis和Alegria(2011)对保加利亚、Fernandes和Caroline(2012)对智利等研究均发现了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具有正向溢出效应的证据;然而,也有部分研究发现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的溢出效应不明显甚至为负向,如Aiken和Harrison(1999)对委内瑞拉以及Lu等(2017)对中国的研究。外资进入的溢出效应可理解为竞争效应、示范效应和人员流动效应的加总(王争等,2009)。一方面,外资进入加剧东道国市场和产品竞争,挤出本土企业市场份额(包群等,2015),对内资企业产生负向溢出效应(路江涌,2008;Lu等,2017;毛其淋和许家云,2018),最终抑制本土企业生产率增长。另一方面,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优于本土企业,通过示范效应和人员流动效应等提高本土企业生存概率(包群等,2015),改善本土企业生产率。跨国企业在东道国设立新企业,不仅引起市场上企业数量变化(陈艳莹和吴龙,2015),影响东道国市场格局,还进一步加剧行业内高、低效率企业之间的竞争,通过低效率企业退出等方式引发资源再配置。从总体上看,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取决于上述正负效应产生的综合效果。
部分学者认为外资溢出效应的发挥受到一些因素的限制。其中,一些研究考虑企业层面的因素,如Xu(2000)对美国的研究强调了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Blalock和Gertler(2009)对印度尼西亚制造业和Girma(2010)对英国的研究认为本土企业的研发活动有助于外资溢出效应的发挥;另有部分研究者从企业所有制角度入手研究发现,民营企业较国有企业受到更强的外资负向溢出效应(Lin等,2009),Liang(2017)发现外商独资企业比中外合资企业表现出更强的示范效应。
除此之外,学者们还从其他角度考察了外资进入对东道国企业绩效的影响,如Héricourt和Poncet(2009)研究发现外资进入有助于缓解中国本土企业的信贷约束;Chang和Xu(2008)关注FDI对本土企业生存的影响,邓子梁和陈岩(2013)进一步指出外资进入通过竞争效应加大了国有企业面临的生存风险,但高效率国有企业通过利用外资的正外溢效应,有效降低了生存风险;周浩和陈益(2013)则将视角转向新设企业,考察了FDI对企业选址的影响。近年来,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出口行为(韩超和朱鹏洲,2018)、企业成本加成(毛其淋和许家云,2016)以及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毛其淋和许家云,2018)的影响也开始得到一部分学者的关注。
在最近,部分学者将《目录》在2002年的调整作为准自然实验,考察了中国情景下外资进入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Lu等,2017),如企业利润率(刘灿雷等,2018)、企业出口产品质量(韩超和朱鹏洲,2018)等。然而,以上文献均未区分I类和II类政策调整的差异性。本文深入比较分析了两类外资进入自由化的差异性,丰富了评估外资进入自由化的经济效应方面的研究。本文在考察企业层面外资进入的生产率效应基础上,还进一步地研究了行业层面外资进入自由化与制造业总体生产率变动的关系,在文献中揭示了资源再配置效应是外资进入自由化促进制造业总体生产率增长的重要途径,并深入检验外资进入改善资源再配置效率的具体渠道。本文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外资进入溢出效应这类文献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更为全面、客观地评估外资进入的生产率效应。
研究方法与数据
我们借鉴Lu等(2017)的研究,把2002年《目录》修订视为准自然实验,把制造业本土企业划分为处于外资管制程度放松行业的企业(处理组)和处于外资管制程度不变行业的企业(对照组),进而构造倍差法模型。指标构建上,因变量(tfp)采用Ackerberg等(2015)提出的ACF方法分2位码行业进行估计。控制变量考虑如下因素:
(1)企业层面:企业规模(size),以1998年为基期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平减后的企业销售额取对数;企业年龄(age),当期年份加1与企业开业年份之差并取对数;资本密集度(klr),以1998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进行平减,以平减后的值除以从业人员数并取对数;企业融资约束(fincon),利息支出与固定资产比值,该比值越大表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小;出口密集度(expr),企业出口交货值与企业销售额的比值,用于控制企业出口因素对其生产率的影响;企业所有制(soesdum),国有企业取1,否则取0。
(2)行业层面:外资管制放松前的行业特征可能会影响外资进入的程度与方向,我们将衡量外资管制程度的4位码行业变量对上述潜在因素进行回归,识别出对外资放松管制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并将其与时间虚拟变量形成交互项,加入基准倍差法模型(Lu等,2017),具体包括:行业新产品密集度(NPI),行业新产品产值与工业总产值的比值;行业企业数量(LNF),行业的企业个数取对数;行业资本密集度(KLR),经过平减的行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与行业从业人数的比值并取对数;行业出口密集度(EXP),行业出口交货值与企业销售额的比值。此外,还加入2001年4位码行业中间品关税、最终品关税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以控制贸易自由化对本土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毛其淋和许家云,2016;孙楚仁等,2019);加入2001年4位码行业国有企业数量占比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叉项,以控制国企改制政策对本土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1998—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我们将实收资本中外资占比超过25%的企业认定为外资企业并剔除,选取制造业本土企业进行分析,并按现有文献通行做法进行处理(Brandt等,2012)。
估计结果与检验
外资进入一方面挤占行业内本土企业的市场份额,抑制本土企业产出(路江涌,2008);另一方面,给予本土企业通过学习和模仿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提升生产效率的机会,即正向的技术溢出效应(Atiken和Harrison,1999;Javorcik,2004)。本文基本估计结果表明行业内外资进入引起的技术外溢为负,倾向于降低本土企业的生产效率。为确保识别过程的可靠性,本文还从预期效应、平行趋势假设、控制行业时间趋势、两期倍差法和安慰剂检验等五个方面进行倍差法识别的有效性检验;从考虑存续企业、控制行业固定与年份固定效应、加入企业生产率的滞后1期项、更换外资企业认定标准(实收资本中的外资占比大于0%,根据企业登记注册类型)和更换聚类标准(企业、城市4位码和省份2位码-行业聚类)等五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通过上述检验后发现,本文的核心结论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识别过程具有可靠性,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在异质性分析部分,我们将外资进入自由化分为以下两种形式:I类进入,即外资政策由禁止/限制外资进入变动为允许外资进入;II类进入,即外资政策由允许外资进入变动为鼓励外资进入。I类由抑制转变为开放,近似从无到有,II类则释放了希望外资扩张的信号,是从有到多。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仅有I类进入对本土企业生产率存在明显的负向溢出效应,且I类进入的溢出强度总体大于II类,不同类型的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生产率确实产生了差异性影响。我们认为两类进入对行业内外资进入程度和结构上的差异性影响,以及两类行业原有外资开放程度的差别带来的外资进入冲击差异,是两种外资进入自由化的溢出效应存在明显差异的原因。进一步的,我们考虑企业所有制(国企与民企)、企业区位(沿海与内陆)和企业吸收能力(企业研发密集度、企业专利申请数和企业管理效率)对外资进入自由化溢出效应的异质性影响,发现外资进入自由化对民营企业具有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而没有证据表明对国有企业具有类似效应;对沿海企业的负向溢出效应强于对内陆企业;提升本土企业吸收能力有助于缓解外资进入自由化对本土企业的负向溢出效应。
此外,我们在基准倍差法模型基础上引入地区制度环境变量与倍差法估计量的交互项以考察制度环境的作用(毛其淋和许家云,2015)。估计结果表明,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外资进入自由化对企业生产率产生显著抑制作用。对此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技术的市场价值降低,减弱跨国公司将先进技术和管理技能转移至东道国的动力(蒋殿春和张宇,2008),并可能催生相当数量的技术落后外资或“假外资”;另一方面,在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经济交往的不确定性降低,行为结果的可预见性提升了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的意愿。对此,我们区分外资进入自由化类型,同时考察制度环境、I类和II类进入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良好的制度环境强化了I类而削弱了II类进入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上述结果在以制度变量的滞后1期项替换当期项重新估计后依然稳健。
外资进入自由化与制造业总体生产率变动
我们比较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外资进入自由化究竟会如何影响制造业总体生产率?尽管从企业个体层面来看,外资进入自由化引致了负向的生产率溢出效应,不利于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但外资大规模进入带来的市场竞争可能会淘汰一部分低效率企业,以及引致市场份额从较低效率企业向更高效率企业转移,如果后者产生的效应大于前者,那么外资进入自由化则有可能会提高制造业总体生产率。事实究竟如何?我们首先采用Melitz和Polanec(2015)的分解框架(M-P法)对制造业总体生产率增长进行动态分解,发现1999—2006年制造业总体生产率的增长量为0.087,资源再配置效应对行业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度为40.23%,在中国制造业行业生产率增长中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接下来,我们以M-P法分解后的各项为因变量,采用基准倍差法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表明外资进入自由化显著提升了行业的资源再配置效应,即通过优化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制造业总体生产率增长。
此外,我们在影响渠道检验部分,采用就业资源来衡量市场份额和资源配置情况,并进一步关注外资进入自由化是如何影响行业总体的资源再配置。Probit和Logit模型的估计结果均表明,外资进入自由化对不同生产率企业的就业资源变动具有异质性影响,在促进低效率企业就业破坏的同时,提升高效率企业的就业创造,进而引导资源向高效率企业转移,通过提升资源的使用效率,促进制造业总体生产率的增长。以上分析反映了存续企业的就业资源配置情况,接下来,我们以企业退出虚拟变量为因变量考察外资进入自由化对企业退出的影响,结果表明外资进入自由化有助于降低高效率企业的市场退出风险,并促进低效率企业退出市场。外资进入挤占了国内市场份额,进而加剧行业内竞争,迫使低效率企业更快退出市场(包群等,2015),同时低效率企业难以吸收外资的技术溢出,进一步加剧了外资进入的竞争冲击。资源再配置效应通过企业更替行为,促进资源由低向高效率企业转移。借助较强的成长能力,高效率企业通过资源再配置过程进一步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有助于其吸收外资的技术溢出,提升自身生产率,同时削弱了外资进入引起的负向溢出效应,大大降低了退出市场的可能性。
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以中国在2002年实施的外资管制放松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研究了外资进入自由化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资进入自由化显著抑制了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且I类外资进入自由化对本土企业的负向溢出效应大于II类外资进入自由化。引入企业特征的分析表明,外资进入自由化对中国本土企业生产率的溢出效应受到企业所有制、吸收能力和地理区位等因素的影响。我们发现良好的地区制度环境强化了外资进入自由化对企业生产率的正向溢出作用,且I类进入的影响效果更强。此外,使用M-P法分解行业生产率后,考察发现外资进入自由化主要通过资源再配置效应显著提升了制造业总体生产率,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外资进入自由化与生产率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最后,我们考察了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可能渠道,结果发现:一方面,外资进入自由化倾向于促进高效率企业的就业净增长,引导就业资源由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业转移,通过资源再配置效率的改善促进行业生产率的增长;另一方面,外资进入自由化倾向于降低高效率企业的市场退出风险,并促进低效率企业退出市场,进而提升制造业总体生产率。
本文为客观评估外资进入对中国制造业本土企业的影响效应提供了微观证据,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有关外资进入与行业资源再配置效率的研究视角。外资进入自由化虽然未能对企业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提升效应,但通过资源再配置效应,在总体上提升了中国制造业生产率。这一发现肯定了中国引入外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做法,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因此应该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减少外资准入限制,将“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由自贸区向全国范围推行。同时,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地区制度环境可以强化外资进入自由化对企业生产率的正向溢出作用,地方政府在积极引入外资时,应注意营商环境的构建,以完善的制度设计助力本土企业吸收外资的正向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