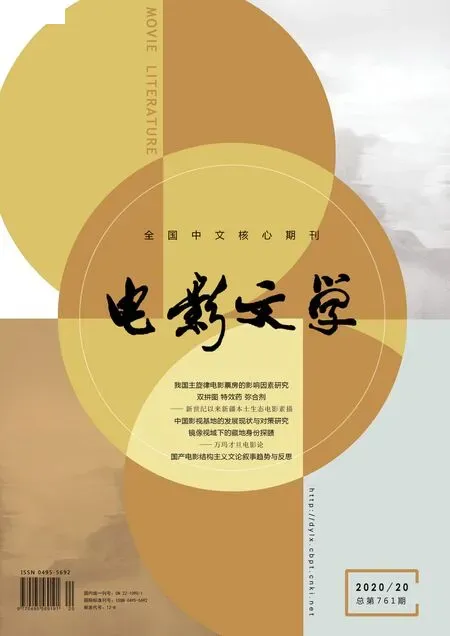第六代电影《紫蝴蝶》的美学风格分析
朱晓溪
(江苏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社会发展至每一个时间段都有着不同的时代特征指涉,艺术作品作为时代产物的重要代表,一直以来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在电影作品中也表现出不同代别的导演群体,他们将各自成长的时代背景融为电影的主要情绪基调,呈现出各自不同的时代性特征与精神内核。第六代导演便是其中风格极为鲜明突出的一代,他们中的多数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影视学院,90年代在影坛崭露头角。不同于在少年时期便卷入社会动荡旋涡中经受深刻历史性创伤的第五代导演,第六代导演多出生于“动乱”结束后,成长于中国改革开放旧体制与新思潮交替的新时期,在中国电影市场面临的各类诱惑与压力中开始各自的电影创作。
第六代电影也由此表现出了特殊的影视特征与美学风格,不跟随第五代导演们在宏大叙事中探索主观性、象征性、寓意性在历史和民族心理的影视力量,而是将视角缩小放置到草根群体或者个人,以尽可能还原真实的镜头语言和弱化叙事的情节安排展现强烈的个人印记与情绪色彩,并对各类事物都持有深刻的怀疑与抵抗态度,在导演们各自迥异的影视风格中表达着叛逆与反思,呈现出独特的美学风格。本文将以第六代导演重要代表娄烨的经典作品《紫蝴蝶》为例,重点分析个人小视角、纪实性手法与碎片化叙事背后的第六代电影独特的美学风格。
一、个人视角的悲剧感与虚无感
如果说第五代电影是从社会整体架构出发的现代性思考,那么从微小视角对社会进行审视则是第六代电影的重要突破,并在这个审视过程中逐步形成第六代电影的特殊美学风格。在经济与社会大跨步式发展,但精神与文化却滞后的生存世相下,个人的现实性意义、真实生命状态、内心渴望与诉求被各类影视作品忽略和回避,在银幕上缺失了很长一段时间,第六代导演将镜头对准了这片空白,将边缘人物、底层民众这些个人从被遮蔽而失语的状态中解救。借此将社会的阴暗面、人性的丑恶面悉数展现出来,以这种民主性特征明显的方式赋予观众更加主动的可能性,感知到社会环境的窘迫和压抑、生命的艰辛与悲剧以及个体意义的虚无。
《小武》中的小偷、《任逍遥》中的混混与抢匪、《安阳婴儿》中的妓女工人与黑社会、《极度寒冷》中的艺术家、《盲井》中的矿工……贾樟柯、王超、何建军、王小帅、张元等第六代导演们在对边缘人群中个体的细细描绘中,感受社会与个体,生命与价值意义的内涵。作为第六代导演的娄烨,其作品自然也多聚焦于对个体视角的探究,电影《紫蝴蝶》的故事虽然是放置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这一宏大严肃的历史背景下,但是关注的更多的是历史背景下的个人故事。
《紫蝴蝶》的故事在女学生辛夏(后改名为丁慧)与日本翻译伊丹英彦的青涩爱情中展开,在女特务丁慧与革命者谢明的爱情中结束,中间穿插着公司小职员司徒与接线员伊宁的爱情故事。未曾大篇幅地讲述国仇家恨或者渲染革命氛围,甚至未正面回答丁慧“我们为什么而战斗”的疑问,更多的是讲述个人在其中的悲剧命运与意义虚无。无法改变的国家与信仰注定了辛夏与伊丹英彦的悲剧结尾,无论如何谋划与运作,都只是与命运作困兽斗。曾经心意相通、亲密无间的情人成为各怀鬼胎伺机利用甚至杀死对方的仇敌,过往的情分成为今日的讽刺和成功的牵绊,以终结了双方生命的方式为各自的信仰献祭,激起了一朵并不起眼甚至无人知晓的浪花。丁慧与谢明两人则是在战乱中两朵无依无靠聚在一起的浮萍,因为地下革命事业而聚在一起,但是又无法准确地知道战斗的目标和原因,任由时代社会将他们推着向前走。
如果说辛夏、伊丹英彦与谢明三人是尝试过发出疑问与反抗,但无法摆脱的是时代悲剧与个人虚无牺牲品的命运,那么伊宁与司徒就是彻底的时代蝼蚁,像是被伊宁装在玻璃罐里面的紫色蝴蝶,有着看似安稳的一方天地,但却是极其易碎的。伊宁与司徒是乱世中一对普通的情侣,没有参加革命也没有投身抗日,只求守好现有的爱情与生活。时代灾难来临时从不顾及个人的历史贡献与生活态度,铺天盖的厄运落在了每一个的头上,伊宁在接爱人的路上被革命的枪战误杀,目睹爱人死去却无能为力的司徒只能选择以命搏命报仇雪恨。鲜血弥漫的动荡年代中个人的生命存在极为渺小,个人的价值意义更是经常被忽略。娄烨以特殊的个人视角展现大时代背景下渺小个人的悲剧命运与价值意义虚无,探视内心的主观世界,完成了对社会与时代的反叛和抵抗,具有强烈的现代性审美特征。
二、纪实性视听手法的情绪表达
第六代导演们对现实社会具有明确的“不确定”认知,其抵抗与反思决定了对电影的表现真实性的追求,尽可能地将导演认知的原汁原味的世界构建完整。因此第六代导演们会采取诸多创新性的手法,使用地方日常化语言、选用非职业演员、拒绝排练走位、提倡即兴表演,将现实生活真实存在的残酷、复杂、撕扯,个人所经历的痛苦、悲痛、无力等负面情绪展现出来,从而实现真实感从银幕带向观众脑海的效果,表现出对纪实美学的强烈追求。
电影《紫蝴蝶》中,娄烨对道具、服化、布景有着极高的要求,复刻式地再现了一个20世纪30年代所特有的时代场景,阴暗狭窄的弄堂、黑白蓝灰的着装、半现代化的街道、示威游行的群众……辅以灰色的色调越发显得缺乏生气,无助与压抑似乎从银幕中浸出,将悲剧的人物生命底色显露出来,也更多地展现出虚无的个人价值与意义,并创造性地借助摄影、剪辑与演员表演,在纪实性的基础下将真实情绪尽可能放大。
影片最开始,切换了四个空镜头伊丹英彦才正式登场,接着近景、中景、远景镜头不断变换地跟随伊丹英彦的脚步穿越过铁桥、火车铁轨、工厂,将东北铁路附近的场景真实地呈现出来,又能在晃动的跟随式镜头中营造战事的紧张感。辛夏的哥哥被激进日本分子当街捅死的情节中,激进日本分子从接近、杀死辛夏哥哥到引爆炸弹与辛夏哥哥的战友们同归于尽用时不过几十秒,跟随式拍摄晃动的镜头更是加速了观众对这一行为的感知节奏,而辛夏目睹哥哥死亡后从震惊、难以相信到震惊的面部表情特写则持续了一分钟,不断放大观众的情绪感知,加上章子怡痛彻心扉宛如真的痛失所爱的精湛演技,将撕心裂肺的痛苦展现得淋漓尽致。
剧中伊宁接到爱人司徒电报后前往火车接站的长镜头,是影片中长镜头运用的优秀代表,摄影机跟随伊宁的脚步从检票进站、沿着月台不断地往前走并四处寻找用时近三分钟,在手持摄像机特有的抖动中跟随镜头走进人物角色,将伊宁对司徒的焦灼期待与不熟悉站台的迷茫之感这些真实的情感传递给观众,并在镜头主客位置互换中带入了丁慧与谢明这另一个叙事线的角色中。伊宁沿着月台走向前时,一辆黑色的汽车行驶在轨道的另外一端,丁慧、谢明等三人下车走向镜头中央并成为镜头与剧情的主角,伊宁从镜头中的无故消失就像在剧情中无辜被枪杀般让观众感受到伊宁这个生命的脆弱并激起对弱者的同情与怜惜。
导演娄烨相比于情节更重视人物情绪表现,并且擅长记录和放大人物角色对事件发展变化的情绪反映。比如司徒在目睹爱人的死去,遭受了一遍遍非人殴打与凌辱后准备在伊宁的厕所自杀,导演娄烨使用由近到远再到近的推进式镜头将演员刘烨愤怒、羞辱、痛苦、怨恨又留恋的复杂情绪悉数捕捉。娄烨借助场景重新与还原式拍摄的方式,立体式再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社会,将动荡、混乱、茫然的社会背景下个人的情绪色彩展现出来,从而实现视听语言的情绪表达和对纪实性影像中纪实性美学的高度追求。
三、碎片化与拼接叙事的意境效果
与第五代导演相比,第六代导演在创作上少有明确的电影主题和教化内涵,更多的是从导演个人出发的自传性精神表述或者是现实社会出发的状态与情绪表达,是一群抽象的意识流追求爱好者,因此他们并不追求电影叙事的完整性与合理性,甚至热爱挖掘不完整叙事的特殊魅力,碎片化与拼接性电影叙事的不确定效果也为电影增添更多意境效果,能放大意识表现的片段成为影片重点,以“意识流”为连接主线搭建导演所要描绘的精神世界,充分呈现出意识流之美。
电影《紫蝴蝶》中,以辛夏与伊丹英彦的爱情故事展开,但是影片中并未对这个爱情故事本身做铺垫与交代,只是在碎片化的镜头中呈现出两人非同寻常的关系。辛夏定定地望着在人群中走向自己的伊丹英彦,带着他走过熙攘的街道、穿过逼仄的弄堂小巷,走到辛夏的宿舍开始一场情事然后将他送走,全程只有一句“明天见”的简短道别,但是后续叙事中并未安排“明天见”,只有伊丹英彦乘坐火车离开,辛夏隔着火车候车室玻璃看的镜头。这种碎片化的叙事让两人的关系呈现出扑朔迷离的色彩,在视听呈现的渲染上更是将隐忍与压抑的意境氛围推至顶峰,观众也对俩人关系充满了疑惑期待。直至丁慧与伊丹英彦再次相遇后,在伊丹英彦的对白中才拼贴起两人相爱的故事,但两人的政治立场与信仰已经走向完全的对立,只留下了无尽的无奈和嘲讽。
日本人在我国东北引发的多出爆炸、尸骸遍野的运动镜头之后,准备出发见爱人对镜整理头发的司徒出场了,运用了淡出的镜头叠化,将严肃用宏达的历史背景与个人拼贴在了一起。收到电报的伊宁前往火车站接司徒,在登上公交车时,街上大量的群众在进行抗日示威游行,镜头一转是在漫长车程中转醒的伊宁的脸部特写,她发现天已经黑了,车外变成了枪林弹雨、炮火连天的战争场面,迎接爱人的小姑娘被迫与残酷战事拼贴在了一起。这一对乱世下的普通情侣被战火的阴霾笼罩着,他们无法抵抗也无处抵抗,终究要葬生在战火中成为时代的一粒沙,凄美的意境得以愈发鲜明。
导演娄烨热衷于捕捉在碎片化的镜头与叙事中传递出的不完整的魅力,一方面是留白能够带给观众更多的补充想象空间,引发观众的个人见解;另一方面是碎片化在连接的过程中,少了来自叙事合理性与结构完整性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毫无关联的人物、事件与场景等都能够连接起来并且以“意识流”为纽带紧紧地交织在一起,将战争带来的对个体生命的绝望、混乱意境有效搭建起来。
第六代电影在美学上进行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探索与实践,不是一味地歌颂或批判宏大的历史与社会现实,而是将视角放平到平民视角,聚焦个体命运关注平凡的人和事,以纪实性的视听手法传递真实力量背后的情绪感染力,并借助碎片化拼接的叙事来实现电影整体意象的构建,最终完成对时代的精神生活叙述。第六代导演们将在现实社会中所感受到的压抑、惶惑、迷茫、愤怒、期待的情绪全部灌注其中,但是由于更多是个体精神与情绪表达,缺少更为坚实的现实支撑,部分第六代电影仍旧局限在具体化还原现实生活的层面,缺少优秀第六代经典电影作品那般直击社会肌理的力量,这或许会成为第六代电影保持特殊风格并进一步发展的自我限制,需要进一步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