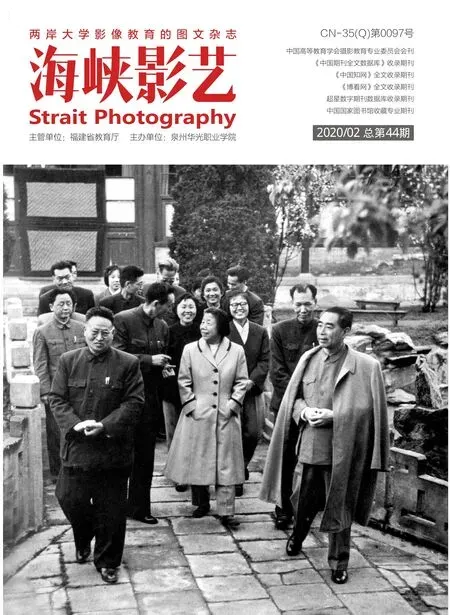图像“复制”理念:蒂娜·莫多蒂的革命影像
邓立峰
纯洁是你甜蜜的名字,纯洁是你脆弱的生命。
你用蜜蜂、阴影、火、雪、静默、火花,
你用钢、线和花粉建立你的坚强,
你的纤秀的结构。
——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
1942 年1 月,蒂娜·莫多蒂(Tina Modotti)在行驶于墨西哥城街头的出租车上突发心脏衰竭离世,走完了自己历尽波折的一生。她的朋友诗人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写下了这首诗歌《蒂娜·莫多蒂去世了》,来缅怀这位与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 几十年过去了,人们依然津津乐道于莫多蒂被革命信念点燃的充满激情的一生。莫多蒂出生于意大利的一个劳工家庭,随父亲移民到美国,之后又在革命后的墨西哥度过了八年令她“赢得身后名”的摄影时光,然后是流亡柏林、苏联、西班牙,最后她默默地回到墨西哥,在孤寂中离开人世。回顾莫多蒂历经坎坷的革命道路,她那短暂到仅有七年的摄影生涯无疑是她一生中最大的亮点,她留下了众多优秀的摄影作品,这些作品以独特的表现手法“复制”了莫多蒂的政治理念,让那些枯燥的思考和空洞的口号呈现出了形式上的美感。莫多蒂赋予了影像表现更多的可能性,也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它们。
革命与摄影:莫多蒂的两个印记
1896 年,蒂娜·莫多蒂出生于意大利北部城市乌迪内的一所小房子里。父亲在工厂工作,母亲偶尔做做裁缝活儿,家庭收入微薄。这样的出身,让莫多蒂从小就对社会的阶层分化有了深刻的印象。在她儿时的记忆里,5 月1 日劳动节这天,父亲会把小莫多蒂扛在肩头,走在游行队伍中,唱属于工人阶层的歌曲,听关于革命的演讲。莫多蒂仅仅在学校读了四年书就辍学了,为了补贴家用,她进入一家当地的丝绸厂工作,每天工作12 个小时。为了改变家庭的经济状况,1905 年,父亲独自一人到了美国,但他寄回家的钱不足以让远在意大利的亲人吃饱穿暖,莫多蒂的工作收入成了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很多人认为,莫多蒂的青少年时期生活决定了她未来激进的政治理念。
莫多蒂17 岁时,父亲在美国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他把家人接到了美国,莫多蒂踏上了旧金山的土地。美国的生活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刚到美国时,莫多蒂在一家店铺做裁缝,她的技艺是从母亲那里传下来的。但莫多蒂还有更大的理想,她想从事艺术方面的工作。这之后,因为长相姣好,莫多蒂主动向演员方向发展,她出演了几部并不出名的舞台剧和电影。
此时的莫多蒂有意参加各种艺术活动,这期间,她结识了一些贫穷的艺术家,慢慢进入了由激进的画家、摄影家和批评家们组成的艺术家圈子。就是在这个圈子里,她认识了著名的摄影家爱德华·韦斯顿(Edward Weston),莫多蒂的人生走向了新的方向。韦斯顿看中了莫多蒂的长相和身材,把他当成了自己人体摄影和肖像摄影的模特,莫多蒂进入了韦斯顿的工作室,也进入了摄影的世界。
1923 年,被墨西哥轰轰烈烈的文化复兴运动所吸引的莫多蒂,说服韦斯顿,两人一起来到了墨西哥城。在墨西哥,韦斯顿开办了摄影工作室,莫多蒂负责经营这家工作室。除了摄影事业,韦斯顿和莫多蒂还成为了当地前卫艺术家中的一员。在韦斯顿的资助下,莫多蒂每周都会组织一场“波西米亚式”的聚会,在她的家中,墨西哥的革命者和前卫艺术家们聚在一起,热烈地讨论革命和艺术观点,唱歌跳舞,有说有笑。正是在这种氛围中,莫多蒂的革命意识越来越强烈。
在那个火热的革命年代,莫多蒂也拿起了相机,将与革命和政治相关的影像拍入自己的镜头中。
在她刚到墨西哥时,受韦斯顿的影响,莫多蒂拍摄了大量的静物景观,这其中,既有韦斯顿擅长的各类植物,也有人像和建筑作品。但从1926 年开始,莫多蒂的镜头出现了转变。那一年,韦斯顿离开了墨西哥,回到美国,在当年给韦斯顿的信中,莫多蒂写道:“今天早上,我把几个行李箱翻腾了一遍,发现有很多老物件儿都破损了,想想挺伤心的,但‘失去也是种幸福吧’。从现在开始,我拥有的一切都将通过摄影来表达,剩下的,特别是我异常喜欢的、实在的东西,我将会让它们经历一场大变形——从实在的变为抽象的,这样,它们便会继续存在,存在于我的心中。”
回头再来读这段话,我们会发现,这成了莫多蒂“转型”的证言:从那时起,莫多蒂不仅开始用图像“复制”自己的政治理念,还以她独特的拍摄手法和题材选择,在理念表达和审美表现之间寻找到了有效的结合方式。
符号与形式:政治元素的秩序排列
在刚开始学习摄影时,莫多蒂深受韦斯顿的影响,她早期的静物拍摄大多带有韦斯顿作品的影子,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她的植物摄影。1925 年,莫多蒂用韦斯顿送给自己的玫瑰拍摄了一幅照片:四朵正在开放的玫瑰陈列在画面中,上边的两朵玫瑰已经开始绽放,它们如含羞的少女,慢慢张开自己隐秘的面容。在它们的左下方,则是一朵还未开放的小朵玫瑰,就像一个懵懂的孩子惺忪着双眼。而在画面的右下角,则是开得最盛的玫瑰,它已经完全打开了自己的花瓣,花瓣的边角甚至又了衰败的痕迹,跟其他三朵玫瑰相比,这朵最大的玫瑰更像是一位母亲,呵护着旁边幼小的孩子。
除了玫瑰,莫多蒂还拍摄过马蹄莲、百合、仙人掌、甘蔗等植物,在她的镜头中,马蹄莲和百合像是人体的器官,仙人掌像是女人高高竖起的发髻,而直挺的甘蔗则错落有致地挤满了镜头,除了它们投下的阴影,没有任何额外的细节。可以发现,此时的莫多蒂已经从韦斯顿那里学来了对形式感的把握和对象征性表达的运用。
当然,莫多蒂没有跟随韦斯顿的拍摄路径走下去,她的摄影越来越关注社会问题,在没有改变作品的形式化倾向的同时,莫多蒂开始尝试用镜头“复制”自己的政治理念。
1926 年,墨西哥城爆发了一场劳工游行,站在朋友家屋顶上的莫多蒂目睹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游行,莫多蒂拿出相机,拍摄了游行的场面。因为是俯角拍摄的缘故,在莫多蒂的照片中,最吸引人的元素是两种帽子:占据中间位置的是墨西哥农民常戴的阔边帽,而画面的左侧则是中产阶层男士常戴的绅士帽。在画面的上方,是一条条大幅标语,标语下方,“阔边帽”和“绅士帽”逐渐走到了一起,一同走向前方。
我们都知道,帽子向来是身份的象征,在过去,不同阶层的人会佩戴不同的帽子,而这些千差万别的帽子也会成为一种身份认知的符号。在1926 年之后,莫多蒂拍摄了很多墨西哥农民的照片,他们出现在镜头中,都是带着具有墨西哥民族特色的阔边帽。可以想见,莫多蒂已经认识到了作为符号的帽子的象征意义,所以在拍摄游行场景的过程中,她只是将能直接呈现革命理念的标语放在次要的位置,而把画面的主要部分留给了帽子。这在之后经过裁剪的版本《工人游行》(Workers’ Parade)体现地更为明确:画面中只剩下了帽子,标语被莫多蒂完全地裁掉了。
在视觉呈现过程中,相比于对拍摄对象的直接呈现,对于符号的突出显然是一种更为深层次的话语建构,它使基建于表达主题的象征结构更为稳固,也使观者的阐释更具张力。当然,在提取并表现符号的过程中,莫多蒂仍然没有忘记对形式的把握。在拍摄劳工游行的画面中,她以精妙的构图加强了画面的视觉纵深,旁边围观的市民被置于边角的位置,而行进中的队伍则好似源源不断地走入画面,基于这样的视觉感受,原本不算整齐的游行队伍也显现出一种秩序感。
莫多蒂对符号的运用和对形式感的把握还体现在对《弯刀报》(El Machete)的呈现上。《弯刀报》是1924 年3 月创刊的以农民和工人为发行对象的革命报纸,从创刊开始,莫多蒂就参与到《弯刀报》的活动之中,后来《弯刀报》成为了墨西哥共产党的机关报,莫多蒂的不少照片都刊登在这份报纸上。
莫多蒂也为阅读《弯刀报》的农民拍摄了照片。1927 年,她拍摄了一位墨西哥工人阅读《弯刀报》的照片,工人垂下的眼睛正在阅读报纸版面下半部分的内容,而《弯刀报》的报头的头条新闻出现在整个照片的下方。1928 年,莫多蒂又拍摄了一幅《农民阅读<弯刀报>》(Campesinos Reading El Machete)在这张照片中,带着阔边帽的墨西哥农民围在一张《弯刀报》周围,阳光洒在报纸上,而农民的脸则埋在帽子之下。这是两幅充分运用了象征符号的照片,帽子和《弯刀报》结合在一起,表现了革命的主体和革命的宣传者相互联结的场景,而《农民阅读<弯刀报>》特殊的构图方式,也使它被认为是最能体现莫多蒂形式主义美学的作品之一。
对形式主义的重视还体现于莫多蒂的四幅“摆拍”作品——《子弹、玉米、吉他》(Bandolier,Corn,Guitar)、《锤子和镰刀》(Hammer and Sickle)、《墨西哥草帽与锤子、镰刀》(Mexican Hat with Hammer and Sickle)、《子弹带、玉米、镰刀》(Bandolier,Corn,Sickle)。在这四幅照片中,代表着工人的锤子、吉他与代表着农民的帽子、玉米、镰刀以及代表着战士的子弹摆在一起,利用多种组合方式,它们被摆成了共产主义的标志性图案。这四幅照片是莫多蒂的政治影像中最容易被识别出其政治理念的照片,虽然这样的表达显得“赤裸裸”,莫多蒂依然赋予了这些政治元素以象征意义和形式化的美感。这4 张照片均拍摄于1927 年,在这一年,莫多蒂加入了墨西哥共产党。
形象与隐喻:革命观念的抽象表达
在以相机进行政治表达的过程中,莫多蒂参与了一场被称为强硬运动(Stridentism)的前卫艺术运动。
强硬运动开始于1921 年,墨西哥艺术家曼纽尔·梅普尔斯·阿斯(Manuel Maples Arce)宣言式的公告表明了这场激进艺术运动的诉求:强硬运动与时兴的未来主义和达达主义运动的主张相似,表达了对现代技术的赞誉,阿斯表示,由于广播、电报和飞机带来的信息的迅速传播,整个世界都会保持同步,旧的“中心-外围”式的框架已经不适用了。这是一个主张现代性和全球化的艺术宣言,它的参与者们尝试吸取现代主义的艺术语言,表现和赞颂现代科技。
融入墨西哥前卫艺术家圈子的莫多蒂自然也被强硬运动所吸引,从1924 年开始,她拍摄了一系列带有强硬运动特色的作品,1925 年拍摄的《电话线》(Telephone Wires)被认为是其中的代表作。照片中,密集排列的电线在天空中纵横交错,伸向远方,电话线被认为是文明进步的代表,可以将墨西哥广阔的地域联系起来。从这张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将彰显现代化的内容和隐喻的修辞语言进行融合的尝试。
这种尝试还出现在其他带有强硬运动特色的作品中。1928 年,莫多蒂拍摄了《梅拉的打字机》(Mella’s Typewriter),在这张照片中,莫多蒂的情人、古巴革命者朱利奥·安东尼奥·梅拉(Julio Antonio Mella)的打字机成为了画面的主体,光线打在打字机上,使它具有了强烈的金属质感,让人想起了工厂的机器。然而,这张照片却是一张关于革命隐喻的作品,作为激发隐喻机制“比喻词”的,是打字机上被敲打出的文字,这些文字是苏联革命家托洛茨基关于艺术与革命关系的论述片段。明了这些文字的意义,在观者眼中,打字机的形象会被重新定义,此时的它更像是武器,而不再只是代表现代科技的机器。
以《梅拉的打字机》为代表,引入相关元素来激发隐喻修辞是莫多蒂在图像中“复制”自己政治理念的主要方式之一。
因为天然地缺乏比喻词,视觉文本成为艺术隐喻修辞实践的“集大成者”,在影像中,由线条、色彩、光线、块面、构图等视觉元素乃至图像符号本身所呈现的相似性元素,都可能成为隐喻机制的发生动因。莫多蒂与其他摄影家一样,深谙隐喻的表意策略。莫多蒂与其他摄影家一样,深谙隐喻的表意策略。
如果说表现强硬运动的作品是一种基于与外在艺术思潮相互联系的隐喻机制,莫多蒂以木偶为表现对象的作品则表现了一种带有内部叙事性的隐喻方式。
1926 年,年轻的艺术家路易斯·布宁(Louis Bunin)从芝加哥来到墨西哥城,准备跟随墨西哥壁画大师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学习壁画。在墨西哥,布宁受到革命者们的感召,将自己擅长的木偶艺术改变为宣传的手段,用来教化不识字的农民和工人。他把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的戏剧作品《毛猿》(The Hairy Ape)搬上木偶剧的舞台,《毛猿》的主角是轮船上烧火炉的工人扬克,他因为被一位富家女人侮辱,而渐渐迷失自我,最后只能与动物园里大猩猩做朋友……
布宁的木偶剧本身就带有社会批判色彩,当莫多蒂把提线的布宁和被布宁手中的线所拉扯的“扬克”拍入镜头中,更体现了一种戏剧化的张力。手臂粗壮的布宁摆弄着手中的线,他垂下头直直地看着“扬克”,口中惬意地叼着一只烟斗,而木偶人“扬克”的身体则在空中摆动,它似在跳舞,又似乎已经变得畸形。在另一张照片中,布宁将“扬克”放在腿上,他一只手捏着木偶的脖子,另一只手让它摆出单膝跪地的姿势。
莫多蒂为布宁和他的木偶拍摄了一系列的照片,当然,谈到莫多蒂的这些照片,很多评论家都将它与资本主义对人的控制联系在一起。在现当代艺术的实践中,提线木偶已经成为重要的表现元素,比较典型的例子出现在影视剧创作中,人们很难忘记美国电影《芝加哥》(Chicago)里的场景,为了表现被明星律师所操纵的媒体,导演用到了提线木偶来表现操纵的过程。作为喻体出现的木偶,往往有着明确的隐喻本体——权力,不管这种权力是政治权力还是资本权力、信息权力,操纵的主题都可以在提线者与木偶的互动表现中得到彰显。
除了直接表现天然带有喻体基因的木偶,莫多蒂还拍摄了操纵提线木偶的双手,在莫多蒂的特写镜头中,手被线缠绕起来,仿佛那双善于操控的手也在密集的提线中没有了方寸。
肖像与纪实:自然主义赋予的力量
莫多蒂将政治理念嵌入艺术创作,不只体现在作品的表现元素与形式构建等方面,还体现在她的题材选择上。莫多蒂选择的拍摄对象,不只是与革命直接相关的元素和场景,她更多地将镜头伸向了墨西哥广阔土地,那里有被政治活动者视为革命主体的大众和能建构墨西哥民族认同的民风民俗。
在1926 年之后,纪实影像成为莫多蒂表现自己的政治旨趣的重要媒介。1926 年,莫多蒂和爱德华·韦斯顿受委托为学者安妮塔·布里诺(Anita Brenner)关于墨西哥文化与历史的作品《祭坛后的偶像》(Idols behind Altars)拍摄插图,他们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在墨西哥旅行,拍摄了数百张作品,布里诺最后选用了70 张照片。也是从1926 年开始,莫多蒂为《墨西哥民俗》(Mexican Folkways)杂志拍摄反映墨西哥民俗的照片,《墨西哥民俗》一共刊登了莫多蒂45 张照片。
无论是安静的城镇街道,还是喧闹的乡间市场,莫多蒂都把镜头对准了生活中的墨西哥人——这片土地上的普通人才是民风民俗最主要的承载体。她喜欢拍摄劳动中的人物,在她遗留下的作品中,有为数众多的肖像照片,在莫多蒂的镜头下,最常出现的是两种对象:戴帽子的男人和头上顶着陶罐或篮子的女人。
1927 年,莫多蒂在位于墨西哥东南部的韦拉克鲁斯拍摄了《三种穿披肩的方式》(Three Ways to Wear A Serape)和《戴阔边帽的墨西哥男孩》(Mexican Boy in Sombrero)。在《三种穿披肩的方式》中,三个披着披肩的男人站立在画面之中,他们戴着阔边帽,左边的男人把帽子抬高,露出了脸,中间的男人被帽檐的影子遮住了眼睛,只能看到他似乎是在笑的嘴巴,而右边的男人则完全被阔边帽和披肩遮住了脸。仅仅是这三张不同形态的脸就让人觉得趣味盎然。而更有名的作品是《戴阔边帽的墨西哥男孩》,在为《墨西哥民俗》拍摄照片的旅途中,她拍下了一个带着小型阔边帽的墨西哥男孩,莫多蒂以仰视的角度表现了男孩略带羞涩的表情和微微皱起的眉头。这是韦拉克鲁斯农民的孩子,他的脸已经晒成了古铜色,衣服的纽扣敞开着,在他稚嫩的面孔下,已经看到了些许沧桑的感觉,这种感觉,来源于莫多蒂对墨西哥农民特征的精准把握。除了戴帽子的男人,莫多蒂还拍摄了许多顶着陶罐或篮子的女人。
关于这两种对象的拍摄,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照片都呈现“上下结构”:头顶上的帽子或陶罐与头部及身体形成了一种一分为二的构图方式;除了构图特点,帽子或陶罐代表的静止的物体与位于其下的鲜活的面部表情也形成了一种对比关系。可见,对于纪实影像的拍摄,莫多蒂同样注重表现形式美感。
除此之外,在墨西哥民间采风的过程中,莫多蒂也拍摄过系列母亲与孩子的肖像,如《哺乳孩子》(Nursing Child)《喂孩子的女人》(Baby Nursing)《母亲与孩子》(Mother and Boby)《又一次》(Once Again)。过往涉及母子主题的摄影作品,往往会呈现“圣母化”或“圣子化”的倾向,为母子之间的关系带上超越血缘的神圣光环。但在莫多蒂的镜头下,母亲和孩子都是真实生活面貌中的形象,她用自然主义的视角呈现了墨西哥妇女哺育孩子的真实瞬间。在《喂孩子的女人》中,莫多蒂将母亲的乳房置于镜头的中心位置,这是她唯一出现在镜头中的身体部位,而襁褓中的女孩把嘴凑到乳头上安静地吸允,孩子深棕色的小手轻轻地放在母亲的乳房上,她的眼睛微微垂下,似乎正沉入睡眠之中,又似乎在享受这哺乳的瞬间。这是一幅经典的乡间生活景象。学者艾米丽·亨诺芙(Emily M.Hinnov)认为,是莫多蒂之前做演员和模特的经历,加强了她反映真实场景的意识,莫多蒂的照片以尽可能明晰的方式呈现了精确的生活经验。
需要注意的是,莫多蒂关于母子主题的照片,多是表现女人的身体局部——正在哺育的乳房或将孩子揽入怀中的手臂。在莫多蒂的镜头中,乳房是丰硕的,手臂是健壮的。出现在镜头中的身体局部除了可以更加鲜明地表现主题之外,还通过带有性别印记的身体特征而呈现了性别观照的意味——身体的主要部分消失在镜头之外,哺乳中的乳房或怀抱孩子的手臂因而成为一种单纯的性别符号,形成了区别于传统男性凝视女性肉体方式的特殊视角。
正如母子主题摄影体现的性别视角,莫多蒂在后来的摄影中,也越来越多地将镜头对准墨西哥土地上的女性。1929 年8 月,莫多蒂前往墨西哥东南部的特旺特佩克地峡(Tehuantepec)旅行,她带着相机,边走边拍,而在特旺特佩克地峡拍摄的照片也成为了莫多蒂最著名的一组作品。在这组照片中,女性成为镜头中的主角,正在写字的女童、提着篮子的女孩子、头顶陶罐的妇女都成为了莫多蒂表现的对象。而这些墨西哥女人的照片为后来对莫多蒂的女性主义视角分析提供了素材。“她们的活动既不是理想性的工作,也并不琐碎……莫多蒂展现了女性必须要去从事的劳动,虽然这些劳动不会被计算薪酬。”学者莎拉·M·洛恩(Sarah M.Lowe)认为,莫多蒂意识到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可以归为“无产阶级中的无产阶级”。
无论如何,这些纪实影像都是震撼人心的。作家、评论家阿尔维托·曼古埃尔(Alberto Manguel)写道:“莫多蒂用不着某些纪录片拍摄者的那种残酷来激起观看者的同情,或‘强化’某种道德立场。她的观察所见凭着不动声色的确切而使她的作品有说服力、有热情、有深长的意味。”正像曼古埃尔所说的,莫多蒂的纪实摄影从来不致力于突出贫困、压迫和抗争这些革命家们所宣扬的主题,她的镜头如一首缓缓的乡村歌谣,唱尽了墨西哥乡间的风土人情。也正是由于这种充满自然主义色彩的记录,莫多蒂的纪实影像有了一种“未加修饰的”力量,当照片出现在观看者面前,这种力量从她个人的视角转移到了被拍摄对象的身上。
结语
正是通过对政治符号形式感十足地运用、对革命理念的隐喻性表现和对墨西哥民间生活的纪实拍摄,莫多蒂成功地将自己的政治理念“复制”到影像之中,为政治表达寻到了一个艺术化的出口,使这些作品不会因为时代的更迭而失去价值。
不过,在1930 年因为政治原因离开墨西哥之后,莫多蒂仅仅拍摄了少量的照片,再也没有进行系统的创作。她先是到了德国,然后成为苏联政府的贵宾,她倾尽全力为共产国际下属的援助组织工作,西班牙内战前夕,莫多蒂与丈夫、共产国际的官员维托里奥·维达里(Vittorio Vidali)一同来到西班牙,为反抗法西斯的事业工作。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不久,她以化名回到了墨西哥,直到去世。
蒂娜·莫多蒂没有再拿起相机,在流亡到莫斯科的时候,她给聂鲁达写信,告诉他自己已经把相机扔进了莫斯科河冰冷的河水中。无论将相机扔进河水中的故事是真是假,这都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声明,莫多蒂以这种姿态拒绝了苏联提出的拍摄毫无美感的宣传照片的要求,也以这样决绝的态度告诉世界,自己要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革命事业之中。
注释
① [智]聂鲁达:《聂鲁达诗选》,陈实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82 页。
② Margaret Hooks,“Tina Modotti”, Könemann,1999,P5.
③ [美]赫雷拉:《弗里达》,夏雨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 年,第115 页。
④ Sarah M. Lowe,“The immutable still lifes of Tina Modotti”, History of Photography,Issue 3(1994).
⑤ 邓立峰:《蒂娜·莫多蒂和她短暂的摄影生涯》,《中国摄影报》2020 年1 月17 日。
⑥ Margaret Hooks,“Tina Modotti”, Phaidon Press,2002,P90.
⑦ Tatiana Flores,“Starting from Mexico: Estridentismo as an Avant-Garde Model”, World Art,No. 1(2014).
⑧ Tatiana Flores,“Strategic Modernists: Women Artists in Post-Revolutionary Mexico”,Woman's Art Journal,No. 2(2008).
⑨ 鹿咏:《现代图像叙事的隐喻机制及其话语生产》,《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10 期。
⑩ Emily M.Hinnov,“The Maternal Utopia in Tina Modotti's Modernist Madonna and Child”, Women's Studies: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No.3(2011).
⑪ Sarah M.Lowe,“The Immutable Still Lifes of Tina Modotti”, History of Photography,issue 3(1994).
⑫[加]阿尔维托·曼古埃尔:《意象地图》,薛绚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101 页。
⑬[智]维吉尼亚·维达尔:《聂鲁达传:闪烁的记忆》,崔子琳译,译林出版社,2017 年,第11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