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送人身保险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曾廷雪 西南财经大学保险学院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国银保监会多次下发文件要求银行业和保险业支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各家保险公司纷纷出力,积极捐赠物资,扩展现有保险合同责任,同时也向一线医护人员定向捐赠保险。截至2020年2月24日,保险行业已经累计捐赠保额11.58万亿元的保险保障(数据来源: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gwylflkjz28/index.htm)。赠送保险的规模可以说相当庞大,有关赠送保险的相关法律问题也值得探究。
本文仅研究赠送人身保险的相关法律问题。
一、赠送人身保险的法律现状
(一)赠送人身保险的相关定义
根据2015年修订的《保险法》,人身保险是指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等条件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
根据原中国保监会《关于规范人身保险公司赠送保险有关行为的通知》,赠送保险是指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免除投保人支付保险费的义务,或者代替投保人履行支付保险费的义务。
本文将赠送人身保险分为狭义的赠送人身保险和广义的赠送人身保险。狭义的赠送人身保险,是指保险公司赠送人身保险的行为,此时保险公司并不能得到保费收入,该部分新增风险的保费由保险公司自己承担。广义的赠送人身保险,是指除狭义的赠送人身保险外,还包括除保险公司以外的第三方赠送人身保险的行为,此时保险公司能够得到保费收入,保费由做出赠送行为的第三方承担,被保险人依旧不承担缴纳保费的义务。
(二)有关赠送人身保险的法律法规
目前我国《保险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中并没有关于赠送保险的相关法条。
2005年11月1日,原保监会下发《关于规范寿险公司赠送保险有关行为的通知》。这是我国第一次对赠送保险这一行为做出规范。
2008年5月21日,原保监会发布《关于促进寿险公司电话营销业务规范发展的通知》,其中“加强售后服务管理”部分提到,“对通过电话方式赠送的保险以及销售的短期意外险产品,可按一定比例回访”。
2015年1月23日,原保监会印发《关于规范人身保险公司赠送保险有关行为的通知》。这是我国第一次清晰定义赠送保险这一行为。该文件第二条规定:“人身保险公司赠送的人身保险产品仅限于意外伤害保险和健康保险,且保险期间不能超过1年。对每人每次赠送保险的纯风险保费不能超过100元,以公益事业为目的的赠送保险不受此金额限制。”
2015年7月22日,原保监会下发《关于印发〈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暂行办法〉的通知》。《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暂行办法》第十四条提到,“保险机构及第三方网络平台以赠送保险、或与保险直接相关物品和服务的形式开展促销活动的,应符合中国保监会有关规定”。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我国对于赠送人身保险行为的法律法规还很不完善,仅有的关于规范赠送人身保险行为的文件效力有限,这也使得实际业务中赠送人身保险行为的法律参照较少。
二、赠送人身保险存在的主要法律问题及案例
(一)文献综述
一些文献从赠送保险是否符合保险原理的角度出发来探讨。吴兆如、易文祯(2011),李玉泉(2020)认为,赠送保险存在的争议主要在于其不符合等价有偿和互助性的保险原理,被赠与人未缴纳保费而享受保险保障,保险公司不收取保费而承担保险责任,侵害了其他被保险人的权利,威胁了保险基金的稳定。吴兆如、易文祯认为,赠送保险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广告宣传的目的,本身是一种保险资金运用的方式,不会损害保险公司的赔付能力。李玉泉则提出,保险公司应当从其他渠道筹集资金,以此作为赠送保险的保费来源。

一些文献对于赠送保险这一行为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赠送保险对于保险公司是否利大于弊。李思瑶(2012)从实务出发,认为保险公司赠送保险行为不规范,如隐蔽增加收费的附加条款、保单未发放到位等,因此弊大于利。卫新江(2020)从公司角度出发,认为赠送保险应当按照法人治理的要求,履行一定的董事会审批程序,但赠送保险行为本身会损害公司股东、现有被保险人和股东的利益,对纯新客户的保险赠送还涉嫌输送利益、不正当竞争等问题。
一些文献探究赠送保险行为相关的法律问题。张坤(2020)提出,公益赠送保险行为需要与《保险法》相衔接,公益赠送保险本身具有无偿性、公益性和社会性,与一般的保险合同不同,因此可通过立法,在公益赠送保险时适当免除保险公司的说明义务、扩大保险利益范围、采取被保险人未明确反对即同意等措施。
还有一些文献主要研究赠送人身保险行为的实务操作问题。梁鹏(2020)探讨了谁更适合作为投保人的问题。他认为,保险公司在向一线医护人员赠送保险时,可直接以保险公司作为投保人。保险利益原则的出发点是为了防范道德风险,当投保人为保险公司时,并没有产生道德风险的动机,因此保险利益原则不应限制保险公司作为投保人。
总的来说,赠送保险行为与一般的商业保险不同,不符合互助性和等价有偿性的保险原理。但并不是说赠送保险不应当存在,而是应当从保险原理、立法、产品设计、实务操作等多方面统筹推进,协调赠送保险与一般商业保险的关系,从而释放政策红利,促进保险市场健康发展。本文主要从赠送人身保险存在的保险利益不清问题入手,结合林建智教授提倡的“三位一体”理论,提出相关的立法建议(编者注:林建智教授为我国台湾地区知名保险法学者,提出“三位一体”的概念,即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三者一体。他认为,谁拥有利益,谁就是契约当事人)。
(二)赠送人身保险存在的主要法律问题
1.效力有限且覆盖范围小
通过对有关赠送人身保险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总结,可以发现涉及赠送人身保险的法律法规仅为原保监会下发的一个规范性文件,且仅涉及寿险公司赠送保险的行为。立法层次低、监管范围小这两点问题十分突出。
2.投保人不明,保险利益不清
根据我国《保险法》第三十一条可以看出,我国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主要采取利益主义与同意主义相结合的原则。人身保险合同得以成立生效的前提是投保人在投保时对被保险人拥有保险利益。
在赠送人身保险行为中,由谁作为投保人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明确,常见的操作一般是以缴费的人作为投保人,或者直接由保险公司作为投保人。投保人不明造成了保险利益是否存在也难以确定,由此引发保险合同是否成立生效的问题。
3.告知义务、说明义务难以履行
根据《保险法》第十六条,投保人应当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如实告知关于保险标的或被保险人的相关情况。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保险人负有向投保人说明合同内容的责任,尤其涉及免责条款时,保险人未明确说明的,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
保险公司在赠送人身保险时,一般针对不特定人群。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保险公司一般利用互联网进行人身保险赠送,以此达到广告宣传的目的。在这种时候,投保人不确定,因此履行告知义务的主体不确定,保险公司履行说明义务的对象不确定。
(三)案例分析
本节案例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根据温某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市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的相关民事判决书,温某参加了邯郸市红十字会组织的2016年“博爱一日捐”活动,并捐款50元,获得了该红十字会赠送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在保险期间内,温某发生保险事故致残,要求保险公司赔偿。保险公司认定以合同依据的残疾标准为准,温某未达到残疾,因此拒绝赔偿。经法院认定,保险公司采取的标准比国家标准更为严格,属于免责条款,而保险公司未向温某明确说明,因此该条款无效,保险公司应当赔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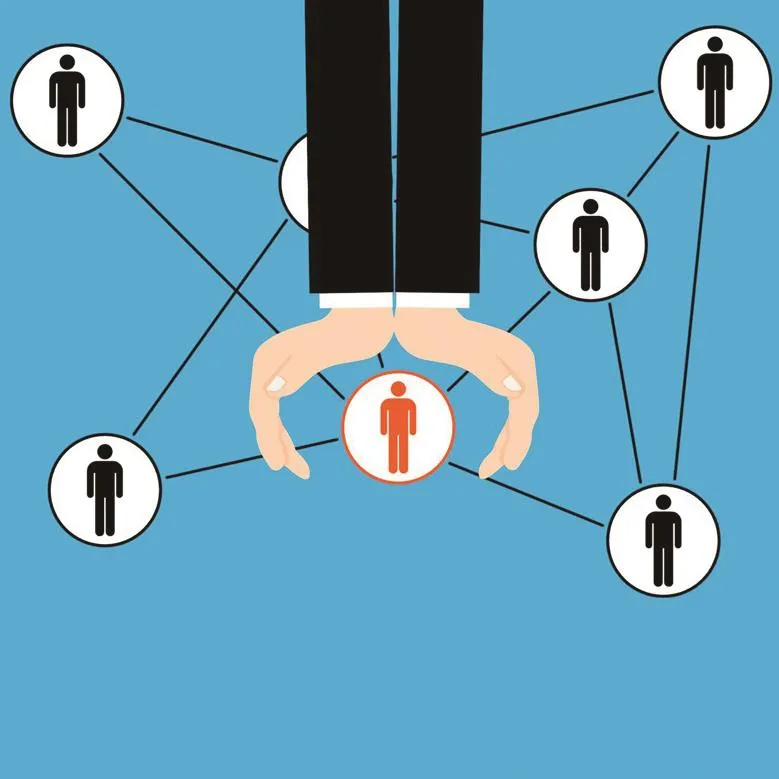
保险公司主张,邯郸市红十字会为投保人,自己与邯郸市红十字会签订的协议中明确载明该项条款,因此已经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而法院根据保险合同中载明的内容认定该保险的投保人为温某,因此保险公司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免责条款无效,保险公司需要赔偿。
这个案例反映了目前赠送人身保险中投保人不清晰的问题,而投保人的确定关系到保险利益是否存在、说明义务和告知义务的履行等,因此,应当在今后的立法中明确赠送保险的投保人的确定问题,以减少法律纠纷,促进保险市场发展。
三、赠送人身保险相关法律问题的解决思路
(一)提高立法层次,扩大监管范围
赠送保险的规模日益增大,尤其是受本次新冠疫情的影响,赠送人身保险规模更是急剧增加。我国应当在实践中吸取赠送人身保险的相关经验和教训,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赠送人身保险的法律依据,并逐渐扩大监管范围。一方面扩大监管人身保险赠送主体的范围,将财产保险公司以及其他非保险公司的第三方赠送保险的行为也纳入其中;另一方面还应扩大监管赠送保险种类的范围,将责任保险、车险等财产保险也纳入其中。
(二)明文规定以被保险人作为投保人
以被保险人作为投保人,可同时解决保险利益不清、告知义务和说明义务难以履行的问题。
首先,以被保险人作为投保人解决了保险利益不清的问题。因为被保险人对于自身拥有保险利益是毋庸置疑的,这就规避了同意主义的风险。
其次,以被保险人作为投保人解决了告知义务承担主体不明的问题。《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如实告知义务是由投保人承担的,这里隐含的假设是投保人对于被保险人的职业、身体状况等条件十分了解,因此才能充分体现最大诚信原则。在赠送人身保险中,显然各个主体都不如被保险人更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和风险,由被保险人作为投保人能够更好地履行如实告知义务。
再则,以被保险人作为投保人解决了说明义务履行不到位的问题。根据《保险法》,保险公司向投保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投保人会据此判断是否继续投保。然而实际受到保险保障的主体依然为被保险人,被保险人对保险是否满意更为重要,这一点在赠送人身保险中显得更为突出。在赠送人身保险中,保险公司履行说明义务的对象应当是被保险人,被保险人比其他主体更需了解保险合同的内容。以被保险人作为投保人,明确了投保人,履行说明义务的对象也就明确了;同时,能够使被保险人更加了解该保险内容,被保险人也能够更好地利用保险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其实,一般的商业人身保险合同中,也应该使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相统一。当缴费主体与被保险人不一致时,可将该份保险认作是缴费主体赠送给被保险人的保险,属于上文中提到的广义的赠送人身保险行为。由被保险人担任投保人,履行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应当履行的义务,这也与林建智教授提倡的“三位一体”理论相适应。
——与林刚先生商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