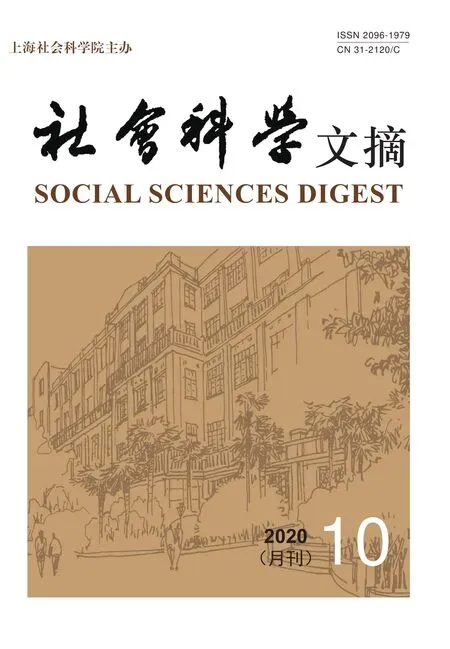中国伙伴国在联合国选边站还是左右逢源?
文/漆海霞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竞争日益加剧,中美贸易战有愈演愈烈之势。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会在中美之间选择一边,还是同时与两国保持密切关系?如果是前者,则中美关系的紧张可能扩大为两个阵营间的对立;如果是后者,在中美竞争态势日益明显的情势下,这些国家左右逢源的空间是否会受到挤压?在这些国家中,本文重点关注中国的伙伴国,尤其是那些与中国的伙伴关系得到升级的国家。本文所指的伙伴关系升级,是指按照建立伙伴关系文件与升级伙伴关系文件声明中关于政治合作程度描述话语的变化,双边伙伴关系在原有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得到提升的情况。在中国保持不结盟政策的传统下,中国与各国伙伴关系的创建和升级受到普遍关注。在中美权力转移进程中,中国伙伴国的选择可能对中国的国际地位具有深远影响。这是本文的研究缘起。
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与假设
本文研究的问题是,在中美竞争关系日趋紧张的局势下,其他国家如何选择?在开展研究时,我们必须明确研究对象。本文选择中国的伙伴国作为研究重点,这既是因为在中国的不结盟政策下伙伴国身份具有特殊的意义,也是因为中国的伙伴国涉及范围广泛,不仅包括亚、非、拉各洲的发展中国家,也包括欧洲的发达国家,同时需要强调的是,英、法、德等国既是中国的伙伴国,也是美国的盟国,这种双重身份下的立场选择更值得探究。
对于中国的伙伴国,基于数据的公开性和可比较性,本文重点考察其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由此,本文的具体研究问题可以细化为:在中美之间,中国伙伴国的联合国大会投票有何立场特征?我们认为,身份立场对于各国的联大投票有明显影响,所处阵营、政治体制和本国实力等都可能导致国家有不同的身份或者投票倾向;大国也会采取措施影响各国投票,例如,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对投票立场的一致性有较高影响,同时,对外援助也是大国发挥影响的重要手段。对于本文的研究问题即中国的伙伴国在联大投票中的选择,上述两方面因素均产生影响。
首先,从身份立场上看,中国的伙伴国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身份。自从1996年中俄伙伴关系升级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来,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受到了学界的普遍关注。伙伴关系可以区分为一般性伙伴关系与战略性伙伴关系,其中战略伙伴国与中国关系更为密切。学者们认为,尽管战略伙伴关系不是传统的同盟,但他们承认这是一种特殊关系,战略伙伴国的身份将使得其对外政策选择与非战略伙伴国不同。而且中国的伙伴国也存在多重身份,有些国家既是中国的伙伴国,也是美国的盟友。此外,是否实行民主、经济水平发达与否等不同类型的国家也在中国的伙伴国中各占比例。因此,我们需要研究在诸多身份中,哪些因素会对它们在联大投票上的选择产生影响。
其次,从大国影响看,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都与中国的伙伴国存在千丝万缕的经济依赖,既往关于贸易与结盟关系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分析结盟对贸易水平增加的影响。因为同盟是安全承诺,显然有助于改善双边贸易。然而,国家间贸易水平的上升也有助于政治关系的维护和改善。随着贸易量的增加,两国国内的不同利益团体均获得收益,且经济繁荣有助于两国政府维护统治地位,甚至可能促进两国结盟。另外,由于经贸上高度依赖的国家间发生冲突的损失比其他国家更高,因此,这一机会成本也遏制了贸易往来较多的国家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随着中国与伙伴国的贸易额迅速增加,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程度也明显上升,我们可以预期,各伙伴国在国际组织中对中国的政治支持力度将有所上升。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如果中国与某国的伙伴关系实现升级,该国在联大投票中与中国的立场将会趋近;
假设2:如果中国与某国的伙伴关系实现升级,该国在联大投票中与美国的立场将会拉大差异。
本文重点关注中国的伙伴关系问题,因此上述两个假设都探究伙伴关系升级的效果。假设1可以用身份和经济依赖等理论加以解释,而假设2则考虑中美竞争的大背景。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等议题的白热化,国际组织中两国的影响力也会出现消长趋势。因此,我们还需考虑美国的拉拢措施对中国伙伴国在联合国支持中国程度的可能影响。
(二)样本选择与变量
本文的数据样本包括20个国家自1993年至2014年期间的数据。它们都是与中国升级了伙伴关系的国家,包括俄罗斯、韩国、法国、英国、南非、巴基斯坦、尼泊尔、柬埔寨、德国、土耳其、波兰、哈萨克斯坦、蒙古、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西、智利、斯里兰卡、秘鲁和印度尼西亚。本文之所以选择1993年为起点,是因为这一年是中国首次与他国建立伙伴关系,选择2014年为终点,是因为部分变量的数据截至该年。
本文所用的核心因变量是各国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数据来源是联合国大会投票相似性指数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了自1946年以来联合国各成员国关于每一议题的投票信息。本文所采用的具体指标有两个,一为各伙伴国与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投票差异,二为各伙伴国与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投票差异。投票差异是指该国与某国在联合国大会投票差值的绝对值。
为了检验假设,本文共有两类自变量,第一类是伙伴国与中国关系的变量,第二类是伙伴国与美国关系的变量。首先,关于伙伴国与中国关系好坏的变量,本文从两个角度加以衡量:一方面是该国何时与中国升级伙伴关系,如果实现伙伴关系升级,意味着双边关系受到两国的重视;另一方面是伙伴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程度,本文主要采用贸易量为衡量指标,包括伙伴国从中国的进口额、伙伴国对中国的出口额、伙伴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占该国总贸易额的比重,这些指标也常被用于衡量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其次,关于中国伙伴国与美国的关系,本文也从两个角度加以衡量。一方面是政治领域,此处有两个指标:中国伙伴国是否为美国盟友以及美国是否宣布“重返亚太”战略,如果中国伙伴国为美国盟友,则显示两国政治关系密切,这会影响该伙伴国的政治立场;美国是否宣布“重返亚太”战略这一指标可以衡量中美关系的紧张程度,该战略会挤压中国伙伴国的选择空间。另一方面是经济领域,本文将中国伙伴国与美国的贸易视为衡量两国经济依赖程度的指标,数据来源为COW数据库。
除了以上自变量之外,本文还将各伙伴国自身的因素,如政治体制、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军费开支等作为控制变量。
统计结论与检验
(一)伙伴关系升级与投票差异的数据模型分析结论
笔者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上述变量进行分析后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本文的核心自变量——伙伴关系是否升级——对各伙伴国与中国或美国的投票差异具有显著影响。这符合我们的假设,即若中国与各伙伴国的关系更进一步,实现升级,则体现在联大投票上的结果就是中国与各伙伴国的投票一致性增高,差异度降低;若中国与各伙伴国关系实现升级,对这些伙伴国与美国的联大投票差异也有影响,其结果是差异性增加。
第二,各伙伴国与中美联大投票立场的差异存在内在张力。数据表明,如果各国与美国在联大的投票差异较大,则与中国的投票差异较小,反之亦然。可见,随着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各国很难在其中左右逢源,与中美两国之间一方的立场接近可能会拉大与另一方的投票距离。
第三,从各国政治立场的影响看,对于中国的伙伴国,如果它们同时为美国盟友,则与中国的投票差异较之那些并非美国盟友的伙伴国略大,同时,其与美国的联大投票差异比非美国盟友的伙伴国差异更大。对于中国的伙伴国,意识形态因素即该国是否为民主国家不影响该国与中国的联大投票近似度;若中国的伙伴国为民主国家,相比于非民主国家,其与美国在联大上的投票立场更接近。
第四,从各国的自身特性来看,“军费”既体现各国军事实力,也体现出各国的威胁感,军事实力强或者威胁感强的国家存在与中国的联大投票差异较大的可能性,对于军事实力较强或者威胁感较大的中国伙伴国,其与美国在联大的投票差异较小;富裕的中国伙伴国可能在联大与中国投票立场更为接近,比较富裕的中国伙伴国与美国在联大的投票差异比贫穷的中国伙伴国与美国的差异更大。可以认为,发达国家的身份不一定导致这些国家在联大事务上立场与美国一致,反而可能由于其经济比较富庶,对美国的经济依赖程度低,可以更自由地在联大表达不同于美国的立场。
第五,从有关经济相互依赖的指标看,一方面,从伙伴国与中国联大投票立场距离看,如果对中国的出口占该伙伴国的贸易总额比较高,则意味着中国对该伙伴国在贸易问题上比较重要,与此相应,该国在联大的立场愈加接近中国。对美国贸易依赖度高的国家,其在联大的投票与中国的立场比较接近,这符合对冲的判断。另一方面,从伙伴国与美国联大投票立场距离看,如果中国的伙伴国对中国出口较多,其与美国在联大投票的立场比较接近,而如果中国伙伴国对美国出口较多,则其与美国在联大投票的立场比较疏远。可以认为,中国伙伴国在经贸领域选择的是对冲战略,即不受双边经贸相互依赖的影响,同时与中国、美国保持投票立场距离。
(二)稳健性检验
基于以上判断,尽管我们不能说当前联大投票出现了类似于冷战时期两大投票集团分立的现象,但是投票差异和离心现象确实存在,与中国立场更靠近的国家与美国的立场距离较远。然而,以上结论是否可靠,还需对数据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在静态面板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因变量的滞后项,采用动态面板估计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回归结果印证了本文的核心假设,即若伙伴国与中国实现关系升级,体现在联大投票上是该伙伴国与中国的投票差异降低,伙伴关系升级的影响可能会被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和美国盟友身份抵消;当伙伴国与中国关系实现升级,该国在联大投票中与美国的投票差异会拉大,同时,伙伴升级的影响会被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所抵消。
(三)对俄罗斯、英国联大投票立场的分析
为了使论证更加直观,笔者将对俄罗斯和英国的联大投票略加分析。在图1和图2中,笔者描绘了1993年至2014年俄罗斯和英国分别与美国和中国的投票差异,其中,折线表示的是该国与美国投票差异减去该国与中国投票差异的差值。

图1 1993—2014年俄罗斯联大投票与中美的差异

图2 1993—2014年英国联大投票与中美的差异
我们可以看出,根据图1,俄罗斯联大投票立场的转折点在1996年;而在图2中,英国联大投票立场的转折点是在1998年。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转折点都和该国与中国的伙伴关系的建立与升级有关。1994年,中俄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升级为“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8年,中英正式宣布建立全面伙伴关系;2004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我们也可以从具体案例中看到“是否为美国盟友”这一身份以及“美国是否宣布重返亚太”这两个因素的影响。首先,从身份上看,俄罗斯不是美国的盟友,与中国关系密切,而英国与美国长期保持密切的同盟关系,这体现为上述两个图形上的整体趋势差异。英国既是美国的盟友又是中国的伙伴国,双重身份使其在拉近与中国投票差异的同时,更不会疏远与美国的关系。其次,“美国是否宣布重返亚太策略”这一因素对俄、英两国在联大与中美投票距离之差有明显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在图1中,自2009年起,俄罗斯与中美投票距离之差呈下降趋势,这正好是美国宣布“重返亚太”战略前后;在图2中,2009年前,英国与中美在联大投票的差异大体呈缓慢上升趋势,而之后则为明显下降趋势。可见,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使各国在中美之间的选择更为谨慎,避免选边。
尽管在安理会投票中英国的立场没有明显转变,但是2015年英国向中国申请加入亚投行,是首个采取如此行为的主要西方国家。这一举措显然背离美国的期待。可见,英国并不想完全站在美国一边制衡中国,而中国与英国的伙伴关系升级和日益密切的经贸往来有助于避免英国对中国的疏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会在中美之间更亲近中国。英国的选择是针对不同议题、在不同领域采取不同立场的灵活对冲策略:在经贸领域(如亚投行问题),未必完全与美国一致;而在网络安全等领域,则与美国立场更为趋近。
结语
本文对于中美竞争态势下中国各伙伴国的立场进行了分析,上述发现有助于我们对当前形势进行客观判断,在美国“重返亚太”、挑起贸易摩擦等一系列举措的压力下,中美难以回到21世纪早期共同反恐的合作阶段。未来美国对中国的施压仍存在加剧可能,因此,若能在国际场合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将有助于缓解中国面临的来自美国的压力。根据本文的研究,采用提升外交关系等政治手段是可行的方案选项。当然,各国基于其身份、利益的考量,目前多数国家在中美之间更可能会采取对冲策略或者中间路线,没有明确选边站的迹象。因此,中国在和平崛起过程需要多加谋划,化敌为友,降低各国与美国联合对付中国的可能性。
囿于数据所限,在最近时间段的数据无法获得的情况下,本文无法分析最近几年各国的行为特征,包括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等因素对各国外交权衡的影响。但是笔者认为,本文的核心结论对于近期中国面临的外交局面具有解释力度。当然,如果美国对中国施压加剧、竞争关系升级,其他各国面临的选择空间将受到压缩,可能不得不选边站,这也是未来存在的可能性之一。诚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只要中国的外交举措得当,各国的支持将会有助于中国化解压力、和平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