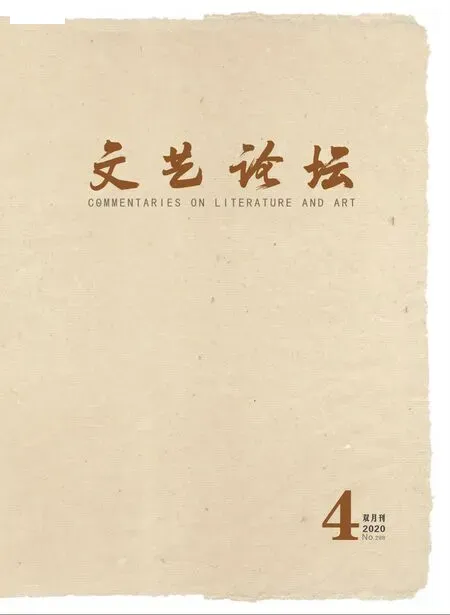论当代海洋诗歌中的海洋意象
芦海英 赵晓琳
纵观中国诗歌史,海洋意象的数量不多,但源远流长。最早可上溯到先秦,从《大雅·江汉》中“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到《老子》中“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再到《沧海赋》中“美百川之独宗,壮沧海之威神”……有关海洋的次生印象愈来愈立体丰满,距离上也由“远望”达到“近观”。到当代,“也许不是一个诗歌繁荣的年代,但是诗歌仍在生长”。“神秘而遥远的海/汹涌而壮阔的海/诱惑我们永远地打开向海的窗户” (《航海去》),鼓舞我们走向“海”的诗歌海洋,迎接新一轮浪的洗礼。
一
跟以往诗歌相比,当代海洋诗歌中的海洋意象在海洋审美意境营造上越来越多姿多彩、饱满丰富。而注入了诗人灵魂的海洋意象在失去了其纯自然的属性之后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具有丰富且独特的审美价值和审美意义。
(一)海洋意象的虚写和实写
狄德罗说:“美在关系。”诗歌的艺术魅力就在于活泛地利用意象的虚实关系,达到“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境界。由此可知,一方面,诗人构造海洋意象时所凭借的海洋物象可以是实指,即“诗人对描写对象如实描摹,或直接正面地加以叙述,它以具体详尽的‘明写’的形式出现”。“一早我向大海辞行,大海在雾罩里还没有醒,踏着沙沙作响的沙滩,‘再见,大海’,我回头向大海投一个青眼”(《再见,大海》),脚踩沙滩,眼望大海,此时的海真实地展现在眼前。这是臧克家临行前对大海的告别,没有轰轰烈烈的难舍难分,也没有匆匆离别的遗憾不甘,一个轻轻的“回头”,一瞥淡淡的“青眼”,足以让人看到臧克家对大海的喜爱以及自身的洒脱。
另一方面,构造海洋意象时所凭借的海洋物象也可以是虚指,即描述的是心中的海洋物象,用暗示联想等手法巧妙地把所要表现的客观事物表现出来。戈麦认为幻想是诗歌的灵魂,它能突破思想与存在的界限,使不可能变成可能。在戈麦的《大海》里,现实生活中他“没有阅读过大海的书稿”,“没有遇见大海的时辰”,他没有见过大海,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在梦里”他“翻看着海洋各朝代晦暗的笔记”,“海水的星星掩着面孔从睡梦中飞过”,诗人猛然拉近了他与海洋的物理距离,调动自己的幻想与想象将自己精神维度中的大海呈现出来,渲染了一个玄妙的氛围。当然,还有一种虚写情况是指代性象征。“有过咒骂,有过悲伤/有过赞美,有过荣光/ 大海——变幻的生活/ 生活——汹涌的海洋”(《致大海》)。从古至今,大海以其壮美神秘的外貌吸引了无数人前去探索,但即使是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依然无法对大海“一探究竟”,大海也因此成为“理想”的代名词。可纵然人们如此迷恋着大海的神韵,还是有无数承载理想的风帆被无情的浪涛淹没,那是现实带来的“失落”,海洋即生活。
(二)海洋意象的修辞艺术
海洋意象作为海洋诗歌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理解诗人主观情感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也注定了它在修辞艺术上的丰富性。大体可归纳为三类:
第一是寄托式象征,诗歌中的海洋意象主要承载了诗人的主观情感及内心感受并被直接反映在海洋物象里。比如舒婷的诗作《双桅船》,“岸啊,心爱的岸/昨天刚刚和你告别/今天你又在这里……不怕天涯海角/岂在朝朝暮暮/你在我的航程里/我在你的视线里”,诗人用双桅船象征自己,海岸象征恋人,描述了双桅船与海岸的“死生契阔”,借以寄托自己与恋人的生死之约。双桅船,一辈子在海上漂泊摇荡,渴望着被拥入岸的怀抱。在这场生命的流浪中,大海被定义为一段遥远至极的地理距离,相遇的途中有千般艰难万般险阻,但“双桅船”与“岸”爱的誓言终将得到履行。片刻的相聚,漫长的分离,痛苦的离去,甜蜜的憧憬,这就是人生。人生无常,祸福难料,生活中的种种不可控因素如同浪涛裹挟着我们四处横冲直撞,逼迫着我们不断地聚散离合。但是,欢聚时的相依相爱、别离时的忠贞守节都再次印证了彼此的约定:崇高的爱情,不只有朝朝暮暮的相守,更有跨过千山万水的心灵相依。再如郑愁予那一把“被离别磨亮/被用于寂寞,被用于欢乐/被用于航向一切逆风的桅蓬与绳索”的“古老的水手刀”(《水手刀》)。水手刀是水手随身携带的必备工具,在每一个的悲、欢、离、合的时刻都有它相伴左右,诗人以“水手刀”为载体来寄托水手的内心感受无疑是再合适不过。水手刀一次又一次地挥动,斩去一缕又一缕的情思,多次离别磨亮了刀锋,也磨硬了水手的心。水手渐渐习惯将“寂寞”,“欢乐”都藏在内心,只留下表面平静无波的镇定,以一颗坚强的心来面对漂泊中的各种未知。
第二是比喻式象征,诗人运用比喻的手法将不同的内涵赋予海洋意象,这种艺术手法“以‘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点’为纽带,使不同的意象物境之间实现挪移流通”。例如郑愁予的《如雾起时》,诗人把日日相对的海洋和时时思念的女孩联系起来,以海为喻来叙写爱情。“我从海上来,你有海上的珍奇太多了……/迎人的编贝,嗔人的晚云/ 和使我不敢轻易近航的珊瑚的礁区”,诗中“迎人的编贝”比喻女孩儿整齐的皓齿,“嗔人的晚云”比喻女孩儿娇羞的红晕,这“海上的珍奇”活脱脱描写的就是一个天真烂漫、纯洁可爱的女孩子。“珊瑚的礁区”暗喻女孩儿的娇躯,一句“我不敢轻易近航”写出了年轻人情窦初开之时,面对心爱之人小心翼翼既想亲近又怕且怯的矛盾心理。大海烟波浩渺而又富于变幻,它因其朦胧未知而充满魅力,恰如一位神秘绚丽的女郎,激发起诗人无边的想象和无尽的思念,而《如雾起时》正是捕捉到了这种似幻非幻,亦梦亦真的瞬间。类似的还有绿原的《航海》,“人活着/像航海/你的恨,你的风暴/你的爱,你的云彩”。海上的风景变化多端,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浪涛滚滚,“恨”似愤,怒发冲冠,心情就如“风暴”一般剧烈,“爱”似乐,喜不自胜,心情又如“云彩”一样灿烂。诗人用海景的风云变幻来比喻情绪的高低起伏,富有生活趣味。此外,运用这种修辞艺术的还有北岛的《一束》 《船票》和昌耀的《海翅》以及余光中的《乡愁》等。
第三是暗示式象征,“诗人仅仅抓住海洋物象和主观情绪之间朦胧的‘契合点’来对自己的心潮作含而不露的暗示而不作直接的说明”。如同舒婷的《致大海》,诗中描绘了一片复杂多变的海来暗示生活的变化无常。诗人生长于动荡的年月,小小年纪就经历了生活中的种种跌宕起伏,因此她比常人更清楚地认识到平静的生活下的“汹涌”。诗人正是抓住了“生活”与“大海”下的“汹涌”这一契合点展开创作,肆意泼洒自己的灵感。总有一些人力所不可逆转的因素让我们对现实生活充满挫折感和无力感,这些磨练或许会磨平所谓的“书生意气”,在承认社会人生的种种矛盾后,别放弃对人的价值的追求,没有激进,没有毁灭,只付诸清醒的等待和执著的坚持。同样使用暗示式象征手法的还有蓝海萍的《听海》,以海洋从古至今夜以继日的流动暗示民族文化的流传以及杨炼的《瞬间》中以海洋的一望无际来暗示未来的不可预知。
二
诗歌,呈现了个人的感思,记录了时代的风雨,归档了民族的秘史。其中,“海洋”以其意象的蕴藉深厚和新鲜活跃,镶放在时代的语言序列中,绽放出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当代显明的精神标志。毫无疑问,海洋意象是一种极其多元化的存在。宏观而言,基于不同的民族、地域、文化等因素,关乎海洋的意象十分繁多且千差万别。此外,海洋意象还是一种流变性的存在,体现于不同历史维度下主观情感体验的沿承和发展。海洋以其辽阔与宽广,给人类带来了思想价值和情感体验的无限可能。
(一)心之谛视:从思想禁锢到多元绽放
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禁锢了思想的自由,也冰冻了滚滚的海浪,海水失去了昔日的活力,变得毫无生气。但细翻这一时期的诗歌作品,我们会在一片整齐的合唱声里听到一些细碎的声音。这些声音就像冰面下浪涛的低吼,苦守着大海内心的声音,苦守着对自由的坚持。食指对海洋意象的创造,给文革时期的海洋诗歌吹来一阵清冽的海风,是集体化激进潮流中个体无奈的独游。海洋意象真实地记录了食指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他的代表作品《海洋三部曲》既是三首海洋诗歌,更是三段内心的剖白。在1965 年的《波浪和海洋》中,诗人强烈地渴望着能够融入海洋实现理想,自我“惆怅”所以“喜爱大海宽阔的胸膛”,自我“怯懦”所以“喜爱大海的无比坚强”,自我“能力寻常”所以“渴求大海的巨大力量”,自我“形体丑陋”所以“酷爱大海的碧蓝和明朗”。海洋代表了一种理想型的人格:坚毅,宽容,抗压性强,具有无穷的力量。两年后,“文化大革命”陷入党派之争,红卫兵运动全面开始落潮,《再也掀不起波浪的海》是食指当时的有感而发。“离开这再也掀不起波浪的海/我噙着热泪劝你/去寻找灿烂的未来”。现实是无情的,人生是虚无的,当理想遭到毁灭,热情变得冷却,诗人哀叹文化大革命对于思想的禁锢和戕害,曾经那浪花滚滚的大海已不能再掀起波浪,他伤心地呼吁朋友们忘却这片沉默的海,珍惜青春去寻找光明的未来。1968 年食指又作《给朋友们》,离开那“再也掀不起波浪的海”后,诗人大喊“开船嘞——”,号召年轻的朋友们再一次为了心中的理想奋力拼搏。航行于这片满是惊涛的“命运之海”之上,诗人始终展现出不屈不挠的抗争姿态。《海洋三部曲》展现了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里诗人从期望到失望、从心伤到反抗、从沉沦到振奋的心灵历程。贯穿始末的“海洋意象”有别于同时代的红色意蕴,对理想和信念作了最真切的反思。
十年的浩劫带来的不只是物质生产的暂停,还有精神世界的“残垣断壁”,无理的狂飙突进使处在这个时代的青年被笼罩在这片灰暗中。当阴霾渐渐散去,北岛扬起风帆,“如果大地早已冰封/就让我们面对着暖流/走向海”(《红帆船》),激励每一个怀揣着梦想的年轻人踏上自我救赎的道路。为了心中的梦而浴血奋战,去揭穿那一个个春天即将来临的谎言,去寻找心中光明的“理想之海”。当再一次面对这片熟悉又陌生的海,诗人们重新燃起咏海的热情,海洋诗歌像海浪一般滚滚而来。在经历了一夜的“风暴”之后,舒婷“一早”就奔向大海,打破时空的枷锁把自己的心紧紧贴上了大海“胸膛”,年轻的诗人决定做大海“呼唤自由的使者”,做大海最忠实的朝圣者。在这里,大海就是远方和理想的象征,鼓舞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带上自己的灵魂在大海中自由地飘荡,从此迷途无惧。
在这个全民造神的时代,对“理想之海”的追求也就是对“神”的追求。在那样一个信仰缺乏的年代里,国民需要一个神的存在来照亮前行的道路。诗人将自己的信仰付诸于笔下的意象,以此支撑起大众的信仰,但当大海肩负起人类过多的理想和希望时,大海就脱离了原先的自然物质属性,异化成一个国民信仰般的存在。时代的车轮滚滚前进,改革开放的大门越打越开,从服从“共性”到推崇“个性”,新时代的思想给海洋诗歌创作注入了新鲜海水,以强大的创新驱动焕发出海洋意象新的生机。诗歌的土壤之上不再是一片贫瘠,而可以自由地开出五颜六色的花朵,万紫千红,百花齐放。
当海洋脱掉虚无的外壳,“神”的形象骤然崩塌,诗人们更多地开始从自身的情感体验出发来描述心中的那片蔚蓝。海子有一个简单的理想:住在一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房子里,成为“一个幸福的人”,但是这个理想的实现时间却是“明天”。“明天”,一个永远无法抵达的时间。当海子意识到自己的理想将永远都无法实现后,他选择卧轨自杀,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纵使凡人心底已是百转千回,大海仍一如往昔,周而复始地潮起潮落。海以其永恒的深邃与浩荡,超越时空般无限存在着。人类却是有限的存在,我们无法抵达无限,只好用海水充盈自己。理想之海,永远都在彼岸。
(二)浓情颂歌:从眷恋陆地到以海为家
一群人久居一地,人们依托环境而产生出一种玄妙的空间体验感,而这种空间体验感逐渐融入人类的遗传谱系,经久相传,成为生物进化后的一种本能,影响着后人对其生存空间的感知意识。这种意识就是乡土意识。随着主观情感的投入,“乡土”具有了强烈的社会意识形态,演变为诗人心中的一块“圣地”——故乡。受强烈的乡土意识的影响,各个时期的海洋诗歌在描写家园的情感体验上,总体情况呈内向回归。纵然诗人赞美歌颂海洋,仍时时牵挂着内陆,留恋着他们离别的那一片故土。乡愁,乡愁,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相较于陆地,对大多数人而言,海洋是一片完全陌生的地理空间。旅居他乡,面对陌生的坏境,乡愁就成为海洋诗中一种普遍的情愫。“飘泊得很久,我想归去了/仿佛,我不再属于这里的一切”(《归航曲》),一曲归思,一曲愁,海上的生活是终日如浮萍般飘荡,那是一种无根的虚浮感。漂泊得太久,以至于都变成了一个精神上的浪荡者。中国人强调“落叶归根”,“乡土”意味着他们精神的家园,“每一片帆都会驶向/斯培西阿海湾/像疲倦的太阳/在那儿降落”(《归航曲》),在外漂泊的游子渴望回到来时的故乡,安放失重已久的灵魂。
家中的俗世情爱往往更能牵动诗人对故乡的想念,海洋雄伟,海洋壮丽,海洋一望无际,一番激情的感慨过后,诗人往往都沉溺在对故乡的亲人朋友的想念之中,难以自拔,感慨的依然还是中国最传统的陆地乡愁情。江河的《帆》中描述“海那边/有我的妻子/海的那边/她歌唱/比帆洁白/比帆遥远”,诗人被远方的帆船实景勾起对“比帆洁白”“比帆遥远”的妻子的无尽思念。白帆飘荡在大海之上,而妻子徘徊在脑海之中,海洋变作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鸿沟,隔开了诗人与白帆,也隔开了诗人与妻子。远方的白帆随着海波起起伏伏,越飘越远,恰如诗人的心潮跌跌荡荡,思念越流越长……
在那个国共内战的特殊时期,许多文人被迫转居大洋彼岸,从此,乡愁便是一道难言的殇。余光中写过许多动情的乡愁诗,游子生活就是他的个人体验。他的一生伴随着漂泊与流浪,故他的诗中常常表现出被故乡放逐的无根感。一句“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乡愁》)道出了海峡两岸多少人的心声。从对一块土地产生认同感开始,一旦徘徊他乡,就注定是一场宿命般的流浪。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诗人视海洋为一片陌生的地理空间,由于对故乡的牵挂,使海洋诗歌成为“乡土抒情诗”,散发着浓郁的泥土味。
许是人类“发祥于大海”吧,在人类的灵魂深处,有着对大海深深的眷恋,那是胚胎对母体的记忆,也是人类生命伊始对海洋的初印象,所以对海洋的亲近,人类天性使然。在大开国门的1980 年代,中国人越来越意识到海洋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整个社会的眼界开始宽阔起来,不再只局限于眼前的这一方土地,而慢慢主动去亲近海洋。臧克家用眼睛“看到了”海的颜色,用鼻子“嗅到了”海的气息,用手掌“触到了”海的体温,用耳朵听到了海“有力的呼吸”(《海》),海色斑斓、海味腥咸、海水微凉、海声涛涛……他从视觉、嗅觉、触觉和听觉四个角度立体地感知着海的形象,与大海在不断地磨合中走向契合。
走向大海,主要体现于海洋诗歌文学创作的规模化,这是诗人将目光从内陆转向大海的一个重要佐证。诗人不再苦苦抓着陆地不放,而开始努力挖掘玄妙莫测的海洋对于人类与宇宙的价值和意义。海洋作为人类生命的起源地,不仅予以人类生命,更予以人类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养育,而“养育”正是父性与母性的核心特征,“海洋对人类的‘养育’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生’,海洋给了‘自然人’以生命;二是‘育’,也就是对‘社会人’的哺育”,海洋成为人类思想的载体,总览各个领域,都能寻摸出海洋存在的痕迹。在这一父一母的共同参与下,海洋就是我们的家!
家园,涵盖了“家庭”“家乡”之意。先有家的庇护和养育,然后就会产生精神的发展和提升,一个人长时间的与一片空间休戚与共,就会逐渐对这片空间产生家园意识。“鱼”作为海洋中最基本和广泛的生命物种,其形象逐渐成为海洋文学中的首要之选。从开始人类将鱼类视为果腹的对象、经济的来源,再到人类面对海洋而感受到家园归属感,希望化身为一条与大海唇齿相依的鱼,体现出人类对海洋看法的转变以及对海洋生物观念的转化。于是,野曼想象“我赤裸裸的/顿时变成了一条飞鱼”(《我浮游于海》),靳亚利“常常幻想长出了鳃变成了鱼/跟随他走来走去”(《海之恋》),王蒙在《游》中也将自己幻化为鱼,与海洋的兄弟姐妹们一同在水底深处遨游。无论是料峭的春天、炎热的夏天、萧瑟的秋天,亦或是寒冷的冬天,鱼儿永远依偎于大海,它的一生都与大海聚结成状,交错纠缠。“生活在海上的人,对海洋有一份偏爱,这份偏爱,正如同乡土的口音和怀念一样,终生难忘”,对于长期与海为伴的人来说,海洋早已融入他们的生命。“鸟附身向我,以清澈的眼界栽我成水仙”(《饮浪的人》),朱学恕将自己的茎系狠狠植根于大海,伴海共生。太多的诗人爱上这片海,又把这份喜爱内化为语言,为自己搭起了诗意栖居的“家”。
(三)人海关系:从对抗疏离到平等亲密
历史上的第一个小舟的创制过程早已漫不可考,但这足以代表人类与大海的初次较量。“海者,晦也。”一望无际、神秘莫测是人类对海洋的初印象。这种未知的神秘感一直挑逗着人类去探索海洋,去挖掘海洋。但在这过程中,大海常常以其巨大的力量吓退人类前进的步伐,“只轻轻一扫/就永远地卷去了我们的父兄/把幸存者的脊背/扭曲”(《划呀,划呀,父亲们》)。大海的力量是如此恐怖,仿佛吞灭天地也就是一念之间,人在大海面前完全是如蝼蚁般弱小无力。然而“去掉了暴虐的大海不是大海。失去了大海的船夫也不是船夫”,“暴虐”使“大海”更具魅力的同时,也燃起“船夫”熊熊的斗志。于是,祖祖辈辈的人开始“划呀,划呀”,“沉没,意味着永不生还/但赶海的风帆总在升起呵”(《航海去》),在大海以绝对性的力量在压制人类的同时,人类也在以自身坚强的意志与不屈的精神同大海展开搏斗,在这场双向征服的较量中,人类不断地释放出自己潜在的能量。从人类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的前进与繁荣。
一直到工业文明以后,科学技术水平达到空前的高度,人类自我意识极度膨胀,一切行为都实行利益优先原则,盲目地向自然进行无休止的掠夺,人与大海的关系已由“较量”变成了“对抗”。人类以胜利者的姿态自居,肆意向海洋排放废水,投放垃圾。如今的海,“只有浑浊的海水、污秽的烂泥/一两艘破旧的小船、废弃的渔网/垃圾、避孕套、黑塑料袋遍地皆是” (《并不是所有的海》)。大量的有毒化学物质污染了原本纯澈透镜的海水,海洋生物受到巨大的生命威胁,于是,“鲸鱼们正在自杀”(《藏枪记》)。水上摩托车手们因为追求瞬间的快感,“踩脏”海的“衣衫”,不惜在海上“划开一道血痕”,使摩托车的汽油“污染了”海的“血液”,“侵占了”海的“身躯”(《海殇》)。由于长期占据地球的统治地位,人类逐渐习惯于将所有的“非人类”视作资源,自以为拥有了对自然的支配和改造能力,即使强悍如海洋也已被驯化,但是果真如此吗?
长期的掠夺行为在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同时,正加剧着海洋灾害发生的频率,然“几个回合生死/大海依然大海”(《形》),当海洋真正发怒报复之时,其后果是人类所不能承担的。海啸、飓风、龙卷风、海平面上升……每一场灾害都给人类招致了难以承受的后果。面对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分岔口,工业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当务之急是审视人类对海洋造成的破坏。当代海洋诗人围绕生态主义将人类和海洋置于一个大的复合生态系统中,重新低头反思人类与海洋的关系。
开天辟地说中,盘古“垂死化身”,不但“目为日月,脂膏为江海,毛发为草木”,而且“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氓”。所以,“我的血和海浪同潮”(《浴海》),人与海,就其本源来讲应该是一种一体化且平等的存在。王敖“在秘密的岩石码头上”“和几千只螃蟹握手”,“微笑着”与螃蟹高谈阔论,聆听他们诉说对自己的爱恋,并愿意与他们“分享这几个气泡,一起上岸”(《我曾经爱过的螃蟹》)。诗人给予螃蟹以高度的人格化,不仅用平等的姿态与他们对话,还与他们进行情感上的交互。这种类似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际行为,体现了诗人的生物平等意识,在面对人与海洋之间的关系时,往往能换位思考,将海洋生物看作一个与人同等地位的独立个体。这个个体的形象塑造也与诗人的关系越发亲近,“海更像邻居,每天打过招呼后/我才低下头,读书,做家务,处理公事” (《邻海》),李少君临海而居,他和大海的关系是那么亲密熟稔。海洋于辛龙既是“知己”又是“高邻”,“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海是他“久别重逢的恋人”,他们依偎在一起呈现出一种“脉脉不得语”的美妙状态,而“在阴云翻滚的日子里”,海是他“狭路相逢的诤友”,他们在一起互相争辩却又惺惺相惜。他们“情投意合声息相连”,彼此之间有一种奇妙的融合,那是一种外力所无法打破的亲密。(《大海·知己高邻》)当起先略带傲慢的人类中心理论被完全推翻后,一种浪漫多情的生态环保观应运而生。“我们统治自然,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无论人类文明发展到何种高度,都无法改变“人类依赖于自然”这一事实。于是,“我们走向海”,“手挽手继续向前走去/像野马奔向大漠/像雄鹰腾向九霄”,只因“我们是海所失落的原子”(《我们走向海》)。在当代新时期,“海洋生态文明是以人与海洋的和谐共生为核心,以海洋资源综合开发与可持续利用为前提”,它宣扬的不是凌驾于海洋之上的沾沾自喜和洋洋得意,而是融于海洋生态系统中的亲密无间。“热爱海/让海藻缠满你的名字/让海蛎子爬满你的名字/热爱海/长出鳃来/长处鳞甲来/ 像一条鱼那样热爱海吧” (《老兵箴言录》),人如鱼,终将“浮游于海”。在这海洋生态主义之下,人与海洋,正在平等中走向和谐与亲密无间。
注释:
①袁晓红、刘进:《“海洋”之歌——当代诗歌中的海洋意象》,《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2期。
②杨慧:《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浅析梅尧臣诗论的意境说》,《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 年第3 期。
③④张中来:《诗歌意境的“虚”与“实”》,《潍坊教育学院学报》1999 年第6 期。
⑤李杰:《物虽胡越合则肝胆——比喻是诗歌意象的有效手段》,《语文学习》2010 年第10 期。
⑥盛晴:《情、知、理:现当代海洋文学抒写及其形态》,山东大学2017 年硕士学位论文。
⑦梁纯生:《海洋的德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47 页。
⑧冷卫国:《中国历代海洋诗歌评选》,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246 页。
⑨[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518 页。
⑩陈凤桂、王金坑、蒋金龙:《海洋生态文明探析》,《海洋开发与管理》2014 年第1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