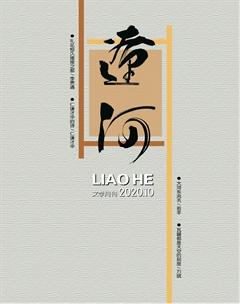南国的榕树
张国民
我喜欢榕树,由来已久。
有一年夏天,陰雨连绵,出不了门,下不了田。为了打发寂寞的时光,我便借来许多书本阅读。
一天下午,我忽然读到了巴金先生的《鸟的天堂》。从此,南国的那一片水域,以及水畔那巨大的榕树,还有那于黄昏时分前来投宿的叽叽喳喳的鸟群,便在我的脑海里落地生根了。
那时候,我天天想:什么时候能去一趟南方呢?去一趟榕树的故乡?去看看那绿如伞盖的大榕树?
一段时间里,去南方看榕树,成了我的一块心病。
春去秋来。光阴一年年过去了,我也一天天地变老了。去南方看榕树,似乎成了我今生难以实现的夙愿。
算了,这辈子,我恐怕都没有去南方的机会了。见见大榕树,也只能是痴人说梦了。
山不转水转。终于,机会来了!
过完2018年的春节,我和二连襟一块去塞外打工,由于那里的工作量太大,我不堪重负。于是,我一个人辗转来到了深圳,这里是榕树的故乡。镇头、村前、路口、河畔,大榕树随处可见。有的是单独的一株,有的是两株并排而立。远远地望去,一棵的像一个人把一把绿色的巨伞撑在了那里。两棵的像两个人把两把绿色的巨伞撑在了一起。它们的根系特别发达,一根根藤蔓,蛇一样从树杈上垂直下来,扎进泥土里。年深月久,就会变成另一株树干。许多粗细不等,年龄不同的树干,共同组成一棵大榕树壮硕的树身。风来撼不动,雨来是把伞。
在深圳,我在一所大学里谋得了一份清洁工的工作。这校园里就有不少的榕树,特别是我负责的二号门,三号门,四号门,门门都有一株,两株,或三株大榕树。朝夕相处,耳鬓厮磨,这样的一来二去,我们便结下深厚的情谊。
南方是多雨的。而且多是那种说来就来不容功夫的急雨。你来不及备好雨具,雨点就噼里啪啦砸了下来。雨幕里,你一抬头,看到不远处有一株大榕树。你立马喜出望外,它们已经把大伞撑开在那里了。正举着,眼巴巴等你过去避雨呢!
你跑到它的跟前站下,那雨点干着急,只能在伞盖上胡乱叫唤。一点一滴都砸不着你了。
这时,你会很自然地想起老家的母亲父亲,奶奶爷爷。想起她们温馨的臂弯,慰藉的眼神。
但同时,南方的夏天是很漫长的。炎炎烈日,犹如蒸笼。特别是我们这些户外工作者,每日里挥汗如雨。身上的工作服从来没有干过,整个人每天都像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而当你打扫到一颗或两棵大榕树下的时候,啊,那般惬意!沁人心脾的清凉,便一滴一滴渗进了你的血管,继尔,浸透了你的整个肌体。
蹲在树顶上的白云,时不时探头往下瞅瞅,也想司机跳下来享受些许清凉。可它们哪有那份福啊?
冷不丁,你回头望望,哦,原来是一位慈祥的老者为你撑起了一把遮阳的巨伞。这时,你也无需道一声:谢谢。他从你的眼神里,早已心领神会了。
我常想,过两年,等年纪大了,干不动了,就在这里选一块地皮,盖一间屋子。但门旁必须有一棵或两棵榕树。
而榕树下必须摆一张小桌,小桌旁必须放一把小凳。这样的环境,多么适合读书写作啊。即使再笨的人,也能长出一支生花妙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