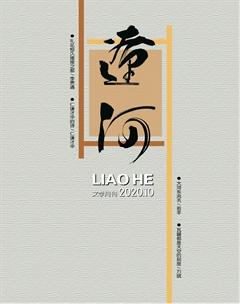仁谦才华的诗

雨后,一只向日葵勾下头颅
面遇你的这个下午
一场雨刚刚走过
灰色和静,正在放大
白露过后
阳光背对你
你,很真实
真实地脱落燃烧,勾下头颅
什么也不想,什么都想
残缺的地方是谁抠取的
一对情人还是一位暮年老者
籽粒里大片黑暗,风雨,以及数不清的光和线
温暖,凄凉,热烈,凋敝
最终会停在身体的
哪个部位
这个下午
陪着你的也就是枯黄的几根草了
也就是一场雨后的清冷,孤寂和
雨一样的我啦
一根枝挑起的世界里
我们互为光照
孤独到了尽头也许就是饱满
而饱满到了尽头
又该是什么
眼泪花儿把心淹了
你猜猜这是第几次想见这个女人了
可我还是没有见到她
六盘山的风依旧吹过她的百叶窗
呼哧,呼哧的
我在想
那一夜,是怎样的血涌堵了她
是怎样的泪淹没了她
风,拨响一根胡弦
喊叫水的固原
没有因缺水而出名
也没有因一个诗人的走进或者离去而出名
土墩矮下去,草就高过了天空
她,是否躲在今夜的雷声里
一路向西
一路走远的那个人和他的歌声
穿过雨水,阳光和尘埃
穿过单永珍浑厚撕裂的嗓子
被风揉皱又舒展
七粒蝌蚪漫游
像飞雪,河流,海子
像太阳雨幸福或者忧伤的两片蝴蝶
七粒蝌蚪被一条路串起
牧鞭掀起
天山的盖头
路
我扯开鞭麻和鞭麻的交错
几朵黄花落下无奈
一匹蝴蝶扑闪眷恋飞身天空
路,就在荆棘的缝隙里
像条遗弃的缰绳
蚂蚁和蜜蜂是最先的探路者
其后
是麝、鹿、狍子和欲望
我是在琵琶,香柴花和一地斑驳的光里
找到你的
踩着酥软的身子
我踩到山花和蜜蜂偷情的呼吸
踩到一个远去的背影和心跳
剥开荆棘,艰难前行
我没有嗅到麝尿的味
也许
麝的种族早已在人类下的套中灭绝
我嗅到的只是雨
打在一朵花上又跌下去的
一声叹息
思念
夜,深了
就像此刻渐渐深起来的思念
烟头 掐灭又燃起
这个反复
我只留住燃芯那么大小的
一点点光
在同样厚深的寂寞里
你的温度,扯心或者沉默
是这眼前的烟头
把你的气息一明一暗地放大到眼底
放大到血液,以及心脏的纹理
这时,我经过的桥面
猛的 晃了起来
月光和雪的禅意
步出莲花
骋怀一根草的生长与凋零
以及众生的苦闷、忧郁和磨难
佛珠流转
在一次次玉化的心路上
渐次抵达清净
你的世界
像一朵花被阳光和雨水打开
从葳蕤到凋谢
一直都浸泡在风雨雷电里
霜卷叶子,枝条就会疼痛
花落大地,根脉就会颤抖
在花一样短暂的再生路上
你,打开参悟的天眼
用智慧、仁慈、悲悯的光芒
给苦难的人生修出一条长长的
度化之道
莲花素心,大善若水
一枝一叶,一条叶脉的走向
一坤尘世,万千众生的生命
都渗进你月光和
雪的禅意
门
灯光暗淡
木几上一本书歇于520页
与其说是书还不如说是人
其实,他并没有歇息
只是把目光从书页移到门外
门外是海
海上挂着一轮明月
一层层,一层层海的波光被月催动
一层层,一层层
漫过心的沙滩
一道电光把海面劈开
心的裂缝被幼鱼、贝壳、咸涩的海水
海光减弱的速度和浪击礁石的声音填满
他,猛猛吮了口烟
页面上的字行
波浪一样涌动起来
墙面是空的
是那种海面喧嚣起来的空
身体被抽走水分和灵魂的空
墙,自来就挡不住
盛放在里面的人和物
村落:你很得体
拼车的司机把我卸在黄酒馆站
一个荒野村落
踅进巷子,三两老人蹲在柴火上唠嗑
一头散步的猪和两只摆架子的鸡
像是提醒巷子的存在
——空寂,能听到虫子走动草尖的声音
背后是绿滚动的山峦和
扯来扯去的雾
不知道里面还活着什么
晚饭时才知道
我们吃的肉都是从那里买来的
都是村落阡陌散过步的
顿然,胃口大开
村落
散著泥土,炊烟袅袅的味道
光和影隔着土墙边的篱笆对视
像刻有中国诗歌创作基地的石碑
和石碑上抠掉的粉末
要知道
立起的风骨里不能没有那些抠掉的
粉末
像我们命定的创作
多一句是缺陷
少一句同样是缺陷
凌晨,我被蚊子咬醒
凌晨三点我被蚊子咬醒
才想起去雾灵山时忘了关窗
一次疏忽竟让它们轻易得逞
吮走我的瞌睡
坍塌搭起的一场美梦
有时候,疏忽也会犯罪的
譬如
打开的通道
本想让阳光,氧气,雨水的气息进来
却偏偏引来蛾子,蚊子,蜘蛛……
凌晨三点
我智慧地灭掉三匹蚊子
也把愤懑撒在蛾子和蜘蛛身上
或许,它们是来和我交心的
一只虫发现我时
迅疾把自己贴在壁上
这个细节感动了我一秒钟
之后,还是下了毒手
蛆虫蚂蚁们
你们的禅心在草木之间
你们不该陷入人的世界
更不该遇上凶残的
我
仁谦才华,又名车才华,中国作协会员,甘肃省作协理事,曾就读鲁迅文学院。作品散见于《诗刊》《星星》《民族文学》《海燕》《飞天》《四川文学》等刊物,入选50多个选本。出版诗集《阳光部落》《藏地谣》《大野奔跑》。获第十九届鲁藜诗歌奖、黄河文学奖、玉龙艺术奖、乡土诗歌奖、《飞天》十年文学奖。《走进天祝》《文学天祝》等10部文化丛书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