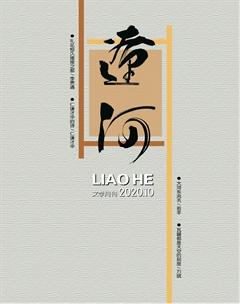大河东流去
若非

1
叔叔回来那年夏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下在了落水湾。
倾盆大雨从白天下到黑夜,又从黑夜下到了白天,从未停歇。人们呼天抢地,传言说天漏了,河水就要朝天,他们纷纷拿出锄头镰刀耙子背篼等农具,摆放在庭院里,冲着倒灌一般的雨水对天祈求,苍天啊不要再下了,可怜可怜我们庄稼人吧。大雨淹没了村民们的声音,苍天一个字也听不到,只顾玩命地下著雨。
有人透过狭小的窗户,看到雨幕中有一个黑影,从村口移来,于是好奇地睁大眼睛,把头伸出窗户,看着那个黑影走进村。直到走近,好奇的人才依稀辨认出来,来人正是离开落水湾多年的叔叔。叔叔脚踩一双结实的高帮皮鞋,披着一件部队上发的厚实大雨衣,脑袋窝在雨衣的大帽子里,目不斜视地冒着大雨走着,发出“吧嗒吧嗒”的声音。
那时候,二爷爷正坐在地火边唉声叹气,这大雨是没完没了,要把天下破了,地里的庄稼可怎么办?二奶奶说怎么办也不行,由它下着,老天不要我们吃饭,谁也没办法。门“吱呀”一声开了,叔叔高大的身躯站在门外。二爷爷和二奶奶都一下子惊住了,他们差点没认出叔叔来,叔叔也没有提前告诉他们要回来。爸、妈,我回来了。叔叔走进屋,站在地火边,摘下雨衣帽子,脱掉雨衣,露出一身有些微湿润的军装,很神气。整个过程中,二爷爷和二奶奶都死死地盯着他的左手,眼里充满疑问,儿啊,你的手。
雨再大,叔叔回来的消息,还是像个爆炸性新闻,第一时间传遍了落水湾。
叔叔是全落水湾第一个当兵的,但走的时候一点也没有去当兵的样子,别人家孩子去当兵,都是村里人拥护着戴着大红花送出村。但叔叔走的时候,悄无声息,只有二爷爷陪着,二人一前一后一言不发出了落水湾,几乎可以用逃来形容。在那之前,叔叔偷了别人家一只鸡,拿到镇上去卖了,被查了出来,二爷爷很生气。他从小就有些不听话,闯祸结怨就算了,偷东西可容不得,于是二爷爷赔了人家一些钱,再把他暴打了一顿,说,送你去当兵吧,我管不了你了。
叔叔走后,村里人都说,他这回更是惹不得了,以前就不服管教,当了兵学了本领,回来还不得称王?叔叔去了好几年没回来,家里为他准备好了娶媳妇的钱和房子,他还是没有回来。人们就说,他不会回来了,谁会念着落水湾这种落后贫穷的地方呢?又有人说,就算回来,也肯定是飞黄腾达衣锦还乡。
谁也没有想到,叔叔会以这般模样回来。他的左手齐手腕处断了。
第五天清晨,大雨终于停了,人们收回庭院里的锄头镰刀耙子背篼,伸着懒腰,迫不及待地,不约而同地,怀着好奇心来到了二爷爷家,围住叔叔。
你的手是怎么了?他们对叔叔的手很好奇。
是被人砍的吧?有人抓起叔叔的手,打量着他光秃秃的手腕,你看,齐刷刷的,丁点凸凸都没有,是被敌人砍的吗?那人说完,又赶紧放下叔叔的手,稍微往后退了退。
其他人来了兴致,七嘴八舌地追问,是哪个国家的坏蛋,有没有被消灭……对了,断下来的那一截手呢?
不知道是谁冒了一句,不会是部队上又偷人了,被抓住打断的吧?
叔叔原本笑着的脸突然僵住了,脸部有一些扭曲,眼神里含着一些难言的什么。围观的人都吓得不敢说话,他们在叔叔当兵前就已经领教了叔叔的厉害。但很快叔叔脸上就恢复了自然,动了动嘴,有了要说话的意思。大家都很期待,以为他要说自己的故事了,都眼巴巴地看着他。结果他说,乡亲们,口干了吧,我给大家倒杯水喝。在大家失落的起哄中,二爷爷用半人高的旱烟杆敲了敲又矮又圆又大的土地火,咳嗽了起来,大家便安静下来。二爷爷咳了五声,喃喃地说,大伙说,这样,可怎么办啊?
没人给二爷爷出主意,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没辙。落水湾可从来没有出过断手的人,叔叔这是第一次。良久,有人说,这手是当兵断的,应该国家负责。大家眼前轰然一亮,哦,对,国家负责,该国家负责。
这时候,叔叔站起来,跳到一张板凳上,举起断了的左手,像举起一根壮壮的秃秃的木材。他说,大家就别为我这手操心了,看看,虽然断了,但我不一样活得好好的吗?吃饭,睡觉,干活,揍人,可没有一样事是干不了的。
有人说,胡说,锄头把你都握不住了,地也就刨不了了。
叔叔说,活又不只有刨地。
……
正在大家为叔叔该怎么活下去争论不休的时候,有人从村外往村里跑来,边跑边喊,不好了,大河涨水了,大河涨水了。人们听到喊声,都不以为意。村外的大河,是千里乌江的一个支流,浩浩长江的一个部分。一路流淌而来,到落水湾,深陷在群山底部。峡谷像一道深深的伤口,把河水死死地捏成一道长长的绿带,再汹涌再狂野的水也挣不出它的手掌心。
每年雨季,大河都少不了涨水,人们世世代代生活于此,早就习以为常了。但奔跑回来的那人,依然疯了似地大喊,不行了,不行了,大河涨水了。他恐惧的神情,颤抖的声音,让人们慢慢紧张起来,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叔叔从板凳上跳下来,走,看看去。他在前开了道,往村外跑去,人们便跟在后面。
大河涨水了,长得很高,几乎就要翻过山垭口了。大河年年涨水,但从来没有涨过这么高,至少活着的人都没见到过。人们被吓坏了,有人语无伦次地说,河水真的是要朝天了。河水朝天,是落水湾祖祖辈辈口耳相传的一个传说。说很久以前发生过一次河水朝天,有一对兄妹,坐在一只大木瓜里,在水面上漂荡,侥幸存活下来。等到大水退去,兄妹俩从大木瓜里面爬出来,发现除了他们二人外其他人都淹死了,他们成了人类的幸存者。在熬过七七四十九天之后,哥哥对妹妹说,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只有我们结合在一起,才能繁衍后代,不然我们一死,人类就真的灭绝了。妹妹很为难,可是我们是兄妹,我们不能结合,否则会遭天谴的。哥哥也怕天谴。他们想了很久,决定问问上天的意思,兄妹俩一人背着一块圆石,爬到落水湾边大云和羊山两座相邻的大山顶,将石头滚下来,结果两块石头滚到一起,紧紧结合在一起;兄妹俩又站在山顶上,各点燃了一把大火,火烟盘旋而上,又扭成圆圆的一股……这是上天的意思,所以他们结合在一起,才有了后来的人类。这传说一代人讲给一代人听,可从来没有人当过真。
大河浩浩荡荡,雄浑凶猛,奔突向东卷去,很是恐怖。人们被吓坏了,边往回跑边喊,是真的,要朝天了,要朝天了。叔叔跑到人前面,张开双手想要拦住大家,大家别胡说,哪有什么河水朝天,我们这里是云贵高原,就算大水要淹,也得从平原淹起,大家不要怕。没有人听叔叔的,他们一溜烟跑回村里了。
当村人们忙着拿出家里最好的食物,找出最宝贵的物品,拿出珍藏的钱款,准备趁河水朝天之前消耗掉时,叔叔面临大河,一个猛子扎了进去。
2
有人远远地看见叔叔扛着一个红色的东西回来,那东西软塌塌对挂在叔叔的肩上。看起来不重,因为叔叔步履很稳,一点累的样子也没有。等到走近,那人才看清,叔叔扛回来一具红衣服的尸体。那时,人们已经把家里值钱的东西清点完了,有的人已经准备出发去往步行三小时开外镇上的路上,但当他们看到叔叔扛回来一具尸体时,又都纷纷围了过来。
他们把叔叔拦在村口,咦?这是怎么回事?
叔叔头发和衣服都是湿漉漉的,他擦着汗,河里捞的。
大河里?那么大的水,你跳进去?你不怕死?
叔叔喘着气,就是大河里捞的,不怕死,我在部队上学会游泳,还拿过冠军呢,我不怕。他又轻声补充说,现在是有一点怕,但那时候没想。
他们让叔叔把人放下来,死人,不可随便送进村,再说了,不明不白的一个人,你拿进村里,人家家里人来找,你脱不了干系的,人家会说谁知道自己家人是淹死的还是被人怎么整死的。
叔叔不屑地说,怎么会,人没那么坏的。话是这么说,他还是把尸体放了下来。人们这才看清,叔叔捞回来的是一具女尸。大红的上衣和蓝色裤子上尽是污垢,但偏偏脸部很干净,看起来眉清目秀,年纪二十多岁,长相很是好看,就是脸白得不行。叔叔说,脸是他洗干净的,人都已经死了,一身很脏,把脸洗干净,算是一件善事,这样的姑娘,哪里容得下自己脸上有半点尘土。
人们纷纷猜测起来。出过远门的人说,从落水湾往上,是纳雍县维新镇,再往上是毕节。从装束上,他们断定躺在地上的这个已经死去的姑娘,不是维新镇上的,就是毕节城的,不管是哪里的,一定是有钱人家的姑娘。
他们对叔叔说,好好守着,等人家家人来找吧,少不了给你一笔钱。
叔叔说,我把人捞上来,可不是为了钱。
大家就笑,不为了钱,你是为了什么?难道是好玩?你竟然喜欢女尸体,你是不是想媳妇想疯了?
叔叔很生气,他抓起一根木棍,作势要打人,那些人惧怕他,一溜烟跑了。叔叔冲他们背影说,说来,你们也不懂。
一具被大水冲来又被叔叔捞起的女尸,并不能影响村民们的任何决定,他们依旧要忙着去置办后事,毕竟河水这就要朝天了。村民走后,叔叔就地打基,搭起了一个小窝棚。那几天,落水湾笼罩在一片难以名状的恐惧和悲伤中,人们都闲了下来,吃着最好吃的食物,穿着平时舍不得穿的新衣服,日子过得很好,却依然充满绝望。只有叔叔忙着,他在窝棚里用米草和竹子架了一张简易的床供自己睡觉,白天黑夜地守在那里,旁边的地方铺了一张席子,上面躺着那具女尸。偶尔有人想着去找叔叔聊聊天,他们对叔叔在部队上的经历尤其是他的那只断手充满好奇,但他们只要走到窝棚附近,就不敢前往了。他们怕。
有一天,二爷爷终于忍无可忍,依旧拄着他半人高的旱烟杆,来到村口,远远地站在窝棚外,大声喊,儿啊,我的儿。叔叔走出来,爸,你叫我什么事?二爷爷说,你到底还要守多少天?那点捞尸钱不要了行不行?叔叔用断了的左手靠在窝棚摇晃的柱子上,右手揉着眼屎,冲二爷爷说,爸,给你说多次了,我不是为了钱。二爷爷说,你看你回来多少天了,可在家里睡了几天?你寻点正经事情干可好?手断了,也有手断了的活啊,你这么守着个尸体算什么回事?叔叔说,爸,你回去吧,说了你也不懂。二爷爷有些生气地回了家。
叔叔在村口守了好几天,都没有人来寻尸。尸体已经开始发臭了。村民们不高兴了,督促叔叔,赶紧处理掉。无奈的叔叔便来到河边,在坡地上寻了一块向阳的荒地,请人挖了个坑,把那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年轻姑娘给埋了。
埋完人时,河水已经消退了一半,人们站在坡地上,看着依旧混沌不清的大河,陷入沉默。他们的心里五味杂陈,河水朝天的谣言不攻自破,天下灭绝不了了,但他们感觉不到开心,因为能吃的食物已经吃得差不多了,能花的钱也都花得差不多了,接下来该怎么办,这是他们面临着的新的绝望。但这毕竟只是一时的事情,他们回到村,打了素碳,消了身上的晦气,就重新拿起锄头走进田地,把大风吹倒的玉米扶起来,把大水冲垮的土坎砌起来,那些倒地的玉米和垮掉的土坎也没关系,早一点晚一点,只要记得去扶、去砌,它们还是能差不多回到原来的样子。
落水湾的人们也是一样的,重新回到田地里,生活也就有差不多回到了原来的样子。好像锄头重新挖进泥土里,没有了的东西,都能慢慢挖回来。
等所有人都忙起来时,叔叔却闲了下来。他的手真的抡不起锄头把了,挖地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挖地就算了,一根倒地的玉米杆,都难以扶正固稳。在落水湾,一个被锄头抛弃的人,也意味着同时被生活抛弃了。人们都口耳相传,说他真的是废了。闲下来的叔叔,這里看看,那里走走。有时他会穿上一身军装,一个人来到大河边,面对大河久久沉默,思考着什么。看牛的孩子喊他,那个断手的,你在想什么?他不应。干活的人远远看见他,你可别想不开,手断了没事,气还没断呢。有时候,叔叔也早早跑步,把“一二一、一二一”的口号,送到村民们惺忪的耳朵中。像疯了一样。这话,是一些村民说的。
大河重新回到原来清澈的样子,差不多用了一个月。叔叔的脸上也慢慢有了一丝奇异的光。有一天,他早早起了床,穿上军装,出了门,径直往大河边去。中午回来后,叔叔顾不着吃饭,张罗着,雇了几个年轻力壮的人,围住了二爷爷的一棵大树。
兔崽子,你要干什么?赶来的二爷爷,用旱烟杆指着叔叔,大声呵斥。
造船,爸,我要造一艘船,渡河用。叔叔站在大树下,大声说。
你你你,儿啊,你到底还要折腾什么?二爷爷很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你就给我好好在家呆着,行不行?
叔叔把绳子递给一个人,安排他爬上大树捆绳子。爸,我还没废呢,你不要管我,你的树,我会折成钱给你的。
二爷爷说不过,眼不见心不烦,走了。
我的断手的叔叔,决定成为一名船夫,在村外开设一个渡口。说开设也不合适,村外原本是有渡口的。大河是大方县和纳雍县的交界,渡口就是附近几个村庄去往纳雍的最便捷通道,后来老船夫死了,再没人干渡船的活,人们去往纳雍便绕道而行了。没几年,他的船破了,被水冲走了,渡口荒废了,小路也被野草淹没了。
船造好了,二爷爷的气也早消了,关心地问,你一只手,怎么撑船?
叔叔一乐,很自信地说,渡船不要气力大,只要四两拨千斤。
木船下水时,叔叔挂了红布头,杀了红公鸡,点燃一串鞭炮。鞭炮声很响,在峡谷间来回响,人们都捂住了耳朵,只有叔叔没有。他站在船头,看着天空,等鞭炮响完,才说,这声音,和打子弹的声音,还真有点像。
人们来了兴致,又想问他部队上的事情,他却话一转,来,烫鸡,买酒,吃肉。
3
成了船夫后,叔叔就忙了起来。他在渡口不远处的山崖下,寻了个安全的地,搬来石头和树干,搭建了一个窝棚,里面砌了火台,置一些简单的锅瓢碗盏,铺一张简单的小床,作为自己的休息之处。夏天时常在那过夜,冬天则只用来供白天休息。
有人要过河,走到山垭口处,打上一两个哦嚯,一路哼些山歌,到了叔叔的窝棚下,叔叔就从窝棚里钻出来,跳到狭窄的路上,来到渡口,把人渡到对岸去。夏天里落水湾的孩子们喜欢到大河里去游泳,却常常给叔叔吓一跳,他把他们赶走,常被孩子们记恨,反倒受了村民们的喜欢,反复嘱托他看到孩子下河赶紧赶走。冬天里他每天早早出门,傍晚回来,有时候半夜还要去开一趟船,因为过河的人多。他一跳上船,右手抓住竹竿,左边腋窝紧紧夹住竹竿,往河底一用力,船就飘了出去。看起来,一点也不费力,真有点四两拨千斤的意思。
渡船的叔叔划船不收钱,每年每家会给他交一斗玉米的“皇粮”,落水湾都是自己送上门,但外村的往往需要自己上门去收。这样下来,一年倒也有不少粮食,加上部队回来时有一些钱,叔叔的日子过得还不差。唯一的不足是,他没有媳妇。二爷爷和二奶奶倒是操心,张罗着去远一些的村庄说了几个。姑娘家一听叔叔是当兵回来的,都很乐意,但一看到他的手,脸色就变了,谁也不愿意嫁给一个断了手的人。叔叔倒也不急,就那么一日日地过着。
有一年冬天,天快黑时,叔叔从外村收皇粮回到家门口,一下子栽倒在地上,晕了过去。醒来时,他已经被人抬到床上躺了好久。据他说,天黑时他走进院门,感觉很黑,这时候有一只大手,冲他挥了过来,他躲闪不及,被一巴掌打到在地。
二爷爷说,哪里来的人,这落水湾能有人一巴掌把你打倒?谁不知道你当过兵,体格好?
人们附和说,就是,就是。
叔叔说,怎么就没人信我呢?
人们说,你说得太假了,鬼才信你。
叔叔爬起來,发现自己并无异样,只是很饿,赶紧给二奶奶说,妈,我饿。
看着叔叔吃完一大碗面条,大家很放心,纷纷说,知道饿,还想吃东西,证明没问题了。
那次晕倒,叔叔把原因归结为收皇粮背的东西多,加上又饿又累,低血糖才晕倒的。但那之后,叔叔的身体就越来越不好了,人瘦了下来,常常感到头晕,没力气,精神也有些不太正常了。去了镇上检查,没问题。来年春天快结束时,人们把叔叔送去县里检查,结果还是一样。医生说,无大碍,多注意休息,按时饮食就行了。
从县城回村的路上,叔叔睡着了,再醒来已经到了家。他感到口干舌燥,想喝水,二爷爷就赶紧给他打了水,喝了水的叔叔说,爸,我做了个梦,梦到一个红衣服姑娘,一直在追我,我一直在跑,爸,你说我为什么要跑?
二爷爷、二奶奶和村人们愣住了,谁也没有说话。有人想起了叔叔刚回到落水湾那年他从大河里捞起的那具红衣服的女尸。
晚上叔叔睡着了,村人们还聚集在二爷爷家里,低声商量着什么,一直到深夜。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二爷爷就差了人,急匆匆出了村,晌午时分,那人领着一个白胡的老算命先生,到了叔叔家。
那时候叔叔坐在院子里晒太阳。自从身体不好后,家里人便不让他渡船了,他一天天闲得无聊,就是睡觉和晒太阳。他半靠着,把玩着手里的一枚勋章,很痴迷,直到听到脚步声,才回过神来。
老先生点了三炷香,围着叔叔转了三圈,口中念念有词,一会儿拍手一会儿跺脚,突然“呔”地一声,把叔叔和围观的人都吓了一跳。“呔”完之后,老先生失魂落魄地坐在地上,半天才爬起来,着急地找水喝。所有人都好奇地盯着他的喉结一上一下地动着。老先生喝了水,道出其中原委,叔叔是被鬼缠了魂。
二爷爷便把老先生拉到一边,将叔叔刚从部队回来那年从河里捞出红衣女尸的事情,慢慢道与老先生听。老先生掐着指头沉默半晌,一拍手,对,就是她了。原来那被大河冲来的女子,是一名黄花大姑娘,心中诸多不甘散不去,人便没有投生,魂魄兜兜转转世间,缠上了叔叔。末了,老先生叹气道,唉,这是一段孽缘呀!
就没有什么可解的法子?二爷爷急了。
老先生又掐指一算,有倒是有,就是有点,唉,我们还是屋里说吧。二爷爷领着老先生进了屋,好奇的人们跟了去,一帮人把叔叔晾在院子里。
不行,这是迷信,什么鬼缠身,我看你才是鬼缠身,你个老不死的。听说要给自己动法事,驱女鬼,叔叔很生气,大家能不能相信点科学,这世界上哪里有什么鬼,都是骗子,骗子。
但没有人听叔叔的,大家依旧忙开了。
两天后,法事就开坛了,院子里挂满撕成条的红布,弥漫烟香,四周悬挂很多画着奇怪突然的破旧布卷。老先生带领一干弟子,身着奇怪的衣服,敲着锣鼓,唱起了含糊不清的唱词。鞭炮响过三轮后,一群人簇拥进家里,把叔叔架着来到院子里。叔叔边骂骗子,边挣扎。见叔叔反抗,老先生一声令下,捆住他。叔叔很快就被捆在了一架准备好的木梯子上,除了嘴能动,其他的都不能动了。
在先生们的敲打唱跳中,叔叔不停破口大骂,老不死的,你放我下来,放我下来……
老先生倒也不气,面色不改地唱着,好像根本听不进去什么。
唱得差不多了,四个人一人一只角,抬起叔叔,跟着先生们的锣鼓声,往大河边走去。到了大河边,又做了会法事,老先生才对众人说,下水时间到。这时候,叔叔才明白,他们是要把自己放到河里去。
叔叔慌了,他像一只困兽,身子不断挣扎扭曲,却丝毫无用,他歇斯底里地大声呼喊,你们这是杀人,杀人,什么鬼缠身,你们才是鬼缠身,你们是杀人鬼,杀人鬼……放我下来……救命啊……
空气很安静。春日大河默默流淌,群山静默,叔叔的声音在山间回荡。谁都没有说话,只有锣鼓声和叔叔的声音彼此争锋相对。人们迟疑了一下,虽有不忍,但还是把他放进了大河里。
先生们依旧敲着锣鼓,唱着歌,所有人都死死地盯着河面。谁都没有说话。按照先生的说法,把叔叔淹入河水,如果唱完那段唱词,还没死,证明女鬼已经放手了;如果叔叔死了,一切都是天命。
那段唱词长极了,唱了许久。每个人都很紧张,都恨不得先生赶紧唱完。当先生唱完最后一个音,人们几乎闪电一般,把叔叔连同梯子拉出了大河。湿漉漉的叔叔,软塌塌地挂在梯子上,垂着头,看不出来是死是活。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去试探。
最后,是二爷爷走了过去,儿啊,你是死是活?突然,叔叔一个激灵,甩了二爷爷一身水。他突然声音更加洪亮,冲老先生喊,老子宰了你,你个杀人犯。
看到叔叔气急败坏的样子,人们露出放松、开心的表情,开心地笑了,相互说,好了,这下好了。
4
人们放倒梯子,解开叔叔。叔叔突然爬起来,冲过去,照着老先生的脸,啪地就是一拳,老先生的鼻孔里很快就流出了鲜血。人们惊呆了,二爷爷也傻眼了,在落水湾,这种事还是第一遭。
说来也奇怪,那之后,叔叔的身子竟然渐渐好了起来。身子渐渐好起来的叔叔,也就开始忙了起来。夏天到的时候,叔叔又回到了河边,打理自己的窝棚,清理牛羊的粪便,割掉渡口上的杂草,重新撑起了船。
好了的叔叔并没有宰了那个差点淹死自己的老先生,但他坚信那是迷信,至于身体为什么又好了,他也说不上来。他依旧如同往日,一日日穿行在大河上,把附近的村民从此岸渡到彼岸;依旧在雨季时从河里捞起一两具尸体,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最终都被沿河寻来的人们领走了。叔叔没有收过他们的一分钱,他说这种钱不能收的,家属是一定要给的,把钱直往他怀里塞,逼急了,他就说,我们人民军队,决不能拿人民群众一针一线的。绝不拿人民群众一针一线的叔叔,每次都收下了不少的香烟、白酒,香烟多是几块钱一包的劣质烟,酒也多是二三十元一瓶的劣质白酒。叔叔又有了理由,不多少收点,人家心里也过不去,毕竟人情大比天呢。
有一些年,人们几乎就要淡忘叔叔的故事了。落水湾的人多已经丧失了对他最初的兴趣,他在部队上到底经历了什么,生病那时候到底有没有感觉到女鬼的存在,人们甚至对他的断手习以为常或者说忽略了那只断手,只有在需要过河的時候,看着他撑船的样子,才会多少注意起他的那只断手来。
大河边上,除了陡峭的悬崖,还有一大片倾斜的松软的淤泥地。泥沙每年涨水时都要被大河冲刷一遍,冲走一些,大水消落后,从远处冲来的泥沙又落在了河岸。淤泥地松软肥沃,但因为每年都被大水淹没,无人肯播种,渡船的叔叔就给撒上了油菜种子。每年开春,油菜花沿着渡口一线,开得很好,像一床粉黄色的毯子,斜斜地铺在河岸上。叔叔很喜欢油菜花,没人过河时,他便来到花丛中,这里看看,那里嗅嗅,人们说他,一看到油菜花,就像个老姑娘一样。
那几年,落水湾突然时兴种油菜,大抵便是从叔叔开始的。家家户户都种,来年打菜油吃,大片大片的油菜花吸引了周边很多人进村来观看,村民们便摆了小摊,卖起了一些地里产的东西。没几年,落水湾成了一个小旅游村,每年春天都有附近的一些人慕名来看油菜花,很是热闹。
春天,油菜花开得很好,满山坡铺满了一层粉红色的绸缎的样子,煞是好看。一个女人进村时,就被人注意到了,并不是因为她的长相。因为这两年油菜花开时来村里的人太多了,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人们注意她,是因为她怀里抱着一个灰布包裹的什么东西,小心翼翼的样子,好像抱着什么宝贝。那女人三十几岁的样子,一副城里人打扮,长得高高挑挑的,长脸、大眼、细腰、细腿,头发老长,听话地披着。
女人一进村,村口的村民就围了上去,叫卖手中的货物,更贴近地打量她。
女人摆摆手,见大家没有离去的意思,便操着普通话,脆脆地说,老乡们,我真不买东西,我只是想找大家打听点事。
大家一听,失落地走远了。
女人移步到路边一个洋芋摊前,问卖油炸洋芋的大妈,大妈,我能不能找您打听点事?
卖油炸洋芋的大妈答非所问,洋芋五块钱一碗。
女人无奈,说,来一碗,少放辣椒。
大妈边往一次性饭盒装洋芋,边斜眼打量女人,你说,什么事?
女人说,我想打听一个人。
大妈问,打听人?
女人嗯地点了一下头。
大妈问,谁?
女人说,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只知道他断了一只手,当兵的。
大妈说,当兵的?断手?哦,你找断手的。
女人来到大河边时,叔叔正把一波人渡到对岸。
那几日,看花的人尤其多。因为都是外乡人,需要过河时,叔叔便每人收取两元费用,人多的时候,一天也能收下不少钱。叔叔把一拨人送到对岸,返回的时候,叔叔撑着杆,唱起了山歌。
叔叔嗓子好,中气足,唱得好听。一首歌唱完,渡口上的人说,船家,再唱一个。叔叔打着哈哈,却不唱了。
到河心时,叔叔看见半坡上有一个人,站在油菜花丛里,一动不动地看着自己,油菜花很宽阔,那人很小,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出来。随后,那人跌跌撞撞地向渡口走下来。
女人来到渡口时,叔叔正好撑着船靠了岸。
叔叔放下竿,走到船头,跳下来,右手抓住船头,使劲一拉,船就更紧地靠在了河岸的泥沙上。他用力的时候,断了的左手,像另一只手的拉拉队一样,使劲摇着,却没能帮上什么忙。
叔叔看到女人奇怪的眼神,问道,要过去吗?
女人跑过来,抓住叔叔的断手,“噗通”跪在地上,恩人啊!
叔叔愣住了,赶紧去扶女人,你,你起来,这是怎么回事?
女人仰起脸,满脸已经湿了,恩人,我可算找到你了。
叔叔依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女人打开怀里的包裹,露出一个透明的玻璃器皿,器皿内的黄色液体里,赫然泡着一只残破的断手。
叔叔呆了,突然也跪在地上,嚎啕大哭。
女人在叔叔家住了下来,虽然没有什么仪式,但大家都知道,女人和叔叔结婚了。我们叫她婶婶。婶婶重新打理起叔叔丢荒的土地,照顾起二爷爷二奶奶,很让人羡慕。他们家衣柜的上面,就放着婶婶带来的那个玻璃器皿,里面泡着叔叔的那只断手。
婶婶的突然到来,让叔叔那只几乎被人们忽略掉的断手,再一次被落水湾的关注起来。叔叔的手是怎么断的?叔叔和女人之间有什么故事?这些问题成为了大家茶余饭后的主要论题。大家充分发挥想象力,纷纷猜测,拿出了很多个版本,在乡民之间流传。
其中一个版本,很受人信服。有人是这么告诉我们的。
说叔叔在部队上的时候,有一次山里发生泥石流,叔叔所在的部队奉命救援,叔叔冲在了最前面。在救那个女人(后来的婶婶)的时候,一块大石头掉下来,叔叔受了重伤,锋利的石头也砸断了他的手,因为山里交通不好、医疗不行,没赶上最佳时机,人虽然是脱离了危险,但叔叔的手再没能接上去。在医院治疗时,是婶婶一直照顾他、陪伴他,相处时间长了,也就慢慢产生了感情,后来叔叔慢慢康复,看到自己的断手,对未来心灰意冷,又绝望又自卑,便趁婶婶出去时,偷偷跑出了医院。
那人说完,神秘一笑,你知道到为什么他喜欢油菜花吗?我们齐齐摇头。那人乐了,得意地说,我知道,因为那女人很喜欢油菜花。你吹牛,吹牛的,我们对讲话那人说。我们跑去问婶婶求证,婶婶沉浸在一片回忆中,一脸陶醉,喃喃地说,在我的家鄉,每年春天,大片的油菜花会把房子包围,像海一样……
我们气馁地离开婶婶,又去问那人,可是为什么断了的手他自己没有带回来呢?还有还有,为什么叔叔一开始没有认出婶婶?那人犯难地摇摇头,看着我们,这,你们得去问他了。
我们来到渡口边找叔叔。看到叔叔正撑着船从对岸返回。叔叔已经老了,头发上已经有了一些白发,他撑船的身子不像以前那么强壮了,看起来已经很吃力。大河在他身下平静无波,默默流淌,我们眼前的那一刻,似乎是大河最温柔的时候。
叔叔靠了岸,冲我们说,是不是又想划船?但我偏不给,太危险了,等你们长大了再划吧,到时候给你们划个够。我们说,我们不划船,我们就想知道。叔叔好奇地看着我们,想知道什么?
大河流去哪里了?
我也搞不清楚,但一定是向东流的。
他还会流回来吗?
不会了,流走的,就没必要回头了。
我们终于没有问出口,默默地离开了汹涌的大河,离开了叔叔和他的渡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