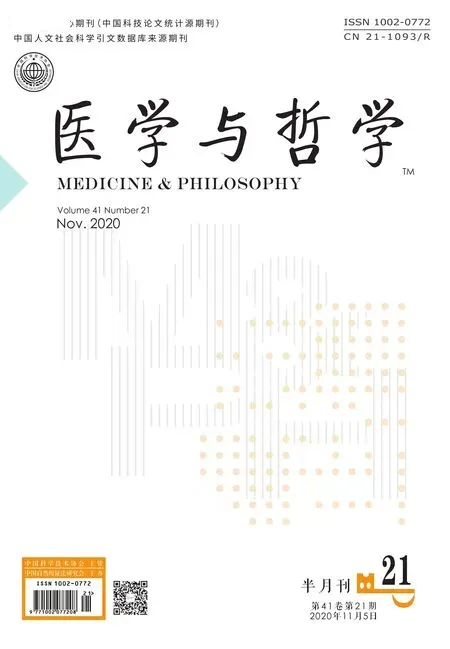评中医“实在化”及对中医真理性论证途径的思考
喻 国
中医“实在化”是指在以中医为本位的研究中,将中医的知识对标或还原为物理实在,更通俗的理解是:用科学、西医学对人体等物理存在物之物质结构的知识阐释、验证、发展中医。这样的观点及研究特别多,如王海洲等[1]提倡将中医的“证”对标于人类基因的单核苷酸多态性,吴泽明等[2]认为可以通过代谢组学阐明中医学证候的微观本质,邢玉瑞[3]认为应当充分吸收现代科学技术,可以通过西医生理、病理理论诠释来对标甚至还原中医理论。当然反对者亦不少,如黄煦霞[4]认为西医的标准不适于中医,反对使中医成为一门物质基础明确、实验指标客观、数据精确、标准具体的科学,王振华[5]认为以西医、西方科学以及西方文化的思想、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医实是当代中医的一种严重误区,孙学刚等[6]认为对中医“实在化”的还原分析是非实证性内容的“盲人摸象”和牵强附会、实证性内容的同义反复和皮里春秋。尽管中医“实在化”并不符合中医本位已被很多人认同,但这种研究仍大行其道,这也导致学界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一方面学者们要求回归原汁原味的中医,另一方面却在事实上或隐或显地攀附科学、西医学之名,在研究中采用“实在化”的方法,这一二律背反不仅使中医发展之路充满混乱也难免使中医成为笑柄。笔者认为这一悖论形成的根本原因是认识论,我们普遍将科学、西医学与真理等同起来,将其背后的认识论、方法论作为获得真理的唯一路径,故而在中医的研究中攀附科学、西医学之名,大行“实在化”的研究方法,即便学者们坚持中医学的独立性,但仍不可避免地在认识论根底上仍是唯科学、西医学的真理观,或者在当今的学术氛围中不可避免地去附和主流的价值观、真理观,如此悖论必然产生。因此,笔者认为要彻底反驳中医“实在化”,解决以上悖论需要从认识论根源着手,然而这并不是举几个例子,论述一下中医的特点就能解决的,首先这必须是认识论上的解构,其次论证应当是逻辑自洽的。最困难的是面对那些所学深厚的评论者,他们往往站在自己固有的学术立场来评判,要使他们真正信服,就要运用他们的学术语言,论证思维。笔者就将展开“西方科学式”的论证过程,引出对论证中医真理性的途径的思考。
1 理论基础——现象主义的中医
中医不以具体物质结构为主要研究点,更关注外在现象,因此,中医是现象主义的,科学、西医学以具体物质结构为关注点,因此,其是实在主义的,这是学界比较公认的看法[7],当然这里的实在非指形而上学本体论的范畴,仅代表物理存在者。举个例子,“湿邪”总结了人体趋下、粘滞、重着的病理现象,如四肢困重、头昏蒙等[8],它是将人体病理现象通过取象类比与“水湿”联系在一起形成的。如果人体患上疾病,如何治疗呢?当然是“辨证论治”,观察人体外在现象,如果出现了趋下、粘滞、重着的病理现象就可以辨为湿邪,拟定祛湿的治法,这就是中医思维的过程,可以看出现象是贯穿这个过程的关键。反观西医,如果人体出现四肢困重、头昏蒙等表现,诊疗流程是需要做生化、影像学检查,甚至病理、病原学检查,以将现象还原为具体物质结构的变化,治疗上就是给予能相应改变物质结构的药物。因此,中医和西医在认知基础上根本不同,前者以现象为基础,后者以物理实在为基础。中医“实在化”从认识论讲就是将现象主义的知识体系对标或还原为实在主义的知识体系,但认知基础的不同意味着两种知识体系是相互独立,各成一体的,不可混淆,更不能混用,如果硬要将两者拉在一起就会产生悖论。
2 中医“实在化”带来的悖论
还是举湿邪为例,湿邪对应趋下、粘滞、重着的病理现象,如四肢困重、头昏蒙等。按照中医现象主义的认识路径,决定湿邪判断的是现象,但如果我们把湿邪对标或还原到物理实在如代谢组分、细胞因子等就会产生矛盾。为便于推理,这里先将病理现象记为A,中医证候记为B,代谢组分、细胞因子等物理实在记为C,以下分析需要逻辑知识。中医“实在化”意味着将B对标或还原为C,B和C就联系起来,B和C的具体关系呢?首先通常的研究是我们对某一证型B探究其物理实在的变化即C[9-11],因此,由B可以推理出C。其次我们将B和C联系起来更多的是希望通过C来解释及判别B,我们期望当得知了人体物理实在的变化C时就可以推断此人具有证型B[12-13],以达到科学化、标准化中医的目的。尽管事实上以上关系是否成立并不确切,这需要由研究方法决定,但如果中医“实在化”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具有现实意义就必须承认由C可以稳定地推理出B,如果不能由物理实在C稳定地解释和推断出证型B,那么中医“实在化”就毫无意义。因此,基于研究期望,本文在逻辑上将B和C定为充分必要关系,由B可以推出C,由C也可以推出B。另一边,按中医的认知路径,B是由A判决的,由A可以推出B,但由B不一定能得到A,A和B为充分非必要关系。这样,ABC综合形成的关系是由A推出B,B和C互推,其中一条关系路径为由A推出B,由B推出C,以B为桥梁可以得到A推出C,这也是充分非必要关系,转换到湿邪的例子就是四肢困重、头昏蒙等病理现象可以推出代谢组分、细胞因子等的变化。接下来需要回答的问题是由A推出C符合实际情况吗?
答案是:非也!在逻辑上由A可以推出C,但实际情况却产生悖论。首先中医是由病理现象A推出B,实际可能存在多种病理现象组合,四肢困重、头昏蒙我们记为A1,它可以推出B即湿邪为患的证侯,但另一组合如汗出粘滞、舌苔腻可记为A2,也可以推出B,B可以推出C,如此A1、A2两组病理现象各自都可以推出同一个C,即同样的代谢组分、细胞因子等变化。但从实际情况看A1和A2所对应的生理、病理变化是不同的,如果认为四肢困重、头昏蒙和汗出粘滞、舌苔腻两组病理现象具有相同的代谢组分、细胞因子等变化是十分可笑的,因此,逻辑推理结果与现实情况相矛盾,这说明由A推出C是不正确的。就中医本位来说由A到B并无问题,A1和A2都可以得到B,导致矛盾的是由B到C也就是中医的“实在化”,B到C使得A1和A2在逻辑上可以对应到同一个C,而这和实际情况矛盾。这时有人会反驳说,以上推理是严格的形式逻辑,实际过程并不一定形成如此严格的关系,如虽然经过“实在化”的研究,但B并不绝对对应C,A和C不会形成严格的充分非必要关系,但存在联系。但这会面临两方面的反驳,首先这就回到了上一段对B和C关系分析所产生的问题,如果中医证候或理论并不稳定、唯一的与物理实在相对应,那这种“实在化”研究有何意义?对临床运用有何意义?难道我们不正是希望通过这种稳定的关系来帮助中医的现代化吗[3]?其次即使A和C的关系仅为存在联系,但就现实而言这种由中医“实在化”得出的联系也是十分可笑的。四肢困重、头昏蒙等现象简简单单地就以中医证候为桥梁联系到相应的代谢组分、细胞因子等的变化,这太过随意了。以上现象大的方面涉及运动系统、神经系统、感觉系统、内分泌系统等,小的方面涉及神经递质、细胞生理等,这是十分复杂的大系统,不能如此简单联系。为了避免以上不稳定相关带来的随意性,可能有人会提出解决方案:我们可以继续深化和扩展C,以便更精准、更本源性地与B唯一对应从而与A对应,这时“实在化”中医的一个根本性悖论就浮出水面了:如果我们需要以深化和扩展C来和A对应,那中医有何存在的理由?因为病理现象和物理实在的关系事实上是西医的任务,这个过程不需要中医,经过逻辑分析中医“实在化”的最终结果是取消中医。
最后可能的反驳意见是:A到C的推理导致中间的B悄然消失了,但以中医为本位的研究,应该以B为中心,中医“实在化”并不是想通过C来对标A,而是希望通过C来对标或解释B,这样对理解、判别、标准化B有帮助[3],但这种反驳是掩耳盗铃。只要研究定位在中医,那么由人体现象推知证候即A到B的过程就必然存在,没有这个过程B也不会存在,就更没有B和C的关系,中医“实在化”将重心放在B和C并不代表A和B的关系就消失了,A和B的关系一直在那里,A通过B为桥梁形成的A和C的关系也一直都在那里,以B的消失反对探讨A和C关系的观点是掩AB之耳盗BC之铃的自欺欺人。如此,只要是中医“实在化”的思路,人体现象A和物理实在C之间的关系必然存在,而诚如上段所论证的,A和C的关系探讨必然带来与现实情况的悖论。关于以上悖论的论述见图1。

图1 中医“实在化”带来的悖论
以上悖论说明中医“实在化”是不妥的,只要以中医为本位,这条路是不可取的,为什么会产生以上悖论呢?根本原因在于中医“实在化”违背了中医现象主义的认识论原则,混淆了现象主义和实在主义。A和B关系的形成是基于现象主义的,B是在现象基础上形成的特殊的中医概念,中医“实在化”从B到C是想利用实在经验来对标或还原B及A和B的关系,因此,其是在用实在主义的认知方法来对标或还原现象主义的知识,将两种认知结果强行拉在一起。但在本文第一点理论基础中已经指明现象主义和实在主义是两种不同的认知路径,自成体系,不可混淆。当通过B到C的实在主义结果推广到A和C的关系以及A和B的关系时就会因为与原来现象主义认知内容的不相容导致与现实情况的悖论。中医“实在化”是想沟通中医和科学、西医学,或者为理解、判别、标准化中医理论提供帮助,但实质是混淆了两种认知途径,是不可完成的,如果一味如此走下去就会得出“取消中医”的结论。
3 中医“实在化”有损现象主义的独特优势
既然中医是现象主义的,那么中医“实在化”在一方面就是去现象主义的,一者如上文的讨论这有悖于中医的认知基础,另一方面这有损现象主义带给中医的独特优势。现象主义在认识论上的优势之一是整体性,一个事物的外在现象是该事物内部物理结构相互作用的整体表现,如人体出现发热、咳嗽,这些现象不只有呼吸系统参与,循环、神经系统甚至运动、内分泌系统等均参与,它是人体整个内部结构相互作用的综合反映,所以中医关注外在现象事实上就是关注了人体物理结构综合运动的整体[14]。西医由于只关注具体的物理实在,因此,它必然会对现象进行切割,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还原论方法[15],现象的切割必然带来整体信息的遗漏。对一个巨系统、复杂系统来说,我们根本难以完全研究清楚里面所有的结构和关系,发热、咳嗽的表现,如果去询问西医专家,他们没有能力告诉我们这些现象的发生在人体内到底有多少物质结构参与以及其所有的机制,但整体的现象却包含了所有。因此,对事物整体信息的把握是现象主义独特的优势之一,以此为认知途径的中医继承了这一优势,这是科学、西医学不具备的,但中医“实在化”却是在丢掉这一优势,这是倒退。如湿邪对标的是整体现象,是对人体物质结构综合运动的说明,它如何能对标或还原为某种或某组物质结构?一边包含了所有物质结构,一边只是局部物质结构的说明,这根本不同,如何能将两者硬拉在一起?中医“实在化”不仅导致整体现象和局部实在的矛盾,还会因为丢弃整体现象的认知优势而损坏中医的真理性价值。
4 需要区分中医相关的“实在性研究”与中医“实在化”
虽然中医“实在化”不可取,但中医相关的“实在性研究”并无问题,如果反对后者,那很多成就就不可理解,如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青蒿素研究。反对中医“实在化”是站在中医本位的立场,在此立场就应该遵守中医自身的认识论原则,但假如前提不是中医本位的研究,就没有必要以中医的认识论为原则,我们完全可以在其他学科的指导下做与中医有关的“实在性”研究,这类似“中医研究”和“研究中医”的区别[16]。中医和西医的对象、目的都是人,两者对同一事物的研究必然有相通的地方,中医的理论和实践很可能对科学、西医学有启示,促进其取得成绩。关键是要定位清楚,是“中医研究”还是“研究中医”,平心而论作为“中医研究”主流的“实在化”有几个真正的重大成果?就实践而言有几个研究对临床有实际指导意义?反而一步步将中医带向深渊。如果是科学、西医学认识论基础的“研究中医”就只能是借鉴中医的理论或实践,不能囿于中医本位的东西,应该按照自身的方法深入挖掘,这样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就,而不是导致“四不像”。
5 中医真理性论证的必然途径
反驳中医“实在化”是本文的目的,但笔者更希望想通过本文表达对中医真理性论证途径的看法。文章开始提到的攀附科学、西医学之名引起的二律背反究其原因还是潜藏的真理观作怪,我们很多人或隐或显地将科学、西医学作为真理的代名词,即便是坚定认为中医是独立的,仍不免屈尊于科学、西医学的“真理性”,要打破这个魔咒必须在根子上纠正唯科学、西医学的真理观,论证中医学独特的真理性价值。当代西方哲学思潮之一已转向人本主义、非理性主义,而反中医者仍然陷于传统西方哲学形而上的理性思维基调评判事物;科学哲学也越来越厌弃实证主义,转向历史主义、多元主义、构建主义等,而反中医者仍以传统逻辑实证主义的基调来评判中医,我们的真理观该变变了!“实在化”中医被很多人作为现代化中医、规范化中医的途径[13,17],这暗示中医的真理性需要以此求得,通过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这条路是走不通的。那中医的真理性该从什么地方求得呢?答案在中医的认识论基础中。本文对“实在化”中医的反驳是根本彻底的,这种彻底性来源于对认知基础的剖析,认识论在根本上决定了学科的思维、方法,一旦基础出现问题整个学科体系都可能会崩塌,所以一门学科的真理性根本反映在认识论上。我们并不缺乏有说服力的中医有效的证据,如调理气血类中成药在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therosclerot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ASCVD)防治中的有效性[18],如“经穴效应特异性循证评价及生物学基础研究”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9],但这并不意味科学、西医学会承认中医,因为中医的认知方法仍然是被质疑的。尽管科学、西医的理论并不代表绝对真理,但他们始终认为自己的认识论、方法论是追求真理的唯一道路,而非此认识论、方法论的中医是被排斥的,因此,论证中医真理性的必然途径是认识论的途径。认识论的探究就必然需要研究本体论,有什么样的本体观就会有什么样的认识观。科学、西医学为什么是实在主义的,原因在于他们在本体承诺上将物理实在作为一切的本源,如果追根溯源又可追溯到古典西方哲学对“存在”的志趣,中医为什么是现象主义的,为什么要构建“虚拟”的东西,如湿邪来认识人体,原因在于它的本体观并不是物理实在。因此,要论证中医的真理性要回到认识论和本体论的途径。
6 结语
中医“实在化”存在的问题已被很多学者认识到,但其依然兴盛,这让我们深感焦虑,希望本文在认识论上彻底的反驳能帮助改观这一现象,更希望读者能从本文看到认识论和本体论是探讨中医真理性的必由之路,这才是一切的根基,深入于此才能真正发现问题、厘清思路、解决问题,是一切中医真理性论证及学科发展理论探究的照妖镜,是一切奇特学术现象的正身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