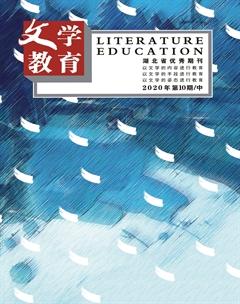浅谈汪曾祺《鸡鸭名家》
黄睿哲
内容摘要:《鸡鸭名家》这篇文章在汪曾祺先生的写作中具有重要意义,既反映了他文风的转变,又体现了许多“汪曾祺式文章”的典型风格,例如:语言朴实隐秀、人物灵动。无论是从叙述上还是人物塑造上看,都是一篇难得的好文。本文从叙述和人物两个方面,分析《鸡鸭名家》文字风格及产生原因,重点分析陆长庚这一人物形象,挖掘《鸡鸭名家》中的人物之美、人情之美、人生之美。
关键词:汪曾祺 《鸡鸭名家》 真善美
《鸡鸭名家》是汪曾祺先生于27岁创作的作品,亦是他“大器晚成”的“晚成”转变之作。
首先来谈叙述。
汪曾祺先生文字的风格,正如他自己在《岁朝轻供》中说的那样:“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可是在早年,他的文字也是张扬的、华丽的,《复仇》《职业》《老鲁》中都可见一斑,直到《鸡鸭名家》,才能够明显感觉到先生语言风格的趋淡,这种淡不是白水,而是像高汤一样,返璞归真,可清甘可醇厚,总之令人回味悠长。这里摘录《复仇》和《鸡鸭名家》各一段文字以示对照:
从山顶上滚下去,滚下去,滚下去,落进山下的深潭里。从极低的地方传来一声牛鸣。反刍的声音(牛的下巴磨动,淡红色的舌头),升上来,为一阵风卷走了。虫蛀着老楝树,一片叶子尝到了苦味,它打了一个寒噤。一个松球裂开了,寒气伸入了鳞瓣。鱼呀,活在多高的水里,你还是不睡?再见,青苔的阴湿;再见,千草的松软;再见,你硌在胛骨下抵出一块酸的石头。老和尚敲磐。现在,旅行人要睡了,放松他的眉头,散开嘴边的纹,解开脸上的结,让肩膊平摊,腿脚舒展。 ——《复仇》
小徒弟不放心,轻轻来问一句:“起了吧?”摇摇头。——“起了罢?”还是摇摇头,只管抽他的烟。这一会正是小鸡放绒毛的时候。这是神圣的一刻。忽而作然而起:“起!”徒弟们赶紧一窝蜂似的取出来,简直是才放上床,小鸡就啾啾啾啾纷纷出来了。余老五自掌炕以来,从未误过一回事,同行中无不赞叹佩服。道理是谁也知道的,可是别人得不到他那种坚定不移的信心。这是才分,是学问,强求不来。 ——《鸡鸭名家》
《复仇》的节奏是紧凑的,像快餐店里的用餐铃,一下接一下地响着,《鸡鸭名家》的节奏是舒缓流畅的,像柴火一点点、细细地烤着签子上的肉,偶尔翻个面,听小火“啪啦”“啪啦”的声音。
汪曾祺先生的文章朴实却不落于流水,与音韵和节奏的运用有很大的关系。《人间草木》中写道:“牛肝菌色如牛肝,滑,嫩,鲜,香,很好吃。青头菌比牛肝菌略贵。这种菌子炒熟了也还是浅绿色的,格调比牛肝菌高。菌中之王是鸡,味道鲜浓,不可方比。”,全段读下来就像唱了一首民谣,长短句相间,用词精确,朗朗上口。
如果说朴实的风格细水长流,朴实中的俏皮则足以撑起“隐秀”二字。
汪曾祺先生喜欢用问句,在这一篇中更是问了6遍“刚才那两个老人是谁?”,关于这点褒贬不一,有人觉得突兀累赘,有人觉得别有韵味,我更倾向于后面那种说法,倒不是说我“唯名家论”,而是这实在是与我小时候的生活太过贴合。《鸡鸭名家》中的“我”是一个不怎么机灵的憨小子,他的视角更像是一个小孩在发呆,胡思乱想,“我”先是思考“那两个老人是谁”,看到父亲在处理鸭掌,又想到了鸭掌,看到父亲活动着的手,又想到手,忽然又想回那两个老人,于是又思考,可是“我”看到鸭子又想到了买鸡鸭的回民、店主人的酒糟鼻、金彩绚丽的大公鸡……汪曾祺先生的文字结构很“随便”,所以读起来很像是在话家常,“在叙事中抒情,用抒情的笔触叙事。怎样表现倾向性?字里行间”。如此,反复问“刚才那两个老人是谁”就更像一个这种性格的小孩的风格。说到这里,汪曾祺先生自身在进行创作的时候,也是这种状态,在他小辈们写的《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中,就描写过汪曾祺先生创作时常常在字里行间发呆,呆痴“进去了”,如香菱学诗“精血诚聚”,一篇篇好文章就是如此诞生的。
《鸡鸭名家》里的问句还有结尾:这两个老人怎么会到这个地方来呢?他们的光景过得怎么样了呢?类似的结尾还有很多,比如《大淖记事》:十一子的伤会好吗?会。当然会!汪曾祺先生善用问句,旁人模仿起来只会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可是汪曾祺先生用起来却总能让人拍手叫好,原因在于先生文字中的俏皮“不着急”,因为“不着急”所以才显得真诚,驾轻就熟,不然实在容易落入“耍花招”之流。文如其人,这种文字风格与汪曾祺先生的个人经历与性格有关,先生的一生曲折、漂泊,但他依然认为“生活是很好玩的”,颇有“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之感。他不嫌弃栀子花“品格不高”,说它香得痛痛快快,不认为君子就应该远离庖厨,反而成为美食大家,高邮的咸鴨蛋因他一篇《端午的鸭蛋》畅销多年。哪怕是在改造时期,汪曾祺先生的文字(如《葡萄月令》)也是充满着对劳动的尊重、对自然的热爱,他亲自体验葡萄种植,化身“果农”,像养孩子一样记录了葡萄的成长。但这并不是说汪曾祺先生就是一个天生的“乐天派”,他展现给我们的淡然和灵性亦是在一次次生活的考验中积累下来的,在纪念沈从文先生的文章《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中,他说到自己想过自杀,而沈从文先生用一句话点醒了他:“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的确,有一支笔就会不怕什么,哪怕到了悬崖也有笔如刀,汪曾祺先生也确实做到了,并用自己的文字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人。
用先生自己的话来说:“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探索一个作者的气质、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态度,不是理念)。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语言具有文化性。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包世成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有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汁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便是汪曾祺先生的文字魔法。
其次来谈人物。
《鸡鸭名家》中写了两个人物:余老五和陆长庚。一个孵鸡,一个放鸭。二人都是名家。
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放鸭的陆长庚,人们也叫他“陆鸭”。他的出场实在特别,首先是倪二的鸭子丢了大家都推荐他,吊足了观众的胃口,其次镜头一转,在嘈杂的茶馆,大家找到了正在赌牌的陆鸭,讨价还价之后讲定了十块钱,又等他不慌不忙把牌打完之后才跟着倪二去了。
汪曾祺先生用很简洁的笔墨描写了陆鸭的外貌——瘦瘦小小,神情总是在发愁,就像一只成了精的老鸭,又说他已经多年不养鸭了,见到鸭就怕。这样的描写实在是不敢相信他是个靠谱的人,可等他到了湖,只见他“把船撑到湖心,人仆在船上,把篙子平着,在水上扑打了一气,嘴里啧啧啧咕咕咕不知道叫点什么,赫!——都来了”,等鸭子都到齐了,他又换了个强调唱,文文雅雅、摇摇摆摆,引导鸭子向岸边游来,舒闲整齐有致,就像用兵似的,落在了“和”字上。更精妙的是,陆长庚望一眼就能估算出鸭子的数量,望一眼就识别出了鸭群中有一只被裹来的老鸭,从众多鸭子中随手挑拣出最肥的,用手一掂就准确说出了数量。
陆长庚养鸭也爱鸭,疼到了骨子里,才拥有了与鸭对话的“魔法”,提及他不养鸭的原因,他说道是因为曾经的一场鸭瘟让他看着鸭子一只只在荡里死去,看着死,毫无办法。陆长庚说是“蚀了本钱”,可我认为对于他来说更像是失去了伙伴、也失去了骄傲。
陆长庚是“什么事都轻描淡写的”,帮倪二找回鸭子之后立马又拿著价值不菲的酬金赌钱,别人说他输得光光的,他回答“没有!还剩一块!”,汪曾祺先生在写这一段文字的时候也是“轻描淡写”的,就像是邻居来我家拜访,向我讲述他一个亲戚的故事,可是一个生动的陆鸭就这样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技艺精湛又活泼真性情,性格骄傲又常常自嘲,我想笑,可是笑不出来,于是也只能跟着文中的小孩问一句:“这两个老人怎么会到这个地方来呢?他们的光景过得怎么样了呢?”
返璞归真,足以见真功夫,温润纯净,足以见真性情,这是我对两位鸡鸭名家的评价,也是对汪曾祺先生的那一份“恰到好处”的笔墨的看法。从小人物落笔是先生文章的显著特色之一,从小人物里折射出的大时代,则是另一个话题。在这篇文章中,我且只将它读为一个故事,感悟里面的笔墨之美、人生之美、人情之美,止于亲和之中的敏锐,达于温情之上的通透。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