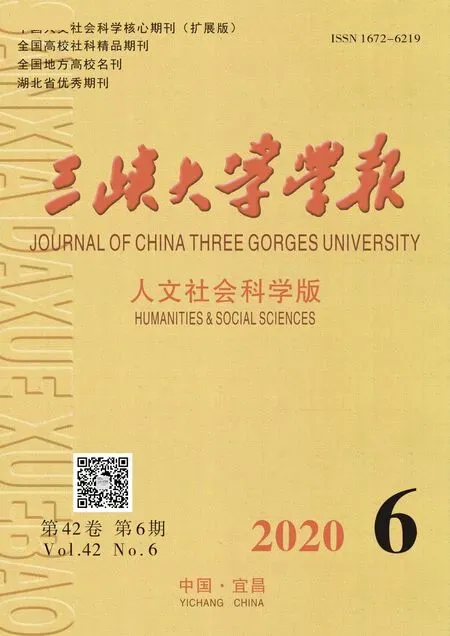论共饮人的注意义务
卢以品, 李南萱
(三峡大学 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 宜昌 443002)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司法实践中关于共同饮酒行为引发的侵权损害纠纷日益增多,对于共饮人是否应担责以及如何划分赔偿责任等一系列问题,裁判者均感到相关法律的缺位,导致出现裁判尺度不一的结果。为深入了解共饮致害纠纷实践现状,笔者进入中国裁判文书网,选择民事案件,以2015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13日的判决书为筛选条件,以共同饮酒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得到4708份裁判文书,笔者以这4708份裁判文书为样本进行了归纳分析。
通过表1可以看出,在样本判决中,3995份文书都判决共饮人承担责任,占比85%,仅有713份文书判决驳回原告诉请,共饮人不承担责任,占比15%。由此得出在共饮致害纠纷中,承担责任是常态,不承担责任是例外。那么共饮人为何要承担侵权责任?担责的依据是什么?在样本文书的裁判理由中,共有3874份裁判文书提到了注意义务(含安全保障义务),占样本文书的82%。其中,以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含安全保障义务)为由判决共饮人承担责任的判决有3381份,占比84.6%;而以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含安全保障义务)为由判决共饮人不承担责任的判决为493份,占比69%。也就是说,注意义务是共饮人是否担责的判断基础。鉴于安全保障义务属于广义范围的注意义务,故而本文只研究共饮人的注意义务。

表1 近五年共饮致害纠纷担责情况及裁判理由
基于对样本判决的分析,我们发现多数法院在共饮致害纠纷中过分考虑对受害人的救济,以未尽注意义务为由要求共饮人承担一定的责任,让公众产生诸多疑惑:共饮人注意义务与过错是什么关系?共饮人注意义务的来源是什么?共饮人应该如何履行注意义务以及该义务能否约定免除?上述疑惑对公众的正常交往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对公众的自由过于限制并加重其负担导致共饮致害侵权案件的滥诉。故有必要对共饮人注意义务深入剖析,为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和裁判标尺。
二、共饮人注意义务与过错
过错作为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在整个侵权法中享有重要地位,其决定了侵权责任最终能否成立。目前理论界对于过错如何认定有三种学说:即主观过错说、客观过错说、主客观结合说。过去的主流观点认为过错是一种主观的心理状态,但随着客观过错理论的发展,在过失侵权领域,对过错的认定大多采取客观标准,并将违法性与过错统一于注意义务的概念之下,借助行为人是否违反注意义务来认定过失的存在与否。
1.客观过错理论与共饮人注意义务
《民法典》第1165条①规定了过错责任原则,在对“过错”的认定上,过去主要是考量行为人主观方面是否存在过错,但随着侵权理论的不断发展,我们发现主观过错理论将民事过错等同于道德过错,而且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并没有衡量标准,很难把握,因此我们逐渐抛弃主观过错理论,对过错的认定采用客观过错理论。客观过错理论以某种注意义务为前提,指行为人在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时候,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行为人的“过错”就是指对该注意义务的违反。比如行为人明知在侵权法上应当尊重他人的某种民事权益,但其故意违反这种义务;或者虽然行为人不知道侵权法上要承担尊重他人某种民事权益的义务,但是在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时候,行为人客观上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从而构成《民法典》1165条所规定的过错。共饮致害纠纷中,对过错的认定即是考察共饮人是否违反注意义务的过程,共饮人是否存在“过错”是共饮人应否担责的基础,共饮人违反了注意义即是有过错,应对损害结果承担侵权责任。
2.共饮人注意义务来源于先行行为
共饮人担责的前提是共饮人存在注意义务,公众疑惑的是共饮人为何存在该种注意义务,其来源和依据是什么?注意义务的来源有法律规定、合同约定、习惯性规则、职业及业务要求、先行行为等等。对于共饮人注意义务的来源,理论界和实务界有不同的声音,总结归纳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共饮人注意义务来源于特殊关系。在邵某、汪某等与张某、顾某等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判决②中,对注意义务的来源表述为“同饮者在饮酒后,在具备某些条件的基础上,确实需要承担注意义务,该种注意义务是建立在特殊关系理论之上的。基于特殊关系理论,行为人需要承担起注意义务”。该观点认为在共同饮酒活动中,共饮人之间一般有着特殊的关系,相较于普通人之间更加亲密,共饮人通过饮酒相互了解,增进感情,从而有着相互信赖的基础。
第二,共饮人的注意义务来源于对信赖利益的保护。在杜某与朱某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判决③中,共饮人注意义务来源表述为“共同饮酒者相互之间基于聚餐饮酒的共同行为而产生合理信赖,该信赖利益应予以保护”。共同饮酒行为多是出于情谊而作出的,不论当事人内心的真实动机,一般情况下,共同饮酒当事人之间应是具有一定的信任的。基于此种信任,在共同饮酒过程中,受害人基于信赖利益认为其他共饮人在其醉酒产生人身危险时会保护其免受损害,当共饮人未保护其免于危险时,受害人的信赖利益受损,法律应介入对其进行保护。
第三,共饮人的注意义务来源于共同饮酒的先行行为。陈某与罗某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判决书④中载明了共饮人注意义务来源为“共饮人之间有提醒、劝阻、照顾、扶助、护送等安全保障义务,这些义务来源于先前的共同饮酒行为”。共饮人一般怀着增进感情的良好初衷一起喝酒,但却无意制造了一个可能致人损害的危险源,饮酒可能降低人的行为能力和辨识能力从而产生危险是一般常识,共饮人在引起相关风险时,也负有消除风险的义务。
笔者认为,共饮人的注意义务来源于共同饮酒的先行行为。曾世雄教授在《损害赔偿法原理》一书中谈到先行行为引发的义务,其解释为“行为人以法律规定和其约定原无作为之义务,惟行为人基于法律规范以外其他社会生活规范之要求而作为,因致直接介入他人生活资源之变动,从而衍生有使他人生活资源发生良性变动之义务。”[1]先行行为无论产生何种评价,只要行为人因自己的行为开启了一项危险,其就有阻止损害发生或将损害降至最低的合理注意义务。饮酒在增进共饮人之间的感情时,也引发并提升了饮酒人的人身和财产可能遭受损害的危险。共饮人因此有义务阻止损害的发生或在损害发生后履行救助义务。法律并不介入共同饮酒这个先行行为,但法律对共饮人引发危险后的不作为做出了否定的评价。如果共饮人在饮酒人醉酒后,未履行照顾、救助等义务,则被法律评价为不作为侵权。王利明教授在与东营法官的座谈中提及了共饮人注意义务产生的依据:“同饮者实施在先行为会引发一种在后的照顾义务,这一义务不是经济活动产生的,是一个在先行为产生的。喝过量的酒也不能说有过错,关键问题是当这个人喝多了离开时,一起喝酒的人就会产生一种义务,意识到他不能保护自己,可能引发损害或受到损害。”⑤饮酒往往导致饮酒者辨认控制能力下降,醉酒更是容易诱发各种疾病,饮酒不仅增加了人身财产所有的潜在风险,而且显著提升了驾驶活动和高度危险作业中的危险系数,醉酒造成的危险更为惊人。所以饮酒本身是一种危险活动,而共同饮酒行为往往是是此种危险的始作俑者,共饮人的劝酒、敬酒等一系列先前行为,使得被害人处于某种危险之下,那么共饮人因此有义务阻止损害的发生或在损害发生后履行救助义务。另外,“特殊关系”引发注意义务看似有些道理,好友之间饮酒的确存在一种相互交流感情、彼此信赖的关系,然而这种特殊关系并不是共饮人负有注意义务的根本原因,且不能以这种道德上的信赖作为民法上承担责任的基础。加之“特殊关系说”忽略了共同饮酒的共饮人之间可能素不相识的情形,互不相识的共饮者之间并没有感情上的特殊信赖关系,不可能因为共同饮酒就产生了感情上的特殊关系,共饮人相互之间也就不会产生注意义务。故而笔者并不赞同共饮人的注意义务来源于特殊关系。对于信赖利益保护说,笔者认为,共饮人之间仅是通过相约饮酒交流感情,又或是商业合作及应酬,彼此无特定法律意图,属于情谊行为,不由法律调整,更不会形成法律关系,亦不会基于信赖利益而产生法定义务。因此,对信赖利益的保护也不能成为共饮人注意义务的来源依据。
三、共饮人注意义务履行的判断
1.共饮人履行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
共饮人注意义务审查的核心问题是判断共饮人履行注意义务是否合乎标准和限度,而判断义务的履行是否符合标准的前提是确定共饮人违反注意义务的衡量标准。共饮人违反注意义务的衡量标准,既关系到侵权责任的构成,又能决定侵权责任承担的比例。这个标准只有平衡好受害人的权利救济和行为人的活动自由才算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标准偏高会导致注意义务泛化,共饮人承担责任畸重,引发公众恐慌并阻碍社会的发展;标准偏低会导致共饮人对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漫不经心,加重饮酒活动的风险,导致受害人的权利救济无法达成。
考察域外法违反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发现对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是由主观过错标准向客观标准转变的过程,目前不管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对注意义务的判断均采用了客观的判断标准,即“合理人”标准。“合理人”并不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真实的人,而是司法拟制的人,它是法律在去除了人与人之间性情、脾气、外形、思维、辨识、认知等方面差异后确定的具有社会平均水平的普通人,其具有普通大众所期待的理性和谨慎。普通人也会犯错误,但在过失侵权领域,只要所犯错误对社会影响较小,能够被公众接受和认可,就不能认定为违反了注意义务。在违反注意义务的判断上,以“合理人”为其假设前提,在英美法系被称为“理性人标准”,在大陆法系被称为“善良家父”标准。结合共同饮酒行为,共饮人在饮酒过程中都了解饮酒行为的性质及可能导致的后果,那么共饮人要对后果予以必要的关注,特别是在共饮人所实施的饮酒行为对他人可能引起损害的时候,就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防范。在确定共饮人履行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上,可以借鉴适用客观化的“合理人”标准,该标准能为参与饮酒活动的公众提供稳定、客观、合理的信赖基础,即只要尽到一个具有社会平均水平的人在相同的境况下能尽到的注意即可。但基于共饮行为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合理人”标准在共饮纠纷的适用中并不应该是一个完全的客观标准,在不同情境中共饮人对受害人的关注程度是不同的,所负担的注意义务也是不同的,该标准也应该对影响注意义务履行程度的有关因素进行考量,从而对“合理人”判断标准进行限缩或者扩张。“合理人”标准有两个不同方面的区分,一方面是根据共饮人和饮酒受害人行为性质进行区分,另一方面是根据共饮人的身份和饮酒人的行为能力进行区分。
2.“合理人”判断标准的微调
(1)依据共饮人和饮酒受害人行为性质确定“合理人”标准
共饮人在履行注意义务时,根据共饮人在饮酒活动中是否有不当行为,饮酒受害人是否有异常行为即是否处于醉酒状态,履行注意义务的标准有程度高低的区别。这里所指的不当行为,是共饮人劝酒、敬酒、在饮酒过程中非恶意的强迫饮酒,附条件的喝酒或者明知对方有疾病依然坚持要求其饮酒等行为。但是排除共饮人故意强迫饮酒或者借酒报复等行为,这种主观上故意通过共同饮酒侵权的行为已经进入刑事范围,在此不予讨论。另外,饮酒受害人是否处于醉酒状态的判断也是实践中的难点,由于个体体质的差异,每个人的醉酒状态可能表现不一,有的醉酒者喜欢大声喧哗,有的醉酒者表现出肢体不协调甚至有的醉酒者直接就睡着了,这些个体差异给判断醉酒状态增加了难度。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明确了醉酒状态的外观标准,比如说美国的酒店法认为如果个人表现出大声喧哗,且言行举止非常粗鲁,则可以认定为这个人处于醉酒状态。我们也可以借鉴国外关于醉酒的外观标准,当饮酒者开始大声喧哗或者出现口齿不清、举止粗鲁或异常、身体严重失调、沉睡不醒时可以认定为该饮酒者处于醉酒状态。
第一,共饮人无不当行为或饮酒受害人无醉酒状态时适用程度较低的“合理人”标准。在共同饮酒活动中,当共饮人文明饮酒,并没有实施劝酒、赌酒等等一些不当行为时,共饮人因共同饮酒这个先行行为所引发的危险较低,共饮人只要尽到程度较低的普通人所应该尽到的注意义务即可避免危险。在共同饮酒活动中,当受害人行为正常,没有呈现出醉酒外观的情况下,共饮人有理由相信受害人意识清醒,具有正常的辨识能力和行为能力,此时饮酒活动所产生的风险相对较小,共饮人只需尽到程度较低的“合理人”标准。此时如果课以共饮人较高程度的注意义务,违反了对危险的可预见性,对于共饮人来说是沉重的负担。比如在段某与赵某等健康权纠纷⑥中,段某在饮酒结束后并没有异常表现,其拒绝其他共饮人的护送而发生损害。判决书载明“在整个过程中,原告没有表现出存在醉酒、意识不清或者失去自制力的情况,原告明确拒绝三被告护送建议的行为使得三被告认为原告能够照顾好自己。本案三被告已经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与劝阻义务”。该案中基于受害人没有醉酒状态,考察共饮人注意义务的履行适用了程度较低的“合理人”标准,平衡了受害人救济和公众行为自由。
第二,共饮人有不当行为或者饮酒受害人有醉酒状态适用程度较高的“合理人”标准。在共同饮酒活动中,当共饮人实施了劝酒、敬酒、赌酒、强迫饮酒、附条件饮酒等行为时,说明共饮人有不当行为,其不当行为使受害人饮酒活动产生的危险性提高,为了防范危险后果的发生,应该提高共饮人履行注意义务的标准,适用程度较高的“合理人”标准,共饮人应该尽一切可能防止危险的发生。如果能够尽而未尽一个“合理人”应尽到的注意义务,就违反了注意义务。当受害人呈现出醉酒状态时,共饮人履行注意义务的标准要程度更高,因为处于醉酒状态的受害人,其行为能力下降、意识模糊,发生危险的可能性大幅度增加,此时共饮人的注意义务也相应提高,需要适用程度较高的“合理人”标准。
(2)依据共饮人的身份和饮酒人的行为能力确定“合理人”标准
第一,根据共饮人在饮酒活动中的身份区分,组织者、发起人、邀约人的注意义务程度高,参与者的注意义务程度低。首先,作为组织者、发起人、邀约人的共饮人是饮酒活动所致危险源的开启者,其负有除去或减轻危险影响的义务。在共同饮酒活动中,组织者对整个活动具有主导性和控制性,所以其应该比其他参与者更能预见潜在的危险,并且更能控制危险。其次,作为组织者、发起人、邀约人的共饮人理应对饮酒的场地和自然环境更加熟悉,因此在发生危险情形时,其能更有效的防范和脱离危险。最后,通常情况下,作为组织者、发起人、邀约人的共饮人对参与饮酒活动的饮酒人更为了解和熟悉,对其个性、酒量等情况的掌握决定了其能更好的控制饮酒活动产生的危险。因此,在司法实践中,组织者、发起人、邀约人履行注意义务应适用程度较高的“合理人”标准。
第二,根据饮酒人的行为能力区分,饮酒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时,共饮人适用程度较高的“合理人”标准;饮酒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时,共饮人适用程度较低的“合理人”标准。当参与饮酒活动中有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时,其他共饮人的注意义务程度相对提高。虽然法律禁止未成年人酗酒,但实践中也有与未成年人共饮而产生损害结果的实例,在蔚某与晏某、彭某等健康权纠纷⑦中,蔚某系未成年人,属于法律规定的不能饮酒的人员,但共饮人对其饮酒行为并未进行制止,在其过度饮酒后也没有尽到高程度的注意义务,因此共饮人需要对损害结果承担责任。在饮酒活动中,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缺乏对饮酒活动所产生的危险的认识,更没有对危险的防范和控制能力,因此,在饮酒过程中,共饮人不仅要制止其饮酒行为,更要高度注意其人身安全,履行最大程度的注意义务。在共同饮酒活动中,饮酒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时,共饮人履行注意义务的程度就相对前述较低,因为其应当知道饮酒可能引发的风险、自身的身体状况以及对酒精的耐受程度,因此在饮酒过程中其自身要控制好饮酒行为,对自己的人身安全尽到最高注意义务,其他共饮人在该饮酒人陷入危险境地时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即可,并不要求其他共饮人像照顾未成年人一样尽到高程度的注意义务。
四、共饮人注意义务与自甘风险
随着共饮致害案件的不断增多,发生参加喝酒人员死亡,满桌人都要赔偿的案例导致公众对于聚会饮酒已经是人人自危,担心共饮即担责,于是出现了喝酒签承诺书、责任书、免责声明的现象,而承诺的内容基本都是“本人承诺,如因饮酒造成本人及他人的损害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与聚会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无关,本人及家属不得追究组织者和参与者的任何责任”,饮酒人希望这种通过此种方式来免除其注意义务,继而不承担侵权责任。那么这种承诺书、责任书、免责协议能否适用自甘风险免除共饮人的责任承担呢?
《民法典》第1176条⑧新增了关于自甘风险的规定,但仅仅将自甘风险的适用限定在文体活动中。当前法律背景下的自甘风险规则主要是解决自发性体育活动以及体育教学活动中发生的损害问题,共饮致害纠纷并不符合自甘风险的适用范围。考察域外法发现英美等国家在自甘风险的适用中并未局限于体育活动领域,而在《民法典》草案二审稿中自甘风险规定为“自愿参加具有危险性的活动”,后因有意见认为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范围不宜过宽,致使自甘风险在《民法典》中仅在文体活动领域试水,那么未来随着自甘风险规则不断丰富发展,扩张到其他具有风险的活动领域也是不无可能。结合本文研究的共饮致害领域,抛开《民法典》对自甘风险适用范围的限制,探讨共饮致害纠纷引入自甘风险规则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共饮免责协议引入自甘风险的必要性分析
首先,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援引自甘风险理论进行裁判的领域有体育活动、好意同乘、进入危险领域、共同饮酒等等,其中体育活动的占比最大,因此在引入自甘风险规则时谨慎起见,仅限定在文体活动领域。类比文体活动所产生的风险,共同饮酒也是一项会产生风险的危险性活动,饮酒会降低人的辨识能力和行为能力,酒后驾车的危险系数也会大幅增加,饮酒人明知饮酒活动的风险而自愿参加,符合自甘风险的基础条件。在司法实践中,确有在共饮致害纠纷中适用了自甘风险的相关案例。比如林某、王某与周某、鲍某侵权责任纠纷案⑨中,法官认为死者潘某与林某等共同进餐期间大量饮酒,程度达到醉酒状态,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自己的年龄、身体健康状况、酒量以及饮酒后身体反应等应有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明确和清醒的认识和判断,其首先应对自身安全负责,但其却放任自己的行为,违反法律相关规定,在醉酒后且无驾驶证的情况下驾驶无牌照摩托车,是导致不幸后果发生的根本原因,死者潘某的行为系自甘风险的行为,应对自身的死亡承担责任。该案适用自甘风险,免除了其他共饮人的责任。因此,在共饮免责协议中引入自甘风险规则有现实的迫切需要。
其次,从免责协议本身来看,关于共饮免责协议的效力,目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王泽鉴教授认为“因侵权行为而生的损害赔偿责任,原则上得预先合意排除或限制之。此项合意得由当事人明示或默示为之。”[2]其认为侵权领域也可以约定免责。梁慧星教授恰恰与王泽鉴教授的意见相左,其对此的观点是“侵权行为法在性质上属于救济法,是人民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的民事救济手段,因此属于强行规定,不允许当事人以约定排除其适用。”[3]其依据是《合同法》53条的规定,约定人身损害免责的生死合同属于绝对无效。基于共饮免责协议的效力争议和自甘风险免责事由并未得到制定法的认可,以往司法实践中并没有认可免责协议效力的案例。而在民法典时代,有必要将自甘风险规则引入,从而根据这一法定免责事由对免责协议的效力进行认定。否则,实践中的免责协议效力将得不到公正有效的认定,无法完成法律对公众行为的指引作用。
2.共饮免责协议适用自甘风险的可行性分析
第一,从理论层面来讲,笔者并不赞同前述“生死合同”绝对无效的观点,《民法总则》第118条规定债权产生的原因有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等,也就是说侵权行为产生的损害可以形成债权。作为私法,要尊重意思自治,在不损害他人的合法利益、违反公序良俗以及法律的强制性的前提下,当事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对债权债务关系进行约定,因此,侵权行为产生的债务也是可以约定免除的。免责协议不能免除侵权领域因故意和重大过失而产生的责任,因为免除这些责任有悖于立法的初衷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但对于一般过失和无过错责任,笔者认为是可以约定免除的。共饮致害纠纷中,共饮人未尽注意义务属于一般过失,共饮人约定免除一般过失导致的侵权责任,不应视为违反民法通则第106条的规定。法律虽然对一般过失做出了否定性的评价,但共饮人之间达成的免责协议对社会道德、秩序以及法律效果的危害较小,法律应该尊重共饮人之间自愿达成的协议。综上,笔者认为共饮免责协议并非当然无效。在共饮免责协议有效的前提下,引入自甘风险规则可以免除共饮人的侵权责任,更加符合意思自治精神和公众期待。
第二,从现实层面来讲,自甘风险的适用条件有:(1)从事活动具有风险性。风险性是指可能产生但是并非一定产生损害后果。(2)主体上的适格性。行为人须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能够预见危险的存在,对风险有认知和选择。(3)行为人明知和自愿。行为人明确知道参与该活动存在一定的风险,仍然自愿参加。(4)从事活动具有合法性和利益性。行为人的风险活动不能违背社会善良风俗及道德伦理,且行为人为了获得某种利益而选择进入危险,其不是为了履行道德或法律义务而承担风险。结合自甘风险的适用条件,笔者认为共饮免责协议可以适用该规则:(1)饮酒人对饮酒行为所产生的风险明知。(2)基于对未成年人饮酒的禁止,饮酒人一般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3)饮酒人明知风险的内容和后果仍然以明示或者默示的方式自愿选择参与饮酒活动。(4)饮酒活动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且共同饮酒大多出于增进感情、达成合作等情谊目的。
虽然共饮免责协议可以适用自甘风险规则,但并不是任何免责协议都可以达到免除共饮人责任的效力。共饮免责协议的有效应符合以下形式和实质要件。
免责协议的形式要件有:(1)免责协议的内容应为承诺人和共饮人知悉,对于放弃权利的部分应该重点标注,必要时做出说明;(2)免责协议必须是书面的,免责条款内容明确清晰。
免责协议的实质要件有:(1)饮酒人的承诺分为三部分:首先是自己文明饮酒,对自己的饮酒行为负责;其次是对自己身体无不适宜饮酒的疾病进行承诺;最后是对饮酒发生损害后的责任承担进行承诺,这里有一个限制条件是其他共饮人并没有强迫其饮酒,也就是说如果其他共饮人不文明饮酒,有强迫、劝酒、拼酒等行为时,并不免除其他共饮人的责任。(2)免责协议并非饮酒人单方的承诺和声明,不仅需要承诺人签字,还需要其他共饮人知悉协议的内容并签字确认,同时为了约束饮酒人以及后续损害发生后的处理,需要饮酒人的家属知悉协议的内容并签字确认,以免出现损害后果发生后受害人家属作出并不知悉协议的抗辩。
自甘风险作为一种免责事由主要适用于过失侵权领域,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王泽鉴先生认为“自甘风险的含义是,伤害或者损失发生前就知道会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却自愿冒险行事,像在搭顺风车时就知道该司机是酒后驾驶还同意上车。”[4]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高密度的社会交往导致发生危险的概率不断增加,当然风险也和机遇共存,只有鼓励人们积极参与,社会才能不断发展进步,所以自甘风险作为正当免责事由应该为法律所认可。未来随着自甘风险规则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笔者建议在《民法典》的修订中将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范围扩张至共饮领域,从而在共饮免责协议中引入自甘风险免责事由,为共饮人注意义务的免除找到出口。
五、结语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我国的饮酒文化亦是如此。传统饮酒恶习的确应该摒弃,但司法的谦抑性决定法律不能过度干涉人们的正常交往和生活。在共同饮酒行为中,应该倡导文明饮酒的风气,人与人之间应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以避免和减少损害的发生。同时,引入自甘风险规则谨慎的认可共饮免责协议的效力才能为责任的免除找到途径和出路,符合公众期待,亦能达到公众行为自由和受害人权利救济之间的平衡。
注 释: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② 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2民初7569号民事判决书。
③ 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2019)浙0281民初542号民事判决书。
④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2018)鄂0506民初1915号民事判决书。
⑤ 王利明.司法实务中的若干侵权法问题——与东营法官的座谈.https://wenku.baidu.com/view/99a262eb172ded630b1cb663.html.访问日期:2019年12月5日。
⑥ (2015)晋法民初字第508号民事判决书。
⑦ (2016)陕07民终1157号民事裁定书。
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6条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⑨ 参见井研县人民法院(2015)井研民初字第884号民事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