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同学陆迪森
刘天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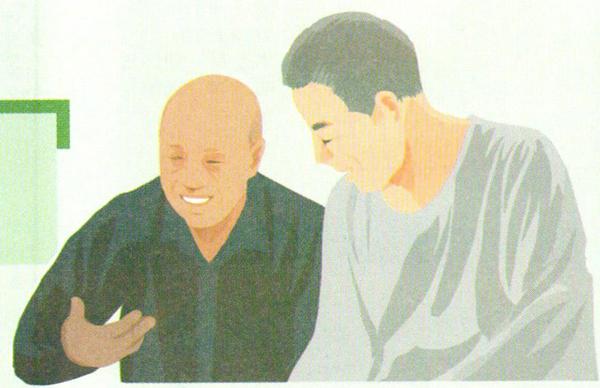
在我记忆的宝盒里,求学阶段的记忆居多,特别是中学时代。但春秋更迭,日月穿梭,那些记忆大都已打上了马赛克,唯独我的同桌却历历在目,清晰得如同分别在昨儿个。
他叫陆迪森,有人打趣儿,舌头一滑,就叫成了“鲁智深”。他一头小卷发,晒得微褐的肤色,焕发着青春的光泽。然而,由于他在操场上耗时太多,文化课落下了。初三学年开学,体育老师将蹲过两次班的他领到我的跟前,说:“你们做同桌。你这学习委员,应该帮帮咱‘体育功臣的文化课。”说他是“功臣”,实不为过。市铅球、铁饼的比赛纪录都是他保持的,学校三年连获桂冠,他功劳最大。体育老师接着说:“你文化课虽然都是优,但体育没成绩,升学——”我腿有残疾,体育课是“站客”。“看你1.80米的身高和150斤的块头,把铅球和铁饼练一练,有可能及格,让他帮你吧!”我在这“贴身教练”的精心培训下,不到半年,这两项竟都达“优”了!
初中最后一个学期,慈母般的语文老师调走了,来了一位严厉的山东大汉,姓韩。我这课代表,都有些怕他。
又是一堂语文课,提问的是前天讲过的语法——状语后置。同桌被叫到了黑板前,声音弱如蚊蝇地说:“我,我没搞明白。”老师用手拂掠了一下他的卷发,说:“小头儿倒是搞得挺明白的,又是钩儿,又是圈儿的。”前排一小男生说:“是他爸整的。”正好赶上下课,同桌回到位上,趴在桌上哭了。我也替他难过,壮了壮胆子,跟着老师进了办公室。“有问题吗,课代表 ”“您刚来,有些情况还不了解,我同桌的头发——”“不是说,他爸给烫的吗?”“不,那个男生是想告诉您,他的卷发是天生的。”“那他爸——”“是原住民,”我回答,“十年前,出海打鱼遇风浪,再也没有回来,家里只有母亲,重活全靠他。这几天刨冻粪,手都肿了,裂了,笔都握不住。”愧疚在老师的脸上迅速蔓延开来,他对我说:“把他叫来,快!快!”
同桌来了,怯怯地在老师跟前垂手而立。韩老师说:“看看你的手。”同桌摊开了双手,
正如我所言,肿了,裂了,还渗出了血。老师突然抓起他的两手朝自个儿脸上击打,因为来得太突然,同桌没反应过来,一只手还是落在了老师脸上,待明白过来把手都抽回来时,老师竟用自己的手,左右开弓:“我真浑啊,你会恨我一辈子的。”同桌“哇”的一声哭了,忙抱住老师的头,说:“不会的,我知道您是为我好……”这一幕,让办公室里所有的老师泪下。特别是韩老师近旁的代数老师,都哭出声来了,她拉开了抽屉,拿出一盒手油,让我转交给同桌。上课铃响了,她说:“下一节是我的课,可这眼泪老也止不住,这课咋上啊?”韩老师说:“正好,换给我,我有话向学生们说。”
韩老师在课堂上向我同桌公开道歉,且号召同学们帮他干干活,补补课。我同桌的知识状况尽是窟窿眼儿,但经师生们共同努力,他还是以高出录取分数线3分的成绩,上了高中。
我俩还是同桌,互帮互助,情同手足。但也有沖突——如何对待课外读物。有时我竟在课堂上看,特别是催眠指数爆表的历史课。一次,我在下边偷看喜剧剧本《金铃传》,有个情节差点儿让我笑出了声。同桌狠狠地掐了我一下,且当即把剧本没收于他的屁股下。下课了,他拿起剧本就朝校后的林子跑去。待我追上他时,已是一地碎纸!我暴怒:“你——”“你是我弟弟!”他也暴怒了,“将来,我们会像这片林子,都是有用之材,但差别会很大,像我升学无望,只能做个锹把,或椽子,或檩子,而你应该是栋梁!”说到这儿,他蓄在眼里的泪水,终于没控制住而溢了出来。“你要考文科,但文史是不分家的啊!”我低下了头,说:“哥,我错了。”揽着他的肩,朝教室走去。在同桌的监督下,历史没有拉低我高考的总分。
再次相见,都已年过半百喽。我从异地调回了家乡。我的头发稀了,他的头顶光了。我打趣儿:“当年若这样,就不会有韩老师的误会了。”他不以为然:“不,它让我遇上了一位好老师。每年开春,韩老师都回老家给我带来几千棵地瓜苗,那儿的地瓜品种好,收获季节,我家屋里屋外都是小孩枕头大的地瓜!母亲每年都喂出几头大肥猪,家境有了好转……”
“给我说说‘鲁智深劫法场吧!”这是家乡流传甚广的“水浒后传”。
他说:“‘文化大革命中,朋友密告,造反派要批斗韩老师!我那时是村民兵连连长,带上240余人,包围了会场。我手提狼牙棒,跳上了批斗台,‘咚咚咚戳了三下地板,说谁敢动韩老师一根汗毛,我立马让他生活不能自理!觉得还不够劲儿,又加了两个字‘永远!那个头头儿直接傻了。”我笑着说:“当年老师讲状语后置,你老不明白,你这‘永远,不就是状语后置吗?”“是吗?我说呢,当时老师的嘴角上挑了一下。哈!哈!哈!”他笑得那么开心,那么由衷,活像《水浒传》里的鲁智深……
(选自2020年6月21日《大连晚报》,有删改)
阅读点击
请分别概括陆迪森和韩老师的特点。
- 中学生阅读·高中·读写的其它文章
- 岁月
- 唐罐
- 去大城市读大学不是对乡情的“背叛”
- 杨梅时节的雨,简称梅雨
- 拾鹿角
- 西湖漫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