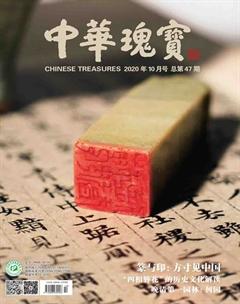卜居清旷以自娱
仲长统重视性命自然而轻视功名利禄的做法,给后世文人带来了深刻影响。谢灵运继承了仲长统对自然的赞美,尽力描摹静观中的山水之美;陶渊明则沿袭了仲长统对性命价值的强调,在耕作中体会返归自然的快乐。
对于生活在汉末时期的人来说,生命的脆弱与无常,现实政治的颠倒与虚妄,是极为普遍的生存体验。这一时期,多次的党锢之祸,击碎了理想的清流之声,也带来了许多境遇陡转的人生遭遇,人在追求建功立业之际阻力重重,流传声名竟多靠傲骨而非才能。频繁的灾异,蔓延的瘟疫,又将人时时抛到无法躲避的死亡面前,接受着面对环境变化之时唯有臣服而无反抗之力的事实。
在这个独特的时代里,士人多有忧生之嗟。魏晋诗文体现出了强烈的时代特质,既有悲怆的慷慨之歌,在直面现实的基础上振奋希望;也有华美的馥丽之辞,尽力描摹着生命的美好瞬间。在诸多的才子名士之中,仲长统拥有一抹独特的色彩,他不仅对时代之殇不以为苦,还留下了著名的《乐志论》。这体现了他思想中鲜明的特色,也在后世引发了诸多回响,值得细细品味。
息四体之役
仲长统在《乐志论》中首先描绘了一种理想的隐居生活:
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步涉之难,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珍之膳,妻孥无苦身之劳。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则烹羔豚以奉之。踟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后汉书·王符王充仲长统列传》)
居住在远离世俗政治权力场域的自然之中,以一种完全符合休养生息的方式生活,闲时招待良朋好友,祝日敬奉祖宗神灵。平日里或在自然中嬉戏,或在房屋中休憩,或与达者论道,或以琴音自娱,无一不是陶冶情志并怡然自得的状态。
这种对隐居生活的描写,在思想上自有渊源。早在先秦时期,孔子便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感慨,并指出了“无道则隐”的待时之道。崔篆在《慰志赋》中也感慨道“遂悬车以絷马兮,绝时俗之进取。叹暮春之成服兮,阖衡门以埽轨。聊优游以永日兮,守性命以尽齿。贵启体之归全兮,庶不忝乎先子”,希望能退隐守性。冯衍在《显志赋》里表达了类似的归隐思想,他在自论中谈道:“年衰岁暮,悼无成功,将西田牧肥饶之野,殖生产,修孝道,营宗庙,广祭祀。然后阖门讲习道德,观览乎孔、老之论,庶几乎松、乔之福。上陇阪,陟高冈,游精宇宙,流目八纮。”他自以为年暮无功,故而想要归隐田园。而在田园中,既能感受到松乔之福,又能体悟到宇宙之精,足以慰志。
东汉张衡所作的《归田赋》,对田园景色的描写尤其动人:“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鸧鹒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尔乃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他描绘了一幅生机勃勃的田园景象,这其中既有万物生灵,也有游玩之乐,与仲长统对田园生活的描绘已经十分类似,都交织着自然与自身的情志。
上述诸位士人,并非是出自对田园生活的热爱而选择归隐,而是因“道不行”而做出的无奈选择。崔篆自悼于“受莽伪宠”的经历;冯衍不得已闭门自保;张衡相对积极,却也有“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的自愧之辞。他们都是在建功立业不成的情况下,才将视角转向田园,以田园之乐来抚慰心绪,缓解无法为现实政治做出实际贡献的痛苦。
仲长统却不一样,根据《后汉书》的记载,他本来就有“狂生”之名,对现实政治参与兴趣不高:“常以为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扬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他从根本上否认了参与现实政治的意义,认为这不过是求名的手段,而名声本就是虚妄之物,在短暂的人生中,应该要尽情取悦自己。正因如此,他对田园生活的描写,丝毫不带自怜身世的情志之叹,而是用饱含审美愉悦的心情,赞美归隐生活的自在优游。相比于上述士人的挣扎,仲长统显得轻松而笃定。他以愉悦的笔触,将归隐生活的乐趣描绘得十分详尽,引人入胜。
永保性命之期
实际上,仲长统的这种自在状态,和他重视生命的价值观念有关。他在《乐志论》结尾处谈道:“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在建功立业和逍遥自得之间,他坚定地选择了后者。他认为前者只会带来无尽的烦恼,以及不可能实现的虚妄执着;后者却能让性命复归自然,得以保全自身,增加生命的长度和本身的质量。
他这种重生的心态在汉代十分普遍,汉代士人对长寿说持有普遍接受的态度。仲长统在《乐志论》里谈到的“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便是一种当时流行的吐纳之法。因为汉代人没有普遍接触到后来的佛教轮回观念,他们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多以求得长生、复归自然为努力方向。仲长统便接受了这样的价值观念,并且坚定不移地实施着。其实,在现实中建功立业所求得的名声,固然并非如金石一般永存,但也自有其意义。彻底放弃进入现实政治的努力,转而求得生命长度的保全,背后隐含的,是对求名不朽这种价值观的彻底否定,而代之以性命至上的观念。
通过建功立业来立身扬名的观念,来自于先秦“三不朽”之说。《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提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无论是立德、立功,还是立言,都是士人用以确定自身价值,并使得自己的性命以名声来延续的方式。这种以建立功业为手段,以追求后世声名为目的的心态,在汉代长时间激励着士人努力奋进。
直到仲长统的时代,曹丕仍在《典论·论文》中以“文章不朽”而“声名自传于后”来鼓舞文人自立自强。但仲长统对此种思路不以为然,他毫不留情地指出名声的虚妄,将视角牢牢锚定在短暂人生的快乐之中。怡情养性,吐納养精,用一种符合天道的方式生活,才是他认为最高的价值。他对田园生活的细致描写,正是为了解构在现实中辛苦造作的虚妄。对他而言,生命本就短暂而脆弱,这是无须去对抗的事实。而我们要做的,只是尽可能地延长和充实这来之不易的一生,在天道的指导下,与自然愉快偕游。
但值得注意的是,仲长统理想中的生活方式,和物质基础密不可分。这种隐居是能够“舟车代步”,而无须“四体之役”的。也就是说,不会被生存本身烦扰。由此,也不需要进入世俗的权力政治中,去换得维系生存的物质条件。不论现实是他是否拥有较好的物质基础,起码在他的观念里,保身全性的重要条件,便是不被生存焦虑驱使。维持一种与天道自然相联系的生活,并不意味着就要亲自躬耕于田野,重要的是,要和现实的政治保持距离,让自己的内心在天道自然间遨游。
不羡帝王之门
仲长统的这种思想,在贵族兴盛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引发了回响。世族出身的文坛领袖谢灵运,便撰《山居赋》以回应当年仲长统描绘的理想。不同的是,谢灵运对景物的描写更加细腻,姿态也更加从容,“抱疾就闲,顺从性情,敢率所乐,而以作赋”。在疾病之中,仍舊能保有欣赏的姿态,“选自然之神丽,尽高栖之意得”,对所见景色进行了极度细致的描写,体现出非常高的审美水平。谢灵运在描绘的时候,基本上是以一种旁观者的欣赏姿态,如“其居也,左湖右江,往渚还汀。面山背阜,东阻西倾。抱含吸吐,款跨纡萦。绵联邪亘,侧直齐平”,这一类的描写比比皆是。其间充满了和谐的音韵与图像式的展现,将他眼中的美景细致入微地传达给了读者,让我们也跟随他游览了一番美好的山居景色。这和仲长统在描绘中嵌入自己对理想生活方式的展望略有不同。
陶渊明给出了另外一种回应。他不是一个贵族式的公子,在现实的政治中也没有得到价值性的回报,但他在回归田园之际,仍旧能描绘出田园生活的美好与乐趣。在《归去来兮辞》的开头,他就直言:“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在他艰难地劳作,“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之际,仍旧能发现“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动人场景,平实而朴素的生活被他描绘得格外温馨。这里有“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的静观之乐,也感发“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的情志流淌。通过一系列劳作与美好相交织的描绘,陶渊明让我们相信,即使保有“四体之役”的状态,心灵也仍旧能够感受到生命的种种美好,而获得自在逍遥。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仲长统重视性命自然而轻视功名利禄的做法,给后世文人带来了深刻影响。正因为性命宝贵,所以退隐不再是无奈之举,而是某种返回天道的方式。在这种与自然交接之际,价值自然而然产生,不再需要外在的功名利禄去证明。谢灵运继承了仲长统对自然的赞美,尽力描摹静观中的山水之美;陶渊明则沿袭了仲长统对性命价值的强调,在耕作中体会返归自然的快乐。正因他们都能从参与现实政治的价值焦虑中解脱出来,欣悦于“有风自南,翼彼新苗”的天地之德,才能有这“永保性命之期”“不羡帝王之门”的脱离樊笼之乐。
陈江月,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