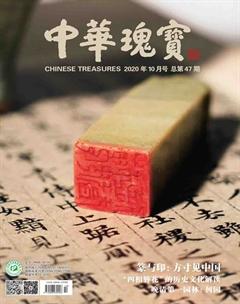方寸之地 气象万千
现代考古证明,在中国,商代便使用了印章,迄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中国的印章,原本的社会功能是“以检奸萌”。通俗一点说就是以“凭信”获取“防伪”的目的。帝王和大臣用它彰显皇权,百姓用它证明身份。在生活中,人们可以将它挂在腰间,此为佩印;百工将印记留在陶器、青铜器上,以表示制作者或作坊地,此为“物勒工名”;在系腰带的带钩上制作印章,谓之带钩印;将印烧烫后,在马的身上烙出印记,标明归属,谓之烙马印。当然,这些都具有“以检奸萌”的作用。随着其社会功能的发展,印章文化如同一种符号,延伸到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可以成为商标,也可以作为装饰,出现在镜子、紫砂壶、古琴、墨锭、青花瓷上……道不尽,数不完。钱行、伞行、纸行、箱包行到处都可看到印章使用的踪迹。
在以竹木简作为文字载体的时代,印章曾普遍使用于封检制度。写有政府公文的卷册,以泥封口,并在泥上加钤印章,这便是今日考古发现的封泥印的原由。印面文字反刻,抑压于泥上则成了正文,这一原理竟使印章成就了文明史上的创举。今天,人们不难在博物馆的陈列中,见到秦始皇为统一度量衡而颁布天下的诏书,俗称秦诏版。若是青铜质的量器,诏书则凿刻其上,然而陶质量器上的诏书,乃是用一方一方印章,四字一印,连续拼接而成全文。印面是反文,钤盖在陶器湿坯上则成为正文,经过烧制便不易磨损。毫无疑问,这一方方印章,可以反复使用,当可视为活字,而陶量上的秦始皇诏书则堪称活字印刷术的滥觞。尽管泥活字的使用要到宋代才出现,但细细想来,印章的使用原理正启迪了中国四大文明之一印刷术的思维。
在世界古文明中,印章并非中国的专利,也并非最早在中国出现。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有中国的印章在历史进程中从实用转向艺术,今天称之为篆刻艺术。汉代以后,纸张替代了简牍,印章封检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实用印章改变了往日的使用方法,以朱色涂于印面钤打在纸上,醒目鲜亮。当书画家、收藏家开始将印章钤于书画作品上,一扇通往艺术的大门被打开。唐代著名书画家、鉴赏家窦臮和张彦远,首先分别在他们的著作《述书赋》和《历代名画记》中著录了书画上的印章,精细地将公私鉴赏印章勾摹下来。尽管他们的初衷主要是在鉴赏中用于参照和防伪,但这种以印章图像著录的方式,既可视为印谱的滥觞,也可视为印章进入书画艺术的最初脚印。
文人画在宋代兴起,写意的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情怀。于是文人亦将其注入印中,歐阳修有“六一居士”印,取《集古》一千卷、藏书一万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加上自己髯髯一老翁之意。米芾则用典故入印成“祝融之后”“火正后人”印,以祝融为上古楚地之火神,隐喻自己是楚国后裔。他甚至还自己篆印—设计印稿,在他收藏的《褚摹兰亭卷》上,钤印多达七方,以示珍重。更有趣者,辛弃疾破其姓作“六十一上人”印,如同以印猜谜。据宋代著录记载,李公麟还在画上使用闲章“墨戏”。请注意,将印章玩出文人情趣来,自非工匠所能,这是艺术家的玩法。可见,宋代书画家手中的印章已经不仅仅只有凭信的意义了。
宋代的金石学兴起,金石图谱的刊行也大行其道。古印章原为金石的一种,自然亦被收集于金石图谱中,渐渐地从金石图谱中分离出了集古印谱,这种分离本身就说明印章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杨克一、王厚之、姜夔都曾辑有集古印谱。由南宋进入元代的赵孟頫也曾摹过古印谱,名曰《印史》。他在《印史》的序言中提倡汉印的质朴之美,而批评南宋风行的士大夫用印“合乎古者,百无二三”,流于习俗。他呼吁士大夫改弦易辙,走汉印的正道。这样的观点,即是篆刻艺术史上著名的“印宗秦汉”观。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自觉选择接受汉印美的宣示,也标志着文人篆刻艺术自觉时代的到来。
赵孟頫身体力行,他自己设计印稿,白文仿汉印,朱文则以小篆成元朱文。作为元代文化艺术界的泰斗人物,他以其广泛的影响力,使印章与文人书画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与宋人不同的是元人书画无不用印,而用印则均以赵孟頫的朱白文两种格局为本。元人张绅在《印文集考跋》中曾写道:“国初制度未定,往往皆循宋、金旧法,至大、大德间,馆阁诸公名印皆以赵子昂为法……其大小繁简,俨然自成本朝制度,不与汉唐金宋相同。……斯时天下文明士子皆相仿效,四方一律,可见同文气象。”尽管赵孟頫只能篆印而不能动手刻印,但这不影响我们判断赵孟頫影响下形成的篆刻艺术流派客观的存在。“四方一律,可见同文气象”,这是文人篆刻艺术史上的第一次,而这样的艺术流派长期以来却被篆刻史遗忘了。
在元代,推动文人篆刻艺术向前的代表人物,还有吾衍、吴睿、朱珪师徒三代人。元代后期的王冕与朱珪,一个用花乳石刻印,一个则用汉瓦刻印。他们已能自篆自刻。文人能自己操刀刻印,缘于印材的变化。这样的机遇,使文人不再借助工匠之手而可以随心所欲地创作了。风气渐盛,至明代中期正德、嘉靖年间,“天下已尽崇处州灯明石”(明·郎瑛《七修类镐》卷二十四《辨证类》)。处州,即浙江青田的古称,青田石作为印材的普遍使用,使文人篆刻艺术得以蓬勃发展。明代篆刻艺术最活跃的地区是苏州,吴门派书画家中,以文徵明、文彭父子贡献最著,他们继承赵孟頫的手法,“白登秦汉,朱压宋元”(明·周应愿《印说·成文》),尤其是文彭在篆刻艺术界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吴门书画家中如祝枝山、唐伯虎、陈道复、王宠、许初、王禄之等,于篆刻一道皆有时誉。于是文人治印竟成为时尚,风气波及南京、徽州、松江、嘉杭等地。
随后,明隆庆六年(1572年),上海顾从德辑成《顾氏集古印谱》,初印二十部,以原印朱钤,收入古鉨秦汉印1700馀方。又三年顾氏再以木板付梓大量刊印。于是在万历初年更掀起了摹汉印的热潮,时人称之为“举国之狂”。在集古印谱的带动下,摹古印谱、创作印谱也接踵问世,印人纷纷以此炫技。由此,职业印人的队伍迅速扩展,杰出者如何震、苏宣、汪关等受到文人的热捧。他们以刻印游走于文人士大夫间,士大夫则乐意为他们的印谱题序作跋,如王穉登、屠隆、李维祯、董其昌、李流芳等文化名人皆参与其中,并借此阐发关于文人篆刻艺术的观念。在这样的热潮中,篆刻家得以名世,印谱得以流传,印论也日渐成熟,如诗论、画论、书论那样,反馈于篆刻艺术实践,并涌现出一批杰出的篆刻理论家。晚明的篆刻艺术迅速攀上了高峰,与小说、戏剧一样,成为这个时代的骄子。
清代的徽派和浙派,是影响最大的两个篆刻艺术流派。前者是徽籍印人程邃所开,继者巴慰祖、胡唐等人;后者的领袖是杭人丁敬,继者蒋仁、奚冈、黄易等被称为西泠八家。清中叶后,邓石如崛起,以“印从书出”别开生面;受此启发,赵之谦更以“印外求印”,将印外金石文字引入印中。这二论在篆刻界影响深远,一时间吴让之、赵之谦、黄牧甫、吴昌硕、齐白石皆获益二论而登峰造极。这一时期的篆刻家大都身兼书家、画家、诗人,有诗书画印四绝的美誉。换言之,此时篆刻艺术的内涵品质已远远超过了前代。
1904年,在杭州诞生了历史上第一个篆刻家社团“西泠印社”,20世纪20年代,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则率先将篆刻课程设置于中国画专业中,这是篆刻艺术进入现代高等教育的起点。而今,全国的艺术院校经过多年的努力,大都设有书法篆刻专业。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以篆刻艺术为研究课题者,已不再是新鲜之事。印社遍布、展览频繁、学术研讨、印谱出版、国际交流都是篆刻艺术圈的常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篆刻艺术获得了新的、飞速的发展。这是了不起的进步,若起赵孟頫、文彭于地下而观之,必会惊叹大呼的。
印章上的文字是篆书,这种两千多年前的古老文字,早已不是人们日常的通行文字。令人惊讶的是,它却通过艺术的形式被保存下来,这正是文化史上的奇迹。篆刻家并不是古文字学家,但仅从识篆、写篆的能力而言,其队伍庞大,且后继有人,却是世界上各种古文字研究史上不可想象的事情。为此,我们更当发展、保护、珍惜篆刻艺术。
印章很小,戏剧或古装影片中的印章多是夸张了的。不过,它承载的文化艺术的内涵却博大精深。印文化、篆刻艺术的外延,其实并不止于与书、画、诗的交相辉映,设计者借印之美,可将“中国印”作为会徽,在北京奥运会上大放异彩;考古者可因印文之释读,确认海昏侯古墓的最终归属……印与历史、地理、考古、民俗、宗教、经济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并不是这篇短文可以展开的。若问印有多大的文化容量,古人云:方寸之地,气象万千。我想,这当是最贴切的表述。
黄惇,南京艺术学院教授,西泠印社理事,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