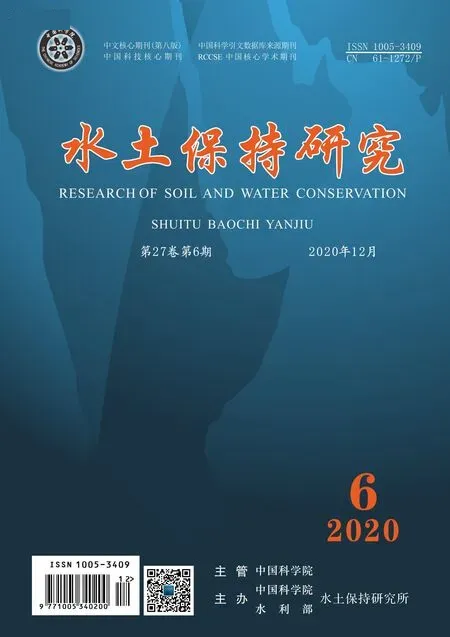基于GIS的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陶金源, 张孟楠, 徐 磊, 张蓬涛, 张俊峰
(1.河北农业大学 国土资源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1; 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3)
乡村聚落是社会、经济、资源与环境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复杂地域系统[1],也是乡村地区实现农村发展和人口集聚的重要空间载体,其结构、规模及形态等特征能够揭示特定地区不同发展条件下的人地关系。作为居民生产、生活的重要活动场所,乡村聚落的形成和发展受到自然背景、区位条件及基础设施状况等因素的强烈约束,环京津贫困带作为典型连片经济欠发达地区,乡村聚落演变呈现出与一般区域不同的发展规律和空间状态,乡村转型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挑战,亟需开展乡村聚落格局演变规律的相关研究,为贫困地区乡村聚落空间优化及京津冀协调发展提供科学精准的决策依据。
乡村聚落不仅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人地关系地域体系的重要研究领域[2]。国外关于乡村聚落的研究早在19世纪末就已开始,研究成果多集中在乡村聚落概念[3]、分类[4]及空间结构方面[5];而针对乡村转型发展的研究较少,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地域发展[6]、经济社会重构等方面[7]。由于我国受重城轻乡思想的影响,乡村聚落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主要从乡村聚落的内涵与类型开始进行探讨[8-9]。随着国家乡村发展政策的驱动,国内学者扩展了乡村聚落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乡村聚落的识别方法[10]、类型划分[11]以及发展程度上不断探索[12],如文琦等以乡村振兴战略与扶贫攻坚为切入点,构建了乡村地域村落空间类型识别体系,并提出了多层次、多维度的乡村振兴模式[13]。随着乡村聚落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利用GIS空间技术[14],结合缓冲区分析[15]、空间叠加分析及样带分析等[16],对乡村聚落的空间形态特征及演变的驱动机制进行了探讨[17]。如杨忍以遥感数据为基础,定量识别广东省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主导因素,并归纳了乡村聚落演变及重构的机制框架[18]。此外,随着乡村地理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国内学者关注重点逐步从乡村聚落空间分异转移到乡村聚落整治与空间优化研究上[19-20]。如梁发超等基于“居住场势”理论,结合三维空间分类法进一步设计了乡村聚落景观空间重构模式[21]。
总体而言,国内外关于乡村聚落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主要呈现以下特征:在研究区域方面,已有研究大多聚焦在县域、镇域和村域等小尺度范围,以城市群、省域或特定连片区等作为研究对象的较少;在探究乡村聚落空间关联的方法上,大多运用传统回归模型分析乡村聚落空间关联性,缺乏对空间依赖性及空间相互作用影响的综合考虑。基于此,本文选取环京津贫困带为研究对象,以乡镇为研究单元,利用GIS技术与景观格局指数等,定量分析2005年与2015年乡村聚落空间分异特征,并引入空间依赖性理论,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探讨乡村聚落空间集聚特征,利用空间计量模型解析乡村聚落分布的驱动机制。为构建区域协调的城乡发展路径,推动经济欠发达地区脱贫致富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关于“环京津贫困带”的相关研究较多,但学术界对其边界与范围尚未形成统一标准,在不同视角下所包含的区域并不一致,本文主要的参考依据有:《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提出的亚行标准、《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提出的国家级贫困县标准以及《燕山—太行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提出的集中连片贫困县标准。依据前人的研究基础,本文设定环京津贫困带是:在空间分布上与北京、天津两市存在较强相互关系,并且集中连片呈“C”型的带状区域,共28个县(区),该区域横贯东经113°45′—119°26′,纵跨北纬38°26′—42°30′,总面积8.48万km2,约占河北省总面积38.9%;地势由西北向东南逐渐降低,地貌类型主要为高原、盆地和丘陵。这些县大部分为国家级或省级贫困县,地理区位特殊,是京津地区防风固沙的天然屏障与重要水源供给地。
截至2015年底,环京津贫困带全年生产总值达2 334.726 9亿元,第一、二、三产业的贡献率分别为21%,43%和36%。人口规模900.72万人,其中乡村人口占93.87%。2005—2015年,环京津贫困带取得一定发展,城镇化率达38.09%,但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均GDP2.72万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34.882 8亿元,约占河北省67.57%和5.09%,社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研究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京津冀2005年及2015年土地利用现状数据,以Land TM 和Landsat-8遥感数据为主要信息源,利用ENVI 与ArcGIS 软件解译所得,空间分辨率为30 m,用于获取乡村聚落斑块信息,分析乡村聚落空间分异特征及关联性。道路水系、城镇位置及边界矢量数据,源于国家地理信息中心1∶100万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数字高程数据(DEM),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http:∥www.gscloud.cn /),坡度数据由DEM原始数据提取所得;借助空间计量模型探析高程、坡度、城镇位置及道路水系不同因素与乡村聚落分布的空间相关性。
2 研究方法
2.1 乡村聚落空间分异指数构建
2.1.1 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用于反映要素空间分布特征和变化趋势,一般表现为每个输出要素由中心向外逐渐递减,区域边缘处密度值为0的趋势,核密度估计值越大,乡村聚落分布密度越大,公式如下。
(1)
式中:f(x,y)为位于(x,y)处乡村聚落的核密度估计;n为乡村聚落个数;h为平滑参数;K为核函数;di为位于(x,y)处乡村聚落距样本乡村聚落的距离。
2.1.2 景观格局指数 从景观生态学的角度出发,定量分析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的规模、密度及形状特征,揭示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景观格局。本文选择斑块数量NP、斑块密度PD、斑块面积CA、最大斑块指数LPI、平均斑块面积MPS、斑块面积标准差PSSD、景观形状指数LSI共7个指标,相关指数公式及含义见表1。

表1 景观格局指数公式及含义
2.2 空间统计学方法
2.2.1 空间关联测度模型 地理空间中几乎所有邻近地区都具有空间依赖性或空间相关性,通过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可以从单一数据中发掘临近单元空间属性自相关性与集聚演变规律。
(1) 全局自相关指数。全局Moran′sI指数用于反映乡村聚落空间关联特征,分析乡村聚落分布是否出现集聚现象,
(2)

(3)

(2) 局域自相关指数
(4)
局部Moran′sI指数用于判断乡村聚落处于高值聚类区还是低值聚类区,能够直观展示乡村聚落在研究区域内空间集散特征,其参数含义与全局Moran′sI指数相同,同样需要进行Z值检验。
2.2.2 空间计量模型 传统回归模型往往欠缺对“空间”因素的考量,而乡村聚落时空分异的形成又与“空间”因素密不可分。因此,本文引入由传统回归模型派生的空间计量回归模型:空间滞后模型(SLM)与空间误差模型(SEM),探求影响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变量之间的关联性。
(1) 空间滞后模型(SLM)。运用空间滞后模型探讨各变量在空间上是否存在溢出效应。滞后效应是指某一地域单元某种变量通过反馈效应与其周围单元相同变量之间产生的相互影响。
Y=ρW1Y+βX+ε
(5)
式中:Y为因变量;X为自变量;W1为因变量的空间权重矩阵;ρ为空间相关系数;β为自变量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ε~N(0,δ2In);δ为ε的方差;In为n维单位矩阵。
(2) 空间误差模型(SEM)。在该模型中,变量的空间相关性主要体现在误差项上,即当空间关联性来自于误差,而不是来自模型的系统部分时,称为空间误差模型。
Y=βX+ξ
(6)
ξ=λW2ξ+ε
(7)
式中:ξ为残差;W2为残差空间权重矩阵,其他参数含义参照空间滞后模型。
3 结果与分析
3.1 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时空演变特征
3.1.1 基于核密度估计的乡村聚落时空分异 运用核密度估计分析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时空分异特征时,搜索半径的选择对结果具有较大影响,随着搜索半径逐渐增加,结果表面更为光滑,但会掩盖密度结构;搜索半径不断减小时,结果表面变化呈现突兀不平的特征。首先,提取环京津贫困带各乡镇乡村聚落质心,借助ArcGIS软件中Kernel Density工具,经过多次试验,最终选定5 000 m为搜索半径,测度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核密度估计值,见图1。

图1 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核密度估计值分布
从核密度最大值来看,2005年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核密度估计最大值为0.23,2015年为0.33,说明相较2005年、2015年研究区部分区域乡村聚落数量明显增加。从空间分布来看,2005年与2015年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核密度估计值空间分布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均呈现东南部、西北部和中部区域核密度值较高、密集,北部核密度值较低、稀疏的空间特征,尤其是在张北、蔚县、易县形成了核密度高值区集聚;此外,乡村聚落核密度中心分布较为分散,两个年份的核密度中心未发生明显变化,核密度较高值区多集聚于平原和丘陵地区,而核密度较低值区主要分布于中、高海拔山区。由于受到海拔高度的限制和影响,环京津贫困带整个区域降雨量和气温呈现由西北向东南递增,尤其是冀北及燕山丘陵区等核密度高值区,温度较同纬度其他地区偏高、地势较为平坦、自然植被相对较少,有利于进行农业生产和生活活动,更适合规划和发展乡村聚落。
从空间演变来看,2015年出现新的密集区域均为原有高值区自身发展或向外蔓延扩散所致,西北部和东部的张承地区增长尤为明显。环京津贫困带作为沟通中原与北疆、连接东西发展的纽带,国家逐步推进“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要战略,并受到“京张”联合申办冬奥会的促进作用,环京津贫困带高速路网与基础服务设施不断完善,有助于形成区域内有辐射能力、有延伸能力的高值集聚区。
3.1.2 基于景观格局指数的乡村聚落演变 本文借助Fragstats软件,选取7个相关指标,测度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2005年与2015年景观格局指数,反映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空间规模与形态特征。具体景观格局指数计算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2005—2015年,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用地规模明显增加,斑块总面积由1.1979×105hm2增长至1.8020×105hm2,年均增长6.04×103hm2;斑块数量由6 579个增长至2015年的11 650个,年均增长507个;斑块密度由0.077 8个/km2增长至0.137 8个/km2,年均增长0.006 0个/km2。一方面,乡村人民扩大宅基地面积的意愿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断攀升;另一方面,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乡镇企业及乡村基础设施用地面积不断增加,使得乡村聚落用地规模呈增长态势。居住用地和建设空间持续扩张,新的乡村聚落不断出现,乡村聚落斑块总数量增加引起斑块总面积和斑块密度的增长,但增加的斑块规模较小、分散化趋势明显,导致乡村聚落斑块破碎程度高、平均斑块面积减少,平均斑块面积由18.207 6 hm2下降至15.467 6 hm2,年均下降0.274 0 hm2。景观形状指数能够反映乡村聚落形态的规整程度,数值越大表明聚落形状越复杂。2005年同2015年相比,环京津贫困带景观形状指数由100.858 8增长至142.083 4,说明该时期内乡村聚落斑块不规则性增强,形状趋于复杂,乡村聚落形成过程在空间上的发展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

表2 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景观格局指数
最大斑块指数和斑块面积标准差反映乡村聚落规模大小的差异,2005年与2015年相比,最大斑块指数由0.005 0上升为0.008 7,说明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发展整体上呈现蔓延扩张趋势,随着土地整治和“空心村”治理工作的不断推进,表现为破碎的乡村聚落斑块被更大斑块所覆盖或者相邻几个聚落斑块合并为一个新的、更大的斑块。斑块面积标准差由21.527 2 hm2上升为25.463 1 hm2,说明贫困带乡村聚落规模与平均规模之间差距逐步增大,即小斑块与大斑块面积之间差异越来越大,新增斑块面积偏离平均水平的程度越来越明显。
3.2 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空间关联性
3.2.1 乡村聚落全局关联格局 以环京津贫困带所辖乡镇作为空间分析单元,运用ArcGIS软件统计2005年、2015年各乡镇乡村聚落规模,借助Geoda软件的空间分析工具计算全局Moran′sI指数,并对结果进行显著性检验。从表3中可以看出,2005年全局Moran′sI为0.638 1年、2015年为0.529 0,且p值均小于0.01,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环京津贫困带全域范围内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呈正相关,且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态势,但这一集聚分布态势逐步减弱,乡村聚落空间分异性增强。

表3 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规模的全局Moran′s I指数与检验
3.2.2 乡村聚落局部关联格局 借助Geoda软件空间分析功能,采用邻接权重矩阵,生成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局部Moran′sI散点图。横轴为2005年和2015年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的面积,纵轴表示相邻各县乡村聚落面积的滞后值。根据横纵坐标将Moran′sI散点图划分为4个象限:第一象限(高—高型集聚)和第三象限(低—低型集聚),表示各县乡村聚落面积呈正相关关系;第二象限(低—高型异常)和第四象限(高—低型异常)表示各县乡村聚落面积呈负相关关系(图2)。
由图2可以看出:(1) 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分布大部分点落于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中,2005年和2015年点数总和分别为196个和156个,远多于落在第二象限和第四象限中的11个和13个。伴随旧村改造、新农村建设等政策推行,将原本零散分布或地处恶劣环境的乡村聚落实行迁并,新建乡村聚落有计划的集中布局,使得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分布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并呈正相关关系。(2) 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分布具有高值区和低值区集聚现象,且低值区占主导地位,占乡镇总数的21.33%。2015年同2005年相比,高值区和低值区乡镇数量均减少,落在第一象限乡镇数量由87个变为72,落在第三象限乡镇数量由109个变为84个。铁路、道路等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改变了乡村聚落空间扩展方向,可供乡村聚落规划选址区域增多,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异质性分布特征加强。(3) 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分布整体呈现集聚态势,但局部异质性增强。散点图中趋势线反映了区域空间自相关水平一般趋势,2005年与2015年大部分数据点在趋势线两侧分布,尤其是落入第二象限的数据点2015年比2005年明显向趋势线集聚,远离趋势线分布的数据点主要出现在第四象限。
为了更加直观反映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的空间集聚特征,进一步探索乡村聚落的空间关联情况,本文在Z值检验的基础上,借助ArcGIS软件将Moran′sI散点图绘制成LISA集聚图,见图3。

图2 2005年和2015年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分布的Moran′s I散点图

图3 2005年和2015年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分布的LISA集聚图
(1) “高—高”类型区的乡镇数据点落于Moran′sI散点图的第一象限内,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该类型区域主要分布在环京津贫困带东南部的涞水、易县、顺平、望都、唐县及曲阳县部分乡镇,以及西北部的沽源、尚义、张北及康保的部分乡镇,零散分布于逐鹿和蔚县的个别乡镇。该区内乡镇之间乡村聚落分布的局部差异小,2015年与2005年相比,乡村聚落高值区在空间分布上出现一定变化,西北部的高值区大幅度减少且呈现向南部蔓延趋势,东南部的高值区呈增加与减少并存趋势,其中曲阳县高值区增幅较为剧烈。
(2) “低—低”类型区的乡镇数据点落于Moran′sI散点图的第三象限内,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该类型区主要分布在燕山—太行山脉附近及坝上高原区。由于区内海拔较高、地形起伏较大,极易发生自然灾害,如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导致乡村聚落数量相对较少,且乡村聚落的规模也较小;从时间变化来看,2005—2015年乡村聚落“低—低”类型区明显减少,主要是人们在居民点选址中更倾向于地形条件好、基础设施完善的区域。
(3) “高—低”类型区的乡镇数据点落于Moran′sI散点图的第四象限内,存在显著的空间负相关。2015年同2005年相比,兴隆县平安堡镇、隆化县汤头沟镇以及围场朝阳湾镇从该类型区转为相关性不显著区,滦平县滦平镇与隆化县郭家沱镇则由“低—低”类型区转为该类型区,由空间正相关转为空间负相关。由于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相对密集的乡镇不断带动周边乡镇发展,致使乡村聚落规模增加,由“高—低”类型区转为不显著区。
(4) “低—高”类型区的乡镇数据点落于Moran′sI散点图的第二象限内,存在显著的空间负相关。2015年同2005年相比,唐县雹水村转为“高—高”区域,唐县迷城乡、蔚县蔚州镇、万全县第六屯乡、怀来县鸡鸣驿乡转为该类型区。该类型区乡村聚落分布规模差异较大,异质特征明显,在乡村聚落规模小的区域,其周围乡镇的乡村聚落规模大,从而形成局部异质的“冷点区”。
3.3 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
乡村聚落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其空间分布和格局演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各种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驱动乡村聚落空间系统的演变和发展。本文引入空间计量模型,从空间维度探讨影响乡村聚落时空分异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参考已有研究[22-23],本文选取各乡镇乡村聚落规模面积的均值(KD)作为被解释变量,以乡村聚落所在高程(DEM)均值、坡度(SLO)均值和乡村聚落距离各城镇(URB)、河流(RIV)及高等级公路(ROA)最近距离的均值作为解释变量,并标准化处理所有变量。基于Geoda软件平台的空间依赖性检验,根据Anselin提出的模型判别准则选取模型,结果显示空间误差模型(SEM)优于空间滞后模型(SLM),更适合判断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分布与影响因素的空间相关性。基于空间回归模型相关理论,探讨影响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影响机理,见表4。
(1) 选取的影响因素对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均有明显作用,两个年份的检验系数均通过5%的显著性。高程、坡度与距城镇距离表现出负相关,其他影响因素均为正相关。其中,高程的高低与坡度的大小决定了该地区土地开发利用难易程度,是居民点选址的首要考虑因素,直接关系到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与集聚特征,因此,高程越高、坡度越大的地区,乡村聚落分布较少。河流流经区域水土条件相对较好,有利于农业生产和居住生活,是乡村聚落选址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交通路网是聚落之间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流动的重要载体,临近高等级公路的村落通勤和生活成本都较低,使得乡村聚落倾向于在河流两侧与高等级公路周边集聚。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城镇除了通过辐射作用影响乡村聚落分布以外,其扩张也会吸引附近乡村聚落用地向城镇工矿用地转变,距离城镇中心越近,转为城镇工矿用地的可能性越大;同时,由于环京津贫困带整体城镇化程度较低,城镇建成区面积用地规模小,大部分乡村聚落距离城镇较远,城镇对其周边乡村聚落辐射能力较弱,不能在城镇周边形成集聚和吸引;因此,距城镇距离变量与乡村聚落分布表现出负相关,从侧面体现出贫困地区城镇化发展对乡村聚落布局影响的复杂性。

表4 空间误差模型(SEM)回归结果
(2) 2005年与2015年各解释变量的系数绝对值大小均为:距河流距离>坡度>高程>距高等级公路距离>距城镇距离。相关系数绝对值大小反映该因素对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影响程度,由绝对值大小可知距河流距离与坡度是影响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分析2015年同2005年系数变化值,距河流距离、坡度、高程与距城镇距离的回归系数分别增加0.044 1,0.040 3,0.082,0.009 1,距高等级公路距离的回归系数减少0.063 7;也体现出高程与距河流距离是引起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变化关键因素,一方面,环京津贫困带内6个县位于坝上高寒地区,其余均位于太行山及燕山深山区,为方便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自然本底的高程因素成为乡村聚落选址时着重考虑的因素;此外,环京津贫困带干旱缺水、河网体系不发达,距河流距离对乡村聚落集聚和空间分布起到了显著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由于该贫困带高等级公路网络不健全、道路等基础设施不完善,导致距高等级公路距离对于乡村聚落空间布局的影响呈减小趋势。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结合GIS技术、核密度与景观格局指数,并运用空间统计学方法刻画了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变特征,识别了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关联性,并初步探讨了乡村聚落时空分异的驱动机制,得出以下结论:
(1) 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空间上总体呈现“东南部、西北部较密集、北部较稀疏”的分布特征。核密度高值区与核密度次高值区主要位于平原和丘陵地区,而核密度低值区主要分布在中、高海拔起伏山地区。同2005年相比,2015年乡村聚落用地规模明显增加,平均规模减小,导致乡村聚落斑块破碎程度高,乡村聚落规模与平均规模之间的差距增大,且形状趋于不规则,空间发展具有不稳定性。
(2) 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规模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和集聚态势。2015年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分布的全局Moran′sI指数较2005年减少了0.109 1,表明在空间上的集聚态势逐步减弱,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异性增强;乡村聚落分布的局域Moran′sI指数呈现高值区和低值区集聚状态,2015年同2005年相比,高值区和低值区乡镇数量均减少。“高—高”类型区主要分布在环京津贫困带东南部以及西北部的部分乡镇;“低—低”类型区的乡镇主要分布在燕山—太行山脉附近以及坝上高原地区。
(3) 空间误差模型(SEM)更适合判断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分布与影响因素的空间相关性。乡村聚落空间分布与高程、坡度、距城镇距离之间表现出负相关,与距河流距离、距高等级公路距离呈现正相关。不同因素对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影响大小为:距河流距离>坡度>高程>距高等级公路距离>距城镇距离,2015年同2005年相比,距河流距离、坡度、高程与距城镇距离对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影响程度增强,距高等级公路距离的影响程度逐渐减弱。
(4) 识别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空间分异与关联性特征是乡村聚落布局优化的重要前提。本文探讨了环京津贫困带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变、空间相关性及驱动机制,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尤其是选取影响乡村聚落格局分布的相关因素时,缺乏针对社会、经济与政策因子的定量刻画与考虑。在未来研究中,如何系统地揭示扶贫背景下经济欠发达地区乡村聚落演变特征及驱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