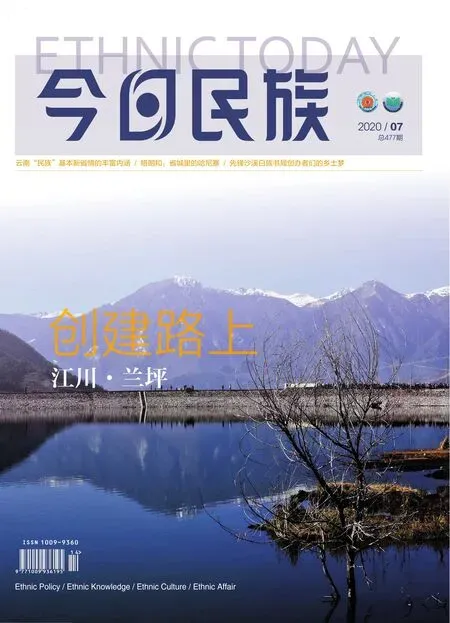新生:告别窝棚的哈尼人
□ 文·图 / 周明清

2018年11月19日,我偶然闯入哈尼族奕车人的一个临时聚居点。这是哈尼族过年的日子,村民筹钱买了一头猪。他们简陋的居住环境和集体生活,给我很大的震撼。而得知他们正期待着一个政府新建的家园,我立即意识到这必定是一个精彩的故事。

① 恰垤村28户村民因地质灾害,从老村搬到靠近乡政府的临时安置点。搬迁时间大约是2016年,在这个逼仄的坡道上新建的居所,他们生活了近3年。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村落”。

② 在临时安置点,家庭生活的完成,经常需要挪移到户外。但户外的空间其实也所剩不多,奕车人热爱集体生活,而这里显然很难满足。比如,过年时,集体伙食,因没有一块完整场地,都分散在不同区域,吃饭也没法在一起。

③ 在临时安置点,家庭生活的完成,经常需要挪移到户外。但户外的空间其实也所剩不多,奕车人热爱集体生活,而这里显然很难满足。比如,过年时,集体伙食,因没有一块完整场地,都分散在不同区域,吃饭也没法在一起。
您的作品《告别窝棚的哈尼人》入选中国文联和中国摄影家协会共同主办的“全国脱贫攻坚摄影展”。您最初是奔着扶贫这个话题去拍摄吗?
近年来我的拍摄大多是关注云南乡村发展变化方面的题材,特别是边远山区少数民族村寨的变化,我关注少数民族山区扶贫进展情况也是有一些日子了。拍摄恰垤村有点偶然。2018年11月,我去红河县大羊街乡过哈尼年,路过车古时见到山脚下有一些很破烂的房子,以为是一个小工地的临时房子。走进去发现,这是临时安置点。村民28户,都属哈尼族奕车人,他们原来住在车古乡哈垤村委会的恰垤村,因村里地质滑坡不能居住,在当地政府的安排帮助下搬来这里。恰垤村原址在车古乡北面12公里,现在这里距离乡政府所在地只有三四公里。当我听说,政府正在临时安置点下面不远处帮贫困户盖房子,我立即意识到这个地方要跟踪拍摄——眼前看到的状况显然不能说明什么。于是,2019年1月,我去宝华参加梯田文化节,借机到这里进行第二次回访。2019年5月17日,村子搬迁时,我又第三次抵达这里。
从扶贫角度看,这个临时安置点究竟有多贫困?
最直观的问题是住房。临时房屋,是石棉瓦、空心砖、竹片片、木板等材料搭建,28户沿山腰排列在半山坡上,基本上每家只有一间屋子,面积不到10平米。通常左边摆放锅碗瓢盆,中间是吃饭的空地,右边是睡觉的床铺——很多人家没有正式的床。其他生活用具很陈旧,到处被烟熏得黑漆漆的。另外,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里不通电。因为坡陡,临时安置点居然连猪圈都没法盖,所以没法养猪。全村28户,有27户是建档立卡户,另外一户脱贫的是因为此前打工挣到些钱买了一辆二手货车,而实际上他的家庭,在很多方面也不比其他家好多少。
贫困原因是什么?
这个问题还有待专门的研究者去研究。据我了解,村民也像别的地方一样勤劳,他们种地——地在老家,还继续种——他们农闲时每家还都有一两个劳动力在县城等地打工。现在搬到新居里,他们表示,还要继续种地和外出打工。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我这样的外来者跟村民交流比较困难,40岁左右的女性,甚至男性,汉语表达都比较困难。这个迹象表明,他们跟外界接触似乎并不多。没有很好地融入开放的外部世界,这或许是他们贫困的一部分原因。在红河县或者云南别的一些村子,如此高的贫困比例也比较少见。

① 临时安置点的室内空间狭小,卧室、客厅、厨房等等功能区分不清。没有电,看不了电视,但对未来充满期待的恰垤人,却也不改其乐。

② 临时安置点的室内空间狭小,卧室、客厅、厨房等等功能区分不清。没有电,看不了电视,但对未来充满期待的恰垤人,却也不改其乐。

③ 临时安置点的室内空间狭小,卧室、客厅、厨房等等功能区分不清。没有电,看不了电视,但对未来充满期待的恰垤人,却也不改其乐。

① 2019年1月19日,我第二次抵达这里。临时窝棚点下方几十米处,政府出资为恰垤人新建的村子正在紧锣密鼓的施工中。而另一面,则是已期待许久的村民。谈论这个新家,成为村民的日常生活,他们期待生活的变革。
新的定居点是什么情况?
新的定居点就在临时窝棚的下面,直线距离不到100米。公路、水电这些基础设施完全具备,政府连猪圈都统一集中盖好,考虑不可谓不周到。新房子的大小,按人口平摊,人口越多,面积越大。多数家庭是两层楼,极个别的孤寡老人,也建有单间。因地制宜,房子呈台地状排列,每家门前修有过道,宽度足够摆一张八仙桌且留有日后绿化空地。房屋内部,进门左侧是单独的厨房,厨房后面是卧室;中间客厅有十三四平方米,右边有卧室、卫生间和通往二楼的楼梯。二楼每家有区别,人口多的二楼还有房间,较少一些的人家二楼留成一个空地,可以晒农作物。从建筑形式看,新居点的屋顶,类似过去土掌房的平顶,很有智慧。在红河县,平地难找,房屋密集,所以每家通常把“院子”建在屋顶。
这种变化,您的观感是什么?
首先变化本身是天翻地覆。恰垤村在短短几年间经历了三个村子,最早因为滑坡搬离的村子,我没有见过,中间过渡的这个临时窝棚式的家和最后搬进去的新家,我都看到了,它们有天壤之别,它所呈现出的发展进步,不需要我强调,任何人都能看得见。

② 2019年1月19日,我第二次抵达这里。临时窝棚点下方几十米处,政府出资为恰垤人新建的村子正在紧锣密鼓的施工中。而另一面,则是已期待许久的村民。谈论这个新家,成为村民的日常生活,他们期待生活的变革。
另外,在目睹这种变化后,即使是我这个来去匆匆的摄影人感恩之情也会油然而生。真的,政府给贫困户免费建新村,里面所付出的代价,不必一笔笔去算,任何人也都相信一定不小,像他们这样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们,真的应该给他们一个家,党和政府就是给他们一个家、送他们一个梦的人。扶贫在中国,并不是这些年才开始的事,上世纪80年代推动农村发展的各项改革,都把脱贫视为目标,但这项艰难的工作,直到目前才取得根本突破,一些很难“扶起来”的地方——恰垤村这样的地方最终得以脱贫。
“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这一历史性进程,奕车人是什么感受呢?
有一个细节。第二次拍摄时,我印象很深的是,村民们很乐于跟我谈论他们正在建的家园。村民兴奋地指指点点,告诉我说,哪栋是他家的。他们显然对新的家园满怀期待,在持续1年多的建设中,他们显然无数次地想象这个家园未来的样子。

① 中午12点,恰垤新村的村民开始杀猪,招待来庆贺搬迁的客人。每家每户的男人、女人,甚至高年级的学生,都安排了工作,全村动员一起来准备一顿丰盛的晚宴。只有孩子们例外,他们在新修的水泥路面上,玩着自制的小车,看他们操作的熟练程度,显然早在正式搬家进来之前,他们已经把这里当成游乐场,这个家早就是他们的欢乐之源。下午4点,恰垤新村里,来庆贺搬迁的亲戚朋友们一起吃饭。每一家至少有2桌客人。桌子摆在客厅和屋前,在联排的小洋楼前,一个浓缩版的“长街宴”终于有了保障。

② 中午12点,恰垤新村的村民开始杀猪,招待来庆贺搬迁的客人。每家每户的男人、女人,甚至高年级的学生,都安排了工作,全村动员一起来准备一顿丰盛的晚宴。只有孩子们例外,他们在新修的水泥路面上,玩着自制的小车,看他们操作的熟练程度,显然早在正式搬家进来之前,他们已经把这里当成游乐场,这个家早就是他们的欢乐之源。下午4点,恰垤新村里,来庆贺搬迁的亲戚朋友们一起吃饭。每一家至少有2桌客人。桌子摆在客厅和屋前,在联排的小洋楼前,一个浓缩版的“长街宴”终于有了保障。
换句话说,我第三次到访时,尽管他们才刚刚搬进去,但他们与这个家,早已完成了必不可少的情感磨合。这点特别重要。可能有的人认为,易地搬迁是硬生生地把搬迁者从一个地方挪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没有认同的地方,因而会产生一些社会、文化问题。但是在恰垤村,在经历过临时安置点种种不便的奕车人这里,这个搬迁是他们期待已久的新生。也因此,他们对党和政府由衷地表示感谢。
我第一次去恰垤村,是他们杀猪庆十月年。因为户外场地几乎无法放下一张桌子,他们的亲朋好友无法到这里来一起庆祝。村子里虽然依旧按习俗杀猪、做饭、打粑粑,但不得不把食物分发到各家,无法实现那种哈尼族传统的“长街宴”。搬进新居后,他们隆重庆祝。这一次,久违了两年多的“长街宴”终于又重现在哈尼人的眼前。寨子杀了3头猪2头小牛,集体做饭,每家根据各自的客人预订桌子数量,然后开饭的时候,在一排排新居门前,“长街宴”一字排开。
哈尼族热情好客的传统和文化,现在在新的家园得到了延续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