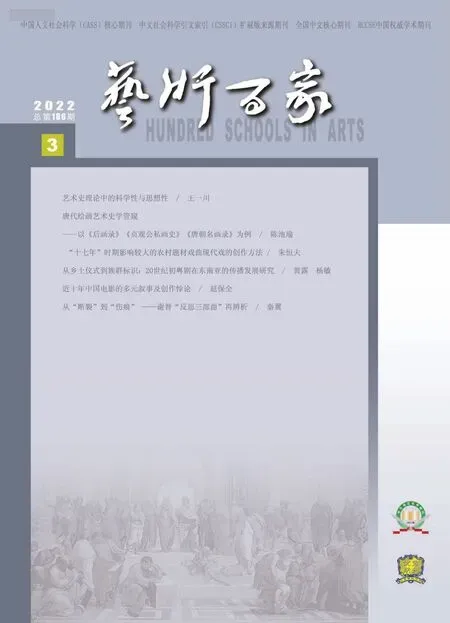东瀛稽考:20世纪90年代中国艺术电影的周边传播*
潘 汝
(浙江传媒学院 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中日两国同属东亚,互为周边。在明治维新之前,中华文明一直是日本文化的师者,然而,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这一偶像地位逐渐丧失,近代中国开始从日本获得思想启蒙。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及其余脉影响下,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日电影曾有过四个重要交互期——伪“满映”时期、太平洋战争之后、50年代、80年代前后,均以日方为主导。
那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日方的主导性是否一以贯之呢?情况似乎并非如此。中国电影经过80年代新浪潮的壮怀激烈与沉郁积淀,其中最具东方美学风格的“诗骚”传统被充分唤醒、培育、充实,到90年代,中国艺术电影以多重奏的方式出现在日本银幕上,抒写着东方古国失落已久的自信,散发着诗歌国度的馥郁芬芳,一度迷倒岛国众生,甚至引发日本学界的评议热潮。
一、20世纪90年代中国艺术电影在日本的传播概况
1978年10月,邓小平“开创了中国国家领导人访日先河”[1]。而在这之前,日本德间康快公司已举办过两届中国电影节,一批“十七年”电影担当了中国文化先行使者的角色。“但对于这些中国电影,日本观众的关心还很淡薄,观众寥寥无几。”[2]981985年,具有标志意味的陈凯歌的“《黄土地》的登场,给日本的影迷带来了冲击。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电影节不仅引起了日本电影人对中国的关注,也引起了广大影迷的关注”[2]100,而且“当时也是对中国文化、中国大陆的兴趣广泛地被唤起的时代”[2]101。如此稍稍改写了80年代初呈现的日本电影的主导走向。但就80年代中日电影对彼此社会文化的影响力而言,日本电影还是略占优势。
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在日本的传播状况发生了逆转。当时,因西方世界的干预、钓鱼岛问题的摩擦等,中日分歧加剧。因而,大规模引进日本电影的情形已不再复现。据统计,整个90年代,在中国大陆上映的日本电影仅30余部,且绝大多数是“日本电影周”的展映作品。而1990年至1997年,在日上映的中国电影逾70部,其中包括《没有航标的河流》《北京,你早》《心香》《阙里人家》《秋菊打官司》《香魂女》《蓝风筝》《变脸》等。倘若再算上张元的《妈妈》等以各种方式流入日本的所谓“体制外电影”,则远超上述数字。另外,如果不是因德间康快公司负责中国业务的森繁于1997年去世,应该有更多的中国影片在日上映,至少被日本观众誉为“神作”的霍建起的《那山那人那狗》(『山の郵便配達』,1998年)应该当年就在日本上映;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初恋の来た道』,1999年)就不仅仅是于1999年由日本文化村(BUNKAMURA LE)电影院点映,而应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公映。因此,笔者将这两部作品,也纳入考查范围,作为20世纪90年代在日上映的中国艺术电影的一个必然性延展。
如此看来,较之前文所述的四次中日电影交互而言,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在日本的传播状况发生了逆转。那么,这些在日上映的中国影片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呢?
从时间上看,大多数影片摄于90年代,在两国的上映时间相差无几,但也有十余部是80年代(如《湘女潇潇》等),甚至40年代的影片(如《一江春水向东流》等);从类型上看,除了如杨吉友的《关公》等为数不多的商业电影之外,85%左右是中小成本的艺术电影;从题材上看,半数以上的影片将镜头对准乡村或小镇,在诗意自然或宁静古朴的环境中进行人性的拷问与文化的追索;从导演构成上看,大部分导演都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或中央戏剧学院,“他们在学校中能观摩普通人看不到的西方高水准的影片,深感那些中国式的教条作品,在世界电影的潮流中显得多么滞后,同时还相互约定,今后绝不再拍那样的作品”[3]143。他们怀揣着学院派一以贯之的艺术情怀,秉承了先辈探索电影的激情与梦想,唤起了东瀛岛国民众血脉中似曾相识的某些文化记忆。
从“日本电影评论空间”①对这一时期中国电影的评分与评论来看,名列前茅的是以下10部电影:

表1 20世纪90年代在日上映的中国艺术电影的评分及评论
总体上,日本观众对中国90年代的诸多艺术电影表示肯定,对第五代导演的作品颇为青睐,尤其喜爱张艺谋、陈凯歌的作品,也十分关注田壮壮、霍建起等导演的作品。对当时刚刚崭露头角的第六代导演贾樟柯,也给予中肯的评价。尽管由于历史原因,第四代导演群体在其才华尚未得到充分施展之时,就被第五代所替代,然而,第四代导演展露的光芒,并没有被日本观众所忽视,他们毫不吝啬地给吴天明等奉上赞美之词。
从日本各大媒体及专业电影评论者对90年代在日上映的中国电影的关注度与美誉度来看,他们对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尤其是艺术电影,积极关注,真诚认同。
日本最有影响力的电影杂志《电影旬报》几乎每年刊出一份全面评介该年度“中国电影概貌”的重量级文章,如佐藤忠男与石子顺分别撰写过《中国92年电影全貌》与《中国95年电影全貌》②。《电影旬报》尤其关注这一时期的中国艺术电影,不仅邀请电影学者上野昴志等以连载的方式介绍中国艺术电影的最新讯息,还经常组织相关专题研讨:如邀请石子顺对《红樱桃》《无人喝彩》《二嫫》《周末情人》等在日公映的艺术片进行评论;邀约吴天明、朱旭、石子顺等就吴天明导演的艺术创作进行专题访谈③;组织是枝裕和与贾樟柯等著名导演对《小武》展开座谈④。《电影旬报》持续不断地推介中国电影,加深民众对中国艺术电影的认知与理解。
与之相呼应的是,日本的另外一些读者甚众的电影杂志,如《电影院》(『シネ·フロント』)、《电影艺术》(『映画芸術』)等,则着力于对中国艺术电影的深度解读。如真下圭二的《〈爱情麻辣烫〉——推陈出新,描写男女情爱》,阐释了这部影片对中国传统爱情题材电影的反叛[4]34—41;《电影艺术》评介了铃木尚之、白坂依志夫、桂千穂、加藤正人、上野昴志等电影学者参与的第九届中日电影剧本研讨会,着眼于当时最新的中国艺术电影剧作,集中探究中国第五代导演作品的群体特征。[5]108—123
除了专业的电影杂志之外,日本的众多杂志学刊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争相刊发关于中国电影的评论文章。如,《中国学志》发表了《再辨“软”“硬”之争——中国电影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以30年代中国电影理论界的“软硬之争”为背景,从电影的社会性与艺术性的关系角度,对新时期中国电影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进行了深入剖析。德间书店编辑出版的杂志《桑萨拉》(音译)(『サンサーラ』)刊登了高仓健与田壮壮的“对谈”,直击“鬼才”导演田壮壮的灵魂内核。[6]146在这样的燎原之势下,连日本县级宣传部门的报刊也不甘寂寞,投入到关于中国电影的言说与评论之中。
相关评介论著数量之多、涉及面之广、探讨之深,可谓空前绝后。在此情势下,日本社会各界对这一时期的中国艺术电影也持肯定态度,对其中代表性作品的由衷赞赏,一直绵延至新世纪。如《那山那人那狗》于2001年被静冈县环境整备审议会推荐为青少年必看的九部影片之一;获得2011年度“日本电影笔会”最佳外国影片第一名及“日本电影艺术奖”最佳外国电影奖;荣登“每日电影奖”最佳外国影片之榜首。20世纪90年代在日上映的中国艺术电影受到持久关注,在日本社会、文化、教育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中方对日本电影关注度下滑的情形下,却有大量中国艺术电影在日本上映,并受到日本民众与评论界的青睐,其中的原因自然错综复杂,然而,主导性的因素或许值得我们探究与深思。
二、分众化:小厅影院、复合影院及社区影片推介会为中国艺术电影提供了多元化传播契机
不可否认,好莱坞一直是日本观众的“心头好”。然而,大众的娱乐需求并不能涵盖一切。日本电影早在80年代初就摆脱了大制片体制束缚,90年代又因本国资本的外流而在一定程度上挣脱了资本绑架,其个性化的影像培育了具有不同审美趣味的受众。而好莱坞90年代以来所采取的“保守主义”文化策略,愈发难以满足日本国内日益多元化的电影文化需求。
同时,由于大制片时代的终结,各大电影公司的发行部门纷纷独立,以应对观众大量流失、边缘影院无片可放的困局。发行的变革,必定带来放映方式的改变,原先动辄几百人的大厅影院,显然无法应对小众化需求。于是,从80年代开始,小放映厅(ミニシアタ)萌芽发展,至80年代中期,“小放映厅在大城市的中心地带呈快速增加之势,并于90年底达到高峰”[7]14,且多放映风格化的外国艺术电影。《那山那人那狗》就是在岩波影院这样一个小放映厅首先放映的。2000年1月,日本资深发行人深泽一夫到中国选片,看中了这部虽获金鸡奖,却被中国观众冷落的艺术电影,于是联络岩波影院(日本最著名的艺术影院)、东宝东和发行公司引进该片,并得到日本《电影旬报》总编辑植草信和的支持。2001年11月起,《那山那人那狗》在岩波、德间等小厅艺术影院里,开始了长达半年的循环播放,口碑爆棚,随后在大阪、京都等地及其周边影院连续放映,人气累积,终于成了日本人心目中永恒的经典。
除了小厅之外,1993年,多厅复合影院出现。日本的电影院数量“从1994年开始呈现稳中有升的趋势,1998年日本电影院总数达到了1988家,原因之一是多厅电影院的形态已经被固定下来”[8]258。1999年多厅电影院达到高峰,几乎占据了日本影院的半壁江山。多厅复合影院可以更为“自由地选择有个性的影片,以单厅新片专映的方式上演”[7]14,这使得低成本的电影制作能够顺利上映。1995年之后在日本公映的许多中国电影,就是在诸多复合影院上映的。正是这样一种灵活的放映形式,让90年代那些迥异于好莱坞特质的中国艺术电影得以与日本观众见面,并获得传播的良机。1999年,最先上映《我的父亲母亲》的日本文化村(BUNKAMURA LE)电影院就是处于综合文化场所的复合影院。
除了小厅影院、复合影院为中国艺术电影提供了传播平台外,日本的“町内会”也为之提供了更为多元的推介机会。所谓“町内会”,就是日本依托社区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的社会基层民间组织。
比如,吴天明的《变脸》能在日本广泛传播、深入人心,“町内会”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笔者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数据库⑤中查到了两份日本三重县津市栄町的《市民生活》,出版时间分别是1999年2月25日及1999年8月25日。短短半年内,日本“津市栄町”所属的“町内会”就举办了多场《变脸》观影会。从影展的文案来看,“町内会”较小厅影院和复合影院而言,在艺术电影的推介方面做得更细致、更灵活。
“町内会”的观影部署细致周密。影展简报上除了介绍电影剧情之外,还说明“本片导演吴天明曾凭借《老井》获得东京电影节最高奖项,主演是因电视剧《大地之子》为大家熟知的朱旭”[9]。《变脸》社区影展会设置了专门的咨询处,即“三重优秀电影欣赏会”可供细节咨询;主办影展会时,做到“一影一方案”,8月份那份展映说明上写着“主办:《变脸》电影放映实行委员会”[10],可见这种社区展映活动,会根据不同影片,设立专门的“实行委员会”,以达到更好的推介效果。
“町内会”还依据社区民情灵活应对。参与观影的社区居民一般应缴纳月会费500日元,而入会的费用则是1000日元。但是,因为这是一部来自中国的优秀影片,所以国际交流方面的机构予以放映支持,凡中国留学生和研修生均可免费观影。另外,“町内会”在展映场次的设定上颇为灵活,在《变脸》影片的2月份观影推介上,有这样一段说明:“由于在东员町综合文化中心举行的上映会上,该片备受好评,因此增开了上午场。”[9]
由以上分析可知,20世纪90年代,日本早于中国成熟的电影分众市场为中国艺术电影提供了多元展示的舞台,使这些在国内颇受冷落的作品,在日本的某些合适的平台、契合的场域中找到了自己的“知音”。
三、“东亚农业文明圈”的共情效应:中国艺术电影与日本电影的乡村主题
日本传承了中华的农耕文明。明治维新以来,农耕文明与工商业文明的冲突,在日本从来没有停止过,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和人的异化,更加剧了这两种文明之间的纷争。日本人试图回归传统文化,为无家可归的灵魂寻求居所,重启对乡村自然的尊崇、对山岳神道的信仰、对农耕先祖的膜拜。
早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日本影坛就出现了一些以自然山村为主题的震撼之作。《远野物语》(1982年)、《楢山节考》(1983年)、《再见了,可爱的大地》(1982年)、《落叶树》(1986年)等,都体现了日本人对土地山林的眷恋与深思。1985年,黑泽明的晚年力作《乱》甚至向世界发出了这样的警告:“一味追求强、追求大而势必走上自毁之路。”不幸一语成谶。90年代中后期,日本经济形势低迷,政治格局动荡,天灾人祸频仍,这让民众对工业文明的质疑、对乡村山林的依恋愈发强烈。
“与自然共生,是1990年代以后日本电影中为数不多但逐渐变得特别明显的主题之一”,较之于80年代,“它作为一个更为重要的主题为人们所认识”。[11]464尽管如此,90年代日本电影类型与主题的多样化,又有冲淡这一重要主题的嫌疑。在这些为数不多的以“与自然共生”为主题的作品中,除了少量的剧情片,如熊井启的《式部物语》、小泉尧史的《阿弥陀堂讯息》等,其余多为纪录片。于是,中国艺术电影中自然与乡村题材的剧情片,刚好契合了日本电影“与自然共生”的主题,呼应了当时日本观众对体现这一重要主题的剧情片的需求,重现了中日同为“东亚农业文明圈”的共情效应。
这一时期在日本上映的中国艺术电影,大部分以原野乡村等自然环境或与自然高度融合的古城小镇为故事的发生地,在“日本电影评论空间”中,日本观众将“自然”作为一个参与剧情的重要角色来解读。
《心香》在日本普通观众心目中地位颇高,有不少评论围绕片中所传递的自然气息而展开,“怀旧的河边村落的风景”使观众心动,“蟋蟀的叫声和古老的房屋味道非常好,(让我的心态)平和了”。[12]他们对《秋菊打官司》中的乡村场景十分赞赏:“阳光从窗户射进来的温暖的农家厨房和起居室的风景真是太美了。”[12]《那山那人那狗》日译『山の郵便配達』,凸显的就是“山中”二字。“鲜艳的绿色山河和静谧的感觉,震撼心灵的绝品!”“如果侧耳倾听,就能听到自然的气息。如果眼睛注视,自然的香味漂浮来。无边无际的绿色世界是终极的‘美’的世界。”[12]由于这种共情与热爱,日本普通观众对这部影片评价极高,钟爱之至。
佐藤忠男在解读这一时期的作品时,也时时关注自然环境这一元素,他不仅在乡村题材的作品中找到了诗意仙境,更善于在影片的城市街景中投射如山村一般古朴宁静的情致:在《边走边唱》中“作为自古以来中国美术传统的表现手法,巍峨群山的风光,宛如水墨画一般的景致,都给电影带来了极大的意义”[3]155;而在《心香》中,他则倾心于小津安二郎式的宁静安详的城市,喜爱“被人们日常生活的良好情趣湿漉漉地浸透着的精神高雅的场所”[3]180;乃至在宁瀛的《找乐》中,首先让他心动的是“平民街区的风情”和“近邻团聚街口”[3]175的古朴一幕。
泡沫经济的破灭、巨大的环境压力、无家可归的漂泊感,让90年代的日本电影在工业文明的困境中抒写回归自然的梦想;而经历了磨难与压抑、渴望舒展人性的中国电影人,则重启了“诗骚”的传统,在影像的“赋比兴”中赋予自然乡村非凡灵性。这种不期的相遇与碰撞,让90年代的日本民众及电影人在中国艺术电影中找到了梦之栖所。
四、“物哀”与“诗骚”:中国艺术电影与日本受众的深层审美共振
除了上述原因,90年代日本受众对中国艺术电影的热切关注,还缘于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的精神共振。日本观众将日本美学的终极追求——“物哀”,投射到当时“诗骚”传统得以复苏的中国艺术电影中。
“物哀”虽有日本特质,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与“诗骚”根脉相连。在古日语中,“哀”是一个感叹词,用来表达欣喜、哀伤、诧异等各种复杂情感,而“物”即指客观对象,不仅包含自然之物,也兼及人及人生世相,“物哀”则是对客观对象的咏叹式抒情,与中国诗论中的“感物兴哀”“感物触怀”“愍物宗情”可谓一脉相承。只不过“物哀”将“诗骚”中“哀感性审美体验推进到了唯情、唯哀、唯美的极致”[13]10。因此,两者的审美共振历千年而不衰,并穿越时空,在中日电影文化的交互中得到呈现。
这种交互最初的高潮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以刘呐鸥为代表的“软性电影”思潮中。曾留学日本的刘呐鸥,站在“新感觉派”的艺术立场来坚守电影的诗性表达,而“新感觉派”源自日本,是打上“物哀”烙印的现代文艺思潮。刘呐鸥在日本“新感觉派”中觅得“支撑个体存在的理想、信念、情感的浪漫表述”[14]113,再一次印证了“物哀”与“诗骚”的亲缘关系。
半个世纪之后,中国新时期文学又掀起了日本“新感觉派”译介的热潮。而几乎与此同时,就有黄健中、吴天明、张暖忻、谢飞等第四代导演的“价值创造与探索之旅”[15]231,随后又有了“经过思想解放运动、启蒙主义思想、现代主义洗礼”的“继承第四代对传统电影观念的质疑和现代电影美学的探索”[16]126的中国电影新浪潮,这并非历史的巧合,而是中国“诗骚传统”与日本新感觉派的“物哀”在现代背景下的互文关系的影像化呈现的一个切面。
而新时期“物哀”与“诗骚”在影像场域中的再一次碰撞,从某种意义上说,对重启中国新时期具有现代性反思特征的“诗性视觉审美空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在日上映的中国艺术电影,虽以“文化寻根”为背景,表现了集体性和民族性特征,然而,这些文本毕竟“在离政治较远的地方,形成了知识分子的言语空间”。[17]55而以贾樟柯为代表的后继者,则进一步构筑“以1990年代的‘个人’意识为中心的电影”,凸显“拍摄自己想拍摄的东西”[17]56的意志。
如若将对这种诗性文化反思与个人意识的关系的考查放在中国电影的“影戏”与“诗骚”传统此消彼长、各领风骚的历程中,则能更多地体悟这些作品内在的“诗骚”光辉,在富有个体精神和独立思考的抒情意绪中“软化”艺术的教化功能,“诗化”家国情怀,与“物哀”达成更多神似的意象空间。因而,深谙“物哀”之美的日本观众与学者很快接受,并对其进行“唯情、唯哀、唯美”的“物哀”式阐释。
日本影评人、汉学家阿赖耶顺宏在对宁瀛的《找乐》(『北京好日』)发表评论时所提出的观点,颇有代表性:“我认为,无论是小说、电影,还是其他艺术作品,从各种角度解读,都是可以的。在作品面前,我们甚至可以什么也不讨论,只要有所感受就行了,说得极端一点,只要能沉浸在艺术的感兴中就行了。”[18]77
在“日本电影评论空间”里,我们看到观众们悲欣交加、以悲为美的审美意趣:“淡泊、美丽又悲伤的故事”(评《蓝风筝》);“惊讶、哭泣、感叹、微笑……唤醒了我所有的感情。该片将百年电影的魅力全部作为艺术养分培育了丰美的莲花”(评《变脸》)。[12]《小武》日译为『一瞬の夢』,凸显的是浮生若梦、转瞬即逝的漂浮感与幻灭感,日本学者菅原庆乃将该片的诞生称为“电影中的私小说登场”,而“私小说”的底蕴就是“物哀”。有观众评曰:“镜头跟随着年轻人(小武),在小镇的街道上乱晃,将杂乱的街景纳入镜框,在飘忽不定的时间中,产生了一种与小镇不同的(生命)原生态。因这种彻底的空虚,反而产生了一种奇妙而又纯粹的充实感。”[12]
日本电影史学家四方田犬彦曾说:“日本的电影研究作为一种媒体,最终没有出现上升到哲学理论高度的钻研与积累。日本人与生俱来的抽象能力的不足,在70年代末使电影评论变成了质朴的印象式批评或晦涩难懂的玄学。到了80年代,电影评论内部越发内向,失去了与时代关系的衔接,完全变成了电影内部的自说自话。”[7]15当然,这种情形在90年代仍然存在。在日本专业电影评论中,也较少见到以哲思见长、纵横开合地构建体系的电影批评。
何以如此?乃是“物哀”的审美追求使然。日本的“物哀”,本身就是感性的存在。“物哀”场域中的“悲”,与西方悲剧中的“决绝的毁灭”不可同日而语,是留有回旋余地的对悲哀的玩味,因此,“没有彻骨的悲,也没有入髓的伤,始终带着随感而发、柔婉优美的情调”[19]26。20世纪90年代再现“诗骚”传统的中国艺术电影在日本观众的“物哀”视域中得到了日常化与唯美化的解读与领悟。
五、结语
有人说,华语片最大的海外市场是日本。日本著名电影制作与发行人牛山拓二也曾用导演个案来印证这个论断:“最爱看张艺谋电影的,其实也许是日本人。”而20世纪90年代中国艺术电影在日本的传播现象,再一次证实了这一点。或许,自明治维新以来,这个最典型、最精致的农耕文明在“脱亚入欧”的口号中,全面抛弃中学、彻底西化之后所遭遇的重重困境,使得他们又频频回首、无限眷恋,在中国的银幕世界中又照见自己曾经的旧影。
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21世纪的中国电影最终又疏离了“诗骚”传统和“物哀”审美。或许,中国电影的产业化、分账大片的冲击、世界电影格局的胁迫,可以为这种“疏离”提供现实理由。但或许也正是这种迫于外力的转型,使得20世纪90年代中国艺术电影与日本受众所产生的深层灵魂共振,难以在新世纪里复现。
① 网址:http://cinema.intercritique.com/movie。“日本电影评论空间”公布日本电影观众观看影片之后的评分与评论,相当于中国的“豆瓣”。
② 佐藤忠男.特集:中国映画の全貌'92[J].キネマ旬報,1992(通号1086):128—131;石子順.特集:中国映画の全貌'95[J].キネマ旬報,1995(通号1157):86—88。
③ 呉天明,朱旭,石子順.呉天明インタビュー[J].キネマ旬報,1997(通号1223):152—155。
④ 是枝裕和,ジャ·ジャンクー,スペシャル.対談『一瞬の夢』[J].キネマ旬報,1999(通号1298):84—89。
⑤ 日本国会图书馆电子化资源网址:http://dl.ndl.go.j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