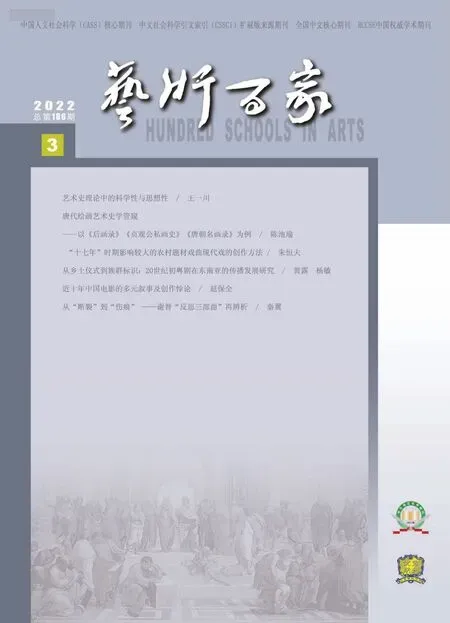大地上的文化记忆重塑*
——以日本越后妻有地区的大地艺术节为例
徐顺毕
(宁波大学 潘天寿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大地艺术”(Land art)①兴起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美,该类型的经典作品多分布于偏远的人迹稀少地区,创作思路则多来自对某地自然环境的随形就势。如迈克尔·海泽(Michael Heizer)创作的《移位的/置换的团块》只是将干燥荒凉盆地上的一块花岗岩巨石挖出,然后再将其送回地下,作者意图通过艺术与自然间的互动来抵抗艺术的商业化倾向。由于大地艺术与自然间的直接关系,其在美国兴起后,很快受到其他国家艺术家的青睐。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旨在“以艺术唤醒乡村”,自2000年始,三年为期,至今已举办七届。此类艺术活动虽以“大地艺术”为节日之名,但有别于其原初概念,在延续了对自然的人文关注以外,更多表达了对地缘文化和记忆的关切。
“二战”之后,日本进入了经济快速增长期,在一系列扶持政策刺激下,城市成为发展的中心,进而导致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失衡状态。越后妻有便为日本城市化进程中被遗忘的乡村区域:年轻人纷纷逃离、人口老龄化严重、经济落后。因此,文章论及的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面对的“大地”并非荒凉的沙漠戈壁或是人迹罕至的海岸,而是满是废墟意象的乡村,虽然古老却丧失创造的原动力,以至于一步步沦为文化记忆缺失的真空地带。
一、艺术节:以艺术唤醒乡村的记忆
对记忆的研究,最初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等学者关于个体记忆的探索。20世纪80年代,英国社会人类学家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在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的基础上延伸出了“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的概念。“集体记忆”指向记忆的社会性构建功能,认为个体会将自身纳入集体之中寻求回忆,纯粹的个体记忆是不存在的,记忆具有整合共识的社会性;而“社会记忆”则进一步将权力的等级序列纳入塑造记忆的重要性序列之中,认为在任何社会秩序中,参与者均具备由“仪式”所塑造的“社会记忆”共识。[1]49在此基础上,阿斯曼夫妇(Jan & Aleida Assmanns)界定了“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概念,他们将“文化记忆”定义为:“关于一个社会全部知识的总概念,在特定的互动框架之内,这些知识驾驭着人们的行为和体验,并需要人们一代一代反复了解和掌握他们。”②与文化有关的文本材料、神话传说、纪念仪式等都是文化记忆的存在形式,而身体和地域场合则是文化记忆的重要媒介。[2]72
本文论及的“大地”更多为文化记忆在乡村衰竭、断裂的缩影。越后妻有这一“大地”区域便面临这样的状况:青年离开乡村去城市发展,乡村老龄化严重,原本的田间耕作停滞,乡土文化的记忆正在逐渐流失。[3]210此等情况下,以下几项先决条件成为了公共艺术在此生根发芽,并逐步唤醒文化记忆的关键:
(一)对越后妻有地区文化记忆的探索
在日本越后妻有地区,独特的乡土文化是构成文化记忆的基础,其中最为核心的时节、农耕、庆典仪式等文化活动便成为承载文化记忆的具体方式。
这种对已有文化记忆的传承与发展体现在两方面:
第一,“越后妻有艺术节”本身就是对祭祀文化的一种传承。“艺术节”也称为“艺术祭”,“节”与“祭”在日语中同义,日本民族主张万物有灵的观念,对自然的一切规律保持敬畏之心,祭祀文化在日本民族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且“祭”的形式随着艺术的介入变得更加多元化。日本艺术家高桥匡太曾于2019年为越后妻有创作《雪烟花》(GiftforFrozenVillage)(图1),相较于通常的艺术作品,其更是一场艺术活动。艺术家将公共艺术与新年活动融为一起,烟花表演、雪地灯光营造出梦幻的新年气氛;同时开展新年祈福仪式,通过艺术活动传承日本传统的祭祀仪式、祈福文化,例如祈求健康平安、风调雨顺的火神祭。

图1 高桥匡太,《雪国》,2019
第二,越后妻有艺术节以作品为载体,将原本的文化记忆留存为物化作品,以艺术的方式见证、书写历史。国松希根太在2018年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中创作了《明日之社》(TracesofMemoryandForestofTomorrow)(图2)。作品位于一片日本杉树的环抱之中,此地在60年前是一处相扑比赛用地,如今因为人口的流失而被废弃,重新回归到原始的自然状态。国松希根太将四根黄铜倒模的樱花树干插于场地中央以界定位置,周围由内至外放置有多圈石头,像是暗示原本相扑比赛时观众的站位。整件作品显露出一种怀旧的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艺术家对60年前实际盛况所作的极简化处理,并非想要在真实再现以往的场景中重构回忆,而是以一种象征的方式让相扑活动的记忆存留于纪念碑性的艺术作品之中。纪念碑总是带有一种永恒性的指向,以仪式对抗遗忘。

图2 国松希根太,《明日之社》,2018
(二)自然环境所营造的“荒漠感”
越后妻有地区位于日本中北部地区,一年中有一半的时间被大雪覆盖,川端康成《雪国》中“雪国”的原型便是越后妻有。寒冷的气候条件造就了独特的聚落文化,聚落的文化记忆对于村民来说和生命一样重要,这种地缘文化的特殊性为公共艺术在此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4]55-57克里斯蒂安·波尔坦斯基(Christian Boltanski)与卡尔曼(Jean Kalman)在第三届艺术节时为越后妻有留下了永久性作品《最后的教室》(图3)。记忆、死亡、个体等关键词贯穿了波尔坦斯基的创作理念,他的作品体现出对唤醒存留记忆的渴望。《最后的教室》以废弃的东山小学为址,用黑纸将所有的窗户遮蔽,营造出冬日大雪封山后的昏暗体验场景。电扇在长椅上吹出混杂稻草气息的热浪,温度尚在,气味尚在,但人已不在,波尔坦斯基试图让人感受这片区域原有的欢声笑语在人离开后所呈现出的黑夜般的死寂。为更好地表达物是人非的心绪,作者还收集了有关这座小学的一系列物品:毕业照、奖状、报纸、文具……用这些承载着记忆的存留物自我言说这座学校的历史。[3]65-69极寒的天气与曾经的聚落温情构成了矛盾,不过也让原有的这种温情显得更加可贵。在冬季,终日的积雪和白昼的短暂总是加剧《雪国》中的荒凉感。那些荒田、空屋和学校曾经存有过的温情回忆,最终因人的离去而陷入无尽的荒芜。艺术家“在地性”的创作具有物理空间和文化记忆双重意义③,这些艺术作品已然成为储存文化记忆的载体,既唤起了本地人的回忆,也让外来者为之动容。[3]1-4

图3 波尔坦斯基,《最后的教室》,2018
(三)可供观赏的“沧桑感”
失去人的村庄只能以“废墟”的面目呈现。关于“废墟”(ruins),其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英国艺术史家弗朗西斯·哈斯克尔(Francis Haskell)在其所著《历史及其图像》的导论中称“废墟”为“能激起鲜活的历史感”的地方,指出:“废墟激活的往昔是一个整体,饱含了对昙花一现的世俗权力及脆弱的人类成就的沉思。只有面对罗马那大片的城墙,以及摇摇欲坠的建筑时,那些参观者的道德说教才会和怀旧感合而为一,凝成一个‘历史的’观点。”[5]8废墟的魅力在于历史映照下的沧桑感,不过东西方人对废墟的理解和感受并不相同。西方废墟美学既要保留历史遗迹主体,又要存有饱经风霜样貌的审美趋向不同,东方人的废墟美学更加强调“曾经出现过”但在此刻已不复存在的无常感,依托于废墟因失去而造就的“空无”(void)④,而非依然存留之物的历史。[6]34-37这种情感在具有“物哀文化”传统,习惯“以悲为美”的日本,存留得更为极致。从某种意义上说,越后妻有地区便不乏令人感伤的“废墟”意象,此种意象为艺术家的“在地性”创作提供了无限的艺术想象空间。
在越后妻有进行“在地性”创作的艺术家通常采用当地器物作为创作原材料,以器物的使用痕迹暗示时间的尺度。张哲溢《灯光寄养所》(图4)便以从居民那里收集来的台灯和蚊帐作为主体材料,以灯光自身的“生命感”体现人已离去的“空无”。例如椅子、台灯一类的物品最能存留人的使用印迹,我们甚至可以由它们的外观联想到原本使用过程中人体的姿态,这类器物给我们的印象不仅是器物本身,而是器物和人构成的共同体,器物功能性和人身体之间的紧密关联让器物单独呈现时有一种强烈的缺失感。这些借用当地收集的器物进行创作的作品,将个体记忆承载于物化的对象之中,相较博物馆中的文物展示,这种器物的“在地性”言说通过艺术的表达,更具共情力量。⑤

图4 张哲溢,《灯光寄养所》,2018
在科幻小说当中,有一专有名词,称为“巨大沉默物体”(BDO:Big Dumb Object),废墟虽在现实生活中较为常见,却具有这类“巨大沉默物体”的神秘感:原本作为建筑的功能性已经褪去,与周围尚在使用的空间形成了时间的断裂。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废墟如同一个纪念碑默然矗立,时间在此不再前进。越后妻有的“废墟”正好和当地的居民各居各位地处于恰当的时间尺度之中,虽不足以像古罗马遗迹那样令人发思古之幽情,但足够以此回溯本土居民和本土文化的历史。越后妻有艺术节的作品并没有将这些废墟就地保护,变为理想之物,而是予以改造,用艺术重塑地方的文化记忆。
二、“艺术乡村”:以温情抵抗同质化的方式
柯林·罗(Colin Rowe)是“二战”之后最具影响力的建筑理论家之一,他于1978年发表了《拼贴城市》一书,针对当时城市布局规划和建筑设计的走向提出了多种特性并存的“拼贴”倡议。需要注意的是,本文所指的“拼贴”一词来源自法语的“bricolaeu”,带有“修补”的意味,但其到了英语中则成为“bricolage”,意为“拼贴”。“修补”和“拼贴”最为核心的差异在于:修补是基于已有物的一种改善行为,是依托于现有条件的一种创造,而在转换为“拼贴”一词时则失去了原本的这层含义,像是随机的组合行为。[7]11拼贴城市并不是简单地将不同功能的区域暴力地并置,而是在已有的建筑功能和城市结构的基础上做新的补充和联系,为城市化发展注入新的潜力。[8]52-53但在现阶段的城市发展中,这种可供拼贴的间隙正在消逝。人们之所以为巴黎圣母院付诸一炬而悲叹,不仅是因为那是重要的历史遗迹,同时也缘于它是在奥斯曼主持改造巴黎之后为数不多存留下来的中世纪建筑,是这座城市中少有的时间间隙。⑥但是在当今的城市布局中,形形色色的商店和餐馆构成了相似度极高的综合体,让人难以区分大城市之间的差异,无论是商业区还是住宅区,在城市规划上都走向了单一化。这种情形是现代文明一味追求多样性所陷入的悖论,即在拥有最多可供选择性和建筑形态多样性的城市之中,有意维持的多样化行为反而成为同质化趋势的根本原因。并且,这种同质化趋势由城市自上而下发展至个人,正如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其所著《文明》中所述:“如今,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穿着方式都大同小异:牛仔裤、运动鞋、T恤……一个旨在为个人提供无限选择的系统最终使人类同质化,这是现代历史上最大的悖论之一。”[9]181-182基于上述原因,在现代的城市发展背景下催生出了无数千面一律的古村,主办方总是以开发旅游景区的名义迁出原有的住户,拆除不具备古村特色的房屋,新建仿古建筑,让整个古村空间趋于合理统一。古村开发初衷应为追溯历史,还原历史原貌,这在古村的内部是一种填补间隙的方式,游客所看到的应是一座充满人文气息和岁月痕迹的乡村,而非被故意抹平,趋同于主题乐园的单一体。
越后妻有艺术节则是以一种“艺术乡村”的方式,将这一20世纪70年代以来因日本高速发展所造成的“遗弃地带”打上富有人文关怀色彩的“补丁”,这是对城镇发展进程中同质化趋向最为温柔的抵抗。越后妻有地区自绳文时期就有先民居住,具有深厚的文明积淀,在此创作的当代艺术作品显然与原本村落中的农耕文化之间形成了强烈落差,但艺术作品“在地性”的创作途径又保证了两者在这片土地上有了共生共存、相互维系的可能,观者可以通过欣赏“蒙太奇”的方式去观看这种断裂与冲突,这种凭借艺术抵抗同质化的方式比对古镇的刻意营造高明得多。[3]1
俄裔美籍艺术家伊利亚·卡巴科夫(Ilya Kabakov)与他的妻子艾米利亚·卡巴科夫(Emilia Kabakov)在第一届越后妻有艺术节之时创作的《梯田》⑦(TheRiceField)(图5)已成为艺术节的常设作品。这件作品自矗立之时便牵动着整个艺术计划的理念核心。该作品的主题源自越后妻有地区的农耕文化,充分体现出公共艺术所强调的“在地性”。艺术家将农耕的每个过程用人形剪影的雕塑予以展现,构成了雕塑与耕地之间的互动关系。观众可以走入田间近距离欣赏,也可以在瞭望台上远观,在瞭望台上可见田间的人形剪影与悬空的文字相匹配,以文字阐释耕作的不同阶段,形成一种特殊的绘本模式。《梯田》即为一件典型的“拼贴式”的艺术作品,其高度几何化的抽象人形剪影就具有着补丁的意味。艺术家采用了鲜艳的色彩来表现人物造型,创造出属于艺术的乌托邦,与原本的农耕文化之间产生了奇妙的间隙。由于艺术作品的介入,观者欣赏这一方土地时会油然而生一种新的心境,这片耕地不再是自然本身,而是时间与记忆的载体,艺术成为观者回溯起文化记忆的温情媒介,由此塑造出了一种带有“孔隙”的景观形式。

图5 伊利亚·卡巴科夫、艾米利亚·卡巴科夫,《梯田》,2000
这类在原有生态环境中运用“补丁”方式创作出的艺术作品在越后妻有地区还有许多,例如田甫律子(Ritsuko Taho)创作的《绿色别墅》(GreenVilla)(图6)。艺术家在大地上用土的起伏雕刻了“火”“水”“农业”“艺术”“天神”五组词汇,以有生命的自然植物作为艺术媒介,通过堆砌的方式把这些象形文字烙印在大地表面,意图将文字的文化内涵注入到了这片文化记忆缺失的地带之中。该作品体现出农耕文化的历史性与当代艺术的现代性之间相互融合的可能性,五组词汇既是对越后妻有地区传统元素的凝练,同时深刻反思了人与自然、历史的共生问题。

图6 田甫律子,《绿色别墅》,2003
伊利亚·卡巴科夫夫妇与田甫律子创作的作品具诸多相同的理念。首先,两者的作品均呈现非常“轻盈”的视觉效应,在体量上,无论是散布田间的人形雕塑,还是与大地同色的象形文字,都力求将自己的作品融于原本的生态环境之中,原本的自然才是构成艺术作品的基础,艺术家的创造只是在此基础上的画龙点睛。其次,两者的表现手法上都较为抽象,人形雕塑采用了单一的色彩表现,而田甫律子所用的文字则是最为抽象、最为符号化的代表。艺术家在此创造的更多是一种观看的方式,而非观看的对象本身,通过艺术家的引导,观者能够更多地将目光回归于作品背后的自然,再次发现当地自然与人文的魅力。这些“在地性”公共艺术意图以艺术唤醒乡村的记忆,在后工业时代的机械图景中格外能够激起观众关于“原乡”的共鸣。城市指向于未来,乡村指向于过去,身处城市之中的人难以找到自身的位置,容易回归到乡村往昔的怀旧情绪中。显然,怀旧和记忆均为人的情感中最为温柔的部分。
三、“生长的艺术”:艺术与自然的动态性
(一)艺术作品本身的动态性
记忆总是在时间的流逝中发生作用,因此在越后妻有的艺术创作中有许多象征时间尺度的作品。这类“在地性”作品打破了关于艺术作品“制作完成”的固有观念,而是将时间的流逝形象化地表现于艺术作品之中,艺术家经手创作完成的艺术品只是在时间中延展的胚胎形态,艺术家、在地的居民和自然共同协作才促成了艺术作品之后的“生命”,此在越后妻有表现为一种“生长的艺术形态”。[3]60
在空间尺度上,《梯田》绝非仅停留于艺术家所作的雕塑和文字之中,原本的梯田空间显然也是整件作品的延展部分。在时间尺度上,《梯田》呈现出了双重的时间线索,第一为观者通过欣赏作品而感知的不同农耕阶段的四时之变,观者能够以此感受到这个寒冷的“雪国”村落的时间尺度;第二为在不同时节观看这件作品时,能够对位到不同的农耕场面,梯田中的作物因季节而展现出不同的生长阶段,自然无时无刻不在涉足作品,与艺术家一起共同创造四时不同的景观。内海昭子在第三届艺术节上创作的《为了那些失落的窗》(ForLotsofLostWindows)(图7)同样成为越后妻有最为知名的常设作品之一。艺术家在乡间树立了一扇孤立的窗户,两片白纱窗帘随风飘扬,将无形的风存留在作品之中。和卡巴科夫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是两组作品都运用到了边界的概念,卡巴科夫用边界在瞭望台上框出了观者观看的区域,形成了绘本的画面感;而内海昭子则用窗户的边界对清津川的景色进行截取。这种方式就像是一位写生的画家在框选他所描绘的画面范围,此种“在地性”形式让观者从艺术家转译之后的自然中脱离出来,可以置身自然之中随着艺术家的眼睛去观看真实的山水,注视在生活中常被忽视的风景。窗户和画框从来都只是附属物,和上文所述的椅子暗示着人的姿态一样,窗户让人联想到窗户以外的原本建筑空间,画框让人联想到以画框为限的画面,观者会以一种对待画作的态度去观看“如画”的自然,简单的边界赋予了观看厚重的仪式感,在对风景重新的审视中同时完成了与自然的交流过程。丹尼尔·布伦(Daniel Buren)在濑户内海边的小城也曾作过类似的户外装置作品,他用极具个人艺术特色的黑白条纹边框来截取作品背后的风景,以几何的纯粹对比自然的万端变幻。但是丹尼尔·布伦的作品属于艺术家个人,他的作品只会让人直觉地联想到艺术家,而内海昭子的窗在界定了风景之余,那随着微风摇摆的白纱窗帘往往让观者体验自然的同时联想到自己的情感,是家的温情,抑或是人离去后的飘渺和空虚。内海昭子的作品相对于丹尼尔·布伦更具有人文关怀意味,此得益于越后妻有艺术节策展人北川富朗(Fram Kitagawa)要求每位艺术家在创作之前先要进行实地考察。

图7 内海昭子,《为了那些失落的窗》,2006
(二)观赏路径的动态性
在都市生活中,追求效率的思维惯性导致了艺术作品过于集中化,观众希望在较短时间内欣赏更多艺术品的想法让以美术馆为核心的白盒子空间成为欣赏艺术的主要场所。此种观赏场合产生了令人烦恼的矛盾:艺术家面对着自然写生,描绘着自然,但这些画作却又重新回到城市的室内空间被展示出来,观者以画框为窗,在室内通过画家的画、摄影师的照片去认识自然之美,必然逐渐丧失了与自然共处的能力。《梯田》《为了那些失落的窗》以及《09号天空捕手》这一类以边界框选风景的作品将自然纳入了作品内部,自然本身的动态性成就了作品的动态性,艺术作品由作品本身走向了观看的媒介,真正的作品是在框和界之后的自然。再者,创作于村落之间的客观条件让越后妻有的艺术作品处于一种分散的状态,作品散布于760平方公里内不同的村落之间,这让观者的巡游路线纳入了更长时间的观看体验之中。有别于在白盒子空间里“作品—作品”之间的观看切换,在此,村落的人文、风景成为观看之间的转换媒介,构成了“作品—村落/风景—作品”的观看路径。这种在空间上的分散和时间上的延长让观者获得“沉浸式”的体验,因作品之间距离的不同造就了对自然和作品的不同感受,参观者的游览路线演化为以艺术为路标的山林巡旅。[3]2-13如今对效率的追求让艺术展览朝着更快速度发展,意图尽快营造起双年展或是三年展的品牌效应,而“生长的”公共艺术则让这种节奏放慢,让居民看到的是时间所带来的改变。德国明斯特国际雕塑艺术展和越后妻有艺术节一样,是以艺术激活城市化发展的成功案例,艺术展以10年为期,并且重复邀请以往参与过这项计划的艺术家再次创作,艺术展览由此成为城市发展中的历史节点,正如总策展人卡斯珀·柯尼希(Kasper König)所言:“一个节奏缓慢、长达10年的间隔是检验雕塑的创作方式及其与社会关系变化的最好方式。”明斯特是中欧的天主教重镇,在“二战”中几乎被完全摧毁,整个城镇人口不到30万,但自行车的保有量却高达90万辆,被称为“自行车之都”,这种机械、战争、宗教的主题构成了明斯特的独特文化记忆。杰瑞米·戴勒(Jeremy Deller)曾在此开展《对大地说话,它会告诉你》(EarthandItWillTellYou)计划。这项计划耗时十年,让普通的德国家庭以“自然日记”的方式记录在这十年中家庭和土地的变迁。民众的参与让艺术作品随着城市一同发展,艺术作品不再是城市的地标,而是承载文化记忆、激活反思的引擎。公共艺术作品在城镇空间中以“生长”塑造永恒,以生长记录新的历史。
四、走向大众:创作主体的转移
苏珊·雷西(Suzanne Lacy)在《量绘形貌——新类型公共艺术》中提出了“新类型公共艺术”(New Genre Public Art)[10]8这一概念,这种艺术类型脱离了以美术馆和博物馆所构建起的价值体系,是真正走向大众的公共艺术类型,越后妻有则是“新类型公共艺术”典型的乡村实践案例。⑧正如北川富朗所说:“在大地艺术节中,艺术只是一个催化剂,用以呈现当地的历史和人的生活方式”。乡民本来就是乡土的主人,艺术家只是越后妻有匆匆的过客,在越后妻有,艺术作品的参与和维护主体由原本的艺术家变为当地居民和艺术家来共同完成,体现了创作主体的回归。伊利亚·卡巴科夫和艾米利亚·卡巴科夫所创作的《梯田》在设计之初曾遭到农田主福岛先生的反对⑨,而在主办方、艺术家多次与福岛先生沟通之后,事情出现了奇妙的转折,在作品安置完成之后,福岛先生又重新在这片荒废了的土地上开始耕种。[11]14艺术和乡村在此得到了和谐的融合,在眺望台上,可以看到福岛先生和艺术家的人形雕塑一同耕作的场面。相较于美术馆中画作前的警戒线,《梯田》以一种开放的姿态欢迎农田主在此耕作,也欢迎观者踏入其中。在艺术作品“完成”之时,这片土地就交还给福岛先生耕作,“梯田”因由他的耕作而改变了面貌,福岛先生的身份和艺术家一样,都是这件艺术作品的创作者。直至2003年第二届艺术节开始之时,福岛先生才终因腿伤而彻底放弃了坚持了6年的耕种,主办方开启了“松代梯田银行”计划来维护越后妻有地区的耕地,将这片梯田的赞助人纳入了艺术作品的参与因素中。至今,在越后妻有认领荒废土地的已有300余人,企业团体8个,赞助耕作面积超过8万平方米。此外,越后妻有还启动了空屋改造等许多涉及当地居民土地和住房的艺术项目,主办方在这些项目的推进中将艺术家安排在当地居民家中进行驻地创作,让艺术家真实地体验当地的生活状态,也便于向当地居民传达艺术计划中的必要信息。在改造方案制定之后,艺术家需要和屋主阐述改造计划,以此确定最终的协商方案;在改造方案中,当地居民拥有和艺术家一样的话语权,他们可以提出自己对方案的建议,也可以将自己的想法和经历融入改造计划之中,让艺术创作和乡村的主体需求完美契合。艺术介入乡村必定会遇到许多难以调和的矛盾,艺术家对创作往往带有理想主义色彩,而乡民更多考虑的是计划落地后所产生的切实影响。因此,相互沟通成为了策展团队的主要任务,只有在与当地居民的交流之后,艺术家才能创作出真正属于这一片土地的作品,让艺术作品和当地生活紧密连接。同时,优秀的作品又增强了当地居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故而,当地居民多愿意主动参与艺术计划,帮助艺术家顺利完成作品。[3]72-83
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为我们提供了当地居民和艺术创作之间良性对接的范例。艺术家不是高高在上的指导者,而是愿意悉心倾听当地故事的聆听者,创作也不只是艺术家的个性表达,而是展现了基于地缘文化的人文历史。[12]11-19这种创作过程保证了当地居民的参与热情,也只有这样的创作过程才能让艺术作品真正地根植于大地,让艺术成为重塑当地文化记忆的重要途径。
五、结语
在每次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之后,主办方都会整理出本次艺术节的报告书,梳理活动成果、提出改善建议。由《2018年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报告书》可知,当届参观人数已达54万人次,其中主要的到访游客为20岁到40岁之间的青年人,并有8.7%的游客来自国外,足以体现艺术节的影响效益。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所导致的乡村人口流逝已为许多地区正在或将要面临的通病,日本越后妻有艺术节的成功经验无疑给中国的艺术家和地方政府以深刻启示。笔者以为,其重要启示当在于:如何在走出都市、回归乡村的愿景中构建起自然生态、策展人、艺术家和艺术作品之间的新型关系,此不失为对当下我国“美丽乡村建设”、打好“扶贫攻坚战”的有力回应。面对乡村人口老龄化和文化记忆缺失所造成的“废墟”,越后妻有艺术节体现出了艺术与地缘文化,艺术家与居民、到访者之间的一种颇具建设性的新型关系,对我国众多需要唤醒的古老乡村的保护与发展极具参考价值。[13]127-128
首先,乡村公共艺术创作需要有效地把握地缘文化特征。“艺术乡村”首先要做的是艺术修复。越后妻有地区在4000年前的绳文时期已有人类居住,“火焰型土器”便出土于此,土地和人一直以来紧密联系,其悠久的历史文脉提供了在此唤醒遗失的文化记忆的无限可能。此类文化底蕴的乡村中国同样为数不少。
其次,乡村公共艺术创作的主体应该回归到当地居民,他们才是这片土地上最有话语权的人。文化记忆不应全然由艺术家之口言说,让当地居民参与艺术创作,不仅能激发当地居民的文化认同感和参与积极性,也能保证艺术计划的顺利落地。
近十多年来,中国各地纷纷出台不同类型的乡村艺术计划,如2007年许村计划、2008年石节子美术馆、2011 年碧山计划、2019年武隆·懒坝国际大地艺术季[14]72-79,可见我们已经认识到以艺术唤醒乡村记忆的重要性与可行性,不过只有在对乡村文化充分感知的基础下,才能真正实现以艺术的方式介入并重塑乡村文化记忆的时代使命。
毋庸置疑,最懂乡村、最爱乡村、最依赖乡村的人,只能是乡村居民,故而我们应该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与关怀,此为“艺术乡村”的出发点,也是最终归宿。
① 大地艺术”也被称为“Earth works”或是“Earth art”,此类艺术类型将自然材料予以重新的排练和制作,以形成景观型的公共艺术作品,吸引参观者关注和讨论自然,著名的大地艺术家有安迪·高斯沃西(Andy Goldsworthy)、杰里米·昂德伍德(Jeremy Underwood)等。
② 阿斯曼夫妇在后期将“文化记忆”定义为“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所特有的重新使用全部文字材料、图片和礼仪仪式的综合”,并由此产生了“一个群体的认同性和独特性的意识”。参考阿拉尔德·韦尔策(Harald Welzer)的《社会记忆(代序)》一文,收录于其所编的《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③ 据统计,到2008年第七届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之时,已经有40座废弃的房屋和10座废弃的学校通过艺术家和当地居民的共同努力转变为艺术展示空间或是配套的功能性空间。
④ 巫鸿在《废墟的内化:传统中国文化中对“往昔”的视觉感受和审美》中借用古代希腊旅行家保萨尼阿斯(Pausanias)的描述进一步阐释了废墟的美学意义,促使人们去欣赏和品位那些由自然而非人力所形成的遗迹。
⑤ 值得注意的是,越后妻有的“空屋项目”也是一种存留文化记忆以抵抗遗忘的途径。通过将当地文化语境下的居民群体与遗留下来的空间相结合,从而挖掘出地方再生的契机。可以说,这种方式是对前述艺术创作的延续与拓展。
⑥ 本雅明曾分析过19世纪巴黎的城市景观,撰有《巴黎,19世纪的首都》一文,曾提及南方的城市构造是“多孔多隙”的,城市的创造者将城市的建筑物视为是即兴创作的舞台,而例如巴黎这样的北方大都市则是形成了一种“幻想”:城市由大众建造起来,但由于巴黎人习惯于群体性活动,个人最终会沉没于人群之中,大众由城市的主体转变为了城市的客体。
⑦ 在日语中称之为“棚田”。
⑧ 所谓“新类型公共艺术”,相对于传统陈列在公共空间的雕塑更具社会性,其以公共议题为导向,让民众介入、参与、互动,并形成公共论述的艺术创作。它也许有形(如壁画、装置),也许无形(如行动、表演);有的长期存在,有的短暂停留,但都以公共利益为依归。
⑨ 从1999年开始,艺术家就尝试与福岛先生相沟通土地事宜,虽然当时这块梯田已经因福岛先生的腿伤而荒废,但因起初对创作的不理解,福岛先生还是拒绝了在此安置艺术作品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