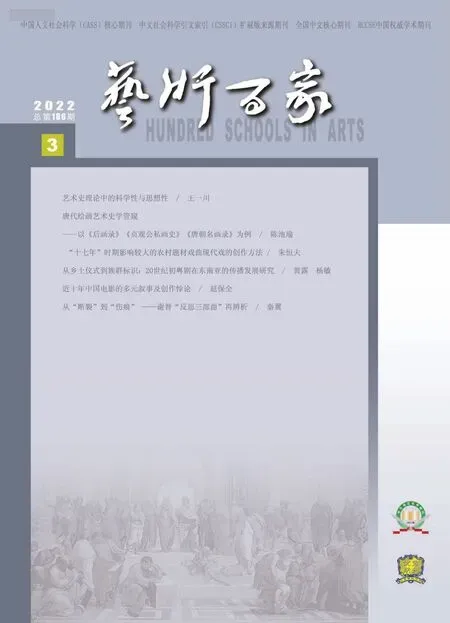论张彭春20世纪30年代对新剧和旧剧关系思考的翻转*
邹元江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张彭春于1913年至1915年、1919年至1922年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分别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在此期间直接接触了西方现代写实戏剧,并创作了《入侵者》《灰衣人》《醒》《木兰》等剧作、导演了《一念差》《新村正》等大量剧目,他最初对新剧和旧剧的认识判断不同于张豂子等从中国传统戏剧出发的学者,这些学者极力反对以胡适等为代表的一批留洋归来的人以西方话剧的思维对中国传统戏曲加以否定的做法,而张彭春则是以他所熟悉的西方话剧为参照,比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钱玄同、刘半农、胡适、傅斯年、周作人等人更早对旧剧加以批判。但在这之后的近二十年里,张彭春应邀参加协助梅兰芳访美访苏的演出策划、剧目选择、舞台调度、宣传传播等,甚至被梅兰芳誉为“京剧的大行家”①,这不仅让他在20世纪30年代对新剧和旧剧关系的思考发生了重大翻转,而且给他的中西戏剧融通思考带来了很深刻的影响。
一、改良“不近人情”之旧剧
张彭春最初对新剧和旧剧的认识判断可参见1916年初其以铁卿的笔名发表在南开《校风》上的《说改良戏曲》②一文。为何要改良戏曲?张彭春认为:“戏剧感人最深,而收效最大,其功用较之小说,有过无不及。”虽然“教育为救国之本”,但中国十之八九不识字,真正有收效的教育就是让百姓听戏曲,因而,“改良戏曲一事,不容缓矣”。但旧戏虽流传甚久,但“其中流弊甚多”,张彭春列举了四点,除了“唱工太多”“词多鄙俚”“多半淫邪不堪入目”外,“最大之弊,即不近人情。舞台之上,一无所设,忽而堂室,忽而战场,使观者全以想象得之,不能如新剧之布景引人入胜,使观者如身临其境。至于演作,则一剧之中,有宾有主。为主者,精神抖擞,不敢有怠容;为宾者,则似与此事无关,木立其旁,不动声色。如演《冀州城》一剧,马超见妻子被杀,痛恸难堪,而其弟则声色不动,即陌路之人,亦不应有此,矧(shěn况且)骨肉之间,乃如此者,揆之人情,有是理乎?又若装饰,则更诡异,他无论矣,即如画面一事,已大不尽情,横涂竖抹,直如奇鬼,假令古人复起,当不识本来面目矣。……夫剧曲之所以能感人者,不过以情感情。今以不近人情之剧,而欲其感人之情,不亦难哉!故演剧之人,不过逢场作戏,毫无深意之存,而观剧者亦不过游目骋怀,不作高尚之想。以故千百年来,未得丝毫之益。揆厥所由,皆不近人情一事有以致之也。此应革不容缓者也”。
如此看来,张彭春在对待旧剧上,比他之后的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钱玄同、刘半农、胡适、傅斯年、周作人等人更早地持批判态度。除了“词多鄙俚”“多半淫邪不堪入目”的确是旧剧应革除的弊端外,像“唱工太多”“不近人情”所涉及的布景、“间情”、脸谱等问题,也多为后来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所诟病。但显然,无论是张彭春,还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最初在对旧剧“唱工太多”“不近人情”等诸多问题的批判上都是以他们所熟悉的西方话剧为参照,张彭春提出要革除这些流弊的主张,也是在他1913年至1915年第一次留学哥伦比亚大学之后,因而,他也像后来的批判者一样,对他所批判的对象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
所谓“唱工太多”是张彭春基于戏曲“观戏为听戏”而言的,但他也并不是绝对反对唱工。他说:“夫唱非不可有,遇悲歌慷慨之时,非纵声一唱,有不能痛快淋漓者。”张彭春所反对的是旧剧“过重唱工,唱工以外,不事讲求。故喉音之佳者,则幼童可以为耋夫,耋夫可以饰幼女,丑态百出,令人欲呕。而观者则只听其音,而不计其他。则戏曲二字,竟以唱工括之也。而欲责以感人,教人之事,宜其不知也;呜呼!此弊安可不急谋改革之哉!”其实,戏曲艺术的特性恰恰在于审美的间离性,幼童所饰演的耋夫并不需要在年纪上与日常生活中的耋夫相仿,关键是幼童的声腔能够传递所饰演的耋夫长者声音的神韵,观众所欣赏的幼童的声腔实际上是与幼童的年纪相间离的。1958年夏的一天,梅兰芳的老朋友苏联名导演柯米萨尔热夫斯基和几位摄影师到梅家,希望为梅拍一段彩色“全景电影”。柯米萨尔热夫斯基说:“这部电影命名《宝镜》,是把世界上许多神秘莫测的事情汇集拍摄的,现在打算请您拍《霸王别姬》舞剑一场和家庭生活,以您的年龄来扮演历史上有名的虞姬,是符合我们选题上的意图的。”[1]396这一年梅兰芳已是64岁。柯米萨尔热夫斯基特别强调“以您的年龄来扮演历史上有名的虞姬,是符合我们选题上的意图的”,这说明起码在苏联艺术家看来,中国戏曲艺术的魅力并不取决于演员的实际年龄如何,即便是已经64岁高龄的梅兰芳扮演风华绝代、年轻貌美的虞姬,实际上仍给人以风情万种的审美享受,观众完全可以忽略或者忘记演员的实际年纪——这正是世界上令人感到“神秘莫测的事情”。由此可见,中国戏曲艺术的魅力并不是建立在真实体验式的基础之上的,训练有素的观众看见(听见)了他们该看见(听见)的,而忽略了他们不该看见(听见)的。
至于张彭春要求应刻不容缓加以改革的戏曲艺术在布景、间情、脸谱等方面“不近人情”的问题,其实也多是他依照西方话剧的思维作出的判断。没有布景,这恰恰是戏曲非对象化审美思维的特性之一。空的空间并不就是空无所有,庙台、戏楼、舞台上非实体的布景(环境)显现是由观赏者的想象力依据唱词、念白的描述和暗示加以意象性生成的“虚的实体”。这与中国哲学美学的阴阳、有无、虚实、黑白、隐秀等基本的思维模式是一致的,即中国戏曲艺术并不意在追求对象性世界的真实性(布景的本质就是提示戏剧表演的真实场景),而是更多倾向于借助极少的舞台象征性砌末(一桌二椅、一只船桨、一条马鞭等)让观众在非对象性的意象世界里感受到活的厅堂、山水、舟船、马匹等“虚的实体”的显现。所以,没有布景,并不就是“不近人情”,恰恰相反,它是最贴近中国戏曲观众想象性欣赏的诗意的人之“常”情,只是它并不贴合西方观众模仿性思维的现实(逼)“真”之情而已。一切从求真出发,自然就认为《冀州城》一剧中在马超为妻子被杀而悲痛欲绝时其弟不动声色显得不近人情。其实,戏曲艺术更关注的是声情和曲情,它是与日常生活中的真情相间离的“间情”。要真正达到这种更具审美意味的声情曲情,其他任何干扰因素都应当被排除,这就是戏曲界行话所说的“不搅戏”。这一点钱穆早就讲过,他以《三娘教子》为例,在三娘大段悲痛欲绝的声腔里,旁边的倚哥毫无表情地跪在那里,甚至有时候饰演倚哥的演员干脆就下场休息,等到三娘快唱完了,再上台跪在那里。[2]127当年在《汾河湾》中,当谭鑫培饰演的薛平贵在窑外用大段声腔诉说自己18年戎马倥偬的艰辛和离别妻儿之思念苦闷时,梅兰芳依照齐如山“合情理”的要求做身段表情,这让谭鑫培惊讶不已,因为,观众这个时候只关注谭鑫培的唱工如何,并不太在意窑中王宝钏的情感如何与薛平贵交流。[3]106—109这就是声腔与人物情感相间离的间情。凡是具有审美意味的纯粹艺术样式,如芭蕾的独舞、双人舞、三人舞,歌剧的宣叙调、咏叹调等,除了舞蹈者和歌唱者,其他台上的人都是不能随着舞者的舞姿、歌者的唱词“合情理”地做表情的,甚至都要退到后台,让观众专心致志地欣赏美轮美奂的舞姿和声腔。戏曲既然是间情的纯粹艺术样式,“横涂竖抹”的脸谱自然也不是“大不近情”的,而是与戏曲的非对象化审美原则相一致的。脸谱的象征性实际上是从中国文化的类型化思维延伸出来的审美表达方式。它绝对不是西方戏剧所追求的个性化现实中的某一个人的表象特征,而是某一类人的本质特征,因而,它恰恰不是“更诡异”,而是更具有形象性的有意味形式,是可以单独欣赏的艺术珍品。
二、以“新的演作者”改革新剧
1931年1月20日,《南开大学周刊》第101期发表了一篇署名“张彭春讲、范士奎记”的《舞歌与剧——怎样改革新剧》文章。这是作为张彭春学生的范士奎“看新剧和日常生活的动作,实在太缺乏美感,也太丑了”,才想到把张彭春前几年谈戏剧问题的意见“追述出来”加以发表。显然,这是一篇与上文在对待新剧和旧剧的观念认识上有所变化的文献。
张彭春首先介绍最近心理分析学家将人类的心理分成两类,一类是Schizoid型,这类人喜欢独善其身、独乐其乐,不喜欢与人交往;另一类是Syntonic型,这类人喜欢与人交往,一听鼓励的话,其能力能够增加几倍,越当着大众做事,他越勇猛。张彭春认为,“演剧是以人体作发表工具的艺术,是当着许多观众前表现出来的,所以Syntonic这一派人居多数,并且也实在合乎他的心理,在人前他的力量全来了,若是听了喝彩声和鼓掌声,那他的表演就更佳了”。那么,“以人体作发表工具的艺术”有哪些呢?张彭春认为有三种,即舞蹈、演作和歌唱。这三种艺术家“藉他自己的身体可以引起观众的同情。观众也可以藉着他的表演,舒畅了感情——许多实际生活得不到的感情,藉他的演作,得到观众的同情。观众同情后,他(演者)就快乐了,观众得到无上的慰安”。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张彭春从人体艺术的角度提出“演作”这个概念,这是百年话剧史上没有出现过的一个非常有内涵的词,它指的是用身体来表现的戏剧和演员。这里的“戏剧”和“演员”是指没有或歌或舞的演作和演作者。在张彭春看来,“要提倡一种新的剧,必需要有新的演作者,新的演作者,比新的剧本还重要,因为就是新的剧本无新的演作者,那只是‘半幅’剧本,只能读,而不能使观众欣赏、领略,所以提倡新剧,必须新的演作者在先”。那么,这个“新的演作者”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能力呢?张彭春认为必须是可以将舞蹈和歌唱结合起来加以“艺术化”的演作者,即过去“新剧”的演作者,虽然是以人体作发表的工具,但显然是缺乏艺术化的,更多依赖于剧作的思想性,而演作者却不能有效艺术化地传递思想。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新剧”的“普通的演员,多半没有经过舞蹈和歌唱的训练……他的举止和声音,都有如吃尽十二分气力的。‘拉锯’者结果还是刺人耳目,一点儿也不受看中听”。也即,当时流行的“新剧”的演作并没有凭借演作者的身体表现性真正实现戏剧的演作感染力。这正是张彭春呼唤“新的演作者”的原因。
但此时的张彭春并没有意识到培养“新的演作者”与借鉴“旧剧”艺术形式的关系,他仍只是从旧剧所表现的思想内涵上认为“中国旧剧已经不稳固了。因为她离我们日常生活太远,不能满足我们的生活”。张彭春之所以希望培养“新的演作者”,其实,并不是因为当时已经有了真正好的“新剧”,急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新的演作者”来呈现,而是非常敏锐地意识到是新的生活还“没成形”,所以“都等着我们给它‘艺术化’”。新的生活还“没成形”,所以,以反映新的生活为宗旨的“新剧”也很难有深刻的内容,只能设法用“艺术化”的外表来遮掩思想内容的贫乏。那么,如何“艺术化”呢?张彭春明确提出“必得和歌舞连起来”。他说:“以前没有和歌舞连起来,所以没有成绩,许多的尝试都失败了,那么将来如何训练新的演作者呢?除了和歌舞连起来,简直没有第二条道。”可问题是,用于训练新的演作者的“歌舞”是什么歌舞呢?张彭春虽然对歌唱的训练内容没有明确说,但却对舞蹈的学习对象给出了答案:“我们不能不吸收希腊的舞蹈。那种舞蹈是全身的、自然的、感情的,合于美的不仅是一个演员,就是常人有这种舞蹈的训练,则他日常生活,亦可以有了‘韵则’。”他说法国一个叫Dalcroze的人将这种训练方法命名为“Eurhy Hrinies”,即“由自然的动作慢慢入手”。
由此看来,张彭春此时虽然仍对旧剧持否定态度,但也并不像他早期那般对新剧一味加以肯定,而是针对新剧表现力太差的问题提出以歌舞改革新剧演作者表现力的主张。此时,他并没有意识到旧剧载歌载舞的表现形式对新剧演作者能力提高的意义,而是将歌舞借鉴的目光投向了西方古代。
三、向旧剧借鉴新剧“新的表达形式”
如果说《舞歌与剧——怎样改革新剧》还只是张彭春对新剧和旧剧认识探索的过渡期想法,那么,1933年7月15日在《南大半月刊》第3、4期合刊上发表的《中国的新剧和旧剧》一文则反映出他对新剧和旧剧的认识已发生了重要转折。这其中最重要的契机是1930年1月18日在华盛顿参加中国大使馆欢迎梅兰芳访美招待会后,张彭春临时紧急应梅兰芳的邀请指导协助他访美演出。③另一个契机是1931年暑期张彭春在欧洲访问期间,曾到苏联莫斯科梅耶荷德剧院参访,并与梅耶荷德作了一次有关戏剧艺术的谈话。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张彭春对新剧和旧剧有了更加理性的认识。他说:“中国的戏剧及其他文化表现形式,已经受到现代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这种复杂的情形中,有两种动态很清楚,即对于戏剧的新形式的尝试和对于传统戏剧的重新评价。”对于戏剧的新形式的尝试,作为南开话剧直接的组织者、导演者的张彭春如数家珍,而作为新剧本的尝试创作者,他也有深切的体会。他说这些剧作家“感到由于周围的社会变化,新的经历要求戏剧要有新的内容和新的生活哲学。旧的戏剧是传统道德观念和传统价值观念的载体,而这些正在经历着不可避免的改革。新的白话剧反映现实复杂的社会生活。……新的生活经验要求新的表达方式”。显然,这里所表达的正是上文《舞歌与剧——怎样改革新剧》所传递的信息,即反映新的生活经验的新剧,需要寻求新的表达形式。这个“新的表达形式”从何而来,《中国的新剧和旧剧》一文与几年前《舞歌与剧——怎样改革新剧》的表述却大相径庭:后者直接将“新的表达形式”的借鉴目光投向了古希腊舞蹈,而前者却回到了传统戏曲艺术自身。这涉及如何重新审视和再评价一度被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以及张彭春自己所否定的古老的戏曲艺术的当代价值问题。
张彭春说:“当新剧正在被人们所适应的时候,当人们尝试着给这种外来形式以一些中国特色的时候,对于中国传统戏剧应采取什么态度呢?具有七百年以上的自己民族的戏剧如何地受到审视和再评价呢?”此时的张彭春已经非常清晰地意识到,“在新文学运动的最初阶段,做出下列断言并非个别现象:传统戏剧不包含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并注定在进化过程中消亡。然而,近来人们已将注意力集中于研究这古老的艺术,看看这日臻完美的表演技巧中是否可能有些值得分析和重新评价的东西。虽然旧戏中可能有些观念不再适应时代要求了,但是在舞台上,在精彩演出中,仍可发现有益和具启发性的因素。这些因素不仅对中国的新剧有好处,而且,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现代戏剧也有好处。两年前,当我参观莫斯科梅耶荷德剧院时得知梅耶荷德训练演员的方法,我感到惊喜。在我有幸和梅耶荷德进行的一次谈话中,他告诉我他观察到了中国和日本传统戏剧演员灵活的形体控制和协调并受其影响。他从中获得启发,演化为他自己的演员训练系统并称之为‘生物——技巧训练法’。每天早晨他要求演员们进行一系列程式化训练,使得身体各部分具有柔软性(Plasticity④)和灵活性,并促使肌肉和头脑的有机协调。”不难看出,张彭春之所以提出要重新审视和再评价戏曲传统的当代价值问题,显然与他1930年协助梅兰芳访美演出和1931年访苏得知梅耶荷德借鉴中国戏曲训练演员的方式训练苏联演员时的“惊喜”有密切关系。梅兰芳访问美国的确让世界其他地区的现代戏剧发现了“有益和具启发性的因素”。张彭春作为直接在异域亲历戏曲艺术被珍视的见证者,显然改变了对新剧和旧剧,尤其是对旧剧的观念。
此时张彭春对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价值的评价之高、认识之深,在其同时代的评价者中甚至可以说无出其右。他认为:“根据中国戏剧的传统,演员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训练,通常从十二三岁就开始,持续七年或更长的时间。这种训练非常严格。舞蹈的基本功——从广义上讲包括身体各部分的运动——和歌唱基本功,必须学习和训练得非常细微。中国传统戏剧演员的和谐和优美就是这种强化训练的成果。就是在这种对身体的灵活性的重视中,我们发现了传统戏剧的一种辉煌成就。”不仅仅是对戏曲艺术身体表现性予以充分肯定,张彭春对戏曲艺术非再现的审美观念也作了深入阐发。他意识到,“传统的技巧显然不是以单纯再现现实为目的的。中国传统戏不是以精确地模仿现实生活的细节而著称的。在中国传统戏剧中,台步、道白、服饰、化妆同日常行走、说话、穿着和面部外观都有着显然的不同。然而,为了舞台效果而从现实生活中提取精华的过程,可不是任意或异想天开的。即使在异想天开中也有一定之规。艺术和现实的区别是逐渐地以协调的方式程式化了的。把艺术从现实生活中分离出来的过程不是某些现代艺术运动所显示出的那种型式。……中国人是以缓慢、渐进的方式演化出现实与艺术之间的区别的”。在张彭春看来,现代艺术的形式都是“突发”的,是断绝与传统的联系的。而戏曲艺术不是骤变的,而是以“缓慢、渐进的方式”与现实加以区别的。这正是后来梅兰芳所发挥的“移步而不换形”的艺术辩证法思想。
张彭春的结论是:“从艺术技巧的角度重新评价,中国的传统戏剧具有启发和教育价值。今天在西方,现代戏剧不是在反对三十年前一直占优势的再现现实的现实主义吗?现代戏剧实践不是正被导向一种简洁、综合和具有启发性的风格吗?”这是非常引人注目的看法,张彭春已经深刻意识到,中国古典的戏曲艺术具有现代西方戏剧所追求的普适价值,戏曲艺术既是古典的,也是现代的。
四、字母组合“构成模式”的旧剧“基本原理”
如果说1933年《中国的新剧和旧剧》一文反映了张彭春在新剧和旧剧的观念上已发生重要转折,那么,1935年张彭春为梅兰芳访苏所撰写的《中国舞台艺术纵横谈》[4]572—577一文,则是他关于新剧和旧剧观念成熟期的代表性文献。⑤在这期间,张彭春再次协助梅兰芳访问苏联演出,并成为整体筹划宣传者,还直接代梅兰芳与西方戏剧家进行对话(翻译),这无疑让他更加深入地发掘领悟了戏曲艺术的审美本质。
这篇介绍性的文章实际上反映出张彭春从20世纪初到当时对新剧与旧剧关系在认识上的一个翻转,也即由最初以旧剧为背景、以新剧为主体而翻转为以新剧为背景、以旧剧为主体的思维格局。此文更是以新剧为参照,着重概括了旧剧的“基本原理”。这个“基本原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以演员的才艺造诣为主导与中心要素”。张彭春认为,中国戏曲艺术既然“以演员的才艺造诣为主导与中心要素”,就意味着“中国演员须同时擅长各种舞蹈、歌唱、说白、哑剧、杂技等技艺……这种着重于演员的综合性技艺的做法,当然需要长期的严格训练。职业演员的训练必须自早年开始,一般从十一二岁,甚至七八岁就开始学戏了。有抱负的演员所接受的紧张、严格的训练往往长达七至十年。上述的各种表演艺术手段,都必须经过细致入微的学习与锤炼。因而只有少数能忍受这种精确的考验,又具有天赋和颖悟的学徒才能升华为才艺出众的演员,而其余的大多数则都半途而废,或成为一些配角。这种谨严训练的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演员在舞台上所展示的身段姿势的匀称和优美,是肉体与精神的完美协调表现于控制自如的造型艺术中。中国舞台上是没有由于个人的魅力而一夜成名的‘明星’的”。张彭春也特别强调,“中国舞台只是我们去看演员们表演的地方”,所以它的舞台布景非常简单,一根马鞭就代表一匹马。但他也提醒我们,“我们主要的兴趣不是马的实体。所谓马鞭代表一匹马,只是说,它的出现使我们注意到演员要进行的是什么模式的动作,是上马还是下马,是表示骑马人正在匆匆地旅行,还是在悠闲地游荡。关键是动作的意义与判断的标准不在于‘什么’,而在于‘怎样’,换句话说,按照舞台艺术的思想方法,重要的不是实物,而是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表演动作的各种模式只是反映人与事物之间的各种不同关系而已”。
二是戏曲表演遵循由“同一种语法所控制”的一系列字母组合的“构成模式的原则”。张彭春说,所谓“构成模式的原则与过程贯串于肌肉运动、口头说唱、音乐伴奏、服装、化装等各方面。可以这样说,在每一种表演艺术手段中都有一列字母组合,而字母组合的各系统又似乎是由同一种语法所控制的”。
三是戏曲艺术由“抒情歌曲和对话交织而成”的叙述方式。张彭春说:“早在十三世纪,在娱乐与表演的各种艺术手段开始融为一体,成为一种统一的艺术时——主要在中国的元代——抒情歌曲就成为主要的组成部分。歌唱总是中国舞台艺术的主要因素。所有的好演员首先必须是好歌手。”
张彭春对旧剧这三个“基本原理”的揭示非常到位。首先是对戏曲的独特叙述方式的确证。源于元曲生旦主唱的“抒情歌曲和对话交织而成”的叙述方式,既不同于西方以对话为主的话剧,也不同于西方以歌唱为主的歌剧,而是介于这两种表演艺术之间的叙事艺术。
其次是对戏曲艺术中心要素的规定。即“以演员的才艺造诣为主导与中心要素”的戏曲艺术虽然与西方话剧明显不同,但却是与西方歌剧相接近的以演员的才艺造诣为主导和中心要素的艺术。所谓以演员的才艺造诣为主导和中心要素的艺术,即舞台只是我们去看这些演员们的才艺造诣如何“表演的地方”,并不太关注剧作的故事性及故事所传递的思想如何。西方的歌剧舞台显然是我们去听(看)演员歌唱(表演)的地方,歌唱的技艺性是观众审美欣赏的首要因素。而西方的话剧舞台显然并不是我们去看演员表演的地方,演员表演所传递的故事及故事所传递的思想是观众观赏的主要因素。话剧演员的表演虽然也有技艺性的一面,但这种更多基于日常生活体验性领悟的技艺性与歌剧演员歌唱基于嗓音先天条件的技艺性,尤其是与戏曲演员唱念做打既基于先天的嗓音条件又基于后天艰苦训练的技艺性相比,显然是有天壤之别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张彭春对谁才是有权利进行戏曲创造的艺术家加以界说:“一个卓越的演员只有在对一般剧目做出了出类拔萃的成绩以后,才能取得创造新格局,对舞台艺术的光辉遗产做出推陈出新的贡献的权利。掌握留芳于青史的特权的人,并不是那些存心扬名的革新者,而是众所公认的艺术能手。”[4]576这段话在张彭春的《中国的新剧和旧剧》一文中表述为:“一位杰出演员在传统的表演中取得突出成就以后就获得了创造新表演程式的权利,并且它可以将自己的成就贡献给舞台艺术宝库,以流传于后世。这样戏剧就向前发展了。只有那些有造诣的艺术名家才有这种创造的特权和将自己的成就载入史册的特权,不是任何存心改革的人都有此特权的。”正是因为中国戏曲艺术是“以演员的才艺造诣为主导与中心要素”,所以,只有真正理解戏曲艺术精髓的卓越的艺术家才有资格取得创造新格局的权利,这是包括西洋歌剧和芭蕾舞在内的所有纯粹艺术样式创新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也正是梅兰芳当年坚持“移步而不换形”创新原则的根本原因。真正的纯粹艺术对内容的依赖性是比较弱的,甚至是“以形式消灭内容”。所以,内容的“移步”是相对容易的,但已经显现为被“同一种语法所控制”的“构成模式”的形式,则具有独特艺术样式所“不易”的本根性,是不能轻易被“换形”的。所以说,对纯粹艺术的“革新”“创新”并不是人人都能轻易呼喊的口号,它是特别值得我们尊重的伟大艺术家的特权。
综上所述,张彭春最初对新剧和旧剧的认识判断是以他所熟悉的西方话剧为参照的,1916年初他发表的《说改良戏曲》一文,比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钱玄同、刘半农、胡适、傅斯年、周作人等人更早对旧剧加以批判。1931年初发表的《舞歌与剧——怎样改革新剧》一文表明张彭春在对待新剧和旧剧的观念认识上发生了变化。1933年7月中旬发表的《中国的新剧和旧剧》一文则反映了张彭春对新剧和旧剧的认识已发生重要转折,其重要的契机是1930年初张彭春临时紧急应梅兰芳的邀请指导协助他访美演出和1931年暑期张彭春到苏联莫斯科梅耶荷德剧院与梅耶荷德进行了一次有关戏剧艺术的谈话,由此,他开始更加理性深切地关注新剧新形式的问题,并对传统戏剧作“重新评价”。1935年为梅兰芳访苏撰写的《中国舞台艺术纵横谈》一文是张彭春关于新剧和旧剧观念成熟期的代表性文献,反映了张彭春从1910年代中期到此时对新剧与旧剧关系在认识上的一个翻转,即由最初以旧剧为背景、以新剧为主体而翻转为以新剧为背景、以旧剧为主体的思维格局。该文对旧剧“以演员的才艺造诣为主导与中心要素”、由“抒情歌曲和对话交织而成”的叙述方式,尤其是对戏曲表演遵循由“同一种语法所控制”的一系列字母组合的“构成模式的原则”等“基本原理”的概括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价值。
① 梅兰芳说:“干话剧的朋友很少真正懂京剧,可是P.C.张却也是京剧的大行家。”参见崔国良、崔红编《张彭春论教育与戏剧艺术》,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88页。
② 之所以说这篇文章是张彭春所写,主要依据一是该文特别推崇莎士比亚,认为“英人莎士比亚编撰戏本,流传海内,为文学中最高之部,乃我国竟无人过问。呜呼!”同一年12月,张彭春在南开大学的英文期刊THENANKAIAN(《南开人》)上发表了一篇随笔,其中特别提及莎士比亚:“今年,全世界刚刚举行了莎士比亚逝世三百周年祭,中国也应当了解这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者……历史剧、喜剧、罗曼司、悲剧——他一概驾轻就熟。大自然向他提供素材——世界就展现在他面前——而他的语言在获取神奇的功效上从未失手。”二是该文用了一个只有张彭春才使用的专有词“演作”,此词在文中一共出现了七次:“至于演作,则一剧之中,有宾有主”“演作姿势虽亦有时注重”“纯以演作及道白为主”“盖演作道白”“方可演作”“若因演作人”“在演作者”。在张仲述讲、范士奎记的《舞歌与剧——怎样改革新剧》(《南开大学周刊》第101期,1931年1月20日)中,张彭春把“演作”作为“以人体作发表工具的艺术”中的一种。在这篇文章中“演作”或“演作者”一词共出现了11次。《从三个观点谈中国戏剧》(《申报》,1935年2月22日)中,张彭春一开始就把今后努力的三个方向的第二项列为“修改剧本及演作”,后文进一步展开为“整理与修改剧本及演作法”。1935年1月中旬,张彭春将梅兰芳在美国访问时(1930年)美国文艺评论家发表的评论文章结集为《梅兰芳在美国:报告及评论》,在序言中张彭春提出“中国的戏剧,如何才能得到世界的地位,决不是闭户自诩可成的,必须注意到世界的需要”,“在演作技术上,世界戏剧感到自己的死板,受写实主义的束缚,而中国戏剧在这方面可给我们不少刺激和参考”。参见崔国良、崔红编《张彭春论教育与戏剧艺术》,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88页。可见,“演作”一词是张彭春前后一贯使用的一个专有词,有其特定的含义。详后。
③ 在此之前,1928年1月初,张彭春在北京与在美国开办华美协进社的孟治同梅兰芳、齐如山等商讨梅剧团赴美演出京剧的事宜。他相信熔歌、舞、剧于一炉的京剧艺术能够被美国观众所接受,并向梅兰芳和齐如山建议由华美协进社办理梅兰芳赴美演出事宜,梅兰芳欣然同意。1929年8月,张彭春给孟治写信说已安排在1930年9月至1931年5月间,邀请梅兰芳访美演出,而梅兰芳多次要求在1930年1月。张彭春给孟治的信中说:“梅之所以如此,就是由于梅认为以他当时在中国的号召力,只要本人愿意,他就能在他选择的任何时间,进入他选择的任何城市的任何剧场演出。……北京、上海都为他赴美演出开过欢送会……梅的支持者已经表示愿意支付一切费用。”孟治照此为梅兰芳访美做了安排。参见孟治著《六十年之追求——中美理解》,华美协进社,1981年版。译文见崔国良、崔红编《张彭春论教育与戏剧艺术》,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67、675、676页。
④ 也译为“成型性”。
⑤ 《申报》1935年2月22日发表的张彭春《从三个观点谈中国戏剧》一文,其基本观点也是来自《中国舞台艺术纵横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