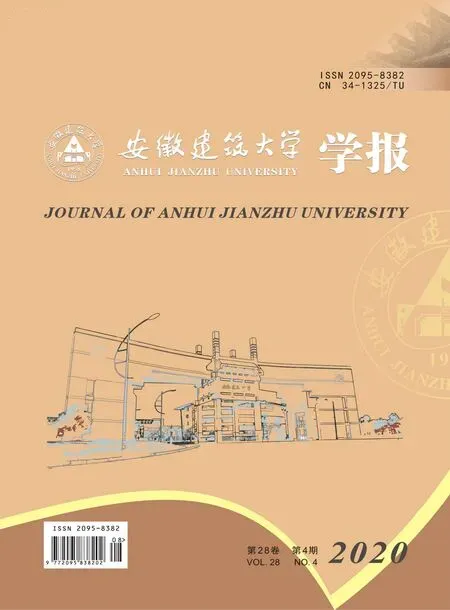浅析古陶瓷修复中残缺美的表达及现代启示
刘宁
(安徽建筑大学 艺术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1 美学视角下残损古陶瓷修复的必要性和价值
陶瓷诞生于我国,不但历史悠久更是有着良好的人文背景和深厚的文化内涵。陶瓷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都非常的稳定,所以古瓷虽然历史久远但仍然可以历久如新。陶瓷有其自身易碎的弱点,精美的陶瓷艺术品是收藏者和爱好者们梦寐以求的佳品,但是面对瓷器的残破艺术家和爱好者们便无计可施。一件古陶瓷完整与残破之间的价值是天壤之别,残破之物便处于一种留之无用弃之可惜的尴尬境地。
作为残损器物虽然收藏价值不如完整器,但是其碎片所承载的历史价值和年代信息仍然是值得学习和研究的最好资料。由于年代久远,物品上留下的岁月痕迹和古风遗韵才是文物价值的体现,这也是收藏艺术家们更喜好陈旧老物的原因,“宁藏残器,不藏赝品”已成为收藏界的普遍共识。如果能换一种方式思考,更多地从它所蕴含的多元文化层面去发掘陶瓷残片的意义,那么残破的古瓷则大有潜力。
2 古陶瓷修复中残缺美思想的运用
2.1 残缺美的思想依托与美学意义
在中华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残缺美有着丰富的传统哲学思想深深地渗透在中国文化艺术各个门类中并散发着独特而夺目的光彩。[1]
残缺美是基于美学视角下,对型体的残缺进行地审美层面的体验和感受。残缺美不同于美的残缺。美的残缺是原本完整美好的事物自身的不完整性,它是一种从美到不美,从完整到残缺之间的过渡形态。而残缺美本身已经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存在形态,它是一种既合理又复杂、多变的审美存在。[2]事物的残缺是一种失去的、被破坏的、未完成的或者是进行中的状态也可以把它理解成空白或者空缺。由于他的空白和不完整,在视觉上带来了一定的不稳定性。为了达到视觉上的完满与稳定,这个潜在的不存在在视觉化的过程中被自动地补全,于是便产生了更大的孕育美的生命力和活力,从而达到了一种美学的意境。
对圆满和完整的追求是审美过程中我们见到的最多最普遍的形式,也是最容易被大多数人接受的形式。但是在我国自古以来审美认识便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局面,这其中既有追求完满的审美封闭也有追求自然天成的审美残缺。[3]儒家的“以和弥缺”,道家的“抱残守缺”,佛家的“大圆若缺”这些残缺都属于美学体系的范畴并具有了极高的审美价值。残缺是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丰富了中国传统美学的层次并且在构成中国传统文化基石的儒释道三家中都有所体现。
2.2 残缺美在古陶瓷修复中的运用
2.2.1 古陶瓷修复的现状和常用方式
通常对待残损古陶瓷的方法是在做完基本的信息采集和预防性保护后,针对残缺拼缝修补完整。保留修复的印迹,使观众能够比较容易分辨或者在较近的观察角度能够分辨出哪些是原器物哪些是被修复的部分,修复的方法完全忠实于原物。
对待古陶瓷我们应该关注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保护”,另一个是“修复”。保护的目标是预防自然老化和人为损坏,停止或延缓败坏发生,持久保护稳定现有状态,而修复的目标则是恢复文物原貌,修补和修饰残缺部分,二者有一定的联系和重复但又有所不同。现有的对待古陶瓷的做法更倾向于文物保护而非文物修复,只是单纯地停留在复原阶段对于修饰的方面的研究甚少,并没有将美学的概念引入其中。这种方式带来的结果是外部形态不够美观,对于大多数非专业的普通观众失去了一定的吸引力。而作为文物本身来说传播历史文化信息,从而吸引观众热爱传统文化进而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才是文物本身的使命和价值。从这一层面上来讲,美学思想中的残缺美表达在修复过程中的介入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2.2.2 残缺美思想指导下的古陶瓷修复
面对古陶瓷残缺遗憾的同时,应该思考的是破碎陶瓷的存在是不是可以有其它的价值和意义。残缺的概念包含心理感受层面和视觉形态层面两方面的内容。我们关注的重点不应过多地放在视觉形态的不完整上而应该更注重精神层面的完整性。[4]在商品修复(商品修复指对于器物的修复部分进行上色以达到淡化修复痕迹,甚至达到天衣无缝的效果,在学术界对于商品修复的合法性颇有争议)的过程中,完全可以将残缺瓷器修复到和原来的器物完全相同,但器物的残缺终究是事实。外形的完整更多程度上是掩盖内心残缺感受的一种方式,或者是以残充好来达到某些商业目的需要的一种手段。关注残缺形态不应只是停留在视觉形态的不完整上,而是要去从更深层次去分析外在形态下掩盖的精神内涵。日本著名禅宗思想家和研究者铃木大拙(Suzuki TeitaroDaisetz)提出:“不完整的形式和有缺陷的事物都更能表达精神。因为太完美的形式容易使人将注意力转向形式本身而忽视内部的真实。”
事物皆具有不完美的特点而这种残缺与不完美并非意味着形神泯灭,而是在光阴流转的过程中留下的时间的印记。社会动荡战乱连连,人为损害自然侵蚀,种种经历烙印于古瓷脆弱的身躯上刻下了残损的伤痕。这是一种对世事无常的感伤,是一种对逝去岁月的悲叹,是一种绚烂之极,复归平淡的东方审美哲学。所以在面对残损的过程中无需回避不需隐藏。因为这就是岁月与器物之间的一种坦白对话和真实记录。这就是器物面对人世无常原有的样子,也是由“惋惜”到“赞叹”,由“悲伤”到“美好”的一个感受过程。
整体的形式美并不被外部形态的残缺与否所左右,恰恰相反由于残缺的存在会在物品上发生预料之外的形式美感。以作者的修复作品《荷塘》为例(图1),此件文物为宋代青瓷印花盘,有一定的残缺但釉色润泽,具有当时器物的典型特征和代表性。作为标本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完成一系列的信息采集和记录之后,根据受损情况制定修复计划。采用物理和化学性质都非常稳定的大漆作为主要的修复材料,大漆瓦灰混合作为填补残缺材料。残缺部位的形状和青翠欲滴的青釉使人联想到夏日的荷塘。利用大漆髹饰堆塑出荷叶清晰的脉络,再以纯金装饰表面。这种漆髹金饰的方法在日本被称为金缮。金缮工艺早在日本江户时代就已经出现,近几年来逐渐被人们重新认识和采用。它是日本侘寂美学的综合体现,和残缺美的表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青瓷的润泽与清澈就像一汪清泉,残缺部位的图形恰似一朵翻转的荷叶。荷花是宋代装饰常用的图案之一,身姿秀丽挺拔生气盎然。盘中有一处落渣,被巧妙的处理成一只蝌蚪的造型欢快地摆动着小小的尾巴,静中有动整体形成一幅美好的荷塘小景。一只残缺的瓷盘原本的命运可能只是作为标本被置于无人问津的角落,而今经过艺术家们的修复重新赋予了它新的生命。使它的美丽得以延续为更多的人认识和欣赏。在整个作品的设计过程中艺术家并没有把残缺的部位与现有的部分在色彩和形式上统一化,而是保留甚至凸显了残缺的部位。从表面上看“金”是一种介入,但这种介入却使人毫无违和感,却和原物达到一种视觉和心理上的双重和谐感。黄金是一种贵金属,代表一种姿态一种身份一种态度,物品的残缺本是一种伤感和悲哀却用这世上最珍贵的材料来弥补这遗憾。在这种美学现象背后隐藏的是一种如何面对残缺和不完美的文化心态和人生哲学。

图1 宋代青瓷印花盘修复作品《荷塘》
再如作者修复作品《秋山圣水》(图2),这件作品由元代印花青瓷盏残片修复而成。原件缺损较多,根据历史资料的考证和现有部分残存信息恢复其形态。由于残损面积较大采用牙科模具石膏打样塑形,并在石膏外部做大漆髹饰。大漆的质感温润柔和与古瓷残片质感相得益彰。由于残损部分面积较大,在视觉上几乎等面积的黑与青瓷势均力敌有冲突之感。于是在修复部分的黑色漆面上进行装饰来削弱这种视觉上的冲突感。中国文人对山水的热爱由来已久,尤其是到了元代“潇洒简远,妙在笔墨之外”。在重视对宋代山水画传承的基础上创新立意,更有元四家他们的创作集中体现了元代山水画的成就。选定题材后在器物的内部设计成波涛汹涌的水浪纹,器物的外部则是险峻的山峰。在图案的布置上沿着残碎的断面展开图形,很好地削弱了视觉上的冲突。利用图案和图形使两部分巧妙的连接,达到视觉上的均衡。修复过程中残缺部分与修复部分的衔接线是修复的一个难点,处理不好就会过渡不自然不平顺。此件作品中图案的设计沿连接线展开很好的避免了连接线的不平顺。

图2 元代青瓷印花盏修复作品《秋山圣水》
在修复的过程中,残缺的部位才是设计师可以创作的空间。而残缺部分的形状是无法预计和不可控制的,也是一种“无常”。由这种无常所带来的设计空间是具有极大的限制性的,而残缺美正是在这种“无常”与“限制”中展现美感,在“圆满”与“残缺”这对看似矛盾的双方中通过艺术家的设计达到视觉美感与心灵和谐的。一件件残损的古陶瓷就是这样在残缺中被巧妙地捕捉到美感并把它们表达出来,这是一种修复更是一种艺术的再创作。
3 残缺美思想对现代设计的启示
3.1 现代设计的形式美——涅槃重生是天成
我们常见的陶瓷器物多为对称形式的几何形态。这种对形体的审美早在几万年前就已经被人类发现并运用,是发现时间早、流传时间久的一种形式美。[5]陶瓷残片不同于完整器,由于破碎大多出于意外和偶然,破碎的边缘参差不齐变化多样。在这种人为或非人为的作用下形成了大小不一长短各异的棱角和边缘线,不可预期不可控制,预料之外情理之中。这是一种自然天成不加修饰的形式美,这种形式美是不能够用标准器的完整和对称去衡量的。
残损陶瓷虽然都具有意料之外的形式变化但却并非都具备美感。具备美感的残片必须符合形式美的法则或者轮廓线具有一定的图形化特征。残留部分的图案或文字要具有一定的装饰性或可识别性。而对于那些不符合形式美法则的残片,则需要经过进一步的再加工使其符合形式美的法则。
克来夫贝尔提出“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残缺”本身就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恰恰给了设计师一个很好的创作空间。将设计的理念巧妙的导入这些变幻莫测的形体中,达到形式与内容的结合。利用视觉上的独特性将其与理性认识相结合产生新的意义和视觉感受,从而完成创意设计的过程。
3.2 历史价值与现代设计的结合——前世今生两相望
古瓷残片自身具有年代信息和历史价值。现代陶瓷艺术品为了追求历史的年代感可以通过做旧的手法做出古旧的效果,但究其价值来说都是赝品是只停留在外在的形式,自身价值不大。如果说陶瓷的残片是器物的前世,那么经过修复的部分则是经过设计师演绎的器物的今生。[6]缺失意味着器物原本历史信息内容的中断,在修复和补足的过程中加入了设计师的理念和想法。这种形式是多样化的,可以是具有时代感的图形具有风格化的表现手法,或者是在现代眼光下对传统图案的诠释等等。设计师通过自己的经验和审美重构一种新的语义最终完成设计,而欣赏者在新与旧,前与后的信息重叠和相互对照中将自己的知识重组,使欣赏者重新理解作品。器物的残余与补缺,创作过程中的前世与今生,二者相互作用不可分割。
3.3 现代设计审美情趣的转化——虽残不废是为美
在窑址出土的残瓷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古代窑口烧制出的残次瓷器被集中销毁或掩埋,这些瓷器或破损或变形或与匣钵粘连,在以前这都属于不合标准而被废弃的瓷器。[7]传统陶艺的审美标准和审美情趣与现代设计是截然不同的。在传统陶艺中陶瓷讲究技术上的娴熟与材料的细腻完美,而在现代设计中尤其是现代陶艺设计更主张凸显的是材料自身的特性表达作者个人的设计理念。材料的粗粝与质朴,制作中的变形与开裂不但不会被刻意隐藏反而会有意识地彰显。设计师更多追求的不是作品的华丽与完美而是陶艺本体语言中的泥性与泥味从而达到一种返璞归真的审美感受。
在很多现代设计中,设计师有意识地打破均衡与对称等一系列的秩序化视觉感受,寻求更多空间形态的可能性,制造出某些残缺与破损,形成新的视觉特征与感受。
3.4 现代设计中的视觉美和心理美——残而不缺至圆满
古瓷的“残缺”也并非就意味着形神泯灭。在这里残缺可以分两个层面的意思来理解即“残”与“缺”。“残”是指物体的不完整,部件或者型体的局部缺失,而“缺”指的则是物体带给观看者的感受以及联想和想象的空间,更多的是情绪和心理上的感受。生活当中人人追求完美但世间万物本无十全十美,这种不完美造成了心理上的秩序颠倒与人们的心理诉求相违背,形成冲突进而产生向外扩散的张力,而这种张力同时也增强了观赏者的记忆。
很多时候当我们放弃对完美的苛求,反而可以用一种轻松的心态面对事物,从残缺中得到愉悦和满足。[8]残缺美思想在现代设计中把更多的想象空间留给了观赏者,使他们体会到了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意境,增加了艺术作品的感染力和表现力。观赏者用自己的方式将作品在内心中实现补足与填充最终实现圆满,这是在现代设计中常常被使用到的设计手法。
4 结语
每当艺术家拿到一件古老的物品时都会默默在想几百年上千年之前是谁也曾经一样注视着它使用着它。这些高古的残器也曾光鲜亮丽,但在历史的长河里它们经历了磨难与动荡使它们残损不再有昔日的辉煌,而艺术家要做的就是令它们残而不废,还它们一个完整的今生。这是一种古老与现代的对话,也是一次前世与今生的遇见。这是一种艺术再创作,更是利用残缺美表达对完满和美好的追求。器物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后,在修复者的完美设计下,以新的姿态再次面对世人,这何尝不是一种涅槃重生。很多时候修复的过程更像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像是一种修行。修复的意义已经远远高于了物品外形上的重建,而是一种对“无常之美”的重新诠释,是一种面对残缺的心理调适。修复残缺的过程是一种抚平伤痛的欣喜。生活终究不会诸事美好,但皆可以温柔以对,在悄无声息中重拾破碎抚平伤痕重塑尊严。这样的态度岂不又是另一种别开生面的天地。
在古陶瓷修复的过程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不是为了修复而修复。而是在修复的过程中更好地展示艺术作品的美感,并不是一味地单纯的追求其完整性。残损是历史的磨砺和时光的变迁在器物上记录的印迹也是对逝去岁月的见证。我们要用艺术的眼光,在残缺美思想的指导下去完善修复。把修复变成一种艺术上的再创造。另一方面在此思想的指导下在现代设计中不断的追求和创新,呈现出更多的优秀的艺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