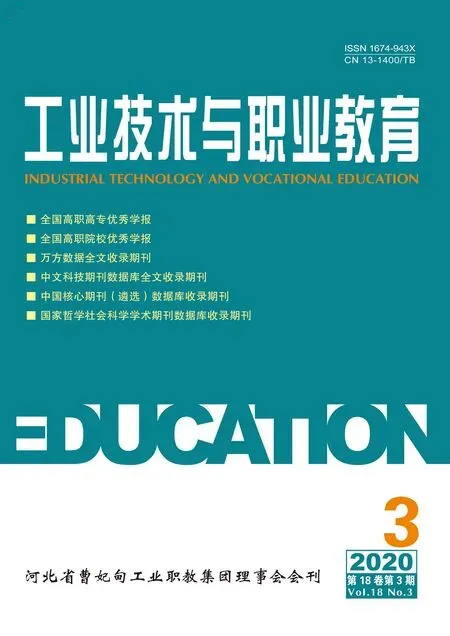成熟青花瓷诞生于元代景德镇的原因
薛 冰
(景德镇陶瓷大学,江西 景德镇 333000)
1 元代之前青花工艺的发展
蓝色在中国一直都属于边缘色彩。钴蓝料的使用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埃及和西亚地区。在我国,钴料直到战国才开始作为装饰色彩被使用,在这一时期的琉璃器上有用钴装饰的痕迹,图1是现藏于甘肃博物馆的战国蓝彩“蜻蜓眼”琉璃珠,于1999年出土于甘肃平凉战国墓中,上面的蓝色即为钴的发色;图2的蓝彩镶嵌琉璃珠,1983年出土于长沙麻园岭战国晚期贵族墓葬,现藏于长沙市博物馆,二者说明战国时期,钴料装饰琉璃的工艺在南方已经出现。唐朝开始生产使用钴料做装饰的铅釉陶器,唐三彩上面的蓝色即是钴的呈色(图3);如果说这只能称之为钴蓝釉,而非钴蓝彩,那么1970年江苏扬州唐城遗址发掘出土的白底蓝花瓷片(图4)则可以算得上是青花瓷的鼻祖;随后1998年在黑石号上也发现了用钴料绘制的瓷盘(图5),2006年在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发掘的唐墓中又出土了2件青花彩绘瓷塔式罐(图6)。

图1 战国蓝彩“蜻蜓眼”琉璃珠

图2 战国四眼蓝彩镶嵌琉璃珠

图3 洛阳关林唐墓出土唐三彩马

图4 唐代白底蓝花瓷枕残片

图5 “黑石号”沉船出水唐青花瓷盘

图6 郑州唐墓出土青花塔式罐
以上文物说明,唐代确实是中国青花瓷的滥觞期。通过科技测试,这些文物中的彩绘料和巩县黄冶窑出土的青花标本有着相似的Fe/Co和Mn/Co比,同属高铁低锰型的钴料,这种原料尚未在国内发现,它们都属于进口料。这表明,巩县窑在停止烧造唐三彩后,利用剩余的进口钴料在自己生产的白瓷之上进行装饰,发明了最早的青花瓷。
从黑石号出水的那件瓷盘(图5)来看,上面的图案应该是模仿自西亚的青花陶盘,图7中的青花绿彩陶碗产自8—9世纪的伊拉克,碗壁上的四瓣棕榈叶和图5巩县窑青花盘上的图案一致,类似的纹饰还出现在了同一时期伊朗南部地区生产的白釉蓝彩阿拉伯文陶钵之上(图8)。唐代后期,由于阿拉伯势力对中亚的控制以及吐蕃人对丝绸之路的阻隔,进口钴料用尽之后,巩县窑便不再生产青花瓷。至于唐青花和元青花之间有没有工艺的连续性和传承性,则有赖于考古界进一步研究。

图7 青花绿彩陶碗

图8 白釉蓝彩阿拉伯文陶钵
宋人喜爱青瓷,甚至认为“白不如青”,白地彩绘瓷在宋代仅流行于民间。根据目前的考古发掘来看,宋代没有发现钴蓝釉瓷,而钴蓝彩绘瓷仅在2座塔基下面出土有一些瓷片,一处是1957年发掘的浙江省龙泉县金沙塔的塔基遗址,共出土13片青花碗残片;另一处是1970年在浙江省绍兴市环翠塔的塔基下,出土了一片青花碗腹部的残片。这2座建筑的年代分别是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和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1]。经过取样测试,着色元素中的铁钴比为0.61,锰钴比为10.25,青花发色晦暗无光,使用的是含有大量锰元素的国产钴料,它们和唐代的青花瓷应当没有关联。浙江拥有本地的钴土矿,所以,这几件青花瓷片很可能是国产钴料用作瓷器彩绘的先例。
青花瓷在元朝迎来了大发展时期,蒙古人的神话体系中有“苍狼白鹿”的图腾信仰[2],所以他们对蓝白二色颇为喜爱;同时,元帝国境内数量众多的穆斯林也是蓝色文化的崇拜者;西亚多沙漠地带,在穆斯林看来,蓝色是水大量富集后形成的颜色,而天堂是又是充满水的世界,所以青花瓷以及霁蓝釉瓷都开始在元代流行开来。
2 成熟青花瓷出现于元代的必然性
结合部分瓷类在唐朝至元朝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一种瓷器成为社会流行商品或大宗产品要具备多个条件。
2.1 要受到统治者的认可和追捧
瓷器的生产过程非常复杂,和采茶缫丝或耕田渔猎这些传统生产活动相比,它需要足够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同时,从大的方面来看,历代精品瓷几乎皆出自官窑或贡窑。最高统治者的认可和赞许,往往可以改变一种瓷器的命运。例如,宋徽宗偏爱天青色的汝瓷,遂使这一瓷种名扬天下,各大窑口争相模仿,包括同属豫西地区的钧窑,最初也将模仿汝瓷作为自己的一大特色。考古学家在禹州刘家门、下白峪、八卦洞等窑址发掘出土的“类汝似钧”风格的标本就是二者关系的最好证明。陶瓷学界也认为“汝衰而钧代”这一理论是完全成立的,而在宝丰县文管所收藏的被定为北宋中晚期的汝窑椭圆八角把杯、天蓝釉带托钵、天蓝釉敛口盂、天青釉带盖钵等,都被归为“汝钧不分”之作。在汝窑工艺融入到了钧窑以后,其他窑口又争相模仿钧瓷,最终形成了庞大的钧窑系。此外,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喜爱釉里红,在故宫馆藏的100多件洪武官窑产品中,釉里红数量竟占到了80%。成化皇帝爱小酒杯,因此,这一产品成为“成窑”的主流。反观青花瓷,在元代以前,并未得到任何一个皇帝的喜爱,因此,也没有工匠愿意去花心思去研究和制作青花瓷。
2.2 要符合社会主流的审美倾向
这里的社会主流并不是按人口数量来划分的,而是按照影响力的大小来定义的。社会主流包括文人士子、官僚贵族、地主乡绅这些群体,他们往往左右着整个社会的文化与审美潮流,而这其中,文人的观点尤为重要。青花瓷作为一种彩瓷,和文人对“如冰似玉”这种审美风格的追求背道而驰,即便是到了洪武年间,他们还没有完全接受青花瓷。当时的文学家和收藏家曹昭认为“有青色及五色花者且俗甚”[3]。在文人的这一观点下,其他有钱、有权、有势的阶层为了附庸风雅,当然也不会喜欢和欣赏这种“俗甚”的器物了。
2.3 要契合民间文化
如果一种瓷器与文化风俗相抵触,那么即使是普通百姓也不会去使用它。在元代以前,蓝色并不是中国人喜爱的色彩,但凡沾上蓝色,多少都带些恐怖的意味,尤其是深蓝色,属于蓝色系中的最冷色调。唐代文学家段成式《酉阳杂俎·虫篇》写道:“蓝蛇,首有大毒……南人以首合毒药,谓之蓝药,药人立死。”[4]闻之让人不寒而栗。佛经中有恶鬼,名字有叫蓝婆,塑像常常是将蓝色涂抹在脸上,用其色唬人[5]。《敦煌变文集·维摩诘经讲经文》中记载有:“身色皆蓝淀(靛),情田尽虎狼”,即妖魔鬼怪的身体颜色尽为深蓝色[6]。早期科举制度中有“蓝榜”,考生文卷如不合程式,或有损污,即被取消下一场考试资格;宣布此种处分的名单,用蓝笔书写,称“蓝榜”,又叫做“蓝单”。可见,蓝色也是古代读书人惧怕的颜色[7]。无论是民间百姓,还是寒窗苦读的学子,都对蓝色充满一种畏惧心理,因此,蓝彩瓷或蓝釉瓷在民间也绝无流行的可能。
2.4 有大量的市场需求
位于河北磁县的磁州窑兴起于宋元之际,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民窑,它首创的许多工艺直接或间接启发了后来南方地区的制瓷业,包括红绿彩、白地黑彩、孔雀绿釉、剔刻花装饰等。在一些元青花上,我们可以发现和磁州窑白地黑彩瓷有着相同的纹饰图案和构图方法。磁州窑作为民窑,没有得到帝王关注;在奉行极简主义的宋代,花哨的装饰技法显然也不被主流审美所接受;但是,依靠民间市场的支撑,磁州窑得以不断发展壮大,甚至在北方窑口集体衰落的情况下,磁州窑依然窑火鼎盛,并且形成了以彭城为核心的磁州窑系,陶瓷界素有“南景德,北彭城”的说法[8]。丰富的装饰技法,喜闻乐见的表现题材以及黑白分明的色彩对比,使得磁州窑产品不仅广泛流行于国内,还深刻影响了日本等海外地区对中国瓷器的认识。明代谢肇的《五杂俎》记载到:“今俗语窑器谓之‘磁器’者,盖河南磁州窑最多,故相沿名之。”[9]至今日本还在使用“磁器”这一名称来代替“瓷器”。
除了磁州窑,长沙窑也是“市场导向型”的窑口,唐代诗人李群玉在《石渚》一诗中记载了长沙窑的盛况:“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迥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10]在1998年打捞出水的黑石号上,搭载了50 000多件长沙窑产品,这也证实了在湘浦口确实存在一处规模庞大的窑址群,弥补了关于长沙窑研究的空白。和磁州窑不同的是,长沙窑主要是供应西亚、北非的外销瓷。为了打开市场,长沙窑瓷器大量使用销往国的装饰题材和构图方法,例如飞鸟纹、阿拉伯文、椰枣纹、棕榈纹、轮状团花纹等,还模仿金银器的錾刻、捶等装饰技法;在执壶上,则流行贴塑的枣椰树、狮子和胡人等形象。所以有学者指出,长沙窑的外销瓷是海外来样定制的产品,甚至有大量胡人直接参与了瓷器制作。在明初景德镇的青花瓷上,也存在大量外来元素,两者的相似性值得关注。
磁州窑和长沙窑作为民窑,不被统治者认可,不符合主流审美,甚至不见于当时的文献记载之中,但依靠广阔的市场,他们得以延续壮大。元代以前,青花瓷由于色彩的原因不被民间接受,国内销售举步维艰,而国外市场也未打开,这其中自然有工艺水平限制的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产品风格没有向销往国靠拢,导致产品没有吸引力,相应的研发和生产也缺少了积极性。
2.5 有发展成熟的工艺和稳定的原材料供应
釉下彩工艺在长沙窑中已经出现,并经过磁州窑工匠的继承发展,逐渐成熟,所以到了元代,用钴料代替铁料在坯胎上绘画就变得水到渠成了。再加上元代后期,国产钴土矿不断被发现,绘瓷用的原料可以连续不断的供应给工匠,而且国产料比进口钴料价格低很多,这也是青花工艺在元代开始普及的原因之一。此外,成熟的“二元配方”在瓷胎中引入了充足的氧化铝[11],也使得烧造大型器件成为可能。大件器是蒙古人和西亚人民喜爱使用的造型,例如最常见的青花大盘,直径通常在35~55cm之间,主要是为了满足穆斯林围坐就餐的饮食习俗[12]。
综上所述,元代之前,钴料依赖进口,生产青花瓷的成本很高。虽然在唐代就出现了高质量的白瓷,而且在巩县窑已经生产出了用钴料装饰的白底蓝花瓷,但由于原料限制,只能被放弃。宋代开始,彩瓷逐渐成为民间喜爱的产品,但不被主流认可,况且蓝色属于忌讳色彩,导致这一时期陶瓷上的蓝色几乎不见,白底蓝彩瓷和唐朝相比更是少之又少;而这一时期的外销瓷,主要是精美的龙泉青瓷,绿色的釉衣也和穆斯林的审美倾较为契合。元代的建立,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陶瓷史上的过渡期。由于蒙古人采取独特的社会治理架构,汉族文化逐渐边缘化,从南北朝开始形成的门阀贵族到了这一时期也消失殆尽,中国社会迎来了一次大洗牌,从前主导社会主流风尚的儒士阶层被蒙古人和色目人代替。从这一时期开始,民间文化地位上升,平民审美成为影响工艺美术风格的重要力量,瓷器也由最初如冰似玉的风格变为“大众化”和“世俗化”,而彩瓷也开始代替单色釉瓷成为日后的主流产品。虽然明朝初期的一些执笔者仍然对青花瓷持不屑的态度,但“青花瓷时代”的到来已经不可阻挡。
3 成熟青花瓷出现于景德镇的必然性
景德镇“水土宜陶”,不仅有丰富的成瓷原料,而且有广袤的富含油脂的松木可以作为燃料,所以这里陶瓷业长盛不衰。此外,景德镇地理位置优越,三面环山,一面拥湖,更有长江天险做保护,自古以来,这里少有战乱,成为工匠躲避乱世的地方。
3.1 各地工匠带来的技术融合
具体来讲,宋代景德镇青白瓷工艺在“南定”[13]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瓷器胎质细白,釉色肥润光洁,透明度高,窑炉结构也十分先进,因此在烧成制度的选择和创新上有着坚实的基础。元代开始,这里也是掌管皇家御用瓷的“浮梁磁局”所在地,在瓷器烧造上开始不计成本。再加上不少磁州窑的工匠追随宋室南迁,来到景德镇继续从事陶瓷生产,他们带来的瓷器彩绘技术被直接移植到了元青花之上。吉州窑也有许多工匠迁居到了景德镇,《陶录》记载:“相传陶工作器入窑,宋文丞相过时尽变成玉,工惧事闻于上,遂封穴不烧逃之饶,故景德镇初多永和陶工。”[14]这一记载讲的是,在宋代的时候,吉州永和窑的工匠有一次烧出了“瓷妖”[15],这种特殊的瓷器其实就是窑变瓷的一种,但是明代之前,窑变瓷均是偶然制得,窑工们不知道其中原理,认为这是天然幻化的奇异现象,所以常将其当做“怪胎”或“瓷妖”,官匠见后会立即打碎,害怕皇上知道后要求他们“每岁皆贡”。吉州窑工匠弃窑北逃之后,来到了景德镇。这虽然只是个例,但它说明景德镇是吉州窑工匠逃亡的首选地。
另有文献记载,南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年),文天祥调任知赣州,积极准备北上抗元;宋恭帝德元年(1275年)正月,文天祥在家乡吉安招募大量士兵在长江口岸截击元军。据统计,仅吉州窑工匠就有3 000多人参加文天祥的军队。战败后,元军占领吉安,对当地百姓进行了清算和镇压,许多工匠携家带口逃到了景德镇。元青花和吉州窑釉下褐彩瓷器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包括吉州窑常用的“开光”、多层装饰、画风细密等技法和风格都成为了元青花上面的重要装饰特征之一。图9是南宋吉州窑白地褐彩缠枝卷草开光海浪纹梅瓶,口径5cm,底径9cm,腹径16cm,高30cm,现收藏于观复博物馆。图10为1992年出土于安徽省濉溪县临涣镇至正十三年(1353年)孙氏家族墓中的青花海水纹瓷盘,口径16.2cm,底径13.6cm,高0.9cm。两者的海水纹画法相近,都是以空心的突角形作为浪头,然后用平行的曲笔描绘细浪。除了磁州窑、吉州窑的工匠,景德镇几乎成为所有古代陶瓷工匠心中的圣地,形成了“工匠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局面。蒋祁在《陶记略》中记载:“窑火既歇,商争取售,而上者择焉,谓之拣窑。交易之际,牙侩主之……运器入河,肩夫执券,次第件具,川凭商筹,谓之非子”[16],可见当时运销状况之兴旺。

图9 白地褐彩缠枝卷草开光海浪纹梅瓶

图10 元青花海水纹瓷盘
3.2 制瓷原料丰富且质量好
景德镇制瓷原料种类全,数量多,质量优。高岭村出产的高岭土,是优质的制瓷原料之一。宋代在湖田窑和繁昌窑的一些窑业遗址中,都在残留的陈腐原料中发现了高岭土,说明在元代以前,已经有工匠尝试着在原有的瓷土中加入高岭土,形成最早的“二元配方”。高岭土之所以这么重要,是因为它不仅组成成分稳定(理论化学组成为46.54%的SiO2,39.5%的AL2O3和13.96%的结构水),而且较高比例的AL2O3的引入,可以提高瓷胎的耐高温性,突破了对大型瓷器烧造的限制,满足了统治者的需要,这也是元代将磁局设立在浮梁县的原因之一。
此外,景德镇附近的乐平、高安还有浙江部分地区都盛产钴土矿,国产钴料的使用,降低了生产青花瓷的成本,为它在民间的普及创造了条件。虽然尚不清楚从元代开始使用的国产钴料具体是乐平的陂塘青、高安的石子青还是浙料,但这种高猛低铁、发色暗沉的钴料从此被永远封存在了透明釉之下,见证了元代民窑的崛起。
3.3 西亚工匠的直接参与
蒙元帝国版图辽阔,四大汗国占据了中亚和西亚地区,和中原地区交流十分密切,蒙元帝国境内的穆斯林,对青花瓷尤为痴迷。在土耳其托普卡帕宫和伊朗的阿德比尔清真寺都收藏了大量质量上乘的青花瓷。再加上进口钴料产于西亚,在元朝可以畅通无阻的运到中国。更为重要的是,经过长期的西征,蒙古人俘获了大量西亚和中亚的制陶工人,由于蒙古人重视工匠,这些俘虏被收编到了元朝的工匠体系之中。在将作院和浮梁磁局中,都有数量众多的西亚工匠,他们被称作“浮匠”[17]。这些匠人直接参与了景德镇青花瓷的制作,使得元青花一出现就臻于完美而冠绝天下。除了战争俘获的工匠,还有一些穆斯林陶工自愿投靠元朝,因为色目人在元帝国享有很高的地位,他们可以凭借朝廷赐予的敕令随意出入皇宫。这些归化的陶工也被分配到了浮梁磁局生产青花瓷,为景德镇制瓷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4 总结
唐青花经过初创期以后,并没有迅速发展起来,而是走向了衰败。直到元朝,景德镇汇集天时、地利、人和三大优势,终于生产出了成熟的青花瓷,它是中国和西亚文化交流的结晶,汇集了百家技艺之长,所以从一诞生就开始风靡世界,成为中国陶瓷史上一颗最耀眼的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