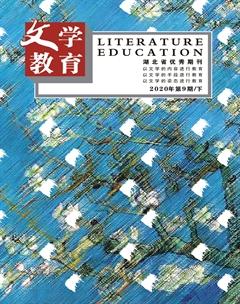张尕怂,或民歌之名
今年疫情期间,因为《早知道在家待这么久》、《甘肃有个大夫叫霞霞》等几首“抗疫”歌曲,名字怪怪的“民(谣)歌手”张尕怂火了。近些日子,因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与沪上弹词演员的合作演出,他的影响明显在持续扩大。张尕怂出名了。但什么是出名,出名意味着什么,对他本人而言,肯定不只是“火了”这一年少时的懵懂渴望所能概括的。人们给了他和他的歌无数的“名”——西北民歌,民谣,农业摇滚,西北布鲁斯,非物质文化遗产,但似乎都不是他想要的名。在采访的镜头中,他以沉默婉拒着这些“辞严义正”的赐名,并尝试着亲自给自己命名——音乐人,根源歌手,尕谣,骚情,等等。
作为一个甘肃人,我听说张尕怂要早一些。几年前在网上搜资料时,我偶然在某音乐网站听到了一首三弦弹奏的《八谱儿》(收入《山头村,人家》),细听之下惊喜地发现,这竟然是我家乡耍社火唱小曲时常用的一个过门,只不过我们的叫法似乎是“八步儿”。这个发现让人激动——没想到我们山里乡民稚拙的弹拨,也能被正儿八经地叫作“音乐”,而且未经“艺术工作者”的改编就放在了还很“小众”的网站!
这是一种平淡无奇的生活被指认、被命名的惊喜。实际上,出名的渴望与被命名的惊喜以及尴尬,无论对于“民间艺术”和“民间艺人”,都是一种绕不开的宿命。出名的张尕怂,在走向更大的舞台,但那里不仅有耀眼的聚光灯,还有暗处虎视眈眈的语言,随时准备命名/捕获、照亮或掩没台上人。作为一个没有学会“八谱儿”弹奏的人,我不懂音乐,但我了解命名的狡狤和危险。
一
给学生上课讲“民间歌谣”时,总要费一番力气区分一些很纠缠的名称,比如民间歌曲、民歌、歌谣、民谣,但实际上许多时候又很难讲清。不过讲不清对于老师学生可能只是个考试失分的小问题,对张尕怂却是个失节事大的大问题。他严肃地将自己与“晚会歌曲”划清界线,有些讨好地将自己与民谣前辈站队,真心实意地拜了许多民间艺人为师,又认为自己和他们不一样,一边和俄罗斯歌手到处巡演,一边宣誓要捍卫家乡靖远的方言。张尕怂是谁,与他紧紧相随的那个“民间”是什么意思,还真不是一个容易说清楚的事情。
但大多数时候,张尕怂是被当作“民谣”歌手而接受的,实际上,如果不是“民谣”热爱者的支持,他这些年漫长的流浪演出基本是不可能的。但什么是民谣,又不是一个可以顾名思义的问题。对听者而言,民谣更多地是一种精神气质,其首要特征恐怕是独立。但是指与什么独立呢?在某部关于张尕怂的纪录片中,导演刻意以《我爱你中国》的旋律做背景音乐,应是一个能让拥趸立刻听懂弦外之音的答案。民谣要远离,要不一样,张尕怂首先是在这样一种接受场域中生存下来的。这是他与那些听众之间的美学约定,他将之命名为“骚情”,这是一种千里之外的听众们也能听懂的身份方言。
独立就是不一样,就是不听话,就是做一个“尕怂”。于是张尕怂唱着被禁忌的酸曲走进了大都市中高调隐匿着的livehouse。他的最早被接受的几首歌像《张老汉》和《张尕怂谈恋爱》就是这类禁忌的声音:“张老汉的手也是一件宝,想当年大姑娘的咪咪摸了不少,如今他老了,实老了,就连那个软柿子他也捏不了!”(《张老汉》)
独立的另一面,也就是反叛——反叛但不是反抗。反叛,是越轨,而不重新铺轨。因为只有越轨之心而无铺轨之意,反叛大多停留在美学领域,剃个光头或挽个道士头,搞些纹身异服,其实和另一些搞笑歌谣有共同点——拒绝某种意义惯制,但也不打算再生产意义,像这首《十嫂子》:“大嫂子病了二嫂子看,三嫂子买药四嫂子熬,五嫂子死了六嫂子抬,七嫂子挖坑八嫂子埋,十嫂子问为什么哭,五嫂子一去没回来”。
作为民谣歌手,反叛的诱惑对张尕怂始终存在。在老家院子里,他戴着墨镜穿着老式对襟棉袄唱了一段《假行僧》。这正是反叛者的歌。反叛者要求独立,但并不是那种遗世独立,反叛者离不开他人的映衬,只不过要将自己与他人区别开来,在他人面前标示优越感。这一层意思,更接近甘肃方言中“骚情”的本义。实际上至少在我的家乡,这两个字听起来更像“梢轻”。有一句俗语说“梢轻打不住粮食”,意思就是谷穗轻了,谷粒肯定不繁不饱。俗语还说,“人梢没好兆,狗梢挨砖头”。“梢轻”的意思近于“轻浮”,是不踏实,不老实,不现实;梢轻的意思,也接近我们方言里的“赞”和“炫”,赞是自赞,是自视甚高,自我迷恋,是炫优越感。梢轻,就是瞧不起老实巴交和认命了的那些“孽障”人。
对民谣来说,“骚情”是表象,“梢轻”才是实质。骚情和反叛掩饰不住民谣里不可救药的自恋,禁不住对自身的迷恋和抚慰。“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恰如少婦顾影自怜苗条的腰身,“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怎么还在人海里浮沉”,则如老妇回视自己日渐衰老的腰身。但二者都反映了民谣的核心教义。民歌不是这样。花儿里唱,“阿哥们是孽障的人,阿哥们世下的太寒酸”,孽障人没什么可赞可炫的。梢轻的审美风格适合民谣,不适合民歌。骚情的歌能迎合那些回视腰身的小资,却也抵不住他们居高临下的审视。无论如何合作,花儿还是花儿,弹词还是弹词。张尕怂想在兰州办一场“谭维维那样”土洋结合的音乐会,把他的民间师父们请到台上,他没找到赞助商。
二
土气难以消除,他也不想消除。民间确实不一样,但不是他们理解的不一样。这是张尕怂的特殊之处,也是令人敬佩之处。
张尕怂让奶奶唱歌,奶奶自然而然哼出来的,是一首在西北广为流传的《穷人歌》:“养着个一头牛,长着个弯弯角,驾上拿它耕地去,把我的铧崩破,世上的穷人多,你们哪一个就像我;娶了个二老婆,瞎着就摸不着,叫她去添炕,她把我的炕捣破!阳世三间的穷人多,你们哪一个就像我”。这是一个比穷人还穷的人的自嘲。民间的意思,其实就是穷,穷是这群人的常态,是大多数时候的现实,也是大多数回忆的主题。在《山头村,人家》里,张尕怂收入了一首《山头村1960'》,伴随着凄凉的二胡,老人念叨着五六十年代挨饿时的“古经”。这是民间挥之不去的记忆,却不是民谣们的记忆。
张尕怂指着自己的家说,这是中国最穷的地方。也许,首先不是出于艺术的使命,而是出身带来的悲悯,使得张尕怂自然而然地唱起“劳着歌其事,饥着歌其食”的那些古老歌谣,如《拉骆驼》、《光棍汉》等;也同样地,使他仿佛带着不孝子的愧疚之情,用歌去触摸乡亲父老们的心灵,他们的苦涩,他们的快乐:“油泼辣子油泼了蒜,割麦子天,辣辣的我们吃上一顿搅团。对坡地割麦子一整天,麦垛子堆成山,高兴着我就唱上个少年。”(《老农》)“碰见了我的小学同学,他骑着三轮车在卖馍馍,生活让他受尽了折磨,至今和妻儿没有定所,身上穿的是儿子的校服衫,拉链都换成了纽扣子。”(《梁梁上浪来》)其中最打动人的一首,是他根据邻居家的真事改编的《姐姐》,唱一位拉扯弟弟妹妹而献出了自己的幸福与生命的女性:“姐姐的命真苦啊,拉扯姊妹真辛苦,又做爸又做妈,一辈子就没出嫁,姐姐的命真苦啊,嘗尽了人世间苦啊,为了姊妹做牛做马,累死在了田埂上。”同样自然地,他唱着都市里的“狗尾巴草”们的卑微梦想:“房子又降价了,啊?我就盼哪我就盼哪;买汽油送汽车了,啊?我就等啊我就等啊;兜里的人民币哟,都变成欧元吧。”(《狗尾巴草》)
但《张老汉》这首更值得重视:“张老汉的头是一件宝,想当年把那个大礼帽戴了不少,如今她老了,是老了,就连那个破草帽他也戴不了!”这是对孽障人的注视,但不是对“底层”的俯视;不是以同情的眼光审视张老汉,而是尝试从张老汉的视角去欣赏世界;不把歌者自己放在更优越的位置,也不把张老汉当成“弱者”相对化。这就如相声演员张鹤伦的段子所说:长得丑又怎么样,我自己又看不见。生活需要这样恬不知耻的无视,对人的真正尊重也需要认可他恬不知耻的无视。
民歌的眼神不回视,不俯视,它低头注视世上的孽障人,仰望着天上高不可见的注视者。民歌的眼神不是少妇的自恋,而是奶奶般的柔和与慈祥,她不声不响,用粗糙的手抚摸一切孽障的生灵。《女娃娃》就如同一首奶奶唱出来的古老歌谣:“有一个女娃娃,不像个女娃娃,坐在了那个土墙就把卷烟咂;红脸蛋,短头发,眼睛嘛扑棱扑棱的转呀她在想啥;有一个女娃娃,奶奶最爱她,扒到奶奶的背上学超人耍;爸爸妈妈的工作忙,打小跟着奶奶生活在村里面”。
三
张尕怂的这些歌,实际上远远超出了民谣,超出了摇滚,但至少能被习惯了民谣的听众们接受;但他的另一些歌,足以让他失去一些同行。比如今年的抗疫“三部曲”,尤其是《甘肃有个大夫叫霞霞》:“中国有一群大夫也叫霞霞,不晓得名字也看不清她们脸。今年的歌舞片变成了战争片,她们穿上了盔甲赛花木兰。防护服脱下一身汗,吃两口又去值下一班。不眠不休啊又是一晚。”无论在音乐上还是歌词上,这首歌都是他创作的一次升华。它的主题毫不犹豫地指向了更大的空间,指向了民族,但也没有脱离民间。
因为,民间从来不拒绝政治,不拒绝宏大叙事,不过对此有自己的见解。张尕怂奶奶唱的歌里,第二首就是秦腔里包公的唱段——民间从来与正义紧密相系。张尕怂没有将自己拘束在为反叛而反叛的歧途,他保持着自己的“政治”立场,他更欣赏罗大佑而不是什么朋克。在歌声里,他以反讽的语气对官员的腐败发出不平之鸣:“孩子哟孩子你快长大,长大以后上学堂,上完学堂把官儿当,当完科长当局长;当上了局长哟,千万不要戴手表呀,千万不要买皮带,千万不要戴眼镜。”(《孩子快长大哟》)而且,他也敢于用教训的语气向民众的不良习气开火:“隔壁的张大嫂你听我给你唠,让你们家的男人再不要胡乱闹,戴了个红袖套 冒充虎狼豹,砸掉人家麻将桌,掌掴人家儿。”(《隔壁的王妈妈》)
同样地,他讨厌不平等与歧视的社会,如《梁梁上浪来》里唱的:“遇见了同村的尕马三,他拉着个狗娃子在遛弯,开口张口是几百万,生意都做到了新西兰,进村走路说话也改变,胡子都翘到了嘴上边,谁说了尕马三走路像妖精,鞋子就飞上了乡亲的脸,吓了身冷汗。”他也会用最民间的办法戏弄自视高人一等的人,比如他喜欢的《亲家母》这首民间小调:“城里的亲家母乡里第一次来,见了个羊粪蛋蛋舌头吐出来,我的亲家母,你是个小气鬼呀,这么多的黑枣儿你不给我装上些。”
正是由于这种自信,他并不畏惧借用或化用主旋律,比如为《春节序曲》填上新词,使之充满生活的平实趣味:“一个嘟嘟果一嘟嘟梨,一个嘟嘟红来一个嘟嘟绿,一个嘟嘟腊肉挂满了枝,一个嘟嘟鞭炮就落了地。”(《过年》)但在歌中又让乡亲和娃娃们正儿八经地来阐释过年的意义和“没意思”,微妙地限制了宏大叙事的越界和生硬。
四
张尕怂唱的是民谣还是民歌?张尕怂算不算民间歌手?什么是民间?从任何一个单一的视角,都不可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他像民间艺人,但唱着许多自己创编的新歌;他是民谣歌手,但有着拥趸们无法接受和容忍的气质;他也是被期待的非遗传承人,但他觉得自己的东西不需要国家的支持。张尕怂是复杂的,因为民间本身就是复杂的。
什么是民间,我们提供了三种不同的回答:独立、“底层”与民族。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阶层可能会支持其中一种答案。但民间不是单维的,它的位置恰恰就在这三维构成的坐标中。任何对一维的坚持都可能走向僵化和背叛。比如,把底层误解为乡土、方言;把独立误解为毫无建设性的反叛,把政治误解为意识形态。而只有在三维坐标中,民间才不会迷失。民间,意味着一种不偏不倚的艰难平衡。
既然不能执着于一维,理解民间也就不能执着于某一种名相。张尕怂问道,进了城里就是城里人吗?我们也可以追问:上过大学就和民间艺人不一样了吗?因为故乡回不去我们就再找不到家了吗?个人的创作就不能回到民间吗?令人敬佩地是,三十而立的张尕怂,对识破名相有着相当的自觉和自信。在媒体的各种命名之间,他以口吃和沉默掩饰着他的不妥协,保护着他的复杂和丰富。
也许,正是由于拥有多维的视野和识破名相的视力,张尕怂自信地穿越在多种传统和风格之间,坦然地用着改造过的《八谱儿》作为日常弹奏的过门,并尝试着直接用秦腔的嗓音吼唱,甚至只把自己当成一个传承者。他的目标,是做花儿会那样的“流行”音乐。民间,不是一种对创作者的刻意区分;民歌,更像是一条滚滚不尽的洪流,任何个人都不过是瞬息泛起的浪花,他崇拜的祖宗朱仲禄(花儿“艺术家”)是这样,他的师父刘延彪(贤孝“艺人”)是这样,他自己也会是这样。
怂,是一个借字,是一个俗名,也是一个无法命名的命名。它是生命之源,精力旺盛,又莽撞无序,有着让人畏惧的禁忌之力。命名是一种生产,但也可能是收编。老子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生命就在有名无名之间出生化育。怂,其实就像民间,它无名,它沉默,它需要吼歌,需要命名,也恐惧命名;怂,也像音乐,像旋律,没有歌词时,它能被随意征用;但只有旋律,才能为语言赋予生命的力量。
胥志强,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