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影院搬进天堂的人纪念电影配乐大师埃尼奥·莫里康内
文字_梦乡
九十一岁的埃尼奥·莫里康内(Ennio Morricone)走了,也许按照中国人的风俗,这应当算是标准的“老喜丧”了。这位与伯特·巴哈拉赫同岁、比桑尼·罗林斯年长两岁的音乐大师,一直都是三位寿星里最高产而又最多才的一员。现在他终于走了,带着满满的荣誉走了。为什么命运不让他再多活几年,让乐迷们再多欣赏几部出自他的佳作呢?
莫里康内人生中的第一部配乐创作于1963年,据说叫《阳光下的十八岁》。除了日本人为它出版过黑胶以外,它的内容至今没有被完整地再版过。有人或许会认为莫里康内根本不是个天才,因为他创作第一部配乐时已经三十五岁了。对于童年时便能够无师自通地创作古典音乐的莫扎特而言,三十五岁早已到达了人生的终点。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将莫里康内称为“电影音乐界的莫扎特”,他靠的既是极高的效率,又是极高的品质。
莫里康内一生总共为五百多部电影配过乐,最为密集的时候一年高达十余部,仅在2006年他出版的“终极大合集”里,囊括其中的唱片就有二十四张之多。虽然莫里康内几乎只为意大利导演的作品写作配乐,但总共有上百部电影因为他的配乐而改变了命运。正是他的努力,才让这些形象的“庸俗”最终转化成了抽象的“优雅”。他出版过的合集多得数不胜数,其中有许多高品质的收藏品来自日本。他也曾破例为日本的电影作过曲,甚至日本的前首相都曾为他的精选集专门选曲。
很久以来,我一直耿耿于怀,为什么我们的国度就没有哪部优秀的影片得到过他的提携呢? 直到他晚年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举行了两次盛况空前的音乐会,我的内心才稍稍获得平衡,而它们的实现仅仅是因为他的朋友向他提到过中国的名字。或许他真的是来探险的,就像他从前的同胞马可·波罗一样。而他之所以垂青我们的邻邦,只因为他在那里获得过莫大的尊重。一位大师需要自己的听众,就像一部电影不能没有自己的观众一样。而我们之所以终其一生都等不到他的配乐,或许只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勇气和诚意,在候选人的名单中写下过他的名字。

2016年,莫里康内的《八恶人》获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奖

莫里康内
人们完全可以把莫里康内看作电影音乐的活化石,这不仅缘于他的年龄,更因为他坚守终生的创作方式。他手中只有一根指挥棒,但他面前绝不仅仅有一个过硬的乐团,而是有各式各样的艺术家与别出心裁的乐器组合。于是他看似永远只执着于最传统的交响乐风格,实际上却在用他的想象力最大限度地改造它的面貌。我们完全应当将他称作“电影音乐的魔术师”,他的“赏金三部曲”里形象生动的口哨和马鞭声让人想起理查·施特劳斯的《阿尔卑斯山交响曲》,而他的《陈旧的楼梯》里摇曳飘渺的和声又让人想起了瓦格纳的《罗恩格林》。最妙不可言的或许还是《教会》里开头的那首《在人间犹如在天堂》,那种将属于原住民的手鼓和属于信仰的弦乐结合得完美无瑕的“节奏圣歌”,早已把那群深入丛林的勇敢教士和他们身边亲如一家的土著信徒刻画得惟妙惟肖,难怪它曾经被人们收入新世纪音乐的第一天碟《纯净心情》(Pure Moods)的第一辑中。
可以说,莫里康内的音乐包罗万象,一切能够为电影服务的音乐流派都能在他的努力下,与管弦乐队完美捏合在一起。于是,由于他的才华和声望,许多优秀的艺术家和他合作录制过唱片,其中有葡萄牙的杜尔塞·庞泰斯,有新西兰的海莉·韦斯特那,也有我们熟知的马友友。而他们全都不必付出过多的努力,只要做好他们的本职工作就足够了,其他的一切都交给莫里康内本人来完成。当一个精通编曲的大师不再需要别人协助他什么,就像一个船长和导演完全可以胜任手下的任何角色一样。但他还是那位经典的指挥家,带着指挥棒赶来,夹着乐谱本离开。最经典的往往是最具有生命力的,就像著名的配乐大师汉斯·季莫所说的:“如果没有我们这些艺术家将管弦乐队的创作方式传承下去,人类的文明或许就会出现断层。”当今天的人们迷醉于五彩斑斓的电子音乐世界时,他们或许正需要回归他的世界。只有在这个纯粹靠人力演绎原始声音的世界里,音乐才会像一个没落的贵族一样,继续高昂起它高贵的头颅。

莫里康内
莫里康内是能够创造经典的,但经典并不意味着全都属于莫里康内。他基本上只为文艺片作曲,这让他与许多来自商业片的奖赏和人气失之交臂。他那五百多部的配乐总数几乎无人能出其右,但其中堪称传世精品的作品其实少得可怜,甚至连他自己都是这么认为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与其他领域的大师们合作的内容,总是来自那几部固定的佳作,甚至连曲目都是固定不变的。而他与马友友合作的那张唱片,可以说几乎网罗了他一生的所有精品。于是在莫里康内身上,天生就找不到多少司空见惯的商业气息。在马友友那张唱片的亚洲版里,最后增加的两首曲目还是来自正片里演绎过的《教会》和《美国往事》;而在他与庞泰斯合作的那张《焦点》里,最后增加的一首曲子出自前面选用过的《陈旧的楼梯》,只不过从英文演唱改为了葡萄牙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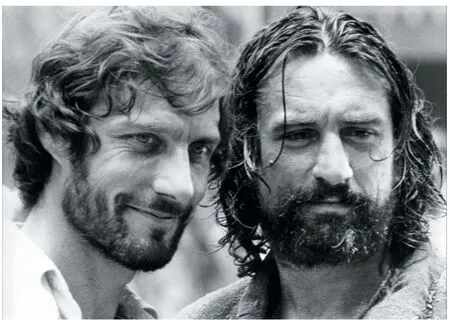
01 电影《教会》剧照

02 电影《美国往事》女主角黛博拉
莫里康内的精品只要听过两三张合辑便能倒背如流,他的灵感似乎早已经在日复一日的创作中走向枯竭了。但那些经典实在是太动听了,以至于你永远都不会产生厌腻感,甚至可以将它们无休无止地循环播放一辈子。即便在他初次登陆中国的那场人民大会堂的音乐会上,他演绎的还是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当重新走上舞台的他终于加演了一两首曲目,合上乐谱夹,精神抖擞却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时,台下的无数听众报以了一声幽默的叹息。他不是乐神,而是一个真实的人。人的才华都是有限的,当他把自己最耀眼的才华一次次倾情奉献在你的面前时,你所要做的不是贪得无厌地想入非非,而是全心全意地加倍珍惜。
对于莫里康内的职业生涯而言,1985年或许是最值得骄傲的一年,但或许也是最令人惋惜的一年。就在这一年,他那部一生只有一次的传奇之作《教会》原声出版发行。也就在这一年的奥斯卡颁奖礼上,这部被AMG数据库称为“任何电影音乐集锦中都不可或缺”的佳作,却最终败给了创作出《末代皇帝》配乐的三个而立之年的年轻人。这似乎是一次讽刺,是对于艺术之美的一种讽刺。因为莫里康内的《教会》实在是太美了,那是一种任何人都可以轻易觉察的美,即便连其中最短的《兄弟之情》也浸润在其中。那种催人泪下的圣洁和温暖似乎写尽了片中那几位虔诚神父的高尚灵魂,让人不能不联想起布鲁克纳的交响曲。但为什么它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呢?因为它美得曲高和寡,而它的对手则美得石破天惊。
这是一场没有输家的博弈,但真正笑到最后的一定是最有个性的音乐。这就是奥斯卡奖甄选作品的标准,有个性的未必是最美的,但喜爱冒险和创新的美国人永远只肯定那种个性本身。这对于一个作曲家的人生而言注定是残酷的,尽管莫里康内还有许多佳作存世,但这无疑是最接近“小金人”的一次。或许是为了补偿他的“精神损失”,评委会最终将一座迟到的“终身成就奖”安慰性地颁给了他。但谁都知道,他的《教会》到底有几分潜在的价值。它有天籁般的旋律,也有无与伦比的音质。百代公司将它制成了极其发烧的SACD,等到后知后觉的我在它绝版多年后终于买下它时,它已经成了我曾经拥有过的最昂贵的流行唱片。一个高雅的奇迹最终在极小众的人群里获得了它的价值,就像极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多产与长寿一样。

莫里康内
一个人不可能在同一个陷阱中跌倒两次,这用在莫里康内身上或许再合适不过了。当年他就是因为个性而与奥斯卡奖失之交臂,而今天却因为个性而获得了奥斯卡奖。2016年,年近九旬的他终于凭借昆汀·塔伦蒂诺执导的《八恶人》(The Hateful Eight)电影原声,第一次获得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小金人”。但这是因为它足够美吗?无疑不是。尽管还是为意大利裔的导演创作配乐,但这次的莫里康内完全不像是他自己。那种神秘主义又危机四伏的旋律,听上去倒很像是他的“老对手”约翰·威廉姆斯。这或许是他一生中写过的最“丑陋”的配乐,就像封面上打上的那个刺眼的“少儿不宜”的标签一样。听着这样陌生的旋律,我不禁联想起英格玛最新的那张名为《坠落逆天使》的唱片封面。听惯了莫里康内阳春白雪般老作品的乐迷们可能会失望了,甚至也许会认为他“堕落”了,但奥斯卡奖看中的就是这个。他真的还在创新,甚至在他如此高龄的时候。一位毕生都在创新的老人真的是难能可贵的,他从来都没有躺在自己的功劳簿上。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将大奖颁给了他,因为奥斯卡奖永远不会颁给“年龄上的老将”,而只会颁给“精神上的新人”。
在所有的西方音乐家里,莫里康内不是最长寿的一个,却是离我们最近的寿星之一。在他之前还有许多耀眼的明星,但大多在并不算大的年纪先行离去了。莫里康内成了其中不多的特例,他创作的音乐本是要求全身心投入的,并且必须极大地调动自己的感情,甚至让自己的灵魂随着剧情游走。但他的生命却在一天天地延续着,似乎在嘲笑那些肤浅的先行者,只有最深刻的人才配最晚离开。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著名的AMG数据库每个月都会在主页上发布刚刚离世的艺术家讣告。每当看到一个自己喜爱的明星和我们作别时,心情忧郁的我总会本能地登录属于莫里康内的页面。只要看到他那生于1928年的信息后面没有下文,我的内心便会瞬间充满安慰。

莫里康内与妻子玛丽亚
但现在,莫里康内也走了,他的那些原本在我听来充满自信的作品似乎全都成了无本之木,在没有主人的人间风雨飘摇。一个和我们并肩生活过的老人的离开必定会让我们由衷地惋惜,但那个年少夭折的莫扎特却不会,因为他离我们太过遥远。但为什么唯独莫里康内让我们感到惋惜,而另一位夏威夷的民谣歌手却不会?他惊人地活了一百多岁,但一生却只出版过四五张唱片。他的长寿无疑来自清净无为,就跟中国人的哲学追求的一样。莫里康内的作品是他的一百多倍,就在他告别世界的前几天,据说仍然在笔耕不辍。一个艺术家是因为他的职业精神而伟大的,我宁可他为自己的追求耗尽最后一丝生命,也不该在追求的道路上虚度任何一寸光阴。从这个意义上说,莫里康内的长寿是值得的,就像他晚年出过的一套唱片的标题所说的,他几乎有着“六十”年的艺术生命。也许在生活中,他早已是许多人的祖父;但在艺术上,他仍旧是多数人的父亲。
就在得知他离世的那个夜晚,我把剩下的所有时间都用来欣赏他那部唯一获得奥斯卡奖的电影配乐《八恶人》。而后我想起了《教会》,也想起了与他合作过的许多明星与其他很多故事。为什么上帝在他刚刚从股骨骨折的伤痛中恢复过来的当儿就召回了他的性命?或许他再也不能走得更远了,无论是他的创作还是他自己。人们不必为那部“无冕之王”《教会》感到遗憾,因为它是为升入天堂的人们所写的,也只配在设在天堂里的影院中响起。当他从人间远道而来,亲自在舞台上为他们指挥自己的作品时,他们一定会对他行一个标准的屈膝礼,就像他们对待信仰时一样。
——贯穿建筑的连续上升走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