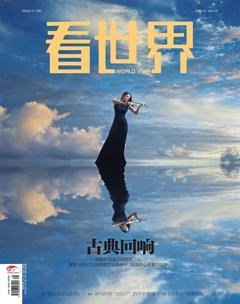从音乐里“识别”民族

荣智慧
“我一听到瓦格纳的音乐,就想入侵波兰!”伍迪·艾伦在电影《曼哈顿神秘谋杀案》里这样描述。在他看来,瓦格纳的音乐是“激情的文化,这种激情煽动屠杀”,并轻而易举地为“政治或宗教压迫服务”。
的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欧洲,音乐在爱国动员上角色吃重。那一时期也正是民族主义、国民主义等概念走红的年代,各个民族经常在自己的音乐传统中、在一位偉大的民族作曲家的形象中认出“自己”。
相比绘画,音乐跟民族主义的关系更紧密。音乐可以召集公众,充当集会伴奏,在庆祝独立或占领的仪式上奏响,更出现在国庆日和盛大的游行当中。人们正步行进的过程中,扛着一幅画的情景就没那么常见了。
在1870年之前,音乐还算一门无国界的“语言”,肖邦和李斯特代表的是“欧洲”的美学标准。不过很快,德国歌剧在瓦格纳那里发扬光大;威尔第被称为“音乐节的加里波第”;柏辽兹受到“法兰西民族音乐家”的礼遇……
普法战争开始时,人们并没想到民族问题开始有了新的意义。但是,整个欧洲的氛围已经改变,拿破仑三世向普鲁士军队投降,意大利完成统一大业,俄国亚历山大二世打出了“泛斯拉夫主义”旗号,迪斯雷利为大英帝国贡献了“英国式”的文化特性。由此,音乐在民族、国家的政治仪式上,开始具有了一席之地。
在不同的时期,音乐甚至可以代表截然不同的民族感情。
1914年,西班牙作曲家法雅写道,从这场“可怕的战争”中,他体会到重划必不可少的“种族领地”的边界是多么令人难以忍受。音乐要承担一种痛苦的历史使命,“为创立中的种族找回艺术特有的价值”。
1918年以后,音乐借助新的技术手段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大西洋彼岸的留声机里,开始播放爵士乐和探戈。
在中国,传统经典唱段—京剧《四郎探母》和昆曲《游园惊梦》,已经变成了少数人的“复古”爱好。伴随着黑白有声电影出现的,是《马路天使》里“金嗓子”周璇的“四季歌”,这首传统曲子已经经过了知识分子的改编,并以“血肉筑出长城长,我愿做当年小孟姜”结尾,直指“九一八事变”后中国艰苦绝伦的抗日历程。
对民族以及民族国家的理解,涉及复杂的认知过程,而音乐或许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对构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至关重要。
在不同的时期,音乐甚至可以代表截然不同的民族感情。比如李斯特的《拉科齐进行曲》,一开始是匈牙利起义者的集结信号,后来是布达佩斯歌剧院剪彩仪式的曲子,它还可以向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致敬—经历了“造反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和效忠皇帝的“官方民族主义”过程。
音乐能够确立民族身份吗?也许可以。或许它的作用,并不比诗歌和文章差。它们一起传递了感情的信仰和寄托,并给一种“普遍性”提供了庇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