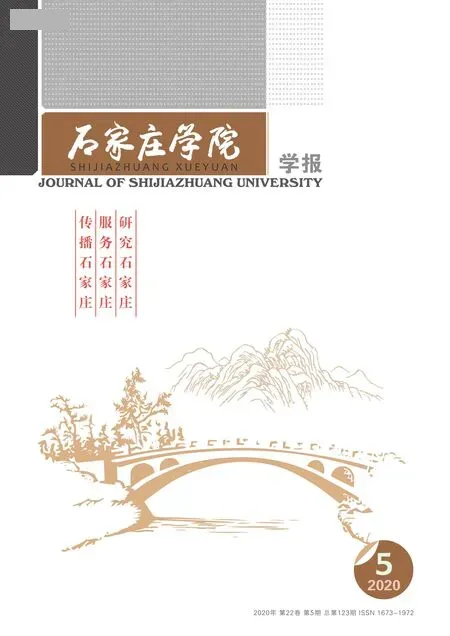《切韵研究》评介
侯 俊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一、《切韵研究》出版的学术背景
《切韵》和《广韵》作为研究中古音的汉语音韵学典籍中的经典代表,一直是20世纪研究的热门。清代陈澧《切韵考》是首部以《广韵》研究其声类系统和韵类系统的代表作。陈澧通过分析《广韵》的反切用字,总结归纳出反切系联法及其三大条例,这一研究反切材料的方法称为“反切系联法”被广泛运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虽然陈澧的研究为音韵文献中音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限于时代和材料,其并没有见到早于《广韵》的各种《切韵》残卷和王韵系韵书,并且无法构拟出具体的音值,因此,这些就成为后来学者研究的目标。
随着敦煌《切韵》残卷和故宫全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发现,为进一步研究比《广韵》更早的隋唐切韵系韵书提供了条件,学者得以进一步窥见早期《切韵》的面貌。与此同时,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传入,使得音韵学界从对音类的归纳跨越到对音值的构拟。在这些条件下,一大批学者开始更深入地重新审视《切韵》,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比如,对《切韵》系资料的整理研究成果更加丰硕——罗常培编写的《十韵汇编》、姜亮夫编写的《瀛涯敦煌韵辑》、周祖谟收集整理的《唐五代韵书集存》等,对《切韵》音类的研究更加细致。学者们开始采用新的材料研究音类,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和数理统计等新方法,并采用域外译音对音等新材料构拟音值;深入探讨《切韵》的性质和其代表的中古音中重要语音现象,如唇音开合口、重纽、重韵、四等介音等。
作为一部韵书,《切韵》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为我们系统地展现了古代汉语音类的结构。系统研究《切韵》的论著,最远可以追溯到《韵镜》《七音略》等早期韵图。明清时代,虽然提出或论著《广韵》的学者的很多,但都未从内部入手探讨韵书的体系。第一个这样做的是清末的陈澧,其《切韵考》的贡献在于首创反切系联法分析切上字得出40声类,纠正唐宋以来三十六字母就是中古声母的错误观念;据反切下字系联考定311韵类,说明《广韵》206韵与等韵开合四等的分合关系,使人们对《广韵》的声韵系统有了正确的认识,但其缺点也是无法从音理上来说明韵书的音系结构。目前国内对于中古切韵系韵书的研究,早已从音类的研究跨到音值的构拟,使音韵学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变迁。《切韵研究》作为一本以《切韵》为研究对象的音韵学专著,其在中古音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总之,20世纪是中古音研究取得巨大成绩的繁荣期,邵荣芬先生的《切韵研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是一本深入研究《切韵》的专著。
二、《切韵研究》对声类分合的探讨
对于历史文献材料的音系研究,一般分为两步:首先是音类的归纳,其次是对音类进行音值的构拟。关于《切韵》声母的问题,也分为声类数量的多少和音值的构拟两大方面。
关于《切韵》的声母数量,各家考求不一。总数有27(黄笑山 2008)、33(王力 1985,舌上音归舌头音)、35(唐作藩1987,采用李荣娘母归泥,不采纳俟母独立)、36(李荣 1956,俟母独立)、37(邵荣芬 1982,泥娘分立)、38(黄笑山1995,于母独立)。黄先生的27类声母是根据互补就合并的音位方法而来,以配合其对韵母的音位化构拟,具体的是将唇音、端知、精庄、匣喻母合并。其余35到38之间数目的差别其实争论并不大,主要反映在泥娘二母的分合、喻三匣母的分合、俟母、于母是否独立等问题上。
关于《切韵》的构拟,其分歧主要集中在日母、船禅母、知庄章、影母、浊音送气等问题上。可见,中古声母的研究大都已经取得共识,反映的问题也比较集中。
从声母的分合上来说,邵先生主要是将娘母和俟母独立出来,并结合具体的音韵材料和反切论证了独立的必要性。邵先生的《切韵研究》对于声母的研究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从内部证据和外部译音材料论证娘母独立
泥娘母是分是合的问题主要产生于:高本汉[1]35-36误认为泥娘与端知组等位不同,泥母为一二四等,娘母为三等是j化声母,这就造成了韵图排列与反切不符的情况;守温三十字母有泥母无娘母。因此,引起了各家对《切韵》娘母存在与否的争论。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这不只是泥娘两母的分合问题,实际上还牵涉到舌头音和舌上音的分合问题。在《切韵》音系中,其舌上音知组是否已经独立出来?其困难在于如何判定知组是音位变体还是独立的音位。在《王三》的反切里,舌音大部分处于互补分布,但也有相当数量的混切和对立的情形。就其内部的混切来看,各声纽的情况也不一致,无论是中古材料《博雅音》《晋书音义》《王三》《广韵》《文选音诀》《李贤音义》都反映出透彻两母的混切数是最少的,最大的是端知,其次是泥娘。这反映出舌音组的混切,其内部不平衡具有普遍共性。再从《切韵》舌音声韵的配合来看,大致是互补的。邵先生[2]41-43将少数的端知小韵对立看作是端知两组分立的依据,从而类比推理出泥娘也应当分合。同时,又通过《切韵》同时期的音韵文献材料(《汉书注》《举要》)的反切和汉藏对音来论证泥娘母有别,说服力很强。这种为少量对立而另立音位的作法,并非违反语言的经济性原则,而是因为对立原则是众多归纳音位原则中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原则。
邵先生通过对汉藏对音的考察,不但表明了泥娘两组对译不同的梵文,而且还为泥娘的构拟提供了参考,因此可以说是有力的证据。鉴于端知组声母后来分化,《切韵》内部的对立证据和外部汉藏对音,将端知分为两组有着充分的理由。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历史文献材料的反切,切不可完全相信。其中很可能存在辗转传抄现象,其内部存在多个不同语音层次的复杂问题。应当以《切韵》中的反切为标准来进行比较互勘,去除其历史文献中因袭的反切再来考虑其本身的性质问题,这样才能不被看似表面上历史累积的不同性质的反切材料所蒙蔽。比如孙志波[3]就通过“存雅求正”的方法发现《玄应音义》《李贤音义》和《文选音决》三家端知声母互切较《切韵》高出很多,但这些“类隔”切很大程度上是因袭传统注音习惯造成的。
(二)为俟母独立提供佐证
董同龢最早提出浊擦音俟母的存在。李荣[4]92根据切韵系的反切、韵图和汉语方言材料,考虑到切上字的互用和整体的音系结构,把“俟、漦”两个小韵从崇母分出来,独立成为俟母,这已被学界所接受。邵先生[2]44-47在这一问题上是沿着李荣的思路,将俟母独立的问题放到《切韵》同时或前后的一些反切材料里找可靠的旁证,从而将各家俟母的音切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俟母字独立,不和其他声母字系联,如《晋书音义》《李贤音义》;一类是俟母字用崇母字注音或作切,如《玉篇》《经典释文》《博雅音》《玄应音义》;一类是俟母字用崇母以外的其他声母字注音或作切,如《字林》《汉书注》。
邵先生将俟母独立的问题放到同时代的文献材料中去考察,扩大了这一问题的研究面。就切韵系韵书来看,从《切三》《王三》《广韵》三韵书的俟、漦反切用字可以看出漦、俟两字从独立系联再到分别与崇母对立的过程。可以说,俟母一直独立至《韵镜》时代。赞成俟母独立的学者中,董同龢、邵荣芬、郑张把它拟为舌叶音,而李荣、蒲立本、潘悟云则拟为卷舌音。这是由庄组其他四母的音值以类相从而决定的。
三、《切韵研究》声母音值的构拟特点
关于《切韵》声母音值的构拟,邵先生主要集中讨论了如下问题:全浊声母送气与否的问题,三等韵[j]化问题,这些是高本汉遗留的问题,邵先生全部予以纠正;知、庄组和泥日两母的音值问题;船母、常母、影母的音值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学者们争议比较集中的问题,笔者在邵先生的基础上分别加以讨论。
(一)纠正高氏浊声母送气说、j化说和知庄组声母的拟音
自从高本汉[1]251-254提出浊塞音和浊塞擦音为送气音的观点后,马伯乐、陆志韦、李荣等学者都不同意。陆志韦在《古音说略》从汉译佛经、一字异读、谐声系列三方面提出反对证据,李荣的《切韵音系》对高氏论据更是逐条加以批驳。
对于高氏气浊音的吴方言证据,邵先生[2]102-106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据此加以批判。他发现:第一,吴方言所谓的浊送气出现的范围广还出现在通音后面;第二,吴方言带[ɦ]的声母只出现在阳调而不出现在阴调;第三,[ɦ]和它后面的韵母元音差不多同时发生,与韵母关系密切。另外,从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和汉藏语系的其他语言来看,浊音都是不送气的。由此可以看出,邵先生的论证有类型学的倾向,即从大范围的数据归纳总结出浊声母不送气的类型学特征。目前,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全浊声母的浊音只有一套,在音位上不存在送气与否的对立。
所谓[j]化问题指的是:高氏[1]28受商克软化观点的影响,通过考查切上字一二四等和三等有分组的现象,认为声母在三等前面是[j]化的。因而,他将见溪疑、晓喻来、帮滂並明、娘、群母拟作j化声母。
学者对高氏的j化观点的批判主要有:没有方言依据;切上字甲乙两类有分组趋势,也有混切的现象,并不构成音位的对立;多采用字典等二手材料;忽视了精组切上字的分组;混淆纯四等韵和重纽韵的区别等。
邵先生[2]102-106对j化说的批评,主要从事实根据和系统性方面来进行。首先就是统计甲乙两类的混切次数来证明甲乙两类的分界并不严格,给人以直观的数字统计实例。接着具体指出高氏所引《康熙字典》的重纽四等的反切例子指出其对重纽四等和纯四等不分的做法。另外,从系统性上指出高氏自相矛盾、没有意识到精组有三等韵的情况。邵先生可谓是论证充分,辩驳有力。
知庄组无论是分合还是拟音都存在争议。自从高氏将知组定为[ȶ],庄组定为[tʂ]。知庄组的拟音一直都有分歧,至今仍未取得一致看法。邵先生首先列举高氏的构拟依据,并逐条加以批驳。邵先生依《古音说略》《切韵音系》的主张将庄组拟作[t∫],知组拟作和庄组同部位的塞音,因为没有现成符号而拟作[ȶ]。由于认为知庄组的卷舌音与三等的介音拼合有困难,因此将它们拟成舌叶音,这一派的学者有王力、唐作藩、李荣等。而另一派根据梵汉对音、现代京剧读音、现代方言如客家方言大埔话等存在着卷舌音可以与三等i介音相拼合的现象,而将知庄组字拟作舌尖后音声母,这一派的学者有罗常培、麦耘、黄笑山等。
如何决定这两种拟音方案呢?首先,应该看到这两种拟音方案有共性:一是认为知组和端组、庄组和精组应该分为两组声母音位,因为端知、精庄对立,精组和庄组都拼三等韵也有对立;二是知组声母应当拟作与庄组声母相对应的塞音形式。
在认识到这两个拟音的共性后再看两者的分歧,就清楚多了。其双方的争论不在音类的分合上,而在于如何构拟音值以期可以最大限度地解释书面文献和方言现象。采用不同的材料证据就会有不同的解释。将知庄组拟作卷舌音的依据在于梵汉对音,而将知庄组拟作舌叶音的依据在于绝大多数汉语方言和音理上的拼合。我们认为后者的解释力更强一些。首先,它符合汉语内部普遍的音值依据;其次,可以解释知庄组何以在同一韵中既拼二等又拼三等的现象;再次,从反面看,对音涉及的问题较多,比如对音的时代、音系基础、双方的音系结构等,情况比较复杂。
(二)接受高本汉对日母的构拟,反对李荣的观点
日母音值是声母构拟中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也是“最危险的暗礁之一”[1]338。高氏将日母拟作[ȵʑ],邵先生[2]115-117接受并对于李荣的两点反对理由逐条加以批驳。首先从梵文对音上罗列各家梵文字母的译音表,一方面说明泥娘有区别,另一方面说明日母带有鼻音性。高氏将日母构拟成[ȵʑ],主要是考虑到现代方言中日母在南方一般读作鼻音,在北方一般读作浊塞音或浊塞擦音,甚至在上海、温州同一个字有两种声母的文白异读。于是,日母的拟音就把这两个读法合在一起。邵先生接受了这个观点,或是手民之误,书中记作了[nʑ]。高氏的这种构拟反映出用历史比较法研究汉语方言的缺陷,即将两个不同层次的读音放在一起构拟。潘悟云[5]52指出其构拟的缺点:一是复辅音与整个单辅音音系结构不适应,二是把文白异读不同层次的读音放在一起比较不妥当。因此,我们赞成李荣的拟音拟作[ȵ]。
(三)多角度论证船、常母的音值问题
船禅两母的问题一是区分不区分,二是是否颠倒。李方桂[6]16认为《切韵》系统分船禅两母有搜集方音而定为雅音的嫌疑,否认船禅两母的区别。不过大多数学者认为两母存在区别。邵先生接受陆志韦《古音说略》中对船母擦音、常母塞擦音的观点,并加以补充论证:一是颜之推的话,一是梵文字母对音。邵先生[2]117-128着重论证了对音材料的证据,指出了8世纪以前常母在梵文译音中对应塞擦音。对于梵文对音和等韵图的排列矛盾,邵先生排除了偶然因素和不同的方言现象这两种假设,指出最大的可能是韵图排列错误造成的。为进一步类比论证,邵先生采用旁系韵书互证的方法,集中考察了同时期的文献反切,如《守温韵学残卷》《经典释文》《后汉书注》《史记正义》《慧琳音义》《集韵》中船常两母的表现,勾勒出中古船常两母在唐宋间由分到合演变的大致情况;接着邵先生又结合现代汉语方言材料,从广州话、北京话等论证船母读擦音,常母读塞擦音的例子亦然存在。总之,邵先生从书面文献的演变和现代汉语方言两个角度论证船母常母的音值应当与韵图排列相反,邵先生论证科学、充分,可以采用。
(四)从语音演变的阶段性确定影母的构拟
影母音值的构拟,国内学者除王力和陆志韦拟为零声母外,各家均遵从马伯乐、高本汉的主张拟为喉塞音Ɂ。从语音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便于解释影母平、入声字在现代北京话读音中的差异。
学者对于影母定为零声母主要是因为考虑到元音的浊音性质。邵先生[2]128从语音发展的角度联系到影母入声字在《中原音韵》里和次浊声母字一起派入去声,再结合现代北京话影母入声字也基本上都变作去声,从而论证出影母在声调变化方面存在平入不一致的现象。邵先生对此的解释充分考虑到影母的发展变化,认为影母原来是清塞音Ɂ,所以平声和其他清声母一起变阴平,后来失去Ɂ,变成元音或半元音开头,所以入声和次浊声母一同变去声。这种解释充分考虑到影母字的演变过程,也照顾到后世《中原音韵》的语音情况。可以说,邵先生从音变的阶段性角度很好地解决了将影母拟为喉塞音的问题。
四、《切韵研究》对韵类的分合讨论
邵先生对《切韵》音系的研究均是先讨论音类分合再据此构拟音值。其对韵母的研究也是首先对根据《王三》制作出反切统计表,使得《王三》反切下字的用字系联情况一目了然。这个统计表为后来的学者保留了研究的数据,非常有价值。
(一)对重纽两类的系联提出新看法
董同龢《广韵重纽试释》列出五点证据论证舌齿音与重四为一类,重三为一类;陆志韦《古音说略》也列出五点论据提出舌齿音庄知组和来母与重三为一类,其余与重四为一类。邵先生均分别逐点加以批驳,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甲丙为一类,乙单独一类。邵先生观点恰好与董氏观点相反。其论证依据为:一是文献材料《韵会举要》《蒙古字韵》里重纽韵都是甲丙同类而乙独立;二是依据的是东南一带的方言,很多甲丙同类而乙独立的例子;三是根据韵图的排列规则。
对此问题,我们认为邵先生的论证可以讨论:《韵会举要》《蒙古字韵》均成书于元代,距中古音近300多年,时代太晚,已不属于中古音的范畴;而韵图的排列也是属于中古晚期的材料不能代表早期《切韵》的实际情况。对于其方言的证据,邵先生[2]84也坦承确实存在反例。
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丁邦新[7]74采取了调和的看法,指出董先生描写的是早期反切系联的现象,反映了早期语音的情形;龙宇纯和邵荣芬所说的是韵图晚期的情形。以上两种看法都反映了语音的演变,只是前后时间不同而已。
(二)合并严凡、真臻韵系,归整韵系结构
关于严凡、真臻韵的分合问题,邵先生重视利用韵系之间的互补关系以整合韵系结构。其论证思路是,列举同时代的反切材料证明韵系相混现象普遍存在,从而说明《王三》分韵之牵强。另外,就是举出《王三》以前的韵书,论证《王三》《广韵》的反切对立不可靠。作者在音理上的解释是在《切韵》基础方言里,真臻、严凡都是在特定声母条件下,韵母主元音随着声调的不同而改变。
邵先生的这种解释并没有被一些学者接受,如冯蒸[8]《〈切韵〉严凡、真臻合并说商榷》对邵先生的论点一一辩驳,认为严凡、真臻应当保持独立。我们认为,邵先生是从音位互补合并、韵系整合的角度而采取的作法。因为为很少的对立作语音区别上的构拟是不经济的作法,必然会增加整个音系结构的负担和不平衡。邵先生的工作是构拟语音系统,这需要全局观念。冯蒸虽不同意合并,但并没有给出音系构拟上两个韵系的具体音值区别,因此这只是作了构拟的一半工作而已。潘悟云[5]62为构拟韵系提出四条构拟原则,其一是认为同一韵目下的字同韵,不同韵目下的字不同韵。但其音系结构也是将严凡、真臻韵合并以求得构拟的经济性。总之,从语音发展和音位的经济性原则来看,我们赞成邵先生的作法。
(三)辩驳前人谬误,判定庚三韵系的类型
《切韵》庚韵系二三等同韵,庄组字有些用二等字有些用三等字,于是如何判定庄组字的归属成为问题。邵先生[2]90-95赞成陈澧《切韵考》以反切下字系联为准,并一一辩驳了其他各家一律归为二等的作法的理由,指出庚三系不能归为三A类韵,不能因为庄组二三等出现机会互补就一定合并。邵先生论证的材料可分为三类:一是切韵系各韵书和同时期的音韵材料《博雅音》《经典释文》《篆隶万象名义》的反切情况;二是从庄组字二三等的历史来源上考虑;三是域外汉字音。经过这一系列的论证,邵先生将庚三系归为三B类韵。邵先生的论证材料丰富、科学,既从历史来源来看又从共时系统下的材料入手,同时还以域外汉字音作为佐证,其作法已被广大学者接受。
五、《切韵研究》对韵母的构拟特点
(一)取消高氏两类合口介音,论证咍灰韵唇音对立不可靠
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取消高氏两类合口介音被国内大多数学者认可,其次是唇音字是否不分开合则没有统一认识。邵先生的论证方法也可以归为三类:首先,唇音字和开合口字可互作彼此的反切下字,并举出诸多文献材料中的唇音反切用字加以说明这种现象在唐和唐以前的文献材料中普遍存在;其次,从《切韵》前后各家咍灰韵反切材料中论证唇音字各家切下字没有开合口的限制;最后,从方言中得出咍灰韵唇音字的归属整齐。
之后,学者们逐渐认为唇音存在开合口之别。黄笑山指出:“唇音字没有开合对立,并不等于唇音字不能有合口。”[9]潘悟云也认为,“中古的唇音没有开合对立,并不等于它们的实际音值就没有开合之分”[5]69,并详细论证了自己的观点,用词汇扩散的理论来解释咍、灰韵唇音对立的原因。近代日本学者大岛正健[10]同样认为唇音有开合口之分,他认为,发生混淆的原因是由于唇音与u发音部位相近,后世的韵图难以说明其原理,所以逐渐设置了诸多繁杂的门法。对于唇音字是否分开合,笔者认为应当分开合,这是因为:一是韵图的唇音开合口排列是比较规整的且符合后世唇音字的演变方向,二是对于邵先生所据的方言材料并不全备。从方言上看,唇音和咍灰韵可以有三种类型:一是唇音和灰韵一类以北京为例,一是三者全同以苏州为例,一是三者相异以南昌为例。我们也承认,从总体上看,唇音是与灰韵演变相一致的。
(二)重拟两类重纽介音
重纽的区别在于介音,这是学界的共识,但对于介音的构拟却多种多样,如表1所示。
邵先生[2]144修正《古音说略》的两类重纽介音的区别,指出三C(重纽三等)和三D(重纽四等)的介音区别在于舌位略低略后一些。因为邵先生将I作为脂韵系的主元音,所以就把三C和其他三等韵的介音写作i,三D拟作j(不表示颚化)。与之不同的是,多数学者普遍把重三拟作带有j音的介音,重四拟作i介音。从音值来看,介音j可以代表三等韵的颚化性质,因此后者的构拟相对合理。
邵先生对重纽的研究并没有过多地考证同时期的旁证材料。21世纪的学者对重纽问题的研究越来越精细化,逐渐揭示出整个中古重纽问题的面貌,从而发现重纽的区别,根据具体的反切用字,不同的材料可以反映出不同的特点。比如中古前期的《释文》的重纽反切主要通过切下字区别达99%,《广韵》主要通过切下字来区别重纽类型达92%,到了中古后期的《慧琳音义》则通过反切上下字同时区别的比例为97%,[12]而五代的《朱翺反切》则能通过切上字区别重纽类型为91%[13]①具体数据来源于李秀芹的《中古重纽类型分析》,浙江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朱翺反切重纽的特点》,载《语言研究》2015年第35期。。由此可以发现,重纽两类的区别已经从介音转移到声母上。
(三)论证纯四等韵无介音,从系统性上构拟纯四等主元音
纯四等韵有无介音也存在争议,虽然论证的材料(诗文押韵、韵图、对音、闽方言)一致,但得出的结果却相反。若纯四等韵存在介音,则四等韵介音的性质及与三等韵介音的音值区别目前还难以确定,因此目前普遍认为纯四等韵的介音是中古后期产生的,邵先生在李荣梵汉对音的方法下,利用严格的陀罗尼对音进一步加以论证。在四等韵主元音的音值构拟上,邵先生从系统性和拟音经济性上考虑采取《古音说略》主元音的构拟ε,这样真蒸侵韵拟作e就省略了一个附加符号。接着,邵先生修正了《古音说略》支、齐三、四等相配的观点,改为祭、霁相配,并在纯四等韵的基础上将和它们相配的三等韵拟作æ,从整体上精简、规整了音系结构。

表1 各家重纽介音拟音统计表
(四)调整重韵拟音
重韵一般是指一、二等韵在同一摄内,开合等第都相同的一对韵系。《切韵》系韵书存在两个一等重韵,即咍(灰)和泰、覃和谈;四个二等重韵,即皆和佳、咸和衔、山和删、梗二和耕。这些重韵的语音区别及其拟音,也是学者讨论的重点。高本汉认为区别在于音长的观点已被国内学者所摒弃。邵先生对高氏所使用的朝鲜借音材料加以研究,指出重韵的区别应该是音色而非长短,另外又借助梵文字母的对音来加以佐证,使立论有力。对于重韵音值的区别,邵先生在陆志韦构拟的基础上,对重韵音值作出三方面的修订:一是利用南北朝诗韵的通押现象调整山韵主元音的拟音;二是采取董同龢的观点,互调黠和鎋的位置;三是确定庚韵拟作一个主元音而非两个。
六、结论
邵先生《切韵研究》是20世纪研究中古音的力作。无论是音类分合或是音值构拟问题,本书都有涉及,并且对前贤如高本汉、陆志韦、李荣、董同龢等学者的观点加以仔细分析,对同时期《切韵》前后多种材料重新充分审视,能够不为前人所蔽,提出自己的见解。本书在多所高校被作为教材和必读书之一,影响极大。本书的优点在于:
第一,善于利用同时期的书面文献材料,针对具体某一问题展开讨论,以期对语音的演变作前后的历史考察。可见,邵先生虽然是作《切韵》音系的研究,但心中有语音史概念。
第二,将书面的某一问题求证于现代汉语方言,以期将文献音韵材料和实际的方言情况结合起来论述。邵先生善于利用多种不同性质的文献材料进行类比论证,如域外汉字音、梵汉对音、诗文用韵、谐声材料、韵图等,对同一问题作不同角度的论述考察,使结论例证丰富、说服力强。
第三,分析材料是研究工作的核心,分析得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研究工作的成败。邵先生对研究对象《王三》《广韵》等反切材料进行校订统计并列成表格,做成声母表、韵母表、反切下字表、反切上字表,对相关问题进行数理统计的说明,使人一目了然。这使研究建立在对材料分析的坚实基础之上,同时又保存了研究数据,方便、启发了后人。
第四,对前人观点进行批驳时,首先罗列相关论据,再加以一一指正,论证清晰明确。邵先生对论点的讨论总是能深入到论据的原始材料里面找产生错误论点的根源,使得批驳有力。
第五,结合实际材料和具体研究问题,灵活运用音位的互补合并的原则。比如:对于庚韵庄组二三等互补,邵先生并没有通归于二等;对于韵图上严凡、真臻、咍灰的对立,却能够通过历史文献的考察、方言材料的运用等多种材料综合考虑,指出其对立不可靠而将其归并,简洁、优化了音系结构,具有构拟音系所必需的整体性、经济性、系统性的认识。
笔者窃以为本书尚有以下几个微瑕:
一是对方言材料的使用不系统,调查的方言面相对较窄。
二是较少从音理上解释语音发展变化的原因,而只是作平面的静态描写。
三是对中古时期不同文献材料所反映的基础音系、基础方言点考察不够,而是均当作与《切韵》同一基础方言点的音系性质来看待。另外,对同一书面文献反映的音系没有考虑到其本身存在“存雅求正”[14]的特征。
四是韵母系统的构拟缺少主元音i,音系整体显得不协调,重纽两类的介音构拟稍欠妥当。
五是对于中古调值的研究论述较少,所占篇幅不多,这也是汉语音韵学研究的通病。限于有限的材料和调值变化快且比较复杂的特点,历来汉语史学者的音韵研究在古音构拟方面,多停留在声韵的构拟上,对古代声调调值的构拟研究不太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