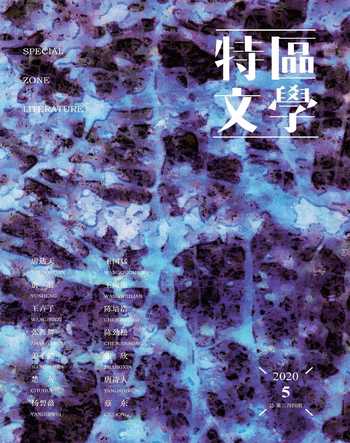现实的真相,及其诗意的翻转
夏汉
相对论
孙文波
巨大反差:阳光下黑暗的话题,
把我们引向心灵的最深处。在那里,
有一些东西是不能触动的—分离,
或者死亡,总是把我们朝绝望的方向推,
为了应付它,需要我们彻底懂得虚无。
但是谁又能真正懂得。因此,我更愿意谈论
生活的表象。譬如今天,我愿意谈论
户外的阳光,明晃晃的光线下,
人们在矮树丛晒花花绿绿的衣裳。你看一下
这样的景象吧!我总是从中感受生活,
它们从来不哲学不神秘,不把人引向想象的黑暗中。
也许我可以因此告诉你:生活,是一次次洗涤,
在绝望时洗尽绝望;在沮丧时洗尽沮丧。
它使我哪怕冬日午后沿着河岸散步,
不论走在青石砌的小径,还是踏入枯黄草坪,
都在努力地寻找让心里轻松的感觉;
看见河水清亮非常享受,看见不知名的雀鸟
从树丛中飞起,也能从心底涌出喜悦。
或许,你会说这些仍然无法留住我们的生命,
死亡终将到来—死亡!我不否认它。
但我希望,活着时,享受活着的乐趣
—我知道死亡绝对,我们不过相对地活。
我与山相对,与水相对,与鸟相对
在相对中,用相对的喜悦,反对绝对。
按照波德莱尔的观点,一切好的诗人都是现实主义的—尽管在某种境况下,仅仅只是一种在否定叙事中再现文化和审美与之对立的社会现实的激情(参见高名潞《波德莱尔的现代性与浪漫主义思想》,王志亮译);而从诗的发生学的角度,诗又是无中生有的。那么,怎样在二者之间寻找一种平衡,的确成为一个问题。以此观察孙文波近期的写作,正好是一个入口—就是说,从内容看,其写作取向一直都在现实的维度上,而且是那样地投入与真诚,不妨说他在写作中杜绝了虚假與造作。而同时,他的每一首诗却又是在对于词语的辨认中趋于完成—或许诗人深信“那种真实的词即是这样的事物”(伽达默尔)的诗训。
当然,一个时期以来,文波面对社会现实的态度几乎是悲观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归于时代的“馈赠”,但他可以把这种持久的感觉融入诗里,“加入到他的词语方阵之中,开始抵抗”(希尼)。同时,在持续阅读中,能够感觉出来,诗人尽管对于政治是在意的,但却在写作中有意疏远或淡化,或者说不屑于把政治牵扯进来,而这种转化显然给他的诗带来了新的样态。故而,他的诗在很多情况下都是靠剔除了某些观念后的真实生活细节来推动,总是以情绪隐蔽起来之后的平静语调进入诗的铺述。比如在《偶像的作用》里,通过对于某些细节的寻找、忽略与排除,陷入复杂的沉思,直到“重新回到我们的现实”,但那已经不是之前所经历的,“我们需要小心地,就像绕过路上的水洼一样”绕过,从而在与现实的疏离中“重新定义自己”。诗人还会在“学校、车辆、疫情。/瓜果、蔬菜、饮料、酒水”的细节铺述里,“变化着组成诗句”,而且做出 “某一次灾难也到来”(《每一天,都有新》)的预言性判断。
缘于对于现实的诗学认同,我在文波的几乎每一首诗里总能看见其独异的身影—或许这也是作为一个见证者的预设。诗人可以在读书之际有所感:“我读过后,很感兴趣”(《读<高适集>作》);可以沉醉于某种风景:“这让我一个早晨全用在/盯着那棵树看了”(《眼前有景》);自然也可以对于自己生活的有所觉察:“每一天,都有新的事情发生。譬如说/今天,从痛疼中醒来。仿佛从地狱中返回”(《每一天,都有新》)在这样的“有我”之境里,其实也意味着一种诗人的自觉,同时也构成了策兰意义上的对于一首诗的“自我忘却”的反证。
着力于现实,必然含括人物,所以,当看到诗里关涉人的事由,就有几分亲切—况且那是一种游离于小说虚构的恳切。比如在《读<高适集>作》里,“有一件事,/人们一直诟病于你,朋友落难,有求于你,/你却没有帮他。而你的朋友大名鼎鼎。/因为你没有帮他,差一点死于非命”无疑,这是对于高适的传记性表达。随后的“官场云诡风谲,/每一步必须走得如履薄冰。你必须格外/小心谨慎”则予以宽厚地理解,不啻说,这是作为诗人间的惺惺相惜,是穿越久远历史的独属于诗人间伟大的体谅。同时,如此的表达还在“应和之作”中呈现的友谊和“诗坛佳话”的体例之中呈现出了某种写作的驳杂与复合—这才是文波作为一位现代诗人的艺术僭越。
作为诗歌,似乎人们的基本期待首先就是审美的想象,在文波看似粗粝、朴拙而并非唯美的文字里—这恰恰是其审美性选择—自然不缺乏想象力,在《眼前有景》里,诗人如此写到:
学校操场边的凤凰树开出了
殷红的花,远远望去,犹如一滩血。
悬挂在空中的血。
接下来,诗人联想到曾经的年代,武斗中脖颈涌出的血,在农村过年时猪羊身上喷出的血,这种恐怖的景象显然跟死亡关联起来。而“花朵是植物的血”与“火山喷发出的红色熔液,/是不是可以称之为大地的血”的诘问则引向生存的深入,从而“世界上我不清楚的事太多了”的感叹才显得有力而自然。有时候,诗人甚至可以将想象逼近梦幻之中:“从天空中下坠,穿过云雾的迷阵。被闪电击中/左胸三次,或许更多,摔倒在石头堆中,/还没有爬起,一群豹子、鬣狗、野猪围了上来。”这时候,诗人已经在日神的护佑之下窥见了诗的“美丽光辉的尊严”(尼采)。
文波的诗里有着一个颇为稳定的文体特征,那就是其思辨性,在近期写作里,这种思辨色彩愈加浓重。这是一种成熟的写作所拥有的知性与诗性智慧,能够体现出诗的力量与“随时间而来的真理”(叶芝)。在《春风不度》里:
自从艾略特写下“四月是一个残酷的月份。”
盛开的意识便凌乱的盘绕在人们疑惑的头脑里。
就像此刻,一只鹰从我的眼前飞过,它已经不再是鹰,
而是一只恐怖。带着巨大的不祥。
显然,文波从艾略特这句诗里截取了“残酷”的蕴涵,而用于描述亲临的生活感受—这是那个时间里很多人的共同感受,恐怖与死亡随时会降临到头上。而不同的是诗人通过联想与想象强化了这个感受,最终转化成一个审美的诗性表达:“我分明看到天空裂开了口,/倾刻之间,会有什么坠落?一口锅,或者是/笼罩我们的谎言。都不是……而是,末日的景象。”而一首《瘟疫思》通篇都沉入思辨之中,“看不透空气。怀疑主义开始流行。那些明亮/都是假象,那些清新隐藏着致命的杀机”“人的确是人的敌人”,在作出“一切都在必然中”之后,依旧让思辨惯性般地潜行,从而跌入“另一个幻想”的虚无。在《短是长的收缩……》这首诗里,诗人的思辨则始于一种语义上的虚无裂变和“词成为词的衍生物”的游戏,而最终在揭示语言秘密的途中,达至词与物意义上的诗意翻转与生命的指向。
在对于文波写作的观察与反思中,始终有一个直觉:他在开始写作的某一刻,或许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表达,尤其没有一个现实的清晰概念,或只有一个诗的萌芽促动着他?这样,反应在他的诗的语调里就有着某种犹疑和不确定性,尽管他的叙述是肯定的,“每一个词都落到实处”(哑石语),可以说,他几乎没有对诗的最终生成抱有先在的预设。他只是从一个原点—生活中的或语言的—开始,悠然地写下去,或跟着潜意识,或跟着想象,有时候就是跟着某个词语的连缀—就这样写下去,直到最后,他似乎意识到了诗已经出来,才顺其自然地罢手。但这种生成是有其内在的合理性,记得艾略特在《诗的三种声音》里,谈到贝恩关于“不对任何人说话”的诗的作者从哪里着手写作的问题,大意是:首先是有一个不活泼的胚芽或者“创造的萌芽”,另外就是拥有语言。有某种东西正在他心中萌发,他必须为它找到词句;但在他找到他需要的词句之前,他无法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样的词句:在他把这个胚芽转换成正确的词句以前,他无法确定这个胚芽是什么。当找到这些词句后,那个不得不为之寻找词句的“东西”却消失了,代替它的是一首诗。文波的《鲸落》这首诗,或许就是如此产生的。首先出现了一个鲸鱼的形象?或一个词语:大海王,然后,诗人展开想象性捕捉;
庞大的纵横家。油脂的产出者。
一生在逃避人类追捕。有时候扑向沙滩找死。
接着,描述喷出的水柱,被太阳染成霓虹;其啼鸣,像夜半歌声在空旷的大海间“犹如海妖被唤醒。足以让闻者心惊”;继而论及鯨鱼之死,“亦带有神圣的纯美的意味。垂直的下落,缓慢而庄重。/向着黑暗深处(绝对骄傲的过程……)/一点点滑向彻底的虚无”,最终演化为对于死亡的礼赞—诗篇完成得漂亮而凝重。
在孙文波近期的写作里,能够确定一个诗学判断,便是他的一个明确指向—个体与世界的关联,这一点构成他写作的一个意涵显在,我们也就在他的文本里始终领略到这一点,而他的每首诗又反应了不同的侧面,这种持恒成为其写作的德性,也为其写作确立了最终的意义,或者说诗人“仰仗自己的机智”(奥登语)完成了作为当代诗人的使命。概言之,孙文波在貌似散乱却是自如、自洽的写作中,针对生存及其时代现实的并非乐观的描述里,显现着诗的真意或真相,或许从这里可以看得出诗人信奉着曼德尔施塔姆的观念:“存在是艺术家最大的骄傲。除了存在他不渴望别的天堂”,“因为他知道艺术的现实更无限地令人信服”而“在诗歌中这现实恰恰正是词语”(杨青 译)。这也是作为一个诗人的当代写作的全部诗学价值。
(栏目责编:朱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