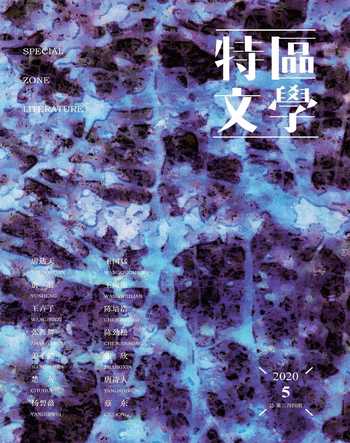十面埋伏
在暗处
树木整夜站在露水中
草地潮湿,或许正在交换它们的种子
而灯光如一道符咒,中止并取消
地下的秘密交易
在可见的边缘
蹲着一只的青蛙,正分泌出粘液
人的脸会在玻璃后面出现
身体陷入黑暗,那是未知的
地平线后面,半个世界滚落进海洋
它们终究摆脱了我们,只有
船依然笔直地航行,被暗处的
马达推动着。为什么驱动我们的一切
都来自地下、暗舱和沉重的黑色丝绒
仿佛中世纪女巫的长裙
也许内衬艳如晨曦,在古代希腊或英格兰
石板路上走来一个中国人,也可能
只是长得相像。而如果你有喜悦
身体内就会出现一道闪电
叶辉简介:
1964年生于江苏省南京高淳区,著有诗集《在糖果店》《对应》《遗址》。
徐江:为什么,要在暗处
《在暗处》是一首“有意思”的作品。说“有意思”,是因为它比较容易被新诗作者和新诗评论者认可为“诗”,也比较便于被泛学院评论者拿来解读。
“暗处”究竟是指什么?诗里没有明说。姑且也不用管,不妨就当作是一个情境的交待,或对某种精神与氛围(也许二者合一)的暗示。总之,阅读者要想进入作品,得先从题目的这种“预设”下进入。
“暗处”里有什么?诗中铺排(或者说“繁衍”)出了一系列元素。很丰富、很具象,带着画面感,却又一飘即逝,很难提炼出某种确定的所指。也许作者这么写的用意,就是让读者随着笔触,做一次思绪飘荡的“旅行”和推测,其意并不在于呈现确定性。
那么,为什么要在“暗处”呢?作者依然是让读者去猜。或者说,想这么猜的读者,并不是作者理想中想要的读者。如此一来,问题又来了,究竟什么思维的读者,是作者理想中的读者?
某种意义上说,《在暗处》也代表了新诗的某种趣味,有理想,有言说,但又不触碰传统的美学,外表上的“绿色”“暗色”,保证着这类诗在各种场域下被视为“同道”,但作者自己是不是真视这类知音们为“同道”,又是另外一回事。
世 宾:我们不能穷尽“暗处”世界却可以感知
叶辉的《在暗处》一诗涉及暗处边缘、暗处、深暗处、历史记忆的遗忘处、各个从诗性上属于“暗处”的角落,但这肯定不是暗处的全部(谁也无法穷尽暗处世界的全部),诗歌只是在引领和唤起我们对暗处世界的感知。一首诗通过一个局部或多个局部,带领读者去感知和认识语言所呈现的或隐藏在语言背后的世界,这是一首现代抒情诗的大部分功能和意义所在;一首诗的另一个功能和意义就是诗人借用具有同一属性的一首首诗歌,去构建一个属于个人的和时代的诗歌世界,我们籍诗人所创造的世界扩展我们的精神空间。一个诗人的成就是看他所建构的世界(每个时代对与它对应的诗歌世界提出了要求),我们看他创造了一个怎样的世界,这世界在历史之中提供了属于诗人所处时代的有利于历史进步或新的、有意味的东西。语言和世界是诗人写作的开端和终极目标,在这两个点上,诗人必然要耗尽一生。少年时抒情,追逐修辞;中年之后,开始意识一个属于自己、可以让自己精神皈依的世界的存在,此时也就不再追逐此起彼伏的情绪,而专注于语言和那朦胧中逐渐成型的世界的气息的吻合;而在晚年,所有经验和思想化成语言引领着诗人的诗歌抵达那诗人头脑中的世界顶点,那里光辉灿烂,却是艰险异常,它的路径时隐时现,难以捉摸,但却魅力十足地吸引着诗人向它靠近并通过语言把它呈现。
叶辉的写作正处于中年的阶段,他的诗歌第一眼扑入眼帘的是语言给人带来的感觉、气息。叶辉是能准确把握和呈现他在意识层面能抵达的世界,那些意识无法抵达和暂时没有抵达的地方,可以借助语言和诗歌形成的张力扩张到文本背后的世界。我们知道,散文所关注的是经验世界和思想世界,它们借用词去深入和呈现经验和思想的世界,而诗歌是把经验和思想转换成语言,并由语言去建构一个诗性、诗意的世界,语言即是诗性、诗意世界的馈赠,也是诗性、诗意世界的建筑材料。这就确保了世界和语言具有了同一的属性。这语言具有强大的建构诗歌世界的功能,并在诗歌没有呈现全部世界时,语言有能力把诗歌带入世界中,让那个被诗人揭示的世界被阅读者感知到。
叶辉是运用通感的高手,他不仅仅在修辞上使用通感,如把暗处比喻为“仿佛中世纪女巫的长裙”,更重要的是他在整首诗中使用通感时的畅通无阻。当然,这也是想象力的表现,但通感是更诗性化的、更具体的,能把外在的形色和内在的精神融为一体,并呈现在头脑中的想象力。诗人借由语言把那头脑中的世界表现出来,因此,我们说语言也是那世界的馈赠。《在暗处》一层层地引领我们进入暗处,直至在历史的遗忘处,我们又仿佛与什么相遇,“在古代希腊或英格兰/石板路上走来一个中国人,也可能/只是长得相像”;在最黑暗的地方,喜悦的闪电也许会由此把我们照亮,“而如果你有喜悦/身体内就会出现一道闪电”。
西渡:意义的延迟,或反朦胧诗
叶辉这首诗在结构上和朦胧诗很相似,由一系列平行的语象组成,这些平行的语象构成了一种相似或隐喻关系。但叶辉写的并不是朦胧诗,而是一种全新的诗。这首诗的语象之间的相似性不是建立在性质的类同上—这是隐喻的标准定义—而是建立在一种纯粹的形式关系上:它们都“在黑暗中”。实际上,一种性质的弱相关正是通过这一形式关系而被召唤出来,而不是相反,性质上的相似导致它们被诗人选中。朦胧诗以意象为基本的写作手段。如果不加细察,我们很容易把构成这首诗的系列语象也认作意象。但这些语象的性质、功能与朦胧诗的意象实在大不相同。意象来自文本,一般都有较为固定的意义指向。朦胧诗的表达尽管打破了当时主流诗歌裸呈式的意义呈现方式,但仍然带有一种快速落向意义的冲动。朦胧诗和当时主流诗歌的区别在于,主流诗歌说“a(意象)=b(意义)”,而朦胧诗说“a(意象)=c(意义)”。而本詩的这些语象,其出生地并非文本,而是经验和精确的观察。它们不带任何现成的意义指向。无论是“整夜站在露水中草地的”,正在地下“交换种子”的树木,还是“在可见的边缘蹲着的”“正分泌出粘液”的青蛙, 或者是“玻璃后面出现”的人脸,都是这样。实际上,这些语象仅仅以它们自身的感性向我们现身。它们彼此之间确实构成了一种隐喻关系,但这种隐喻关系更多是形式意义上的;换句话说,这些隐喻的内涵是空的。这个“空”造成了诗歌意义的延迟,而意义的延迟进一步凸显了诗的感性。正是明晰的感性而不是明晰的或朦胧的意义才是叶辉诗歌的追求。这是一种全新的美学原则。a=b或a=c的美学公式,现在换成了a=x,这个x是一个未知,取决于读者的发现和发明。作为公式,它开放、未知而未成,并不完善。但作为诗的原则,它因为开放、未知、未成而满蕴着可能。在这个美学原则面前,朦胧诗a=c的美学公式,实在并不新颖,更没有那么大的革命性:它和主流诗歌a=b的公式实在是同一个东西。而在这个a=x的意义延迟中,我们确然看到了一种新的当代诗的诞生。
吴投文:在暗处发现隐微的光亮
敏感的诗人都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能从不可见的事物中发现生存的隐秘,从暗处发现隐微的光亮,从互为陌生的事物中发现新的激动。我想,叶辉正是这样的一位诗人。日常生活于他而言,就是一座丰富的矿藏,他总是从生活中的细微之处发现贴紧人性的光彩,即使是日常生活中的无聊状态也能在他的笔下转化为一种值得品咂的甜净滋味。他的诗往往写得非常干净,在简洁中流出一种平静的语调,像是疏离自己的处境,却又保持对日常生活复杂状态的热忱,不激烈亦不回避生活的暗角。
这首《在暗处》仍然是挖掘日常生活的隐秘,在别人忽略的地方抵近隐秘中那份特别的光亮,就像诗人所说的,“身体内就会出现一道闪电”,让人在轻微的颤栗中豁然领悟到生存的实质。此诗写夜景,亦是写诗人的心境,在暗处的一切似乎都笼罩着潮湿的气息,幽暗中亦有未知的明亮。夜色中的草木与灯光是敌对性的,在不可见处暗暗较劲。一只青蛙在可见的边缘分泌粘液,似乎也有它的担忧。至于那张在玻璃后面出现的人脸,似乎也带着莫名的紧张,一半在光亮中,一半在黑暗里。在远方的暗处,也泛涌着诗人情绪上的幽暗,却更深地贴近诗人的忧郁,也更深地贴近诗人深心里的某种渴望。诗人对暗处所有事物的描绘都有实景的依托,却又似乎是游离的,显示出观察生活的一种别致眼光。说到底,诗人的发现主要还不是体现在生活的直观层面,更多的还是体现在生命的内省层面。在暗处,可以让一个人的内心沉静下来,而在远处则有另一种召唤。
此诗的前二节写近处的事物,后二节写远处的事物,诗中的时间和空间并不是静止的,而是从此时此刻滑向古代,从身在此处滑向远处的幽暗。这一滑动的过程既是想象带来的结果,也是诗人在想象中叠加和丰富自我的过程。这是一首写得非常别致的诗,语调舒缓从容,显示出一种克制的力度。在暗处发现隐微的光亮,大概于诗人而言,意味着从不可见的事物中发现生命与生活的某种确定性。
敬文东:幽暗史与身体内部的闪电
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认为,身体不仅把一种意义给予自然物体,而且也给予文化物体,比如说词语。词语在成为概念符号之前,首先是作用于身体的一个事件,词语对身体的作用划定了词语意义区域的界限。正因如此,敏感于语言的诗人们很可能对词语有一种来自肉体上的超强迷恋,在生理上对某些词语格外上瘾几近依赖。这即是现代汉诗中的“身体-本能”式表达。诗人叶辉的《在暗处》一诗便采用了这种“身体-本能式”表达,诗中看似精心挑选的词语站在夜晚的露水中、潮湿的草地上,“分泌出粘液”或“滚落进海洋”,但细读之下不难发现,这些意象更像是从身体内部喷涌而出的—诗人置身于他所营造的晦暗的文本空间之中,用身体去觉察、追忆或想象。在他的笔下,黑暗是为光亮准备的。从某种角度看,是对黑暗的悦纳而非对光明的追求,推动了人类前行的车轮。窸窸窣窣、影影绰绰的暗处是可怕的,但这不过是来自外部的黑暗,是可以轻易破解的:露珠反射的月光,照亮树木的灯光,乃至想象中女巫衬裙般的晨光,都足以点亮暗处的世界。和外部的黑暗相比,内心的黑暗更为可怕。除了人性的黑暗外,艰难的时代生活给人性本有的黑暗再一次添砖加瓦。内心的黑暗和时代的黑暗,决定了这是一束无法回逆的光线。和狄兰·托马斯笔下“通过绿色茎管催动花朵的力”相似,人们也“被暗处的马达推动着”,来自地下、暗舱和沉重的黑色丝绒驱动着“我们的一切”。历史悠久的幽暗意识,使人们警惕外在的暗处,同时悦纳它,而正是这种隐微的喜悦,催生了身体内部的闪电,并再次照亮了内心的暗处。
赵思运:诗意在“暗处”
无数的人歌颂光明,而叶辉却歌颂黑暗,歌颂暗处的人、事、物。我一直认为,诗是对人性边界和生存边界的勘探。因此,诗人往往具有灵视能力。他要在光明之处洞察黑暗的机制,在地面洞察地底的奥秘,在现象背后探究本质或者本质的虚妄。诗意的真相在“暗处”。比如:草地的种子在暗处交流;隐秘的青蛙在分泌;人所陷入的背后的未知;航船运行的马达驱动力……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的判断就会颠覆常识,“仿佛中世纪女巫的长裙/也许内衬艳如晨曦”。叶辉拥有了强大的象喻功能,而这种象喻系统是一種呈现。这种它所隐喻的诗意就像人的身体内部深藏的一道闪电。叶辉照亮了暗处,我们看到了什么?我读过叶辉很多整体象征的杰作,相比之下,这首诗只是提供了一个“比兴”,诗意刚刚开启。
向卫国:这是一个可以让整首诗足够重要的问题吗?
“为什么驱动我们的一切/都来自地下、暗舱和沉重的黑色丝绒”。在我看来,这整首诗完全落实在这一句上。这是一个以肯定为前提的问句。其前后部分都是作为佐证材料而出现在诗中,包括树木、灯光、青蛙、人的脸、地平线后面的世界、航行的船,还有时间、种族差异、喜怒哀乐等各种情感,它们的存在、演变、相互之间的关联,一切的一切,其决定性力量都隐藏“在暗处”,在“地下、暗舱和沉重的黑色丝绒”等不同的暗处,及其背面。
所以这首诗的成败得失,也就取决于这一句,取决于其所提出的问题的分量。
那么,这是一个足够新的问题吗?这是一个可以支撑整首诗,让其足够重要的问题吗?
周瑟瑟:当代诗歌活着到底是什么样子?
古代中国人的诗歌的样子就在那里,我们看得很清楚,古人死了,连骨头都找不到了,但诗歌依然在呼息吐纳,持续着奇怪的生命状态。当代诗歌到底是什么样子?好像我们活着就是活着,而诗与你的生命无关,诗与语言的关系虽然嘴上说关系重大,其实并没有说得那么紧密,大多时候松松垮垮,说不清的关系。
叶辉这个人好像生活在某一个暗处,虽然我知道他在那里生活得很好,但他有意在暗处,让诗的文本出来走动还是有必要的,诗代替诗人走动,人在暗处诗在语言的明处。
叶辉把语言推向明处,他在漆黑的夜里点燃了诗的火光,让人看清诗的样子,像树木“站在露水中”“交换它们的种子”,诗的火光一点点照亮隐藏的诗。当代诗到底在怎样呼息吐纳?叶辉隐藏了诗人的肉身,但我看清了他的语言与语气,这是他的诗歌活着的样子。
“石板路上走来一个中国人”,这或许才是叶辉骨子里的诗歌活着的样子。青蛙在分泌粘液,“人的脸会在玻璃后面出现”,这些都是“未知的”“陷入黑暗”的,而“石板路上走來一个中国人”把暗处的事物带向“喜悦”。我们面对的诗的面目变幻莫测,但诗必然是活着的,哪怕是静悄悄地活着,诗总会传递出活的气息。
叶辉揭示了“暗处”的生命状态,神秘的事物有迹可寻,但又说不清,也不必说清。保持“暗处”的好处尤如清水养育的水仙,好看的洁净的水仙,精致的语言可以触摸。生命建立在“暗处”,包括叶辉“暗处”的诗歌美学与趣味本身。
韩庆成:或许因为“在暗处”!
恕我愚钝,这首诗反复读了几遍,终究没能看懂。
但也有几点感想,不妨记录如下:
一、诗的跳跃很大,这个大包括时间,也包括空间,涉及古今中外;
二、作者好像写了一些具体的事情,但究竟是什么事,找不到线索。虚虚实实,实实虚虚;
三、我猜想,作者或许是想表达“暗处”“推动着”“一切”,并想找到原因,但诗的一半篇幅似乎又与此无关。何况,这个发现也经不起推敲,因为在现实中,很多“推动”都是明火执仗的;
四、诗中用了很多意象、隐喻,因同样找不到线索,而加重了诗的晦涩;
五、诗的表现方式与当下悬殊很大,新诗潮也好,朦胧诗也罢,乃至更早的,晚些的诗人,仍然这么写的不多了,除非是旧作;
六、或许是因为“在暗处”吧。
徐敬亚:读不明白,是诗的本质
八九十年代读叶辉,清新而明丽,略感柔细。今次一读,大吃一惊。全诗意象琳琅,意念似有似无……初读后令人莫名,躲在这些汉字背后的已是一位巫师般的诗人。
杠精们会说,天下没有读不懂的诗。那样说你也没办法—如果放弃对清晰逻辑线索的要求,剩下的的就是一首诗内部与意义无关的纯诗的合理性问题。对于诗来说,合理性高于内容意义。
第一节,不仅是清晰的,也是优美的。“灯光如一道符咒” 与结尾的“身体内就会出现一道闪电” 形成照应。灯光与闪电也双双构成了本诗主题“暗处”的对立元素。第一节可以说隐暗地写了生命“在暗外”的神秘交流。
复杂性在第二节出现:“青蛙”出场了,它仍然可能是原来的树与露水的背景,也可以是另外的场面,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出现一张“人脸”。对于树与青蛙来讲,他是第三者。这个第三者使诗出现转折。地平线与海洋的意象很迷人,“在暗外”的主旨由暗指变为明确:诗人说黑暗是半个世界。
第三节,船承接了前面的海洋意象。之后的几行非常提神:暗处的马达,成为全诗的诗意核心。
在我看来,前面三节是完全清晰的—除了第三节首行“它们终究摆脱了我们”令人不解之外。说看不懂,只因没细读。
倒是最后一节,意念出现了严重漂移。叶辉无情地给我们一个奇怪的结尾,仿佛从另一首诗里摘下来的粘贴。但是不,我找到了与前三节的两个契合点:一、女巫长裙内衬和中国人的相貌,不正是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么。二、那由喜悦而出现的一道闪电!—一首诗写出来之后立刻成为固体。其形成过程任何人都无法猜测。这道闪电虽在全诗最后,但它可能诞生得最早,从《在暗处》的最早起意开始,叶辉一直想写一道闪电。我猜,也许。
这首诗曾令很多高级读者们困惑。
无疑,我们应该更高地预估诗人的智慧。而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愚钝的读者并不存在,任何人读出来的,都是诗文本中蕴藏着的诸多种含义的一部分。尽管诗人给予我们的一定是他认为最好的文字结局。但诗人也常常弄得一团糟。
即使读不明白也不要紧。我以为,读不明白,恰是诗应有的一个先天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