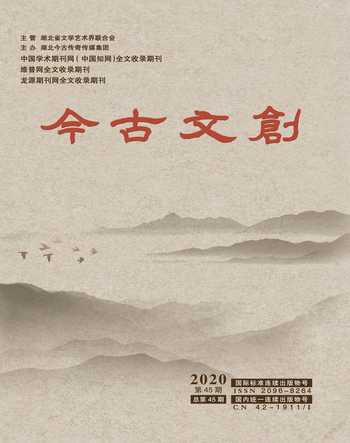从蛇的意象角度辨析希伯来文学中的巴比伦成分
【摘要】产生于两河流域中下游美索不达米亚东南部的巴比伦文化和西亚地中海沿岸巴勒斯坦的希伯来文化同源于闪族(闪米特族)文化体系。本文从为什么蛇在巴比伦和希伯来文学中总是作为敌对者出现这个问题入手,通过对《埃努玛·埃利什》《吉尔伽美什》与《圣经》中蛇意象的分析希伯来文学中的巴比伦成分,发现蛇意象有颇多相似之处,两者存在影响关系。最后得出结论,希伯来文学延续了巴比伦文学中蛇意象与权力、魔鬼和生命母题的密切关系,并且丰富了蛇意象的内涵。
【关键词】蛇意象;巴比伦文学;希伯来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45-0021-04
在《埃努玛·埃利什》中蛇是万物之母提亚马特神,后被马尔杜克神杀死;在《吉尔伽美什》中蛇夺走并吃掉了吉尔伽美什千辛万苦找到的“长生草”;在《旧约》中蛇是诱惑夏娃的撒旦的化身。为什么蛇总是作为敌对者出现?蛇在这两个文明中的有怎样的象征和内涵?为何诱惑人的是蛇而不是其他狡猾的动物呢?围绕这些问题本文试图对巴比伦与希伯来文学中的“蛇意象”做初步的整理和思考。
一、巴比伦文学中蛇的意象
(一)《埃努玛·埃利什》中蛇的意象
1.蛇是权力的象征
从创世史诗七块泥板的记载来看,蛇是作为咸水神提亚玛特的身份出现的。提亚玛特被描绘成“凶恶的怪兽,长着翅膀、鳞片和恐怖的爪子,她的身体有时是一条巨蟒,有时是一个动物①”。第六块石板赞美马尔都克功绩时也表示“‘守护心灵之王’,并擒住了毒蛇” ②。她与淡水神阿普苏生下了众神,是万物之母,原始先民在艰难生存的挣扎中对生命、繁殖及维持生存的食物极端渴求,因此富有生命力与繁殖力的蛇受到崇拜,提亚马特是原始初民对蛇生殖崇拜的文学化体现。但是古巴比伦文学的独特之处在于蛇形的神同时是“命运泥板”的所有者。“命运泥版”是刻有天命的泥版,控制了这块泥版,就控制了宇宙的运数,这是蛇与权力意义相连的体现,而这块“命运泥板”也是众神争夺的对象。
随着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王朝统一两河流域和巴比伦成为国家首都,为提高马尔都克神的地位创作的《埃努玛·埃利什》,核心就是赞颂马尔都克神的战胜提亚玛特的英雄事迹。泥板记载了马尔杜克神杀死了蛇形的提亚马特的全过程:
“95.天主拋出他的网,使她困于网中,96.匿于他身后的狂风现于她面前。97.提亚玛特将嘴张至极限,98.马尔杜克使其口不能闭合,同时使狂风进入[她的身体]。99.狂怒的风充满她的腹部,100.她的心被攥紧,她张大她的嘴[来喘气]。101.马尔杜克紧握长矛,他将她开膛破肚,102.他划破了她的内脏,他刺穿了[她的]心脏,103.他将她归为虚无,他摧毁了她的生命。104.他抛下她的尸体,他站立于其上,129.天主[马尔杜克]肆意蹂躏着提亚玛特的残躯,130.用他手中威严的棍棒,击碎了她的头盖骨。131.他割开她的血管(意为“动脉”)。132.他使北风携带她的血进入地底。” ③
从这段描写可以看到提亚玛特先是被网困住,又被灌于狂风,最后被残忍地开膛破肚。这种男神杀害蛇形女神的描写表明这个时期的蛇意象象征了失去统治权的女神和被男性占领的王位。“在早期文化中,被谋杀的蛇代表了父权对母权的胜利,后来演变成对征服王权的象征。王位本来是带有母权色彩的一种意象,在母系社会结束后,这个意象却被保留了下来。” ④随着父权制文明国家的建立,最高主神的性别也开始发生转换。男权社会下男性作为社会的主宰者,蛇成为被隐喻的女性形象被征服或者杀死,代表了父权制对母系社会的全面取代。
2.蛇是邪恶的象征
神话中的蛇意象表现为向男性神神祗和英雄挑战的反面力量,代表了黑暗、邪恶、死亡。石板中记载了提亚马特在与马尔杜克决战之前,造出了11种怪物:
“113.创造了万物的乌穆库布尔;114.建立起所向无敌的武器,她孵化出大量巨蛇;121.她组织起毒蛇、蛇、拉克哈穆神;122.旋风、恶犬、蝎形人;123.强劲的暴风、捕鱼人、长角的怪兽(可能为摩羯宫);124.他们带着在战斗中坚决而不退缩的武器;125.最有威力的是提亚玛特的判决,任何人都无法抵抗;126.因此她创造出了十一个这种类型的[怪兽]。” ⑤
可以看到采用了夸张的手法强调了这十一种怪物的恐怖性,并且几种不同的表现形式:第一,七头七尾的大蛇,因为头多尾多,难于砍杀,这一夸张似乎是无法斩尽杀绝、不可战胜的象征。使用数量的夸张这一表现形式,在世界各民族中都是常见的。希腊的赫拉克勒斯除掉的九首水蛇、印度大梵天的四首四躯八臂、湿婆的五头四臂三眼、我国帝江的六足四翼、人皇的九头等,都是以数量的夸张展现神明形象的非凡特征。第二,是采取动物与动物之间异体整合的形式进行夸张。动物的异体整合,就是将几种动物身体中的不同部位进行重新组合,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四不像的怪物,借以实现夸张的表现力。如:火焰四射的龙头蛇尾兽,就是一只在长颈上长着龙头、龙头上长着两只角,其尾巴却是蛇的尾巴,而四只脚却长着两种不同动物的脚,两只前脚是狮掌,两只后脚则是鹫爪。这就是由动物的异体整合而成的,既不能称之为龙,又不能叫蛇。这种异体整合的夸张表现形式似乎意味着它像龙一样腾云驾雾,像雄狮一样快跑如飞,在万物面前称王称霸,又能像鹫一样任意抓捕猎物,为所欲为。在世界各地的口头文学创作中,这一夸张的表现形式也是常见的。第三,是人与兽的异体整合。人鱼,是人与鱼的异体组合;蝎子精,下半身是蝎子、长着鸟足的人形怪物。这一种夸张的表现形式,也是为了凸显它们像蛇蝎一样、毫无人性的很毒心肠。此外,第二块石板中提到提亚马特创造出了邪恶。“她将自己的神子们与[邪恶]捆绑在一起,提亚玛特创造出邪恶为阿普苏报仇”,同样可以看到蛇的意象已经与邪恶的寓意相连,成为恐怖邪恶的、令人憎恶的象征。
(二)《吉尔伽美什》中蛇的意象
1.蛇与“盗食”
《吉尔伽美什》包含着古代近东的文学、历史、宗教、民俗等各方面文化元素。第十一块泥板记载了吉尔伽美什终于得见到已获永生的乌特纳皮施提并向他们询问获得永生的方法。乌特纳皮施提向吉尔伽美什讲述洪水故事的经过,虽然乌特纳皮施提没能帮助吉尔伽美什得到他想要的永生,不過他告诉吉尔伽美什有一株仙草能够使人长生不老,永葆青春。吉尔伽美什历尽辛苦找到这株仙草,可惜的是这株仙草却在他返回乌鲁克城的途中被一条蛇所偷吃:“这时,吉尔伽美什看到一个冷水泉,他便下到水里去净身洗澡。有条蛇被草的香气吸引,[它从水里]出来把草叨跑。他回来一看,这里只有蛇蜕的皮,于是,吉尔伽美什坐下来悲恸号啕,满脸泪水滔滔。” ⑥巴比伦人认为蛇之所以长生不老,是因为蛇得到了重返年轻的能力,蛇能够在一年一次的蜕皮时获得新生。蛇蜕皮这一行为令人联想到了死亡和重生,脱去了陈旧的外衣,留下一具皮囊,获得了崭新的躯体。这一行为一点关联了死亡和重生,就已经自带了很强的神性和神圣性。这种本该是人类所享用的不死草或不死药等被一些动植物或特殊的人吃掉,从而动植物等长盛不衰,人类却遭衰老而死的“盗食”母题也出现在印度的“搅拌乳海” 神话和汉族嫦娥飞天神话等。
2.蛇与“长生”
第十块泥板记载了吉尔美什在寻找水生的途中遇到一位酿酒的女子思杜丽,并对她讲述了自己要获得永生的计划。思杜丽对吉尔伽美什说:“吉尔伽美什,你还要游到何处呢?你要寻找的水生你不会找到当众神造人的时候他们把死亡指派给人,把水生留在他们自己手中。”透过这段文字,可以看到巴比伦人对生命的思考,人是否可以获得永生?从吉尔伽美什追寻永生的旅程以无功而返作为结局可以看出巴比伦人认为死亡是创世时即赋予人的属性,永生本就不属于人。
史诗中传奇英雄人物追寻永生的过程中,曾经几乎就要获得永生,最终却因为一条蛇的出现而以失败告终,只能顺从人必有一死的结局。史诗中蛇 “盗食” 灵草而得到 “长生”,由于灵草被“盗食”人类难逃必死的命运。这是巴比伦人对人类为何无法永生的初步认识,而蛇与“盗食”和“长生”的母题也流传在近东文学作品中。
二、巴比伦文学中蛇意象在《圣经》中的嬗变
(一)蛇与权力
在《圣经》中蛇与权力的关系主要集中体现在《出埃及记》和《撒母耳记》中。首先,《出埃及记》中,摩西的权杖是蛇变蛇的,在权势的象征这一点上与古埃及文化更紧密。据金字塔铭文记载,地神“盖伯”把眼镜蛇授予法老,把他作为埃及王位的合法的占有者。“在开罗近郊吉萨哈夫拉王金字塔前的狮身人头像上,在阿布·辛布尔岩窟庙前的拉美西斯二世雕像上,在卢克索神庙的墙壁上,在帝王谷和王后谷的陵墓的壁画上,几乎都有一只头部挺立,颈部膨胀,盘卷在法老和王后的头饰或王冠上的眼镜蛇形象,它是瓦泽特蛇神以超人的毁灭力量保护君主的象征,也是法老统治宇宙权力的神圣的标记。” ⑦在这些神话和传说里,蛇都具有很大的威力,是权利的代表或守护者。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蛇是人类欲望性、财富、权势的象征。其次,在《撒母耳记》中,美男子扫罗受圣灵激励,击败“蛇君”(nahash,亚扪人的王,旧译拿辖)的故事与巴比伦创世史诗《埃努玛·埃利什》中马尔都克击败蛇形提亚马特的故事有相似之处,都是通过“杀蛇”这一行为夺取权力的。不同的是希伯来文化中从杀“蛇母”变成杀“蛇君”,弗洛伊德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指出“许多在神话和民间传奇中代表性器的动物在梦中也有同样的意思如鱼、蜗牛、猫、鼠表示阴毛,而男性性器最重要的象征则是蛇”。⑧在母系社会,大母神为最高信仰的时一期,蛇具有多重象征,蛇象征主要表现为女性,蛇的阴性属性占主导地位。但在父系社会,男性生殖崇拜发生在男性生产力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之后,在这个基础上成为中心信仰。所以从杀“蛇母”到“蛇君”的变化是从女性生殖崇拜到男性生殖崇拜的体现。
(二)蛇与魔鬼
在《旧约·创世纪》中,撒旦化身蛇诱惑夏娃偷食禁果使人类始祖犯下原罪。在《启示录》中“(启12:9)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它被摔在地上,它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启20:2)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它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它不得再迷惑列国。”可以看到希伯来文化中同样认为蛇是魔鬼的化身,是邪恶的象征。历史学家指出,有关魔鬼和邪灵的信仰可以追溯到美索不达米亚的早期历史。古代的巴比伦人相信地下世界,也就是所谓的“不归之地”,是由尼甲统治的。尼甲是一个残暴的神,以专职焚烧人而知名。巴比伦人也害怕邪灵,他们以念咒来安抚邪灵。罪恶之神“被描绘成样子像怪兽,长着细长弯曲的鼻子、宽阔平直的耳朵、僵直分叉的尾巴”。⑨在古巴比伦仪式庆典中祭拜、触摸、尊敬蛇,并且越毒的越好。巴比伦人相信,魔鬼无处不在。魔鬼经常七个一组,人们多半在沙漠中遇见他们。沙漠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对巴比伦人来说,鬼的出现使沙漠更加恐怖。有可能发现魔鬼的其他地方包括墓地和空旷的、据摇欲坠的建筑物。魔鬼可以以多种形式出现:他们可能是蛇,或者蝙蝠,或者任何他们选中的生物。对人来说,抵部魔鬼几乎是不可能的。每个人都知道魔鬼能出入窗口或从门下溜走或者随风而至。遇到魔鬼可能意味生病或者坏运气。如果作物歉收,那可能是鬼的杰作。如果一个女人不能生小孩,那也可能是遭到了魔鬼的诅咒。一般来说,生活中发生的任何坏事都可能是因为魔鬼在作怪,或者因为众神被激怒了。
此外,《启示录》中巴比伦是堕落和罪恶之城,是欲望和放荡的象征,最明显的是被赋予人格化形象的魔鬼意象“淫妇巴比伦”。《启示录》中描写了一名天使扮演了妓女的形象,她身着绚丽的珠宝,手握着一只杯子,而杯子里面盛满了道义的污浊之物。而她的头上则书写着这样的文字:“巴比伦,伟大的城市,是妓女们的母亲,也是地球上所有的罪恶之母。”从中可以发现淫妇、蛇及魔鬼这三个意象由于具备相同的邪恶属性而联结并聚合在一起。这种内在关联与巴比伦怪异的风俗有关。希罗多德的《历史》中记载了巴比伦人有一个最丑恶可耻的习惯,这就是生在那里的每一个妇女在她的一生之中必须有一次到阿洛秋铁的神殿并在那里和一个不相识的男子交合。女人是坐在神殿的域内,头上戴着组帽,四面八方都有用绳子担出来的通路,而不相识的人们使沿着这些通路行走来作他们的选择。女子在被不相识的人把一只银币抛向她的头并和他在神殿外面交合之前,是不能离开自己的位子的。《启示录》中把巴比伦人的这种怪异的风俗上升到一个整体性的魔鬼意象,女人与七头十角的朱红色的兽、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金子宝石珍珠妆饰、手中金杯及杯中的“可憎之物”共同组成了魔鬼意象。
(三)蛇与生命
《创世记》中亚当和夏娃因为蛇的游说而违背上帝的禁令,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被逐出伊甸园,从而不再有机会接触生命树,也就意味着失去获得永生的可能。通过上文论述的《吉尔伽美什》中蛇盗取长生草的故事角度去理解伊甸园的故事,可以看到其实也涵盖了人不可能获得永生这一主题。圣经学者巴尔(James Barr)提出,伊甸园故事就其自身叙述而言,其主题不是关于原罪的,而是关于人曾经如此接近永生。但最终未能得到,亚当和夏娃并不是因为他们背离了上帝、犯了原罪而没有资格生活在伊甸园,而是因为如果他们继续生活在伊甸园,就会吃掉生命树上的果实而获得永生。之后的经文告诉我们,亚当离开伊甸园后一直活到930岁才去世,在世的时候生养儿女(创5:4—5),是圣经中名列前几位的长寿之人。对比伊甸园故事中,上帝警告亚当吃禁果的那天必定死,结果大相径庭。这正说明伊甸园故事并不在意所谓的“罪”以及对罪的惩罚,而在于对生命的探求。在两个文化中,都可以看到蛇与生命的关系十分紧密,《吉尔伽美什》中更侧重蛇夺取了人的长生,《创世纪》中蛇却开启了人类的智慧。蛇不仅是作为破坏者出现的,一定程度上也是引导者。
三、结论
蛇的意象作为一种古老的图腾在各民族文化中的意义十分复杂多变。它在神话中蜕去了其生理意义上的动物属性,上升为一种文化象征和符号,并且超越了地域和种族的限制,成为一种集体意象。从某种意义上说,蛇意象的流变其实反映了人类原欲文明与禁欲文明冲突融合的历程。比较以上两种文化中蛇的意象发展和变异的过程,可以发现以下几点:
首先,蛇与权力关系在两种文化中都十分密切,并且都出现了通过“谋杀蛇”获得王位和权势的故事模式。
其次,蛇都是魔鬼的象征。巴比伦文化中母蛇是邪恶的制造者,希伯来文化中发展了这一观念,把蛇、女人和魔鬼三者由于具备相同的邪恶属性而联结并聚合在一起组成更为复杂的魔鬼意象。
再次,蛇与生命的关系紧密,体现了两个民族对人为何无法到永生的问题的思考。巴比伦人认为蛇之所以长生不老,是因为蛇盗取了本该属于人类的“长生草”获得了重返年轻的能力,人类因此无法得到永生。希伯来人认为蛇一方面使人类犯下了原罪,但另一方面开启了人的智慧和自我意识。
注释:
①②③⑤(英)沃利斯·巴奇、董晓博、晁雪婷译:《巴比伦创世神话》,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35页,第135页,第118-119页,第83-84页。
④(德)埃利希·诺依曼、李以洪译:《大母神——原型分析》,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3页。
⑥赵乐牲译:《吉尔伽美什》,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7页。
⑦李葛送:《圣经影响下的文学艺术中蛇意象探源》,《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⑧(奥)弗洛伊德、罗林译:《梦的解析》,百花州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38页。
⑨于殿利:《人性的啟蒙时代: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艺术与思想》,故宫出版社2016年版,第214页。
参考文献:
[1](英)沃利斯·巴奇.巴比伦创世神话[M].董晓博,晁雪婷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2]张朝柯.论东方古代六大史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3](德)埃利希·诺依曼.大母神——原型分析[M].李以洪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33.
[4]赵乐牲译.吉尔伽美什[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
[5](奥)弗洛伊德.梦的解析[M].罗林译.南昌:百花州文艺出版社,1996.
[6]于殿利.人性的启蒙时代: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艺术与思想[M].北京:故宫出版社,2016.
[7]卜会玲.神话中的蛇意象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1.
[8]李葛送.人与蛇的纠葛[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9,(07).
作者简介:
甘西淼,女,汉族,黑龙江哈尔滨人,研究生,东北师范大学,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