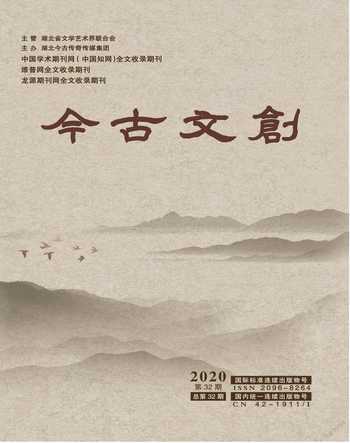从《蒸汽屋》中那纳形象的塑造 看凡尔纳民族起义书写的矛盾性
【摘要】 在《蒸汽屋》中,从东方主义出发,凡尔纳对“他者”印度人的反殖民运动极尽诋毁之能事。他把起义的根据地写成了“土匪窝”,对起义领袖那纳 · 萨伊布则集中笔墨描写他的屠杀妇孺、背信弃诺等等恶行;但作为进步作家,受自然主义影响,那纳斗争的正义性在小说中也得到了体现。这反映出凡尔纳思想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关键词】 东方主义;自然主义;民族起义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32-0035-03
基金项目:2017年度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一般项目“凡尔纳小说中的东方主义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XSP17YBZZ053);2019年度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凡尔纳科幻小说的科技思想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19YBA172)。
在《蒸汽屋》中,那纳 · 萨伊布是一个反抗英国殖民者统治的印度起义领袖,凡尔纳把他塑造得奸诈、凶残,而最后也让他粉身碎骨,不得好死。这反映了西方人对东方人固有的种族偏见和情感态度。但与此同时,在凡尔纳笔下,那纳又是一个争取民族独立的英雄,他的反抗具有正当性,而且有勇有谋,颇得印度人民的拥护。
在凡尔纳小说中,对东方人的这种矛盾看法始终存在。在主观上,他对东方人是鄙视的,甚至是仇视的;但受当时西方自然主义风潮的影响,他也想“客观”地描写东方人,因此他们有时又被刻画得正义凛然。
一、那纳形象的东方主义观照
在凡尔纳生活和创作的时代,随着殖民活动在全球的拓展,东方学成了西方的显学。作为科幻小说作家,凡尔纳在描绘科技事物之外,对书写东方也是充满热情。“19世纪东方学的一个重大发展是将有关东方的基本观念——其纵欲,其专制倾向,其乖异的思维,其不求精确的习性,其落后——凝固为独立的、牢不可破的连贯整体……”[1]凡尔纳受这股思潮的熏染,对东方人习俗和道德等的低劣津津乐道,他尤其喜欢描写他们的“不人道”[2]。
在《蒸汽屋》中凡尔纳延续了这一创作习惯,只不过小说的人物换成了印度人:“在那片二万八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两百五十万居民,他们仍处于原始社会状态;而且至今还残存着一些在蒂波 · 萨伊布统治时期曾抗击过侵略者的游击队员;那里也是著名的勒人专家萨格人的老窝,恐怖之处正在于这些迷信而凶残的凶手杀再多的人也从不见流一滴血;那里的潘达里人曾制造过令人发指的大屠杀,但却没受任何惩罚,逍遥法外;那里的达夸特人和萨格人一样凶残可怕,只用毒药杀人……”[3]这片地区是印度人发动民族革命的根据地,但被凡尔纳污蔑为“土匪窝”。
和以往的东方学家只是一味地描写东方人的野蛮、落后不同,凡尔纳把这一东方人的特征强加在了印度起义战士的身上,给他们贴上了“凶残”的标签,从而污名化反殖民运动。并且他把现实和历史结合起来,把反英斗争和当地人为非作歹的传统混淆在一起,试图从本质上证明革命者的劣根性。这就使凡尔纳的看法比以往东方学家的陈词滥调有了新意,当然也显得更加恶毒。
在《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南部非洲历险记》等小说中,凡尔纳往往是在面上,笼统地粗线条地描写东方人的“不人道”。而在《蒸汽屋》中凡尔纳集中笔墨塑造了一个凶残的印度民族革命领袖的形象,企图更加具体、生动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那纳 · 萨伊布是1857年印度士兵起义的一位领袖,他下令屠杀了坎普尔的英国妇女和儿童。小说强调了那纳的残暴:“我们一进入坎普尔城,就立刻开始四处寻找那些可怜的妇女和孩子们,我们知道她们在凶残的那纳手里,但很快我们便得知了屠杀的消息。在这些无辜被杀害的同胞所饱尝的磨难面前,我们痛苦地发誓一定要偿还血债,同时,我们还想到了一些奇怪而野蛮的念头。心中燃烧着对那纳的仇恨,我们发疯般地奔向烈士们殉难的地方。在她们生前被关押过的那个小房间里,地面上血迹斑斑,各种残片没过了我们的脚背。柔软光滑的长辫子,被撕碎的裙子,孩子的鞋以及玩具堆满了被血浸透的地面。墙面上同样地沾满了凝固的血迹,仿佛让我们看到了她们死前曾作的痛苦挣扎。”[4]
按西方人的规则,在战场上枪炮无眼,双方战斗人员的死伤是正常的;滥杀妇孺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而那纳 · 萨伊布就是一个触碰底线的人。作为印度起义领袖,虽然没有实际动手,但作为下令者,他要承担首要的责任。这时,作为“他者”的那纳和作为“自我”的西方人似乎地位转换了,西方人是受害者,那纳是施暴者。印度人成了强权;西方人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是值得同情的弱小者。西方人只记住了那纳的暴行,却全然忘记了作为殖民者的“自我”对印度人犯下的罪行。这是西方人的一贯伎俩,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在这里,凡尔纳成了西方“自我”的一员,利用话语霸权,散布自己的一家之言,成了文化帝国主义的“传声筒”。
那纳 · 萨伊布的恶劣品性是多方面的,小说还起底了其狡诈、背信弃诺的黑历史。从很早的时候起,大头人那纳就表现出一副对西方人非常友好的模样。在士兵起义爆发时,他假装承诺帮助殖民地政府对此进行镇压,而坎普尔的军队领导人维莱将军没有发现他的阴谋,相信了他。但不久那纳就露出了狐狸尾巴,参与并当了叛军的头。他要求殖民者军队缴械投降并保障他们的安全,维莱将军屈辱地同意了。哈弗洛克将军前往平叛,当那纳获悉殖民军已经离他们不远时,他违反诺言对英国军人和平民进行了血腥屠杀。在西方人的话语体系中,东方人的“阴柔”是另一种陈词滥调。东方人的血气可以用钢枪铁炮来消弭,而“阴柔”却令西方人无可奈何。它代表了與西方不同的文化和传统,与西方人的“阳刚”“率真”形成二元对立,他们仇视它,诋毁它,在不同的文学作品中对其进行鞭挞。那纳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典型东方人性格的人物。他假意投靠英国人,利用他们的信任来施行阴谋诡计,这对殖民者的伤害更大,因而这种“背叛”也更令西方人深恶痛绝。其实,与殖民者的虚与委蛇是东方人的一种斗争策略,是力量弱小时保存自己的有效手段,是在殖民者高压下的不得已而为之,这恰恰反映了殖民者气焰的嚣张和被殖民者处境的艰难。但西方人不会站在东方人的立场来思考问题,他们只会考虑自己的利益,只会戴着种族主义者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东方的人和物。在这一点上凡尔纳与东方学家的观点是一致的,充当了为殖民主义帮腔的角色。
东方学家们不遗余力地宣扬东方人的劣行,在帝国主义时代是有其险恶用心的:“东方是与西方二元对立的,东方学的思维方式即以二者之间这一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区分为基础。这种区分有着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明确西方‘自我’的存在,通过与东方的区别来明确自我的优越之处; 另一方面即为后续的殖民侵略做道德铺垫,因为‘他者’的落后,自然便需要‘我族’的拯救。”[5]
在殖民初期,宣扬东方野蛮、落后是为殖民寻找理据;到了中后期,西方人继续这一论调则是为殖民者镇压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斗争作舆论宣传。如同《蒸汽屋》里描写的那样,经过从17世纪开始的殖民,到19世纪中叶西方人在印度的移民已经是遍地开花。他们在印度到处建立庄园,过着人上人的生活。而民族独立运动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生活在印度的西方平民和军人的伤亡,影响殖民地“繁荣稳定”的局面。这时,为了保卫来之不易的殖民成果,帝国主义的文化策略是高举人道主义的大旗,从道德的高度攻击东方人。这既安定了西方人的人心,欺骗了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更为残酷镇压起义运动找到了借口。作为西方人的一分子,凡尔纳加入到了为维护殖民地长治久安的文化行动中;种族身份、文化土壤使他不自觉地充当了帝国主义的同路人。
二、自然主义实录下的那纳反殖民斗争
凡尔纳用东方主义来观照那纳 · 萨伊布的反殖民斗争,他看到了人性中邪恶的一面。但那纳追求民族独立的事业是正义的,这谁也抹杀不了。凡尔纳用自然主义的笔触把它客观地记录下来,那纳又呈现出正面的英雄形象。
那纳的反抗斗争有正当性,因为英国人在印度殖民地犯下了滔天罪行:“你们的人曾把佩斯查沃一百二十名我们的战俘绑在炮口上,而且从这天起,共有一千二百多印度兵死于这种可怕的刑罚!你们的人残酷地屠杀了拉合尔的逃亡者,在占领德里之后,又杀害了三个王子以及王室的29名成员,还是你们,在勒克瑙屠杀了我们六千名同胞,在旁遮普战役后又死了三千人!全部算起来,已有十二万印度官兵和二十万名平民死在大炮、步枪、绞架或是屠刀之下,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这场民族解放战争!”[6]
凡尔纳内心深处是想为“自我”讳匿的,在《南部非洲历险记》中对西方人所犯罪行的描写就有避重就轻的嫌疑[7]。
同样,在《蒸汽屋》中他写东方人的不人道浓墨重彩,极尽渲染之能事,写西方人的恶行只是用数字列举一下,显得简单敷衍。尽管殖民者的罪恶也叫人触目惊心,但在文学作品中缺乏生动、形象的细节,其感染力是大打折扣的。然而不管怎样,凡尔纳借小说人物之口把西方人在印度作的孽公之于众,这就说明他还是有正义感的,体现了他的进步性。
那纳 · 萨伊布坚韧不拔,士兵起义失败后,过了十年他又准备发动新一轮抗争。他从一个村子走到另一个村子,从一个城镇走到另一个城镇去策动各阶层的人士。他坚信在其努力之后会有许多的印度百姓加入到他们的队伍:“现在,仍应按原计划行事。这一次的运动将是全民性的。让城市、农村里所有的印度人都参加起义,与印度士兵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当我跑遍了德克坎的中部和北部地区后,我发现反抗之心已遍布各地。这次的起义,我们应深入到每个城市,每个小镇。让婆罗门尽力说教民众,宗教信仰会使西瓦和维希努两地的教民听我们的指挥。时机一旦成熟,就按事先约定的信号,几百万印度人同时起义,皇家军队的末日就要到了!”[8]
那纳是一个优秀的起义领袖。对胜利的前景充满信心,浑身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行动有计划,有步骤,坚持群众路线,扩大统一战线,体现了高超的斗争艺术。在这里,那纳表现出的形象和凶残、狡诈等特征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其性格前后显得不统一,人物塑造显示出矛盾、分裂的维度。要解释这一现象,必须了解凡尔纳创作深受自然主义影响的一面。
在法国19世纪中叶,科学技术取得了迅猛发展,在知识界崇尚科学蔚为风气,这股潮流进入到文学领域,形成了自然主义流派。其代表人物左拉认为文学的基础是真实,而真实就是要如实描写现实、再现现实。
他在《戏剧中的自然主义》中强调“自然”的客观性:“必须按本来的面目去接受自然,既不对它做任何改变,也不对它做任何缩减。”[9]作为科幻作家的凡尔纳很容易就接受到了文学创作中要坚持科学理性的自然主义观念。对现实生活做记录式的描写,这使他揭示出符合事实本来面目的那纳形象的某些侧面。
三、结论
凡尔纳在塑造那纳 · 萨伊布人物形象时总的思想基调是东方主义的,他对这样一个反抗西方人的殖民地英雄憎恶远远大于好感。小说中西方人主人公的最终结局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而那纳却受到西方人的严惩,最后和蒸汽屋一起爆炸,尸骨无存。因此,尽管凡尔纳对他做过自然主义的描写,表现了其斗争的正义性,但在作家的意识深处,那纳的命运却是注定要毁灭的。
参考文献:
[1]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1999:261.
[2][7]张岳庭.土著人的无人道:西方人的真实谎言——论凡爾纳的土著人书写[J].青年文学家,2014,(12).
[3][4][6][8]凡尔纳.蒸汽屋[M].吴君,孙婷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160-161,107-108,319-320,39.
[5]施晔,杨蕾.论20世纪上半叶英国小说中的唐人街书写[J].社会科学,2019,(5).
[9]朱雯.文学中的自然主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177.
作者简介:
张岳庭,男,湖南湘阴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法国近现代文学、凡尔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