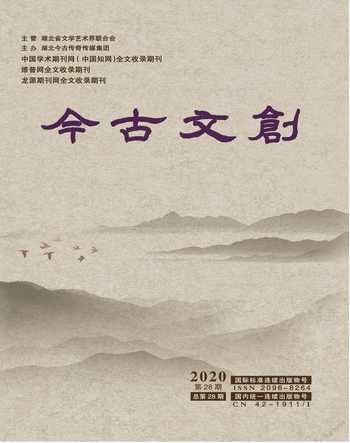叶燮《原诗》中诗人素养“识”“胆”“才”“力”探析
【摘要】 叶燮是清代初期著名诗论家,其诗论专著《原诗》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继《文心雕龙》之后最具逻辑性和系统性的一部理论专著。全书分内外两篇,系统性地论述了诗歌创作主体和客体以及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本文拟从《原诗》文本出发,探析诗歌创作主体的四大素养“识”“胆”“才”“力”以及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以期对一代大家叶燮以及其专著《原诗》有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
【关键词】 原诗;诗人素养;识;胆;才;力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28-0007-03
叶燮在他的诗论著作《原诗》内篇中以独到的见解提出“才、胆、识、力”论:“曰才、曰胆、曰识、曰力……而为之发宣昭著。[1]”他在对创作客体“理、事、情”作了充分的论述之后便提出与创作客体相呼应的创作主体应具备的四个重要能力。他说创作主体具备了这四中能力就能穷尽心中所想,世间万物皆能被用最为恰当的文章发宣昭著。在提出这个要素之后,他进一步对四要素的重要性以及各个要素之间的联系进行了详尽的论述。他认为作为诗歌创作者的四个要素“才”“胆”“识”“力”之间没有所谓的熟重熟轻,四者之间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如果有一项缺失,便不能登上作者之坛。但是“识”却是“才”“胆”“力”之前提,“识”为四者之先,“识”明则胆张,“胆”张则才生,“才”须以力为载。叶燮关于诗歌创作主体的“才、胆、识、力”的论述头头是道,句句在理。故本文拟从叶燮《原诗》文本出发,总结归纳他在“才、胆、识、力”四个方面所论述的详细观点。
一、创作主体素养之“识”
(一)“识”以知好恶
叶燮在论述“才、胆、识、力”中的“识”时一针见血指出:“人惟中藏无识……是非……黑白……不能辨……[2]”他说如果一个创作者心中不具备“识”的素养,那么即使作为创作客体的“理、事、情”就摆在眼前,也是浑然不知所措,是非难晓,黑白难辨。试想,如果是非黑白都不能辨别,又岂能从万千诗作中分拣出大小乘之作呢?故“识”能知是非,能辨黑白,能不人云亦云,能知好恶。严羽在《沧浪诗话》论“夫学诗者以识为主[3]”,他也认为学习诗歌创作之人应该以“识”为前提,方能入正门,立高志。如若不然,则会像叶燮所说是非不分,黑白不辨,误入歧途。既然“识”的地位如此之重要,要如何才能具备“识”的能力呢?叶燮说要“研精推求”,即要苦心钻研精心读书推理方能求得“识”之真谛。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表达了和叶燮一致的观点,即要“熟参”以求“识”,只有在熟读古今之书的基础上,才能做到寓“识”于心。达到起初“不识好恶”,“及其透彻”后“信手拈来,头头是道”[4]的境界。在严羽看来,只有在熟参古今之书,穷尽书中之理后,方能达到“至”的境界。并由最开始的不识好恶到信手拈来,头头是道的质的转变。西汉辞赋大家扬雄也说过“能读千赋则善赋”;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中论“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务先博观。[5]”扬雄以善赋著称,但是他除了对赋的爱好和自身禀赋以外,在他所创作的赋作名声大振以前,他是日夜以书为枕,不曾停歇片刻。而刘勰在《知音》篇中所述在操演了一千首曲子之后就会懂得音乐的奥秘,观赏了一千把剑之后就能识得兵器(的好坏)。推而论之,要想精于一物,必先对此物有不下千百遍的了解,那么一个创作者要想精通于创作,最先之要义必定是熟览博观,这是一切创作的前提。综上可见,叶燮认为“识”乃创作主体之第一素养是有其深刻根源的。
(二)“识”以定取舍
《原诗》载:“惟有识,則是非明……則取舍定[6]”。叶燮认为,有了“识”,就可以明辨是非,能明辨是非,就可以决定取舍。前文已述,“识”为知是非之前提,知是非乃知好恶,能知好恶便能定取舍。环环相扣,不得虚假。如不“识”,则易落人云亦云之窠臼,徒有附会他人,无己之明见。即使是到了创作的地步,也是野狐外道之辈,无有别见。严羽《沧浪诗话》载“看诗须着金刚眼睛……辨家数如辨苍白,方可言诗。[7]”他说看诗必须用最敏锐的金刚眼睛去看,才能不被旁门小法所迷惑,能像分辨浅青白色一样分辨各家流派风格的时候,才能言诗。严羽自述“我評之非僭,辩之非妄……见诗之不广,参诗之不熟[8]”。他说自己评点汉魏胜唐、大历以还、晚唐以及苏黄诗等不是僭越之为,也不是妄加评论。他认为天下即使是有可被废弃的人也没有能被废弃的言论,论诗的道理也是如此,如果认为他所论述的不对,那么就是见诗太少,读诗不熟所致。严羽以身试法论述“熟参”的作用,“熟参”带来的结果就是“识”,他认为自己不具备天才的能力,但是在熟读熟参而后能“识”的情况下方能谈论创作诗歌之道。这从侧面也说明熟读熟参是能够得以“识”的前提,“识”也是得以“言诗”的前提。严羽之所以能对各家诗作鞭辟入里的精准论述,是因为他饱参诗书得以“识”的结果。按照严羽的论述,可以推到出这样的模式:熟读熟参→方可识→方可言诗→方可定取舍。叶燮之所以也能对各家诗文流派作精妙的论述,殊不知也是熟参之后方可“识”的结果。故可“识”便可知好恶,知好恶便可定取舍。
二、创作主体素养之“胆”
(一)“胆”由“识”生
“识明则胆张……无所于怯……[9]”叶燮在论创作主体之“胆”时开篇明义,有“识”才能使“胆”张,任由创作主体随意发挥而没有什么可以畏怯,不论横说或是竖言,左右皆宜。就好像有神力在手,没有什么“理、事、情”是拿捏不定的,或者说无论世间何等物象都可以被有“胆”的创作者拿来做艺术的雕刻。他又说“胸中无识之人,即終日勤于学……亦无益[10]”。心中没有“识”的人,就算是天天勤学苦读,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只会变成“两脚书橱”,终成负累。到真正要下笔时,心中纷繁杂乱,没有头绪,无法摈弃无用之材,取有用之材为己用。愈无法抉择之时,心中愈生怯懦之感,想说不能说,能说又不敢说,说多怕画蛇添足,说少怕篇幅不够,畏首畏尾,终难成气候。归根究底,还是因为心中无“识”。可见,像李白杜甫等辈之诗作能名流千古,皆是因心中有“识”,而后生“胆”,笔墨间方显别致之处。
(二)有“胆”则笔墨自由
叶燮《原诗》载“因无识,故无胆,使笔墨不能自由……[11]”。因为没有“识”,所以没有“胆”,无“胆”则笔墨就不能自由。创作出来的作品也就没有新意,没有内涵。可见“胆”能使笔墨自由,并创造出具有新意有内涵的文章诗歌。叶燮借昔日的圣贤说成事在胆,文章乃成千古事,如果没有胆的话,又怎能千古流传,万代传诵呢?宋代诗论家严羽在《答吴景仙书》中说说自己的诗辩是“断千百年之公案……是自家实证实悟者,是自家闭门鉴破此片田地……非傍人篱壁,拾人涕唾得来[12]”。按严羽所论,他自己的诗辩是断了千百年来未曾破获的一场公案,尤其是中间论述江西诗派的诗病部分,犹如是刽子手直取心肝,而“以禅论诗”等都是自己实证实悟所得,是自己闭关苦鉴开辟的这片荒原,既不是依傍别人所得,也不是依附别家所言。严羽之所以能敢如此说,是因为他有“胆”,若无“胆”,他岂敢读奏一家之言。他的“胆”是他熟参历朝历代诗文之后“识”的体现,也是他自信的折射。所以他的《沧浪诗话》终成千古文,是他以“识”为基础,大胆抒发他的所证所悟的结果。同样是文论大家的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篇中说“趋时必果,乘新无怯[13]”。他认为今古之人各有千秋,不可一概而论,古人有胜今人者,今人亦有胜古人者。要因时而变,趋时就要“果断”,想创新就不要害怕,只管大胆去尝试,这是一种通汇古今的“胆”,是一种敢于汇通古今的勇气之“胆”。如若一味效法古制,无敢出新之“胆”,即使有“识”在胸,笔墨不自由,依然会落入文无新意,章无内涵之境地。
三、创作主体素养之“才”
(一)“才”由“胆”生
“才”字意义众多,大多数对“才”的论述都是着意于人的先天禀赋,如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开篇便提到“才有庸俊”,是说诗人之先天之“才”有好友坏,是指人的才气、才华有深浅之别。张戒《岁寒堂诗话》:“人才气格,自有高下……强学不能。[14]”张戒诗话中的“才”也是指人的先天之才,他說人之才气,本来就有强弱之分,高下之别,这是先天具备的,即使想强学才气也是不能做到的。在叶燮《原诗》中显然也是指创作者的“才气、才华”,只不过叶燮认为的“才”有先后天之分。“胆能生才……才受于天……必待扩充于胆”[15]。叶燮认为人之“才”有先天之才也有后天之才,“胆”能激发出人的先天之才,后天经由书本习得的“才”也需要有足够的“胆”来扩展。像上文所述刘勰的观点一样,作为一个创作者必须不拘泥于仿古,而是要有勇于突破传统的勇气和胆量。这样才能将附着于身上的才气才华外化成文章诗歌。故曰“惟胆能生才”。那么什么是叶燮认为的具体的“才”呢?《原诗》曰:“人之所不能知,而惟我有才能知……人之所不能言,而惟我有才能言之……凡六合以內外,皆不得而囿之……是之谓有才。[16]” 什么是才,晓别人不能晓为才,言他人不能言为才,即使是内心深思氤氲磅礴,上下千年纵横,凡是宇宙之内外,没有可以对其思想产生桎梏的。能以“理、事、情”为材料措而为文为才。这样创作出来的文章至理皆存,万事皆准,深情皆得以拖。叶燮在论“才、胆、识、力”之前先对创作客体“理、事、情”做了详尽细致的论述,综合来看,叶燮眼中的“才”是以能驾驭创作客体“理、事、情”的识别之才,能将“理、事、情”用匠心外化成文章的才,是勇于突破束缚的胆量之才。由此为文才可存至理、准万事、拖深情。
(二)无“才”则“心思”不出
《原诗》内篇下开篇曰:“人无才,则心思不出……[17]”根据上文所述,叶燮认为的人之“才”既包括人的先天之才,也包括后天习得之才,“人无才”就是说一个创作者不具备创作的才能。“心思”即心中对“理、事、情”的所思所想所感,“心思不出”是说一个人心中的所思所想不能以最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所以,归根结底,若想“心思出”,则必先有“才”,“才”的重要性愈发不言而喻。叶燮在强调“才”的重要意义的同时也提出反对“因袭”“模拟”为“才”的做法。他称这些只会附会别人的人为庸人万众,以仿效他人得来之“才”不是己之“才”,仿照他人而出心思不是己之心思。不仅不能对著文起到积极作用,反会葬送才华,使得心思不灵。故此,叶燮提出改变“无才”的方法就是“先研精推求乎其识”,前文论“识”乃“才”“胆”“力”之根基,博览得以“识”,能“识”则“才”渐出。《文学雕龙·神思》篇中论:“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18]”。就是强调“积学”的作用,后天的努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先天不足。
四、创作主体素养之“力”
(一)何为“力”
“力”在中国古代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论语·学而》载:“子曰:‘弟子,入则孝顺……行有余力……’[19]”孔子说,作为弟子,进到家门就要孝顺父母,走出家门要友爱兄弟姐妹,谨慎而言出有信。对大众怀慈爱之心,行仁义之事。在此之外,如果还有余力的话,就要学习文化知识。显然,这里所说的“力”是指剩余的精力。后“力”慢慢外化到文学范畴,延伸为格力、学力、才力、笔力、气力等概念。如严羽《沧浪诗话·诗辩》中“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20]”,此中“学力”即是属于文学范畴。钟嵘概括诗之美“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21]”。其中“风力”便是指创作者对情感的表达生动有力,鲜明利索。
叶燮在《原诗》中所述之“力”也是与诗歌中的诗性相结合而成的一个诗学概念。这里的“力”是一种鉴别“理、事、情”的独特眼力,是能对“理、事、情”运筹帷幄的文学创作力,是别具匠心的创新力,也是敢于发言为诗的自信力。叶燮所论之“力”不是单纯的某一种“力”,而是能“自成一家”之“力”。他以两人同行于一条布满荆棘的羊肠小路为例,弱者于是裹足不前,或是步步有依傍,或是凭借他人推之免之。而有“力”者,则气定神稳,勇往直前,无所畏惧,不但自己过了险境,“反趋弱者扶掖之前”。所以推而论之,立言之人须有“力”,有“力”方可自成一家,不落窠臼,不傍他人。
(二)大“力”与小“力”
叶燮论:“力有大小,家有巨细……[22]”叶燮认为,“力”有大有小,家有大家有小家。他认为古之才人,其力可以大过一个小乡镇,那么他就是一乡之才;其力能在一国之上,那么他就是一国之才;如其力在天下人之上,那就是天下之才。他列举了很多例子,比如有的诗文一出则名气大振,被时人传诵研读,但是在创作者死后,其名声渐渐湮没,诗作也无复再闻。而有的如韩愈之辈在当时不被时人看重,及其没后几世被有识之人识得并大加盛赞,又重新被重视起来,有的一直到今日依然被奉若珍宝。这都是创作之“力”使然。他还认为从古至今,除诗三百以外,“力”与天地同者惟有杜甫。要想成“一家之言”,必当“奋其力”。可见,“力”的大小关系到一个创作者及其作品能否万古流传,其重要性也是可见一斑的。
能将“力”外化到作品上的创作者,必定是含“才”“胆”“识”四者兼具。且四者之间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缺一不可。《原诗》载:“才、胆、识、力,四者交相為济……四者无缓急,而要在先之以识。[23]”叶燮总结说创作主体的“才、胆、识、力”四个素养是相互交融的,缺了其中一项,便不可入作者之坛。四者之间没有熟轻熟重,熟缓熟急,但是最先之要义还是在“识”。无“识”而有“胆”,则是妄为鲁莽;无“识”而有才,则会是非不分,黑白不辨;无“识”而有“力”,则会误人惑世。只有先具备“识”之能力,才能知道何所从,何所奋,何所决,与“才”“胆”“力”合而为创作之自信耳。“识”之后乃为“胆”,“胆”之后乃为“才”,“才”之后乃为“力”。本文未按叶燮“才、胆、识、力”之顺序展开论述,而是熟参文本之后,得出“学生识”—— “识生胆”—— “胆生才”——“才得力托”的关系,故本文以“识”“胆”“才”“力”之顺序行文,以便更好地明确各个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
参考文献:
[1][2][6][9][10][11][15][16][17][22][23]叶燮著,霍松林校注.原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3-28.
[3][4][7][8][12][20]何文焕.历代诗话(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1:686-695.
[5][13][18]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714+521+493.
[14]黄霖,蒋凡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宋金元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114.
[19]杨伯俊.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24.
[21]王运熙,顾易.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上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66.
作者简介:
谭丽琼,女,土家族,湖北恩施人,在读文艺学硕士,单位:湖北民族大学,研究方向:文学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