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威农少女》和波德莱尔
许志强
一
约翰·理查德森的《毕加索传:1907-1916(卷二)》,讲述毕加索的玫瑰红时期;大事件是一九○七年创作的《亚威农少女》,它引发了立体主义的诞生,意义不可谓不重大。此书第一章“‘现代生活的画家”,考证《亚威农少女》的创作渊源,为这幅不寻常的画作寻找解读的路径。
這幅描绘五个妓女的大画,创作时间长达半年;其草稿及相关习作就有四五百件,可以单独办一个展了。学者和收藏家对那些草稿看法不一,甚至关注习作甚于定稿,众说纷纭无非是在暗示,《亚威农少女》的风格分析和主题阐释应该有一个合理的结论。画家本人的做法似乎在助长这种暗示,先是将那些素描秘而不发,后又陆续提供给研究者。约翰·理查德森从隔了半个世纪才提供的一张素描中找到了解读这幅画的钥匙。

毕加索《亚威农少女》

《亚威农少女》草稿之一
此乃一九○七年春创作的一幅纸本炭笔画(65cm×48cm),两面都有和《亚威农少女》相关的构图,题为“布洛涅森林习作”。毕加索说,纸背面才是重点(背面画的是他的女友费尔南多·奥利维耶)。毕加索的话成了解读的关键线索。这幅画和《亚威农少女》的联系是什么呢?据画家自述,《亚威农少女》画不下去了,他便转向另一个构思,画关于布洛涅森林的一幅大画:费尔南多在林中漫步,背景是一匹马和一辆马车。但画家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替代方案,重新回到《亚威农少女》的艰难创作中。
难怪有人提出质疑:这叫什么联系呢?感觉是没有说清楚问题。有关该画的主题,比较著名的是“性创伤”的说法,也有人认为表达的是爱神、死神以及对性病的恐惧。尽管性欲的描绘让人一望即知,具体解释起来却也难有定论。约翰·理查德森未在这方面增添阐释,却根据“布洛涅森林习作”的线索,得出一个新的结论。他说,亚威农妓院和布洛涅森林的马车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主题联系,这个联系的名字叫作“贡斯当丹·居伊”。
贡斯当丹·居伊是波德莱尔的名著《现代生活的画家》的主角,巴黎的插画家和风俗画家,波德莱尔十分敬慕这位低调的“怪才”。在为居伊而写的《现代生活的画家》一书中,波德莱尔提出了现代美学的纲领性论述,这篇长文以其预见性的观点而著称于世,成了现代艺术观念的奠基之作。有人说,不写马奈而写居伊,实属取舍不当。笔者也这么认为。但有一点必须看到,波德莱尔是在和居伊的接触中明确这些观念并加以表述的。尽管人们引用此书更多是出于对纲领而非对居伊创作的重视,但是把布洛涅森林的车马冶游视为重要的现代题材,显然是居伊的观念。居伊擅长的巴黎风俗画有两类,一是妓院,一是布洛涅森林的马车。约翰·理查德森察觉到,毕加索在同一时期既画妓院又画布洛涅森林马车,一定是受到了居伊画风的影响,确切地说是受到了波德莱尔文章的影响。
约翰·理查德森说:“在这篇文章中,诗人向艺术家提出了两个典型的‘现代主题:妓院和森林中行进的马车队伍。毕加索有意描绘这两个题材这一事实与其说他认为自己是像居伊那样的画家,不如说是像波德莱尔所说的‘现代生活的画家。”
是否有证据可以说明当时毕加索读到了波德莱尔的文章?好像没有。画家给予此文极高的评价,这是后话了。不过,据约翰·理查德森考证,毕加索当时熟知古斯塔夫·吉弗鲁瓦(Gustave Geffroy)评论居伊的著作,其中大段引用了波德莱尔的文章以及埃德蒙·德·龚古尔的小说对下层妓院的描写,毕加索受此启发画了一幅戴礼帽的男士骑马的素描,并且开玩笑地签上“贡斯当丹·居伊”(Guys拼写成Guis)的大名。这就足以构成相关联系的证明了。
约翰·理查德森认为,重点是“现代生活的画家”这个观念;毕加索在波德莱尔的文章中找到的身份认同—成为一名“现代生活的画家”—乃是附着于《亚威农少女》的一个意义。这个意义自然不一般。尽管身份认同不会是始于这一幅画,但它无疑是有代表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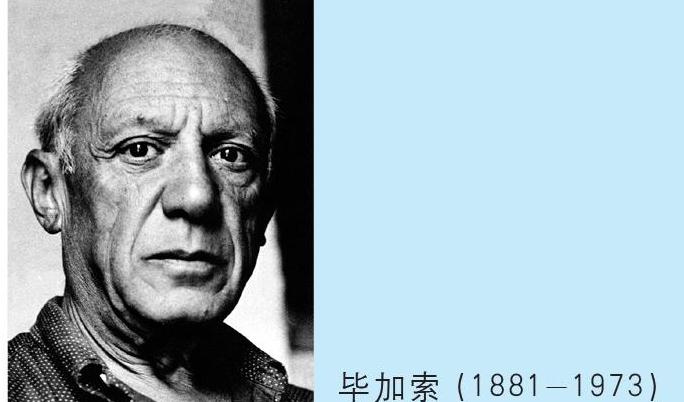
可以说,在已出版的三卷中译本《毕加索传》中,第二卷第一章是最重要的,它用波德莱尔的概念进行纲领性的阐述,而通行的说法尚未能将波德莱尔和毕加索如此这般联系起来。单凭这一点就能说明约翰·理查德森的眼光之毒辣,从有限的端倪(或是刻意隐藏的线索)中窥见深刻的议题;他的论述使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看问题。
二
与《亚威农少女》同类题材的大画,如《闺房》(1905)等,也画五个或站或蹲的裸体妓女,但画风不一样,线条柔美得像夏凡纳笔下的人体。这说明画家还处在犹豫不定的试验阶段。如果说观念决定表现形式,这倒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约翰·理查德森引用波德莱尔的文章,说明毕加索如何接受诗人的教导—“纯艺术,尤其适合于邪恶的美,可怕的美”。引文如下:
(妓女)是野蛮在文明中的完美图像,她有一种来自邪恶的美……我们不要忘记,除了自然美甚至人工美之外,所有人都带着他们的职业印记,一种可以表现为身体的丑,也可以表现为一种职业的美的……特征在这些(女)人中,有一些明显表现出无辜而畸形的愚蠢,在她们大胆抬起的脸和眼睛中,显然又带着生存的乐趣(确实,人们会问为什么)。有时候,她们毫不费力就摆出了大胆而高贵的姿势,只要今天的雕塑家有勇气和才智在各处哪怕在泥泞中捕捉高贵的姿势,那么即使是最挑剔的雕塑家也会喜出望外。在这种烟雾缭绕、金光闪闪、肯定缺乏贞洁的混乱地方,令人毛骨悚然的美女和活玩偶在骚动,在抽搐,她们孩子般的眼睛中射出阴森可怖的光。

最后一句活脱是《亚威农少女》的写照。前面说过,波德莱尔将妓院和布洛涅森林马车作为现代绘画题材推荐给读者,是源于贡斯当丹·居伊的观念。不过,居伊笔下的妓女似乎缺乏波德莱尔的直觉和文字的力度;她们是展现风俗画之群像的“美”女系列,相似的动作和形态流露“活玩偶”的气质。居伊的《在小咖啡馆里》,画了两个穿着制服的干瘪老头紧盯着妓女的胸脯;这些画作表达亵玩的主题是生动的。但和图卢斯-劳特雷克的同类作品相比,技法和表现力似乎要逊色一些。而毕加索的描绘则是一派原始主义的风貌,令人震惊。《亚威农少女》画面右侧的两个马脸裸女,呈现“令人毛骨悚然”的“无辜而畸形的愚蠢”;她们“孩子般的眼睛中射出阴森可怖的光”……毕加索简直是在图解波德莱尔的灵感。
约翰·理查德森在书中谈到,《亚威农少女》的第一张习作画了五个裸女环绕着一个男子(水手),另有一男子(画家本人说是医学院学生)手持书本从左边进入。这两个形象最后被清除了,因为“寓意太过明显”,“他们使人想起毕加索十五岁时,他的父亲强迫他在病床上画的一幅画,用医生和护士作为象征的《科学与仁慈》。毕加索讨厌影射道德的东西,更不用说去讲道德故事了”。

《范妮·泰利埃》(又名《拿曼陀铃的少女》)
也不妨提出别一种解释,即毕加索抹掉两个男子形象主要是从简化图像的角度考虑的,剪除叙事细节的枝蔓,避免让观众陷入风俗性主题的阐释中,从而强化其肖像的野蛮和凝视的力量。图像去除风俗性(及叙事性),呈现观念的集约性,是其创作上的一个特质。因此,说这幅画是在表达画家对梅毒的恐惧,不一定不对,但结论会显得狭窄,未免低估了其形式实验的意涵。
从习作到定稿,这个变化的意图还是明显的,妓院生活的叙事逐渐让位于构成性的一组肖像,呈现所谓立体主义萌芽的形式实验。从一九○七年为水手所画的一张肖像习作也可看到,画家在形成一种革命性的语言,试图从面具的简约性和几何的体量感来描摹人體,甚至还将走得更远,将人体分解为许多个拼贴的小方块。毕加索由此进入其一生中最为激动人心的创作阶段。
再来看“布洛涅森林习作”纸背面的那幅速写,约翰·理查德森的解读也并非不可商榷。画上的圆锥体和倒三角形的身躯,简化了的面具状的大眼和口鼻,和《亚威农少女》的图像联系应该说是一目了然的,尤其是《亚威农少女》左边的三个裸女,和速写里的女子(费尔南多·奥利维耶)神韵相似。那么,毕加索让人注意这幅速写的意图是什么呢?
可以说是在暗示一种风格上的关联。用几何形线条刻画女子的侧身像,简括而不失妖冶,体现毕加索的新风格的精髓,即后来被命名为立体主义的那种东西。
保罗·瓦莱里在其评述德加的著作中指出,(立体主义)错误地将习作当成作品来展示,这是现代绘画堕落的表现。不过,考虑到《亚威农少女》的草稿及相关习作有四五百件之多,可以断言,这个过程和作一幅学院派大画并无区别。毕加索所谓的“苦思图一笔”,在其绘画语言进入革命性阶段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其实并不像瓦莱里所认为的那样,屈从于那种卑俗的不严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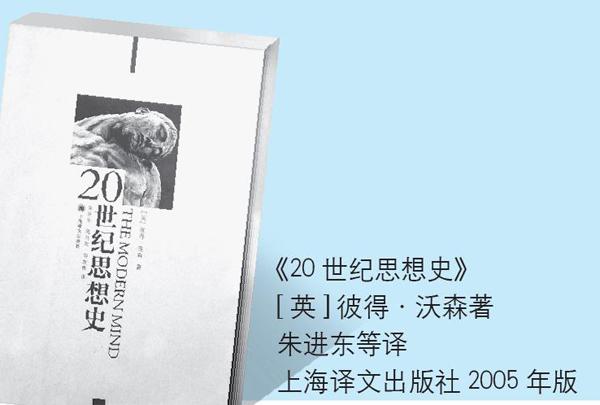
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对几何形状的强调,脱胎于塞尚的观念;试图在此基础上创造一种新的视觉语言。从《水手》《蹲着的亚威农少女》《费尔南多肖像》等一九○七年的习作也可看出,他在塞尚、高更、原始面具之间寻找自我。严格说来,这不能说是风格,而是一种新的语法和视觉表现;尚未脱离传统造型语言,尚未进入抽象,但在独特的概括中追求体量和质感。毕加索那些大鼻子、大脚丫的稚拙粗壮的裸女,含有几分幽默的实验性质,一望而知是在诠释塞尚的理念,夸张而不失妙趣。名作《范妮·泰利埃》(又名《拿曼陀铃的少女》)有着全新的造型趣味,那种叠纸般似可触摸的三维视觉效果,每一寸处理都是精细巧妙的。这种创作语言固然是导源于塞尚,恐怕塞尚都不会想到这样做。至于后来所谓的分析立体主义、综合立体主义和水晶立体主义等,更不是塞尚能够想象的。
关于塞尚的遗产和启示,毕加索说过不少被人引用的话,其中一个说法尤其耐人寻味。他说:“所有现代绘画都是基于塞尚没有做到的东西,而不是他几乎成功的东西。塞尚一直致力于展示他未能完成的东西,他的追随者也是如此。”
毕加索把后期印象派以降的创作视为塞尚“没有做到的”和“未能完成的”,这就诠释了内在的继承关系,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哈罗德·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或者可以说,他在展示激进的绘画语言时,置入了一个质朴可靠的逻辑:我们全都是塞尚的徒子徒孙。
不难设想,从《亚威农少女》到综合立体主义拼贴画,那种“塞尚可能做而未做到”的想法有时会像一束悬浮的神光,照亮孤独而辛勤的画家。
三
约翰·理查德森指出,《亚威农少女》是毕加索最不被认可的作品。毕加索的亲密朋友如阿波利奈尔等,对它避而不谈。马蒂斯对它怒目而视。格特鲁德·斯坦因也不喜欢它。当时几乎没有人接受这幅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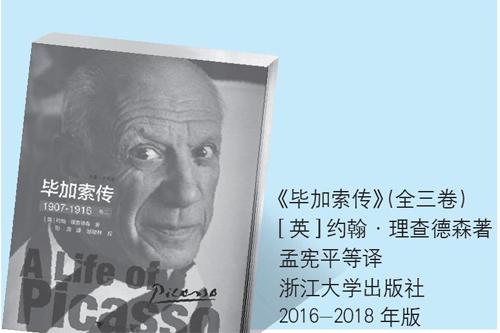
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恐怕至今它都是难以理解和接受的,尽管从美术史的角度来看,二十世纪的实验性绘画都是从这幅画的创作中获得许可的。其刺激性和挑衅性,也不能光用塞尚的体系去解释。约翰·理查德森引入波德莱尔,用后者的观念来加以定位,即关于艺术的“可怕的美”的命题,便是出于这个缘由。《现代生活的画家》第十二章“女人和姑娘”,大半是在谈窑子里的女人,而毕加索的那幅画的原题是“亚威农窑子”。两者的联系不仅在于题材,还在于表现对象的低俗和丑怪。
低俗的题材未必就等同于“可怕的美”,但是,对世纪之交的大众审美或学院派趣味而言,偏离古典式的“理想美的概念”也就几乎与“可怕的美”无异了。
波德莱尔赋予低俗题材以纯艺术的价值,为“可怕的美”正名,仿佛是在打响艺术革命的第一枪。“女人和姑娘”是写给画家、雕塑家的一份指南。
用波德莱尔的文章来进行观察,恐怕不仅对解读毕加索的画作会有助益,对画家的精神和教育的背景也会增加理解。
波德莱尔阐释了现代画家的身份及定义;对世纪之交成长起来、出生在文化保守地区的画家而言,这种阐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毕加索自小是以宗教画家的身份得到培养的。他是世纪末文化转型的产物,是跨文化的波西米亚艺术家。彼得·沃森的《20世纪思想史》中讲到毕加索,强调其街头无赖的成长背景。这种论调在阿莲娜·哈芬顿的《毕加索传:创造者与毁灭者》中也出现过,例如,“他不读书,只是从朋友那里囫囵吞枣地接受了一切”,云云,似乎过于关注画家的野性,未能重视其文化理解力及精神追求的轨迹。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画家在法语还欠流利时不怎么读书,但即便如此,兰波和魏尔伦的诗歌、高更的手记、雅里和阿波利奈尔的手稿等,他是熟读并写下评注的。布拉塞依在其《毕加索访谈录》中指出:画家不仅博览群书,而且有学究式的身体力行。约翰·理查德森的传记也写到,青年毕加索如何以其工作细节吻合了高更的手记《努阿努阿》而为荣为乐。这样的毕加索我们谈论得相对少了些。
波德莱尔告诫道,艺术家应该成为“宇宙的精神公民”。他在《现代生活的画家》第三章区分了“艺术家”和“社交界人物”;前者是“像农奴依附土地一样依附他的调色板的人”,无非是一些“机灵的粗汉,纯粹的力工,乡下的聪明人,小村庄里的学者”,后者则是怀有深刻的“好奇心”的人,他們就像“康复期的病人”并且始终是处于康复期;因为,“正在康复的病人像儿童一样,在最高的程度上享有那种对一切事物—哪怕是看起来最平淡无奇的事物—都怀有浓厚兴趣的能力”。这样的区分是十分必要的。且不说毕加索是如何突破其成长背景的局限,避免成为波德莱尔讥讽的“艺术家”,单从其跨国生活的辙迹也可看到,侨居巴黎的一个意义就是要成为“社交界人物”,而非随处可见的那种风景画家。
关于“社交界人物”,波德莱尔又用“浪荡子”一词定义。这是书中难以摘引的华美篇章(当然,其他部分也都华美),洋洋洒洒好几页。简单地说,浪荡子就是“十足的漫游者”和“热情的观察者”;“欣赏都市生活永恒的美和惊人的和谐,这种和谐被神奇地保持在人类自由的喧嚣之中”。浪荡子“寻找我们可以称为现代性的那种东西”,“从流行的东西中提取出它可能包含着的在历史中富于诗意的东西,从过渡中抽出永恒”。波德莱尔在书中阐述的两大主题,“新的美学”和“现代性的观念”,在此融合为“现代的美学”概念。所谓“现代的美学”,首先是指能够直面现代性的那种观察和表现的创作原则。“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这是他提出的著名的定义。
波德莱尔赋予现代性以美学表现的合法性,但也指出现代性自身的非本质属性。和后来的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相比,他的观点不算激进;虽然预见了现代美学的反传统性质,但并未主张割裂自然,而是保留了一种二元性或两重性的观念,要求艺术家进行提炼,从时尚和转瞬即逝的事物中提取永恒;一种柏拉图或基督教的观念论的遗存。这是我们在解读此书时特别需要注意的。
波德莱尔的对立面是学院派美术,尤其是学院派肖像画的服饰描绘的保守趣味。他说,“宣称一个时代的服饰中一切都是绝对地丑,要比用心提炼它可能包含着的神秘的美(无论多么少,多么微不足道)方便得多”。他认为学院派在这方面陷入了古典崇拜;“因为陷得太深,他就忘了现时,放弃了时势所提供的价值和特权,因为几乎我们全部的独创性都来自时间打在我们感觉上的印记”。现代生活的美学意义于此得到诠释,指出时间这个体验的维度,其延续性的存在就是所谓的历史。毫无疑问,这种解释的意义已不限于绘画了。
必须看到,这本书中表达的历史观(时间观)是建构而非解构的。其“浪荡子”的视角含有一个抒情诗人的限定;也就是说,即便波德莱尔意识到现代性的危机及其历史意涵(如福楼拜的小说所表现的),他也是在“风俗特色”而不是在文化结构的意义上看待都市景观的阴暗面。换言之,他表达的是广博而忧郁的凝视,而不是价值的变易、断裂或破坏。
四
“女人和姑娘”是一篇似乎含有鸦片制剂的芬芳和麻醉的奇文,堪为《恶之花》的注脚,渗透《恶之花》的趣味。在诗人的笔下,沙龙和窑子有时混为一谈,幻象和商品闪耀魔幻的色彩,淫荡和忧郁具有咒语般的力量。可以说,波德莱尔的诗歌中设置的几个主题,在波德莱尔的画评中一样可以找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在世纪末思潮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病态的美”“可怕的美”的主题。
但波德莱尔本人并不认同“病态”“可怕”这些字眼。他承认他所描绘的东西不能讨好读者,却“找不到什么可以激起病态的想象力的东西”;他阐述的无非是人性的“不可避免的罪孽”,诸如懒散、孤独、淫逸、郁闷、乖戾,等等。然而,这里面却存在着丰富的形象。对观察者(诗人、画家)来说,堕落的形象照样能够产生无尽的思想,尽管“这些思想一般地说是严峻的、阴郁的”,“包含着比滑稽更多的忧郁”,却具有“道德的丰富性”;在“纯粹的艺术”中,这些形象同样是“珍贵并且神圣化的”。这便是波德莱尔解释的“恶的特殊美”或“丑恶中的美”的含义。
毋庸讳言,我们对波德莱尔的说法容易产生误解或歪曲。尤其是对其“现代性”定义的引用,只取“流行”和“过渡”这一半,把另一半(永恒)弃之不顾。对“恶的特殊美”或“丑恶中的美”也是如此,夸大其病态、魔性,忽略了诗人的视角和观察的丰富性。其实,就诗人对窑姐的描绘而言,它们既无龚古尔兄弟的自然主义细节的触目惊心,其美学立场也未逾越雨果的《〈克伦威尔〉序言》的范畴。所谓“恶的特殊美”,乃是相对于古典的“普遍美”的一种存在,与“应时的美”和“风俗特色”并列,从观念上讲,有的是浪漫派的活力和趣味,并无偶像破坏运动的颠覆性或革命性。
波德莱尔强调纯艺术的道德活力,其关注丑怪的忧郁感是其美学光谱上深沉的折射。他效法爱伦·坡,对光谱上偏暗的部分采取一种神秘而伤感、精练而恣纵的态度。他连司汤达都无法接受,嫌其对美的定义缺少“贵族性”。这样的波德莱尔,给自己留下足够多的迂回、考究和审计,给他的追随者却带去反叛和颠覆的动力,似乎现代艺术的激进和孟浪行为都可以在他这里找到源头。说起来还真是有趣。
观念的误读性的影响或夸大的暗示,难道不是一个更值得研究的议题吗?是否可以归结说,较之于精确的吻合和全方位的忠实,那种断章取义式的引用,局部的理解,总是显得更为活跃、更富于生产性?事实好像正是如此,即便是颠扑不破的佳作也往往总是以片段的句子和细节存活,发挥其不可预料的影响力。
前面转引的段落,即关于“(妓女)是野蛮在文明中的完美图像……”那一段,对照原文不难发现,引文是做了省略和压缩的处理,为了凸显“纯艺术适合邪恶的美、可怕的美”的论点。引文的压缩虽然必要,但难免会导致观点的简化,偏离原作的氛围,尤其是波德莱尔十分重视的思想的韵律感,那种拉布吕耶尔式的道德透视,聚焦于“集团和种族的差异”,绘制出一幅光色陆离的群芳谱,这些岂能以“可怕的美”笼而统之?
将《亚威农少女》和波德莱尔等而观之,也就模糊了两者的区分,忽视了浪漫派所提倡的“现代性”美学观与现代派的偶像破坏运动之间的根本差异。谈论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概念、波德莱尔对毕加索的影响时,恐怕不能忽视这种差异。
《毕加索传》卷二中讲到这样一个细节:一九一二年六月,毕加索在图卢兹的奥古斯丁博物馆再次观赏了安格尔的名作《你将会变成真正的玛克鲁斯》,留下一句“非常令人困惑”的评论:“安格尔,不是个十分诚实的艺术家。”毕加索的密友、诗人马克斯·雅各布当时在场,对这句话表示困惑的就是他。约翰·理查德森对此评述道:
马克斯要么是听错了,要么是误解了,要么就是没有领会这个反讽性玩笑的要点。由于这次旅行具有朝拜安格尔的性质(他们第二天在蒙托邦参观安格尔博物馆),又由于安格尔影响的痕迹不久就出现在毕加索的作品中,所以对这位启发毕加索下一轮风格转变的大师的诋毁不能当真。如果说毕加索的表现手法(facture)变得更加整洁,他的人体绘画变得更加柔软,他对细节的组织变得更加精确清晰,那都要大大地感谢“Ingres, artiste peu consciencieux”(安格尔这个不太诚实的艺术家)。
约翰·理查德森的意思是毕加索不大可能这么说,就算转述者没有听错,至少也是未能領会“反讽性玩笑的要点”,总之,此类“诋毁”不能当真。
如果我们引用波德莱尔的《现代生活的画家》中的观点,用来说明雅各布的转述无误,是否能够说得通呢?波德莱尔碰巧在此书第四章“现代性”中评论安格尔,他说:“安格尔先生的大缺点是想把一种多少是全面的、取诸古典观念的宝库之中的美化强加给落到他眼下的每一个人。”
如前所述,波德莱尔反对的是学院派那种“理想的美的概念”。他对安格尔的“诋毁”,无非是对学院派孜孜以求的古典观念的完型之美表示不满。在波德莱尔的观念体系中,评价一个艺术家“诚实”与否,并不在于通常所谓的人格和道德,而在于他(她)是否直面现代生活的“应时之美”。毫无疑问,当毕加索说“安格尔不是个十分诚实的艺术家”时,他是在波德莱尔的意义上说的。这么说和他对安格尔技艺的叹赏应该是不矛盾的吧。
二○二○年七月,杭州城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