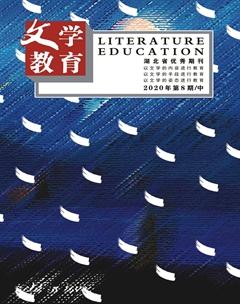基于视域融合理论解读《爸爸的花儿落了》
内容摘要:《爸爸的花儿落了》是小说《城南旧事》的最后一部分,林海音以“英子”的视角讲述了7岁至13岁在北京的童年生活。论文基于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从成人视域与儿童视域、历史时间与现实时间、成长主题与死亡主题这三方面的融合对《爸爸的花儿落了》一文进行多向度地解读,通过三者的交织、碰撞,不断同作者进行对话,生成新的理解,丰富文本的内涵。
关键词:视域融合 成人与儿童 历史与现实 成长与死亡
《爸爸的花儿落了》是小说《城南旧事》的最后一部分,林海音以“英子”的视角讲述了7岁至13岁在北京的童年生活。对于小说前面的四个故事,作者采用了旁观者、外围人的视域进行记述。在《爸爸的花儿落了》一文中,“英子”真正以亲历者的身份进入故事的讲述,通过对父亲的怀念创设成长主题的情景,在叙写当下的同时穿插了历史的回忆:六年里,爸爸一次又一次地逼着“我”闯练,一次又一次地要“我”长大,而“我”也终于不负爸爸的期望,成为了每天早晨等待校工打开校门的学生之一,也能够独自一人去银行寄钱了。六年前,爸爸要“我”好好用功;六年后,“我”真的被選做这件事——代表全体同学领毕业证和致谢词。爸爸的花儿落了,却结出了硕大的果子,“我”实现了成长的蜕变,是一个大人了。[1]
林海音立足于成人视域,借助儿童“英子”的视角发声,将现实的情境与过去的回忆相交织,死亡的沉重与成长的希冀相调和,使文章的内涵与主题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维度。这样一来,读者从自身视域出发,与文本视域叠印、融合,就可以生成多向度的认识。这与伽达默尔提倡的解释者与被解释者之间经由汇合与对话,促使不同视域碰撞、融合,从而产生新的火花和新的理解有共通之处。
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以“前见”为理解的基本前提,强调视域是人的认识和理解能力,通过理解者与文本的对话,超越自身有限的视域,不断扩大本意的外延,达到一种更高层次的、全新的境界,由此生成多重理解。[2]为了能够从不同角度对文章进行多元化的阐释,我将运用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从三个方面对该文进行解读。
一.视域:成人与儿童的融合
《城南旧事》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于1960年出版,林海音写这部小说时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爸爸的花儿落了》原题为“爸爸的花儿落了,我已不再是小孩子”,这里以“英子”面目出现的叙述者,已经不是孩提时代的“英子”了,而是作为一个成年人的林海音,她对爸爸所有的讲述都是在已知结局的前提下展开的。文本所发生的时间也就是故事时间在童年时代,“英子”作为儿童以孩子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通过孩子的感官感知周遭的环境。她的年龄、成长环境、人生际遇、生活经历决定了她处理问题、解决矛盾与冲突的态度与方式,由此生成儿童视域。作者创作时间即叙事时间在成年后,成年的林海音无法再像儿童时代未知人事的“英子”那样感知世界,儿童的单纯天真因为有既定结局的映照,愈发显得痛彻心扉,这是基于作者成年后的境遇而形成的成人视域。
(一)儿童与成人:统一而完整的连续体
儿童视域主张从儿童的视角表达儿童对世界的独特感受、想法,还原被成人所侵蚀的儿童生活图景。[3]故事中爸爸病倒了,住在医院里不能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我”去看望爸爸的时候,爸爸鼓励“我”“不要怕,无论什么困难的事,只要硬着头皮去做,就闯过去了”。但身为儿童的“我”凭借自己的感知与看法观察、审视和对待外在的人、物、事,故而无法理解爸爸当时的身体状况,甚至对其不能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感到委屈、难过。“我”要爸爸去的理由很充分:让“我”不发慌。所以,对于爸爸还是那句让“我”去闯的话,“我”接下来的应答“那么爸爸不也可以硬着头皮从床上起来到我们学校去吗”把爸爸逼上了死胡同,成年人的爸爸看着儿童的“我”,“摇摇头,不说话了”。在爸爸把脸转向墙那边又重新转回来对着“我”的那一段时间里,“我”没有继续追问,也没有做出什么举动,是“我”不想问了吗?很显然不是,是已经成年的林海音在记叙这件事时,以其成人视域站在处于儿童时代的“我”的角度上,进行儿童自我的内省与观察。
事实上,基于成人视域来理解儿童,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成人,只能观察到儿童外显的行为表现,无法洞悉儿童内心的真实体验,从而导致儿童自我表达的失语和存在地位的缺失。然而儿童时代的“英子”和长大后的林海音本质上是同一个人,“我”的童年和成年是一个连续体的两个方面,而这个连续体是一个历史过程,后面的存在意义来源于前面的存在。[4]童年的“英子”和成年的林海音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存在,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儿童、也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成人。小时候的“我”随着时间的推进,成为了长大后的“我”,“我”的童年生活与成年生活是彼此贯通的,儿童视域由于受到周遭环境、境遇、经历以及时间的影响,与成人视域是相互融合的。所以,在爸爸叮嘱“我”“已经大了,明天要早起,不能迟到,要自己管自己,并且管弟弟和妹妹”时,身为儿童的“我”通过成人视域回答了“是”,即使爸爸的话让彼时年幼的“我”“很不舒服”。其实,细细品来,这里的“很不舒服”绝不仅仅是因为爸爸叮嘱“我”不要迟到而觉得他不了解自己,而是话语里隐含着遗言意味的暗示,让“我”不得不接受“没有爸爸”这一即将到来的残酷事实。[5]
(二)幼稚到成熟:沉重却必经的人生路
面对爸爸让“我”去闯,“我”的回答极富儿童的个性,这样的儿童视域以自我为中心,清除了覆在现实生活表层的谎言与虚伪,呈现了生活的真实面貌,与简单地以成人视角构筑的文学世界有了某种疏离。[6]同样富有儿童特征的言行在文末也有出现,结束毕业典礼后回家的“我”看到石榴树大盆底下有几粒没长成的小石榴,生气地质问妹妹们是谁摘下了爸爸的石榴,并扬言“要告诉爸爸去”。“我”真的会向爸爸告状吗?并不会,那么“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其实,“我”在毕业典礼上的心不在焉,不断出现在脑海中的一系列“闪回”:想起去医院看望爸爸时的情景,思考“爸爸的病几时才能好”“妈妈今早的眼睛为什么红肿着”;多处的自我疑问和自我惊讶:“如果秋天来了,爸爸还要买那么多的菊花,摆满在我们的院子里、廊檐下、客厅的花架上吗?”爸爸如此爱花,对于这个问题,答案是肯定的,“我”又为什么要加“如果”一词呢?作为一个正在参加毕业典礼的孩子,“我”的所思所想所感都与当时的场景无关,这并不是一个孩子应有的正常心态。正常心态应该是:哪怕“我”思绪万千,想到最多的可能是六年里与老师、同学们相处的点点滴滴,内心是紧张、兴奋的。但是,这些都没有。“我为什么总想到这些呢?”因为还是儿童的“我”在担忧、挂念生病的爸爸,希望他快点好起来。
然而,故事中的“我”并不全然处于儿童视域,正如“我”“拿着刚发下来的小学毕业文凭,催着自己,好像怕赶不上什么事似的,为什么呀?”“我”的心里预感到爸爸生命垂危,“我”知道爸爸即将不久于人世,“我”害怕赶不上见爸爸最后一面。“我”是以一个已经知道故事结局的成年人的身份记叙这一事件,作者的成人视域使孩子的“我”在得知爸爸“死讯”时早有准备。故,“我”能在之后,以从来没有过的镇定与安静,面对老高欲言又止的话语。儿童的“我”会疑惑老高“为什么不说下去了”,表现出“着急”。实际上,“我”的“大声喊”掩盖了“我”的知情,这是一种孩童式的逃避,但成人视域下的作者不允许自己幼稚、怯懦。因此,年幼的“我”迅速听懂了老高委婉的话语以及那些未尽之意,镇定、安静地面对已发生的一切。这表明“我”完成了长大的蜕变,真正成为了一个大人。
林海音打通了阻隔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壁垒,将二者联系起来,通过融合儿童视域与成人视域,形成儿童视角与成人视角相互交织、斗争的全景视域,直观地再现了儿童的“我”作为“儿童——成人”成长连续體的生活图景。这种复合型视角将原先处于二元对立的儿童视角与成人视角变成了“以儿童视角为旨归的成人视角”和“成人视角支撑下的儿童视角”,使儿童的“我”和成年的林海音获得了对生命和生活的共同理解。[7]
二.时间:历史与现实的融合
《爸爸的花儿落了》是一篇叙事文,主要写了“小时挨打”“逼我汇款”和“毕业典礼”三件事,以“毕业典礼”前后发生的事情为主线,中间回忆、插叙了另外两件事。
小说的情节展开以“我”参加毕业典礼时衣襟上别着的粉红色夹竹桃引出前一天去医院探望爸爸时的情景,通过忆述爸爸鼓励“我”的一番话,特别是叮嘱“我”不要迟到,引出六年前因赖床被爸爸惩罚的情形。在“我”陷入回忆时,毕业典礼开始了。这时,“我”又突然想起爸爸的病和他对花的喜爱。与此同时,韩主任上台讲话,我们唱起了骊歌,由此想到了很多人盼着自己长大,进而回忆起爸爸要“我”闯练,让“我”到东交民巷正金银行汇钱给日本的陈叔叔的经过。最后写毕业典礼结束,“我”回到家看见满院散落的花儿,听到老高的话,清醒地意识到爸爸的花儿落了,自己不再是小孩子了。
(一)故事的打破与重组
根据西方叙事理论的研究,叙事作品的时间可以分为两类:故事时间和叙述时间。故事时间是指叙事作品中讲述的故事和事件的先后顺序,叙述时间是指“叙事者讲述这些故事的时间”。两者并不是一致的。“在原初的故事中,时间是按先后顺序发展,而对这些故事的讲述却可以打乱顺序,如倒叙、预叙、插叙之类都是对原来故事的重新排列。”[8]细读全文,不难发现,林海音在创作时运用了插叙的写作手法。
“毕业典礼”是此时此刻此地发生的事情,立足于孩童时代的“我”的现实视域,整个故事的发展脉络应该是:作为毕业生的“我”坐在礼堂的最前面,衣襟上别着爸爸喜欢的夹竹桃。钟声响起的时候,毕业典礼开始了。韩主任上台讲话,接着我们唱起了骊歌,大家都哭了,“我”也哭了。典礼结束后,“我”急匆匆地赶回家,看到散落一地的花儿和在院子里玩耍的弟弟妹妹。听到老高未说完的话语,“我”意识到爸爸的花儿落了,自己也不再是小孩子了。那么学生在阅读时必然会产生疑惑:“我”为什么要把夹竹桃别在衣襟上?爸爸为什么不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我”为什么急着赶回家?老高没说完的话意味着什么?如何理解“爸爸的花儿落了,我已不再是小孩子”?
在叙述中,作者不时中断对“毕业典礼”的记叙,转而进入回忆,将前一天“我”去医院看望爸爸,六年前“我”因为赖床不去上学被爸爸惩罚,爸爸因为爱花被陈伯伯打趣以及爸爸让“我”去银行汇款的事情插入主线中。不难发现,这些都是“我”的记忆中与爸爸相关的事件,属于童年时的“我”的历史视域。这种打破时间桎梏,不按事情发生的先后次序进行叙述,以叙事者的自由联想来架构故事框架的手法,将历史视域与现实视域相互穿插、融合,不仅充实了文本内容,而且使爸爸的形象更加立体、鲜明,饱含了林海音深沉、浓厚的思想情感。
(二)叙说的节制与突显
作者在记叙故事时有其特定的视域,这是由作者自身的历史境遇所赋予的。林海音生于日本,5岁随父母迁往北京,30岁移居台湾,42岁出版了这部小说。5岁到30岁的这段时间里,她一直生活在北京,北京这座古城里保留了其童年生活的记忆与经历,这种对童年时期北京生活的思念促使她创作了《城南旧事》。[1]不管是《惠安馆传奇》的“疯女人”秀贞,《我们去看海》为了供养弟弟读书不得不偷盗财物的“小偷”,还是《驴打滚儿》中失去子女的佣人宋妈,《爸爸的花儿落了》严慈并济地要“我”闯练和热爱学习的爸爸,林海音在讲述这些故事时,有选择性地略去了复杂的社会环境,尽可能地以淳朴、温暖、真挚的笔触,展现人性美的一面。因为,这是她的童年时光,她生活在一个完整的家庭:有舍不得打她的母亲、有可以寻求依偎的父亲、有贴心照顾她的宋妈、有疼爱她的叔叔以及众多陪伴她的弟妹。[9]对于成年后的林海音来说,这无疑是一段在日后回想起来都会感到幸福、快乐和满足的岁月。
另一方面,文本也有自己的历史视域。文本所讲述的故事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条件,是特定历史存在的产物。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北平,那是一个政局动荡、战乱频发的年代。文中爸爸之所以生病住院,是因为“叔叔给日本人害死,急得吐血”,导致肺病复发,病情加重,很快便离开人世。作者只字未提北平当时的社会背景,只用这短短的一句话简单带过本应强烈的“国仇家恨”。一夕之间,“英子”失去了叔叔,失去了爸爸,也失去了一个完整的家。纯真的童年时光就此终结,因为战争造成的精神断乳,使“英子”不得不长大成人,学着承担责任。12岁的她跟着年轻的寡母,照顾年幼的弟妹,在远离故乡的北京度过艰难的岁月。
林海音写《爸爸的花儿落了》时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而故事中的“我”在那时还是一个孩子,同一个主体在情感、观念、想法等方面因为所处的时间、环境,所经历的境况、际遇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差异。从童年到创作再到出版,中间隔了37年的时间。从北京到台湾,中间隔了一湾海峡的距离。这一巨大的时空跨度将文本的历史视域与作者的现实视域囊括在同一个维度下,历史与现实的碰撞、交融使得本意从先前的限制中解放出来,文本意义的外延得到了扩大,从而超越先前的含义,获得多重理解。[10]
三.主题:成长与死亡的融合
小说有两条线索,与毕业典礼并行的另一线索是爸爸爱花。与“花”有关的字句在文中反复出现,并不是一种偶然。事实上,文章题目“爸爸的花儿落了”语带双关,一是实指爸爸种的夹竹桃的垂落,二是象征爱花的爸爸的辞世。“花”作为一个意象,不仅指爸爸有种花的爱好,更是指爸爸的“生命之花”和“我”的“成长之花”。[11]
(一)生命之花的垂落与永生
文本中爸爸的一生都与“花”连在一起。小说开头提到“我”的衣襟上别了一朵粉红色的夹竹桃,妈妈告诉“我”夹竹桃是爸爸种的。小说的中间写道:“爸爸是多么喜欢花。……他回家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浇花。那时太阳快要下去了,院子里吹着凉爽的风,爸爸摘下一朵茉莉插到瘦鸡妹妹的头发上。”小说结尾,“我”急匆匆地赶回家,发现院子里的“夹竹桃不知什么时候垂下了好几枝子,散散落落的,很不像样,是因为爸爸今年没有收拾它们──修剪、捆扎和施肥。石榴树大盆底下也有几粒没有长成的小石榴……看那垂落的夹竹桃,我默念着:爸爸的花儿落了。”
文中一再提及的夹竹桃、玉簪花、石榴花、菊花、茉莉、蒲公英等,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万物复苏、花团锦簇的春天。春天代表着希望、生机与活力,一方面象征着生命的无限可能,另一方面又意味着人生的初始阶段。这样一来,“花”就成为了一种时间标志。春生秋杀,四季轮回,人的生命也如这繁花一般。花开花落,必然要经历一个“落花”的时刻。人的生命从新生到死亡,也会面临一个告别的时刻。林海音一边借花的柔美调和爸爸性格中的阳刚,使爸爸的慈爱与严格和谐地发展。同时,“花”作为一种象征,意味着爸爸的生命状态。爸爸身体健康时,花开得繁茂、旺盛;爸爸病危时,花成为对儿女的鼓励、关怀;爸爸辞世时,花儿垂落。爸爸的“生命之花”逐渐凋零,预示着爸爸的生命也慢慢地走向尽头。在整体上,这也回应了《城南旧事》前四个故事的结局:故事的主人公都以不同的方式离“我”远去。
(二)成长之花的绽放与希冀
除了“花”,“大”“长大”“大人”这些词语在文中也出现了很多次。“落花”不仅暗示着爸爸生命的终结,还代表了“我”的童年的终结。小说结尾写道:“爸爸的花儿落了。我已不再是小孩子。”死亡令人感到痛苦,成长也未必指向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因此,在毕业典礼这一富有成人仪式感的场景中,“我”再次体会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做大人,常常有人要我做大人。”尽管我们憧憬“长高了变成大人”,但“我们又是多么怕呢”。所以,“当我们回到小学来的时候,无论长得多么高,多么大,老师!你们要永远拿我当个孩子呀”。儿童对成长的想象总是喜忧参半的,长大意味着承担责任,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都是一种能力的验证,需要具备足够的勇气。虽然对生命来说,死亡是不可重复的。但对童年来说,告别是另一个不同的、全新的开始,值得每个人去尝试。故而,在经过沉重的思考后,“我”完成了自己的蜕变,意识到“这里就数我大了,我是小小的大人”。
生命如花,纵使美丽、多情,也会无奈地凋谢。但爸爸“生命之花”的枯萎却促成了“我”“成长之花”的盛开,爸爸的辞世使“我”明白自己“已不再是小孩子”,需要肩负起照顾弟弟妹妹的担子,独立面对生活中出现的任何变故。这种蜕变是痛苦的,却也是必须的,只有这样“我”才能成长。而爸爸的灵魂会超越时间与空间,在“我”的心灵深处继续散发阵阵幽香,在爱的缅怀中永远绽放,得以永生。
花落,结果。爸爸生命的终结促使“我”提前告别童年,脱离了童真状态,褪去幼稚而走向成熟。正如龚自珍所说“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凋零的“生命之花”化为肥料滋养着“成长之花”的茁壮生长。林海音将成长与死亡相融合,以“落花”的意象冲淡了爸爸的死亡所带来的悲痛感,使作品未被局限于“失去”的主题。这样一来,童年的结束并不需要像《爸爸的花儿落了》那般以某个重大事件为标志,很多时候它可能在我们不曾注意到的某一刻悄然离去,让人在成年后回味不已,由此促成學生解读的多元化。
四.结语
一直以来,我们都习惯从单向的维度解读文本:父亲教会了“我”什么?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学到了什么?“我”从中体会到父亲怎样的感情?“我”有什么思想体会?或者,从文章的体裁分析文本:这篇文章记叙了几件事?作者采用了什么写作手法?作者的思想情感是什么?文章的主旨是什么?这样的解读固然可以理清文章的结构、脉络,了解人物的思想、感情,却无法与那时那地的作者取得联系,生成共鸣,仅仅是基于此时此刻自身的视域,单方面、孤立地理解文本。
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既不是解释者完全放弃自己的视域进入被理解对象的视域,也不是简单地把解释对象纳入解释者的视域,而是解释者不断地从自己原有的视域出发,在同被理解对象的接触中不断地检验我们的成见,不断地扩大自己的视域,从而两个视域相融合形成一个全新的视域,这一过程即‘视域融合。”[12]
《爸爸的花儿落了》一文存在三个方面的融合:童年时代的“我”与成年以后的“我”,故事发生的历史时间与故事讲述的现实时间,成长、未来的主题与生命、死亡的主题。在解读该文本时,我们需要考虑到同一主体在不同生命阶段独特且迥异的体验,重视错位、交叉的时间脉络与节点,将生命的终点也就是死亡同成长的无限可能与未知性,或者说是未来相联系。这样一来,我们才能对文本中人物情感的起落变化,情节安排的目的所在,事物象征的寓意内涵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和认识。成人视域与儿童视域、历史时间与现实时间、成长主题与死亡主题这三者在融合中构成一个无限的统一体,通过三对矛盾体之间的交织、斗争、碰撞、补充,从而不断产生新的理解,丰富文本的内涵。
参考文献
[1]魏冬峰.林海音和《爸爸的花儿落了》[J].语文建设,2004(01):24-26.
[2]王成军.论“视域融合”与历史比较的关联和意义[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4):15-25.
[3]冯加渔,向晶.儿童研究的视域融合[J].全球教育展望,2014,43(07):76-82.
[4][美]杜威.经验与自然[M].傅统先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5]马二兰.《爸爸的花儿落了》微妙情感解读[J].语文知识,2014(08):47-48.
[6]王益民.《爸爸的花儿落了》选点突破例谈[J].语文建设,2009(06):50-52.
[7]赵雪梅.儿童视角与成人视角巧妙融合的典范[N].中国文化报,2009-9-15(5).
[8]张红顺.《背影》“主题”教学的反思与重建——基于叙事学的视角[J].教学与管理,2014(01):47-50.
[9]唐川北.乱世中的英子,永恒的儿童——再读《城南旧事》[J].中国图书评论,2016(06):26-31.
[10]张习文.视域融合理论的多维度分析[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05):127-131.
[11]张百栋.双线并行交相生辉——浅析林海音《爸爸的花儿落了》[J].名作欣赏,1992(05):96-100.
[12]张习文.伽达默尔视域融合理论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2:1.
(作者介绍:陈雨师,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在读,学科教学(语文)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