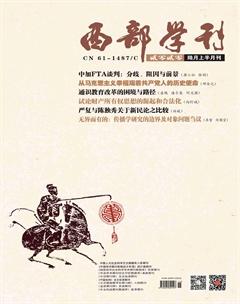无界而有的:传播学研究的边界及对象问题刍议
李智 刘萌雪
摘要:自近代以来,社会科学的发展史既是学科间的分化史,同时又是跨学科的融合史。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传播学具有非学科(属)性,传播学研究是“无界而有的”的:一方面,就研究范围(领域)来说,传播学研究没有边界,是跨界或“无界”而“全域”的;另一方面,就研究对象而言,传播学研究是拥有特定的研究目标、目标问题或标的的。这表明,传播学兼具无界性和有的性双重学科特性。研究问题是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的传播学的唯一学科身份标识,传播学的研究问题是传播本身的问题。在日益鲜明化的问题意识指引下,未来传播学将不断拓展和深化对传播本身的问题研究。
关键词:传播学;边界;跨界;无界;有的;研究问题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20)11-0148-04
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专业化(细分化)程度一度被视为衡量一个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标志,社会科学研究也不例外。几乎可以说,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科学研究的专业化(细分化)过程。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专业化分工使得学科之间的分化越来越明显,因而学科领域之间的边界日益清晰。但与此同时,伴随着社会科学研究的不断拓展和深入,尤其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各门学科之间显现出不断交叉、融合(综合)的趋势,出现了诸多的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学科领域之间的边界因界面的彼此重叠而越发模糊。可以说,自近代以来,一部社会科学的发展史既是一部学科问的分化史,同时又是一部跨学科的融合史——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所谓“一体两面”)。
一、传播学研究的无界性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传播学的边界问题或学科合法性、正当性即独立性(自主性或主体性)问题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议题。进入媒介融合和大数据时代,传播学的学科特性——交叉性或边缘性——进一步凸显出来,这也更为鲜明地印证了一般被称为传播学鼻祖的施拉姆所形容的“十字路口”这一交叉学科境地。既然传播学天然地是一门交叉学科,而且是一门多学科多重交叉的特殊的交叉学科,它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边界很自然地变得极为模糊。交叉学科的交叉性同时意味着开放性,意味着向与之交叉的各门学科开放,那么,作为多重交叉学科的传播学更是全方位地向各门社会科学学科开放,因而成为一门如沃勒斯坦所说的“开放的社会科学”。从学科的诞生历程看,传播学至少是与其所谓的“四大奠基人”的学术活动所属的学科——政治学、社会学与心理学等学科相互交叉而向这些学科开放的。确实,就人类现实经验而言,传播现象或活动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所谓“社会在传播中存在”“社会即传播”“文化即传播”“人即传播”等等论断无不表达出人类传播现象的普遍性和无界限性),遍布和贯穿于整个人类社会及其发展历程。因此,如果认定传播学研究的是人类传播现象或活动,那么就研究范围(领域)而言,传播学研究是没有边界、无界限的,或者说,是跨(边)界乃至于“全域”的。基于此,传播学(研究)旨在划定(学科)边界的边界问题其实是一个伪命题。鉴于传播学研究几乎可以打破和跨越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边界,涵盖整个社会科学的几乎所有学科领域,而不受任何学科范畴(领域或范围)的束缚,所有的传播学研究都是跨学科研究。正是在这个极端的意义上,施拉姆称传播学为“领域”(field),而非“学科”(discipline)。后来还有学者称之为“场域”“走廊”“海港”“海洋”。这里所表达的应该就是传播学的非学科性。正是传播学的这种独特的学科属性——非学科性决定了传播学的任何“学科化”努力注定是徒劳的,而“去学科化”才是传播“学”发展的正道。那么,对传播“学”而言,所谓的学科化或学科建制不够的“学科危机”同样是一个伪命题。
传播学研究之所以是“无界”而“全域”的,传播“学”之所以具有非学科性,恰恰是因为传播学是一門交叉学科,而交叉学科一般都是“后发”学科。在过去两千多年的人类学术研究历程中,社会科学中的众多先行学科逐渐以逻辑的形式占据了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几乎没有给后来的后发学科留下任何空白区域或地带,后发学科因此而必然地成为交叉学科。换而言之,随着人类社会科学的不断拓展、深入和学科的不断增多,几乎没有一个领域可以为某一门学科垄断,沦为它的专有品。因而,人类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领域共有化程度越来越高。越是“后发”的学科越有可能成为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据此,后发的传播学不再拥有独立的研究领域或范围即所谓“自留地”或“根据地”,其研究领域(即人类传播现象或活动空间)都不是为其所独有、独占的,而是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如语言学、符号学、广告学、公共关系学、市场营销学等分享乃至于共享的。
作为交叉学科,本来传播学应该同与之交叉的相关学科相互渗透和影响,进行知识跨学科的输入与输出,实现知识在学科问的相互借鉴。或者说,处在“十字路口”的传播学应该成为各种知识交汇的平台。但自传播学诞生以来,尤其是就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实践而言,为追求和维护、捍卫所谓的学科合法(正当)性,传播学不断地划地自限,出现了学术的内卷化(volution)倾向,从“独立”走向“孤立”。对此,有学者做过实证研究,通过分析传播学主要期刊的引文指数,发现它们引用其他社会科学的文献越来越少,引用传播学自身领域内的文献越来越多。当然,其他社会科学期刊引用传播学的文献就更少了。对此,有学者对美国著名新闻传播学刊《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所列出的35本“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新闻与传播学著作”进行检索发现,“除了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被社会学、营销学和农业推广学之类的学科广泛引用外,其他的传播学著作被传播学之外的学科引用的量并不大,有些著作甚至没有被人引用过”。也就是说,传播学的研究成果既不引用其他学科的知识,也不为其他学科所引用。结果是:传播学在整个学术知识体系中的贡献率很低。这就表明,从学术发展的历程看,传播学研究在学科主体性(或自主性)意识越来越强烈的情境下,在“学科独立”焦虑的影响下,在“地盘保护”的思维模式支配下,越发划地自限,传播学为自身所确立的边界越来越成为与外界学科隔绝的壁垒。其结果是:传播学既丧失了创新和增益自身学科知识的条件,同时又失去了为整个社会科学贡献知识的机会。
二、传播学研究的学科规定性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传播学自诞生以来,一直饱受身份认同危机的困扰。在传播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学科相互跨界、展开跨学科的交叉研究过程中,人们不禁要问:传播学到底研究什么?或者说,其学科的身份标识或表征到底是什么?其学科知识的核心要素又是什么?概而言之,作为一门学科,传播学赖以存在的依据何在?一般来说,一门学科成立的标准或要件包括独立或独特的研究领域(范围)、研究范式及研究方法等要素。但如前所述,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因其“后发性”而不拥有独立的研究领域(范围)。与此同时,同样因为其“后发性”,交叉学科也不具备独特的研究方法,其所使用的所有的研究方法——无论是科学实证(包括质化的、量化的)还是哲学思辨的,无论如何多样化——几乎都是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共享的。由此,特定的研究范式(即观照视角和分析框架)似乎就成为一门交叉学科唯一的身份标识。确实,不同学科面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即使面对相同的研究对象,有不同的研究范式,因而研究范式成为一门学科之所以是该学科而非其他学科的重要表征。这种能够区分学科门类、作为学科标志的研究范式也被称为学科范式——学科研究范式。一门学科对应一种学科(研究)范式。然而,对交叉学科来说,这似乎是不适用的,因为事实上,交叉学科往往缺乏一套像一般性学科所具有的统一的学科研究范式,它所拥有的只是分属于不同学科的各种理论范式。这些理论范式因具有不同的学科属性而繁杂、多元,相应地,这些理论范式所构建的知识体系则极为庞杂和繁复。作为多重交叉学科,传播学尤其如此。有西方学者曾经对7本西方传播教科书中的相关传播理论数量进行统计,发现总共出现249种不同理论,但其中195种理论仅仅出现在一本教科书里,而同时出现在三本教科书以上的却不到7%。还有学者试图通过统计相关传播学理论被引次数来找出最核心的传播学理论,但结果令其失望。这一三十年前的统计数据表明,传播学在西方发展数十年后仍旧没有发展出一套普遍认同的核心分析框架即统一的学科研究范式。随着学科分化和融合进程的加快,传播学统一的核心理论和研究范式的缺失现象只会不断加剧。为此,有中国学者早年曾提出:以“信息人”为研究母题即基本的人性论假设,建构起一种整合经验主义、批判主义和技术主义等理论范式的“综合传播学”范式——新人本主义范式,但这种统一的综合(合成)型学科研究范式迄今也没有成型,而仍然是个“纲领”。交叉(或边缘)学科合法性(独立性)之所以受到质疑,就在于被认为缺乏一套统一的(学科)研究范式。交叉学科之所以缺乏统一的(学科)研究范式,盖因为这种统一的(学科)研究范式是跨学科不同理论范式综合、合成的结果。而跨学科、学科间的融合型学科范式是难以获致的,其根源在于:不同学科理论范式之间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根本分歧难以弥合,基本的学理假设和逻辑前提不可通约(共享)。由此可见,统一的学科研究范式并不能——至少尚未能——成为交叉学科身份确立的要件。
如果说,研究领域、研究范式及研究方法都难以把一门交叉学科同其他学科区分开来,那么,一门交叉学科之所以是该学科而非其他任何学科或区别于其他任何学科的“质”即其内在规定性到底在哪里?或者说,其存在的先决条件、终极依据及其性质和特征的决定因素到底是什么?那么,唯一剩下来的能够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的独特性表征的似乎就只能是研究对象了。一般认为,如同没有一个研究领域(或范围)是一门交叉学科所独占的,也没有一个研究对象是一门交叉学科所独有的(研究对象往往为交叉学科与同其相交叉的其他学科所分享和共享)。因此,研究对象似乎也成不了交叉学科自身的质的规定性所在。然而,在此需要明确的是,严格说来,研究对象不仅不等同于研究领域,而且它也并非指向某一或某类事物(包括人)或现象(这些往往表现为具体的个案或案例)。它特指研究问题——研究所指向和所要解决的问题,即研究者在某一研究领域中所发现、提出和所要解答的疑问、疑惑、困惑——所谓“答疑解惑”。研究问题才是学术研究的真正对象——内涵意义上的研究对象。必须把一般意义上的研究对象予以问题化,把它提炼、转化为一般性、普遍性和公共性的研究问题。研究问题才是唯一的,唯有研究问题才是一门交叉学科不能与同其交叉的其他学科分享、共享之所在。因此,准确地说,研究的对象是问题,研究问题才是交叉学科的“质”。正是研究问题界定交叉学科的学科特性,从而进一步判定围绕该研究问题的学术活动及其成果的学科属性(归属)即是否属于该交叉学科而非其他学科。总之,交叉学科只能由其研究问题来界定。从这种绝对界定的意义上说,交叉学科的研究问题同交叉学科本身具有同一性,前者是后者存在的充分而必要的条件,前者唯一而必然地担保了后者的存在,可以说,两者是“共存亡”的。由此可见,作为一门多学科多重交叉的学科,传播学只能由其研究问题来界定,唯有传播学的研究问题担保了传播学的存在。
三、传播学研究的有的性
就传播学而言,作为其存在的先决条件、终极依据及其性质和特征的决定因素的研究问题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问题才是传播学研究的“问题”或传播学的研究问题?是否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中所有的传播活动或现象都能成为传播学的问题而予以研究?人们一般会笼统地说,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传播现象或活动及其规律即人类所有的传播问题。无疑,传播学肯定要研究传播问题,要研究与传播有关或关于传播的问题,不过,并非所有与传播有关的问题都是传播学的问题而成为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传播学只研究传播本身的问题,即具有本质性(根本性)和普适性即普遍适用于人类一切传播活动和现象的传播问题——传播的基本规律性、共同性内容,包括就传播(行为、活动)的本质、结构、机制、模式、类型形态、意义效应及其媒介形式等方面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才能成为传播学的目标问题即传播学的研究目标、“标的”,也只有这些问题才能构成传播学研究的本体或主体(内容)。换而言之,传播学只研究传播的内涵性(本质性)问题,不研究其外延性(表征性)的问题。这就好比当代兴起的一门交叉性的学问——人学,它只研究人本身的问题,即涉及人本质属性的问题,如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存在方式及异化问题等,至于与人有關的其他诸多问题则由人文社会科学各门学科(包括文史哲、政经法等)来研究。
事实上,从人类学术发展史上看,在传播学诞生前,遍布于整个社会历史的人类传播现象或活动都是人文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与传播相关的问题都成为了这些学科的研究问题。譬如,语言学、文学、哲学、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符号学、新闻学、信息学等诸多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都论及与人类信息传播现象和活动有关的问题,并已产出众多关于传播现象或活动的研究成果。然而,它们都不是传播学,因为它们只是笼统地把传播现象或活动作为研究对象,而不是对传播本身问题的研究。可见,一般意义上的有关人类传播活动或现象的传播问题并不能把传播学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区分开来,能够将传播学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区分开来的只能是传播本身的问题——人类的内涵性(本质性)的传播问题。传播学以传播本身的问题为研究问题(研究对象),这表明:作为交叉学科的传播学是有特定的研究目标、目标问题即“标的”的。正是这一类特定的研究问题——传播本身的问题——成为传播学之所以为传播学的学科根据,亦是其学科标志所在。
一切学科的学术研究都要以研究问题的发现、提出和解决作为第一要务。就学术研究的旨趣而言,相比于研究(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这些只具有方法论意义),研究问题是第一位的。不过,对以研究问题本身作为学科身份标识的交叉学科来说,问题意识则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不仅要求是一个“真问题”(即真实的学术问题),而且还要求是一个交叉学科本身的问题。就传播学而言,其学术研究所探讨的必须是传播学的问题即传播本身的问题。鉴于交叉学科容易受“学科独立”焦虑的影响而执著于独立的理论(范式)体系的规划和建构或发动所谓的“范式革命”,进而造成理论(范式)从研究工具僭越成研究目的本身的学术异化现象,以研究问题为本位的问题意识的涵养和磨砺对传播学来说至关重要。作为一门多学科多重交叉的交叉学科,传播学首要追求的不是划定边界,也不是建构理论(范式),而是找寻学科自身的研究问题,发现传播本身的问题而予以锚定,进而以问题为导向,对不同学科理论采取实用主义立场,通过各学科概念组合进行因果分析,以解决研究的问题。而在研究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有可能建立一套随机综合多种学科理论要素的综合性解释框架(一种有弹性的松散型研究范式,既不是一种同一的理论范式,也不是一种统一的学科范式,因为其概念选择组合的方式因每次所要解决的研究问题的差异而各不相同),可供同类型传播本身的问题的研究作参照。从研究问题出发,回到传播本身的问题中去而予以学理化解答,这将是作为交叉学科的传播学确立其学科合法性的唯一路径。
四、结语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传播学具有非学科性,传播学研究是“无界而有的”的:一方面,就研究范围(领域)来说,传播学研究没有边界,是跨界或“无界”的;另一方面,就研究对象而言,传播学研究是拥有特定的研究目标、目标问题或“标的”的。归之,传播学兼具无界性和有的性双重学科特性。鉴于交叉学科的“质”的规定性既不在于其研究领域(范围)、研究方法,也不在于其研究范式(交叉学科无法建立一套跨学科、学科间的统一的融合型学科范式),研究问题就成为了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的传播学的唯一学科身份标识。传播本身的问题即传播的内涵性(本质性)问题是传播学的研究问题。在日益鲜明化的问题意识的指引下,未来传播学将不断地拓展和深化对传播本身的问题的研究。这也是作为交叉学科的传播学确立其学科合法性的唯一路径。
作者简介:李智(1972-),男,汉族,湖南湘乡人,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传播学理论与国际传播。
刘萌雪(1990-),女,汉族,山东泰安人,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传播学理论与国际傳播。
(责任编辑: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