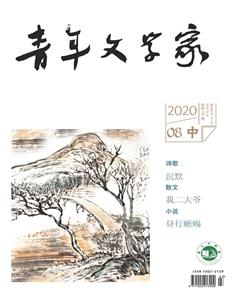罗伯特?弗罗斯特《未走过的路》新译
摘 要:罗伯特·弗罗斯特被认为是20世纪美国最著名、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许多诗作脍炙人口,如著名的《未走过的路》。这首诗一经发表便广为流传,并且通过译文传遍世界各地,中国译界先后有多位译者翻译该作,其中不乏精品。随着时代推移,对于原作的认识以及译文的审美观均发生变化,本文作者对现存《未走过的路》中文译文作出对比分析,同时基于时代背景与个人审美的需求,借鉴中国古体四言律师体例,对该诗进行了重新翻译。
关键词:罗伯特·弗罗斯特;译本;赏析;翻译
作者简介:李晓轩(1989.10-),男,汉族,甘肃定西人,硕士,研究方向:英汉翻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3--03
一、作者及原诗简介
(一)罗伯特·李·弗罗斯特Robert·Lee·Frost1874年3月26日出生于美国西部城市旧金山,1963年1月29日于波士顿去世,享年88岁。弗罗斯特被认为是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诗人,也是20世纪用英语写作诗歌的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聂珍钊著《英语诗歌形式导论》,出版社,年)弗罗斯特一生创作不辍,先后四次荣获普利策奖(The Pulitzer Prize),被称为美国文学中的“桂冠诗人”。
1894年,他在《独立》杂志(Independent)11月号首次发表题为《我的蝴蝶》(“My Butterfly”)的诗作。1897年弗罗斯特进入哈佛大学,对拉丁文、希腊文和哲学极感兴趣,但两年后因肺病中途辍学。在这以后的12年里,他在写诗的同时,教书和经营祖父留给他的农场。1912年他卖掉农场,举家去英国,他专事诗歌创作。在伦敦他很快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少年的意志》(A Boys Will),同时结识了一些英国乔治王朝时期的诗人,其中包括年轻的意象派诗人。庞德当时也在伦敦,十分赞赏弗罗斯特的诗才,曾在美国芝加哥的《诗刊》杂志(Poetry:A Magazine of Verse)上介绍弗罗斯特的《少年的意志》,并努力帮助他出版诗作。1914年弗罗斯特在伦敦发表第二部诗集《波士顿以北》(North of Boston),首先在英国赢得诗誉。英国评论界的热情赞扬引起美国出版界的重视,至1915年弗罗斯特举家返回美国时,他的两本诗集已在美国出版,受到读者欢迎。此后,他继续务农和教书,同时又陆续发表《山间》(Mountain Interval,1916)、《新罕什布尔》(New Hampshire,1923)、《向西流去的小溪》(West-Running Brook,1928)、《又一片牧場》(A Further Range, 1936)、《见证树》(A Witness Tree,1942)、《尖塔丛》(Steeple Bush,1947)、《假慈悲》(A Masque of Mercy,1947)、《诗选》(Collected Poems,1939)、《诗歌全集》(Complete Poems,1949)、《林间空地》(In the Clearing,1962)等诗集。
随着这些著作的出版,弗罗斯特的声誉日增,先后被哈佛等几十所大学聘为教授或客座诗人。他应邀到全国各地朗诵自己的诗作;4次获得普利策诗歌奖。1950年在他75岁圣体时,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向他祝寿,尊称他为美国民族诗人,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1961年他应邀出席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就职典礼。在仪式上朗诵他的诗作《全心全意的奉献》(“The Gift Outright”)。
弗罗斯特一生共写作二十多本诗集。1963年1月29日,弗罗斯特在波士顿去世,葬于佛蒙特州本宁顿的旧本宁顿墓地。
(二)The Road Not Taken《未走过的路》诗歌韵律分析
诗歌原文以及韵律分析如下图所示:
Two roads di verged in a ye llow wood, 9 a
And so rry I could not tra vel both 9 b
And be one trave ler, long I stood 8 a
And looked down one as far as I could 9 a
To where it bent in the under growth; 8 b
Then took the o ther, as just as fair, 9 c
And ha ving per haps the bet ter claim, 9 d
Be cause it was gra ssy and wan ted wear, 10 c
Though as for that the pa ssing there 8 c
Had worn them rea lly a bout the same, 9 d
And both that mor ning e qua lly lay 9 e
In leaves no step had tro dden black 8 f
Oh, I kept the first for a no ther day! 10 e
Yet know ing how way leads on to way, 9 e
I doub ted if I should ever come back. 9 f
I shall be te lling this with a sigh 9 g
Some where ages and ages hence; 6 h
Two roads di verged in a wood, and I-- 9 g
I took the one less tra veled by 8 g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 rence. 8 h
可以看到,全诗形式及韵律分析如下,诗歌采用传统多音步抑扬格写作。首节押头韵,形式为TAAAT;全诗共4节,每节5行诗,尾韵形式为abaab; 第二节、第三、第四节诗每节诗歌都换新韵,但整体上仍符合abaab形式。全诗尾韵总结为abaab cdccd efeef ghggh。
根据全诗的重音分布规律,暂且认为该诗采用抑扬抑四韵步的韵律,但是在第一节3、5行,第二节3、4行,第三节2、3行,第四节2、4、5行均出现音节不符合的情形。
二、已有译本对比
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歌在美国近乎家喻户晓,尤其这首《未走过的路》更是达到了所谓“小学生出口能诵”的地步,追溯此诗在我国的译介情况不在此文的讨论之列,但不论如何,由于弗罗斯特的诗歌清新隽永而富有深意,因此具有“常译常新”的价值,许多国内翻译大家都对这首短诗大加赞赏并译成汉语,下面简单介绍几个比较著名的译本。
曹明伦版本:
未走之路
金色的树林中有两条岔路,
可惜我不能沿着两条路行走;
我久久地站在那分岔的地方,
极目眺望其中一条路的尽头,
直到它转弯,消失在树林深处。
然后我毅然踏上了另一条路,
这条路也许更值得我向往,
因为它荒草丛生,人迹罕至;
不过说到其冷清与荒凉,
两条路几乎是一模一样。
那天早晨两条路都铺满落叶,
落叶上都没有被踩踏的痕迹。
唉,我把第一条路留给将来!
但我知道人世界阡陌纵横,
我不知将来能否再回到那里。
我将会一边叹息一边叙说,
在某个地方,在很久很久以后:
曾有两条小路在树林中分手,
我选了一条人迹稀少的行走,
结果后来的一切都截然不同。
简单分析曹明伦先生的译本,可以发现译者由于本人具备非常深厚的理论基础与丰富的翻译经验,在翻译过程中是具备相当的“自觉性”的,原文中每节诗歌的押韵,诗句中的停顿,以及转行、换韵等技术细节在译文中都可以寻到端倪,但是仔细品味,又可以发现“曹版”译文并没有死扣字眼,为了“忠实”而忠实,而是在新的汉语语境中重新构筑诗味,力图传达原诗的精神内涵,同时也保证目的语读者能够感受汉诗般的“诗意”,也许那些没有如实反映出来的原文技术细节,正是暗合了不要“因形害义”的翻译原则。曹明伦先生的译文体现出了相当的水准,为后来者树立了很高的“准绳”。
赵毅衡版本:
没有走的路
黄色的林子路分两段,
可惜我不能两条都走。
我站立良久,形影孤独,
远远眺望,顺着一条路,
看它转到灌木林后。
我选了另一条,同样宜人,
挑上这条或许有点道理:
这条路草深,似乎少行人;
实际上来往的迹印,
使两条路相差无几。
而且早晨新落的叶子
覆盖着陆,还没人踩,
哦,我把第一条留给下次!
前途多歧,这我也知,
我也怀疑哪能重新回来。
多年,多年后,在某地,
我將讲这件事,叹口气:
树林里路分两股,而我呢——
选上的一条较少人迹,
千差万别由此而起。
仔细阅读赵先生的译作,应当说这首译文在节奏上花费了相当的心思,使目的语读者在阅读译作时,能够明显地感受到诗歌的韵律跳动;技术层面,如此学界牛耳之人,在处理弗罗斯特诗歌时,毫无疑问会注意到类似的问题,处理的方式应当说与前一版本曹明伦教授译本相差无几,两人都是尽力兼顾原诗押韵和律动的前提下,避免出现“因形害义”的死译、硬译问题,从而使译文在新的语境中焕发生机,使原诗以焕然的面貌获得了新的生命,展开新的旅途。众所周知,“翻译是失落(丢失)的艺术”,同时也是“遗憾的艺术”,应当说无论如何,诗歌的翻译都不可能存在尽善尽美的结果,失落的“圣杯”难以寻获,而“上帝的语言”也早已失传。“赵版”译诗在风格上更加追求凝练和节奏的跳跃。总体来说,“赵版”译文仍然是不可多得的佳品。
缀述一句,二位大师的译作虽然都非常精彩,但是细细解读,似乎两人对于原文的理解不尽然相同。诗歌本来就是“朦胧”、“含蓄”的艺术,正所谓“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出现这一现象本也不足为奇,各类关于弗罗斯特诗歌《未走过的路》的诠释文章在国内外更是不胜枚举,上文中也有提到,此处不再讨论。
三、The Road Not Taken新译
罗伯特·弗罗斯特名诗The Road Not Taken一诗不仅在美国家喻户晓,在中国也是广为流传,尤其是互联网时代,更加剧了这一名作的知名度。笔者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拜读”过这首名诗,最初是不知名的中文译本,后来又专门阅读原文诗歌,可以说这首诗对于青少年时期的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偶然的场合,笔者出于派遣心中苦闷的缘由,在网络上打开了The Road Not Taken一诗读了起来,之后映入眼帘的是一串网上流传开来的中文译本,笔者读了几篇之后,大感译文水平参差不齐,甚感遗憾,出于一时冲动再次翻译了这首传世名作,下面是笔者的新译版本。
未尽之路
李晓轩译
黄林前立,道分两行
不可得兼,如饮愁汤
旬立踟躇,谓我何伤
极目尽望,娓娓肠肠
针叶萋萋,前路所藏
无可明断,遂取一行
混沌凿窍,天意冥冥
荆棘砥砺,吾志所向
两行并立,恍如参商
人迹罕至,孤石独躺
前路漫漫,熹微少光
回顾四望,叶之黄黄!
何昨日之不来,叹往日之流光!
纵千回百阻有万险,
亦乘沉舟驾远航!
噫!昨日轻狂唯一叹
今日之日何所傷
黄林前立,道分两行
明知独行无友朋,
毅向天涯取志向!
四、总结
应当说,这首诗的翻译,在笔者可谓一时冲动,整个翻译过程从动念到完成不到两个小时,期间大量的功夫花费在了对于原诗的理解上,必须指出的是,笔者对于原诗的理解借助了前人许多的译本,因此在最终动笔后难免出现他人的“痕迹”。虽如此,笔者在整个翻译期间完全是独立完成,没有任何主观抄袭的意象或行动,前文已说明,笔者翻译的动机就是在于对许多译本的“不满”,所以没有必要再去学舌他人。
翻译完成之后,“创作”的冲动如潮褪去,反思的理性“占领高地”。重读这首译作,可以看出至少有两位诗人,两手诗歌对笔者的翻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分别是曹操的《龟虽寿》和李白的《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下面列出两手诗作:
龟虽寿
曹操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李白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笔者在翻译弗罗斯特这首名诗的时候,很显然在形式上借鉴了曹操《龟虽寿》的八言古体诗,而在后文中情绪喷薄需要宣泄时,又“借用”了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的句式。
诚然,笔者在翻译诗作的过程中,整个人处于一种类似“创作的非理性”情绪中,整个过程几乎没有掺杂理性分析的技术环节(也造成了最终译文忠实不够,“改写”有余的结果),此处强行拉上大诗人曹操、李白,无非是一种潜意识的“贴金”罢了。当然,之所以最终成文如此,合理的解释是汉语作为笔者的母语,血脉中早就融入了汉语的文化传统,类似的译作只是一种偶尔的“灵光一现”罢了,远远没有达到作为译者的“自觉性”。
参考文献:
[1]James D. Hart. 牛津美国文学词典[Z].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2]曹明伦译. 未走之路——弗洛斯特诗选[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3]黄昊炘. 译诗的演进[M].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4]聂钊珍. 英语诗歌形式导论[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5]钱林森,周宁主编[M]. 中外文学交流史.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