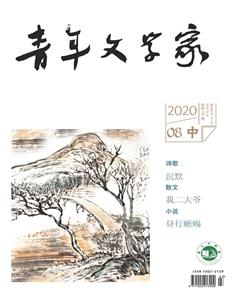沙皮狗儿子
作者简介:曹怀重(1954.2-),男,汉,山东省荷泽市人,笔名:曹廓,本科,东明武胜中学副校长,山东作协会员,菏泽市作协会员,研究方向:小说诗歌散文。
一
这几天,寡居老汉张箩头,经常抱着他的沙皮狗,“娃啊娃啊”地落泪。
对门的二歪嘴笑话他:“狗是你娃,俺箩头婶子就是母狗喽!”
他狠狠瞪他们一眼:“你小子知道啥!想当年我媳妇叶子,论美在咱村数着呢!那时你还在你爸腿肚子里呢!”
张箩头不是个轻易就落泪的人。是他的沙皮狗儿子两天没进食了。它只慵懒地伏在屋当门靠西墙的沙发上,不吃不喝。搁铁打的汉子也受不了哇!
无论沙皮狗多么可爱,对旁人来说,它吃不吃东西都像别家死个雏鸡一样是小事一桩,可对张箩头来说却是天大的事了!
张箩头四岁丧父,八岁丧母,无亲无故,吃百家饭长大。他从小不爱说话,被人们误认为“欠两方子”。从小到三十三岁前,张箩头一直没受到过姑娘的青睐,孤苦伶仃的。
三十三岁那年,他撞上了桃花运,在路上捡了个漂亮媳妇。
那年春天,他在黄河大堤上干“灌泥浆"的重体力活。三月初三那天,-轮红日完全沉入地平线以下,田野里只剩下几缕微弱的红光。张箩头从工地上回家,走到下大堤路口的桥头边,见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带一个沙皮狗呆坐路旁。“天这么晚了,她怎么……”张箩头狐疑了一下过去了。
“饿,我吃馍!”背后传来乞讨声。张箩头转过身来看看她脏兮兮的可怜相,便把在工地上吃剩的半个窝窝头给了她,继续往家走。她狼吞虎咽地吃着跟他走。他进院她也随着进院,他进屋她也跟着进屋。他赶她走,她给他要馍吃。他很可怜她,给了她馍,又喂了她的嗷嗷待哺的沙皮狗。她吃了馍就睡他床上了,沙皮狗吃饱卧院里的柴垛上。张箩头铺个草苫子睡到地上,打算天明再送走她。他问她叫啥名,她好像说叫叶子。
到第二天,张箩头没有能把她送走了,因为早饭后送走,到晚饭前她又回来了,并且还受了伤,她的沙皮狗的脖子也受了伤。一连送几天,都没送走她。邻居都说,张箩头,你孤独一人的,就让她给作个伴吧!
张箩头不再是孤身一人了,有了出双入对的幸福生活。白天他上工,叶子领着沙皮狗在工地旁边玩;晚上,他做饭她烧火,他躺下她陪他睡觉。慢慢的,她扫树叶,割草,挖菜,甚至还给他做饭。慢慢的,叶子知道梳头了,走路利索了,看人的眼光也不很呆滞了。她穿上了箩头给买的新衣服,洗净脸,原来是个很漂亮的女子。半年后叶子怀上了张箩头的孩子!她面色红润,简直可以说是漂亮得迷人了。张庄人都说张箩头拣个大便宜,人家花“三转(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一拧〈录音机〉”的钱都娶不到这么好的媳妇。
可惜好景不长在。也就是捡到她的下年春天,叶子吃过早饭带着沙皮狗到野地拾柴,一去就真的成了一片落进草丛里的叶子,再也见不到了。张箩头四处打听,八方寻找。有人说晌午时见有两个骑自行车的一个老一少的男人把她带走了,沙皮狗见那两人还直摇尾巴呢!人们猜测应该是被她家人接走了。
张箩头要着饭四面八方找了三年,整个人好像由三十多岁一下子变成了五十多岁。而叶子像狐仙变成了一缕青烟在人间杳无踪迹了。
从此张箩头又成了光棍一条。光棍的他便喜欢上了养沙皮狗,他对沙皮狗的感情是一个丈夫对他心爱的叶子、一个父亲对他未出生儿子的感情。如今沙皮病了怎不叫张箩头揪心!
料峭的春风吹进乡政府给建的小院里,吹得院里的白杨树叶瑟瑟发抖。小院是他的归宿,他不喜欢敬老院的热闹,他的生活里只要有沙皮狗儿子就足够了。这只沙皮狗是通人性的。张箩头站着,它给他拉裤角、挠痒,亲得像个媳妇;张箩头坐着,它伏他膝上,亲密地舔他手,乖得像个儿子。
眼前的沙皮狗与他妻子带走的那个简直像從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一身黄色沟沟坎坎的松皮,齐黑的嘴头,额上像是雕刻上去的他根本不认识的字。它伏在沙发上,浑身的每条沟纹都流露着痛苦。特别是那双泪水汪汪的眼睛,似在诉说着难以忍受的苦痛。这种苦痛让张箩头刀割般的难受。
他一刻也不能再等待了!必须马上去镇上给它看医生!
早饭后,张箩头毫不迟疑地拿出枕头下的破棉袄,把破棉袄平铺到电动三轮的车斗里,把沙皮狗抱到棉袄上,然后出了他很少外出的家门。
柏油公路两旁的紫叶梨花开得很美,油菜花也金灿灿地溢着芳香。张箩头没有半点赏花的雅兴,他的心全在沙皮狗儿子身上。张庄距集镇只有三里多路,张箩头很快到了集北街的兽医站。鬓角花白的兽医检查了一番后说:“是狗瘟热。”张箩头紧张地问:“大夫,它没事吧?”“这种病治愈率很低。”张箩头忙从车斗的破棉袄袖管里抓出一个塑料袋。解开袋子,从里面掏出一个黑棉布袋。打开黑棉袋,拿出一沓面值不等的钞票与一个农民养老金卡。他扬起手用力摇摇,像证明自己很有钱,又像表明-种态度:为救沙皮儿子他可以倾其所有。他拖着哭腔说:“大夫,求您救救它!我不能没有沙皮狗!求你给它用最好的药!让那个什么驴高点!”他坚信,只要沙皮狗在,叶子一定会回来的!叶子一回来他的末见面的儿子也就回来了!
“那就尽人事听天命吧!”老兽医熟练地用一次性针管吸好了药液,一手抓住沙皮的额头,另一只手迅速将针头扎进沙皮脖子里。沙皮狗拉着凄惨的长调“吱一吱一”地叫着。张箩头觉着那只大手分明抓的是自己的脑瓜皮,针头也实实在在扎进了自己的脖子里。他用药棉球按着狗脖子的针眼,把它抱在怀里。他看见沙皮流了泪,他吹着狗脖子都哭出了声。
老兽医说:“回家后只能让它喝水,千万别让它吃东西!”
“好!好!”张箩头连忙点头,像望大救星一样虔诚地望着老兽医。他听着老兽医嘱咐时肯定的语气,坚定地认为他是沙皮狗的救星,换句话说他也是张箩头的大救星!
回到家,沙皮狗不再慵懒地睡了。它明显地有了精神,摇着尾巴去了食盆。张箩头忙倒掉盆里早饭时为它做的豆奶粉糊糊,涮净后倒上清水。沙皮狗贪婪地一气便喝光了。沙皮狗喝过水,美美地舔舔嘴角,又在小院里悠然地转了两圈,然后卧到了沙发上,亲热地给他摇尾巴。
张箩头心里像大暑天吃了一根老冰棍一样,生出一阵清心的爽快!他感觉叶子正坐在沙发上,为沙皮狗搔痒。沙皮狗眯着眼睛不停地摇着尾巴。它摇呀摇,摇得张箩头心里一痒一痒的,舒服极了。
晚上,张箩头起床抚摸沙皮儿好几次。沙皮都在沙发上安稳地睡觉,看见他都亲密地摇两下尾巴。
张箩头又带着沙皮连续打了两天针。这两次沙皮像习惯了疗治,都默默地承受了。但张箩头仍感觉自己的头皮被那大手狠狠地抓了两次,脖子被针深深地刺进了两回。看着沙皮狗痛苦的样子,张箩头仍然心痛地落了两阵泪。每打过针,沙皮精神都会好很多,回到家都是贪婪地喝水,然后悠闲地转两圈才爬到沙发上睡,看见他都是摇尾巴。每次他都看见了叶子抚它的头,晚上仍是照看沙皮好几次……
二
到第四天做早饭时,张箩头想:“沙皮儿好几天没吃东西了,不能全听医生的,医生也有说错话的时候,应该少喂它点吃食。”他给沙皮煮一个鸡蛋,把鸡蛋放冷水中浸渍一会,剥好蛋壳用舌头试试热凉,把鸡蛋送到沙皮嘴边。沙皮懒洋洋地用牙齿挂了一点,摇摇尾巴眯上了眼睛。再喂,它懒得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张箩一个馍没吃完,就带着沙皮去了镇兽医站。老兽医看看狗鼻子说:“你带它去县城阳光宠物医院输输液吧!一直不吃东西可不中!”“好!好!”张箩头坚信,只要沙皮狗在,叶子一定会回来!叶子能回来他的末见面的儿子也就回来了!他不能失去沙皮狗!
他连忙骑电动三轮车去了县城。按老兽医的指点,又问好几个人,才找到了那家宠物医院。县宠物医院比镇上的兽医站大多了,临大街的敞院中几棵开得正艳的梨花树下,立着好几根吊针杆。挂吊瓶的有猪、羊、狗、猫,甚至还有袋鼠与荷兰兔。
“大夫!大夫!”他一进阳光宠物医院大门就高声喊叫。眼镜男兽医过来问:“几天了?”“五天了。”眼镜男用一个纸条擦擦沙皮狗鼻子,又把纸条沾沾小瓶子里的水:“细小病毒引起的血性肠炎。”“没事吧,大夫?”眼镜说:“要一得病就来这,保证能治好!耽误的时间长了就不好说了。”“大夫,求求你了!救救它吧!用最好的药,我有钱。”张箩头两腿一弯一弯的,几乎想跪下来。眼镜男说:“好吧!我尽最大的努力!”眼镜男配好了药剂,给沙皮戴上狗嘴套,让箩头抱住,用皮管扎紧狗前腿,细细的长针头扎了进去。沙皮哆嗦一下,箩头忙把脸扭向一旁不忍再看,这针头比扎进自己身上都让他难受。换第二瓶药液时,沙皮躬起腰“吱一吱一"地叫,浑身的毛都竖了起来。张箩头一手抱着沙皮,一手不停地抚沙皮头,按沙皮肚子。沙皮狗用力一抖一抖的,“呱”呕了-片粘液,“噗”屙了一摊血水。箩头吓坏了发疯似的喊:“大夫!快来!你看我的沙皮儿咋了?”眼镜男过来看看:“打针后胃肠蠕动增强的原因,没事。回到家可别让它吃东西!”沙皮过一会又恢复了平静。
打完针回到家快晌午了。沙皮一被抱下车,就急忙向食盆走。箩头赶在它前面,忙换了清水。沙皮狗头也不抬,一气喝干了。过一会,它又躬起身子“吱-吱一”叫,叫得特别响,特别刺耳。箩头吓坏了,出了一脸汗。他一会抚沙皮头,一会按它的肚子。那沙皮仍不停地抖毛,不停地惨叫。箩头转身向村卫生室跑去,路上摔了好几轱碌,弄得浑身是泥,累得脸皮蜡黄,气喘吁吁:“医生!医生!我的沙皮儿快不行了,求你去救救它!”
“大叔,我不会看狗病!”
“就当给人治吧!它比人还精呢!求你救救它吧!"张箩头真的“咚"的一声双膝跪下了。他坚信,只要沙皮狗在,叶子一定会回来的!叶子回来他的末见面的儿子也就回来了!
医生被缠得没法,极不情愿地跟着到他家,沙皮却不见了。
张箩头东找西寻,找很长时间,到后来才找到。原来那沙皮躲在院里柴草边没事似的安稳地睡觉呢。张箩头抱住它又是哭又是笑,像是见到了久别的妻子与背他出生的儿子。沙皮摇着尾巴不住地亲他的脸。
医生不知何时早走了。箩头迷迷糊糊地看到叶子在厨房里烧火,燃着的柴都烧到了灶门口了,他忙进了厨房。这才记起天快下半午了还没吃午饭呢。
又连续去县城挂两天吊瓶,每次回到家,沙皮不呕、不拉、不再贪恋沙发了。还不时地在小院里走走,去食盆的次数越来越勤,或者摇着尾巴盯他吃饭的碗,一幅馋巴巴的样子。
到去县城的第四天,打完点滴,眼镜男说,明天不用再来了,到家可让它吃一些稀软的食物。“沙皮好了吗?”张箩头兴奋地问。“只能治这样了”眼镜医生漫不经心地说。张箩头的心一下子轻松了,好像一块压在心底的沉重的石块终于卸了下来。开药费时,箩头慷慨地推回了七元的零头,千恩万谢地说,全当是为感谢医生买了一盒香烟。
从城里回家时,他像第一次发现,县城两旁的楼那样高大,花园那样漂亮,公路那样宽敞,道旁树那样美丽!别的他也不会用什么词说。他想唱两句歌,却不会调;他想吟两句诗,但不会词。他放开喉咙“啊——"了一声。这一声“啊——”拉得很长,喊得很响。这喊声吐出了他久郁的闷气。前边两個骑两轮电车的姑娘,回头看看他飞快地逃了去。
张箩头割了斤把肉,上午为沙皮做了精美的肉汤,还泡上一块馒头。沙皮狗吃得津津有味。到晚上沙皮又喝一碗甜面汤。一涮好锅,箩头的眼皮就打架了,这几天他实在太累了。他似乎看见叶子正抚摸着沙皮的头,便放心地睡去了。梦中,他觉着自己正穿着大裤衩子,在黄河大堤顶上灌泥浆,他满身泥水,别人也满身泥水。叶子领着沙皮走过来,其他人都邪性地笑着拉直嗓子发出“哦—哦—”的长调。一会沙皮变成了一个胖小子,那小子黑不溜秋的仿他,还甜甜地叫他爸爸!“唉!”他把应声故意拖得老长,故意向旁人炫耀:怎样!我张箩头有媳妇!有儿子!不孤单!我活的得法着呢!
他被“沙沙"的挠门声惊醒,见自己仍睡在那张他睡了几十年的破床上。他知道,门是沙皮狗挠响的,这东西干净得很,它是要出外方便了。张箩头忙下床为狗狗开了门,并将门留一道缝,好让沙皮儿方便完再回来进屋睡觉。虽然已是中春,有病的沙皮儿在院中还是顶不住夜间凉气的。张箩头又赶忙重新躺下来睡,好接着做那个美梦。
三
伴着雄鸡的啼叫,张箩頭半睁开眼,就着门上头的方窗射进来的下弦月的光,往沙发上看看。却没看到沙皮儿。他猛地坐起身来,睡意全无。他拉开电灯,仔细找寻。沙发旁、柜子边、床底下,屋里全找了个遍,都没见到沙皮儿子。以往的日子常常都是这样,他只要见不到沙皮儿,就觉得屋子成了空壳,空得像一个原先盛过柴油的破空铁桶,一敲还会发出空空洞洞的响声。
他赶忙到院里寻。下弦月透过杨树枝叶,在院地上撒下花花打打霜似的冷光。中春的夜,仍有深深的寒意。柴垛、厕所、东西墙根,都找了个遍,却不见沙皮的身影。他觉着,小院突然间扩大了好多倍,空荡得像拆了戏台的大场地,原先还热热闹闹的,一下子冷清得让人心凉。
他出了院门,房前屋后,仍看不到沙皮。他一边找一边唤:“沙——皮——儿——沙——皮——儿——”声音很是凄厉。在月光溶溶、浮光霭霭、冷冷清清的静夜里,给人平添几分野狐阴森怪叫的瘆人!
他不能失去沙皮儿!他不止一次地想,只要沙皮狗在,叶子一定会回来的!叶子回来他的末见面的儿子也就回来了!
他来到院西边的南北大街,两旁的房屋、树,都还在睡梦中。早年的时候,叶子常带着沙皮狗,从这里向村南头池塘旁的杨行里扫落叶,去小河北面的田里挖野菜。听人谈论,他的叶子就是在小河北面的东西公路上被人用自行车带走的,那时候东西公路还是土路。他现在的沙皮狗也喜欢向村南去,也爱在公路上溜达,还喜欢在田里多管闲事的捉耗子,或在村南的水塘旁与黑花白母狗恋爱。
他先到小河北的东西公路上,一边找一边喊。柏油公路在月光下显得光光的,静静的,迷迷蒙蒙的看不到尽头。他又来到田野上唤着寻找,挑旗的麦子在月色里呈墨绿的颜色,昏昏苍苍的望不到边际。
张箩头趟过麦田,寻过杨树行,来到池塘边。他没停止呼唤,一声比一声悲伤:“沙——皮——儿——”声音愈变得沙哑而凄厉。
池塘岸边,旧草软软的铺在底下,新草婷婷地立在上头。他虽然耳朵有些背,还是听到一阵低泣的呜呜声从塘底传来。他快步走过去,只见经常与他的沙皮狗一起嬉戏的那只黑花白母狗,正后翘着白臀,趴着前腿,朝着塘水吠叫。他顺着黑花白狗吠的方向望去,只见塘底的烂泥水里像有一只狗样的东西躺在那里。他再仔细看看,那狗样的东西又很像是他的沙皮。他不顾一切地踏过去,泥水很快没了小腿,又到大腿深,冰凉冰凉的。他拼命快步跑过去,“扑通”倒在泥水里。他又爬起来,淋淋漓漓弄一身水。但他并没觉得冷,只是焦急地前去看清泥水中的那个东西。近了,从外露的沟沟坎坎的狗身体上可认出正是他的沙皮儿!沙皮儿的头都没在水里。“沙—皮—儿,你咋了?”他忙抱起它。沙皮满头污泥,泥水顺着狗头狗身往下淌。张箩头一手抱住它,一手颤抖着为它挖下烂泥。在月光下,狗牙仍是白的,狗眼珠好像转了一下。狗尾巴也似亲热地扫了他-下,狗鼻子却没有了一点气息。“我的沙—皮—儿—啊—”他一腚坐到了泥水中,“你死了——还叫我怎么活啊——”他没哭完,只觉眼前黑了一下……而后看见叶子带着沙皮狗,从空旷的天边向他走来,越走越近,越来越大……他像飞一样跑过去笑着抱住了叶子与他的黑不溜秋的俊儿子……
四
第二天早饭时,黑花白母狗家主人找狗狗吃饭,见张箩头倒在塘坑底里,喊二歪嘴几个人把他拉出来。张箩头紧紧地抱着沙皮狗,一脸幸福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