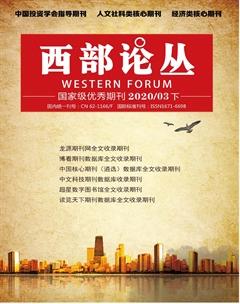零工经济下零工工作者权益保护
摘 要:互联网+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同时对人们的工作选择以及工作、形式种类等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对零工经济环境中平台与工作者之间的关系如何进行认定,我国《劳动保障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还未有明确的认定,对于发生纠纷如何进行救济,我国司法实践也没有统一定论。建立除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之外的第三种用工关系——零工关系不失为破解困境之法,社会保障制度与工会在互联网条件下的创新也是保护零工经济下工作者权益可用之举。
关键词:互联网+;零工经济;权益保护
随着互联网经济发展及代际升级,互联网+在生活中的影响增大,互联网+传统行业形式的出现,社会生活越来越丰富。零工经济逐渐发展,受到广泛欢迎。跟据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9)》显示,2018年我国共享经济参与者人數约7.6亿人,参与提供服务者人数约7500万人,同比增长7.1%。平台员工数为598万人,同比增长7.5%。共享经济成为新型的、弹性就业的一个重要源泉,也成为反映就业形势和经济走势的一个风向标。共享经济不仅成为人们自主择业的重要选择,同时也为社会特定群体提供了广泛的就业机会。 零工经济作为共享经济的性质之一从业人数不断增加,不仅有将零工作为兼职丰富生活的,随着各类零工平台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人将零工作为专职。
一、零工经济相关概念界定
“零工经济”(Gig Economy)是指由工作量不多的自由职业者构成的经济领域,利用互联网和移动技术快速匹配供需方,主要包括群体工作和经应用程序接洽的按需工作两种形式,其本质上是一种短期用工形式。前者通常由一群能够接入互联网的个体在网络平台上完成,包括常规性和技术性较强的任务,工作者的来源具有不确定性。后者是用户通过平台查找信息,寻找一份驾驶、运输、家政等服务,工作者基本来自附近。
关于零工经济还有另外的定义,如国际劳工组织专家认为,零工经济主要包括两种工作形式,一是“众包工作”(Crowd work),即工作的完成通过网络平台实现,该网络平台能够接入不特定的组织或个人,使全球范围内的客户和工人能够相互联系;二是“通过软件的待命型工作”(Work on Demand Via Apps),即工作的提供和分配通过互联网软件来实现,企业通过该软件设置最低的工作质量要求,对工作人员进行选择和管理。而美国国会研究服务中心则将零工经济定义为:通过“零工”模式将资源提供者和消费者的需求进行匹配,以实现按需(On-Demand)商业。在这种模式下,从事零工工作的工人通过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移动软件或网络平台为公司的客户提供服务。麦肯锡全球中心则强调了工作的临时性特点,将“零工经济”定义为就业者通过电子信息市场进行暂时性工作,并将持续性的非全日制工作和未通过网络平台外包的自由职业排除在范围之外。[1]即使定义不尽相同,我们可以看出零工经济是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不特定的劳动者完成单项任务的形式。
零工经济不同于传统的“打零工”,本身属于一种经济新常态,属于“共享经济”的一类。零工经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而是侧重于服务提供者所分享的无形的智力资源,如某一专业技能或特长展示。零工经济双方通过平台发布信息,双方均可对对方进行评估,而不同于征用零工的单向选择性,劳动者只能被动供人挑选。零工经济打破传统用工形式,分享对于劳动者过剩的资源,发挥劳动者价值。
零工经济能够得以传播,得益于社会环境的变迁。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的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形式的增多为零工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更是在其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虽然按需工作的形式有迹可循,但技术革命为按需工作提供了新的表现形式使按需工作得到了新的机遇。零工经济这一术语产生于2009年遭遇经济危机考验的美国,经济的疲软对劳动者提出更多要求,零工经济应运而生,人们有了更多的职业选择。另外,人们对生活的追求不再仅限于获得经济收入,而是追求自由和自我的个性,传统劳动方式对于劳动者的束缚阻碍了就业方向的选择。
二、零工经济平台与工作者间用工形态认定
学界对零工经济下的劳动者与平台之间关系的认定存在争议,部分学者认为为了劳动者的保护将之归于劳动关系,有学者认为应按照合同的形式应当属于承揽合同关系,还有学者基于实践认为应当属于挂靠关系,多数专家认为将其归于劳动关系更为恰当。
(一)劳动关系之否定
一般认为,劳动法是“调整劳动关系以及与劳动关系密切联系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2]我国著名民法学者史尚宽先生认为:“劳动法为关系劳动之法,详言之,劳动法为规范劳动关系及其附随一切关系之法律制度之全体。”[3]
关于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传统大陆法系国家主要采用从属性理论。在劳动关系中,雇员和雇主之间是管理与被管理、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属于隶属关系;双方劳动关系存系时间普遍较长,有相应劳动合同进行约束;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可以不仅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还应当享受法律规定的各项待遇。通常对于劳动关系的认定基本基于从属性的理念来判断。从属性理念可分为人身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对于人身从属性,零工工作者对工作种类、工作时间的选择有较大的的自主性,平台对工作者没有过多的要求,对其约束小,不具备人身从属性的特点;经济从属性方面,以网约车为例,工作者工作时所使用的的生产工具属于其自有,不是网约车平台提供,而且收入所得来自于乘客给付的乘车费不是平台给与的劳动报酬,工作者没有在经济上对平台形成从属性关系。因此根据劳动关系的从属性特点,可以确认,零工经济中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不属于劳动关系。
(二)劳务关系之否定
通说认为,劳动法以劳动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学者一般认为,劳动法是“调整劳动关系以及与劳动关系密切联系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我国著名民法学者史尚宽先生认为:“劳动法为关系劳动之法,详言之,劳动法为规范劳动关系及其附随一切关系之法律制度之全体。”
关于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传统大陆法系国家主要采用从属性理论。在劳动关系中,雇员和雇主之间是管理与被管理、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属于隶属关系;双方劳动关系存系时间普遍较长,有相应劳动合同进行约束;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可以不仅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还应当享受法律规定的各项待遇。通常对于劳动关系的认定基本基于从属性的理念来判断。从属性理念可分为人身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对于人身从属性,零工工作者对工作种类、工作时间的选择有较大的的自主性,平台对工作者没有过多的要求,对其约束小,不具备人身从属性的特点;经济从属性方面,以网约车为例,工作者工作时所使用的的生产工具属于其自有,不是网约车平台提供,而且收入所得来自于乘客给付的乘车费不是平台给与的劳动报酬,工作者没有在经济上对平台形成从属性关系。因此根据劳动关系的从属性特点,可以确认,零工经济中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不属于劳动关系。
(三)承揽关系之否定
《中華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五章第251条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该观点认为平台的身份为定作人,平台上注册的工作者为承揽人,平台发布任务交由工作者来完成这一过程实际为承揽合同的履行。但《合同法》第251条第二款规定了承揽指的是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第252条规定:“承揽合同的内容包括承揽的标的、数量、质量、报酬、承揽方式、材料的提供、履行期限、验收标准和方法等条款。”第253条规定:“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从表面上我们或许容易将平台与工作者间的关系认定为承揽合同关系,但从主体上看,平台根本不能认为是定作人,平台只能被评价为一个工具,平台上的信息是由特定的“客户”来发布的,完成交付的工作后报酬由这些客户来支付,平台不仅不给付工作者报酬,反而会抽取提成等作为平台的维护费或称之为中介费。因此,不能认定平台与工作者间为承揽合同关系。
(四)挂靠关系之否定
实践对于挂靠关系的认定指企业、合伙组织、个体户或者自然人与另外的一个经营主体达成挂靠协议, 挂靠企业、合伙人、个体户或者自然人以被挂靠的经营主体的名义对外从事经营活动, 被挂靠方提供资质、技术管理等方面的服务并向挂靠方收取一定管理费用的经营方式。
有观点认为平台与工作者之间属于挂靠关系,如网约车形式。网约车平台具有运营资质,而网约车司机个人是没有资格的,利用平台的资质和资源,以平台的名义开展网约车活动,符合挂靠的主体特征。行为表现方面,网约车运输合同中,乘客对司机的资质不能个别进行甄别,而只能通过对平台的整体评价来选择,这体现司机对于平台具有依附性,符合挂靠关系特征。在运营支配方面,对于派单模式和抢单模式要进行分别考察。派单模式下,司机只能被动接受平台的派单,没有选择权,不符合挂靠关系的相对独立性特征,不属于挂靠关系;二抢单模式中,平台只是提供服务,不能对具体业务活动施加直接干预,在业务完成后通过乘客的反馈来评估司机,符合挂靠关系的相对独立性。运营过程中,平台将自己的资质作为服务提供给司机,司机每完成一单任务,平台从司机获得的报酬中提成获得利润,符合挂靠关系的特征。
但也有观点认为,网约车司机与平台间不属于挂靠关系。其认为首先,在一般情况下,挂靠人一次性只能挂靠到一家被挂靠单位,不能随意变更。网约车领域,具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的司机,可以同时在任何具备《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的平台注册运营,不属于一对一的挂靠关系。其次,挂靠关系中,挂靠人以被挂靠人名义开展运营,但具体如何运营,挂靠人有很强的自主性。而网约车平台在司机的每一次交易中都深度介入,不符合挂靠要求。第三,挂靠在我国是否定性评价,建筑领域法律没有规定为挂靠而是表述为“借用”,在符合其他类型关系时,不应考虑挂靠关系。
三、零工经济下零工工作者权益的保护
我国法律对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还没有明确的界定,但归入劳务关系来判断能够使得争议的判断更为简洁,不易造成困扰。但劳务关系不适用劳动法,长远来看,对平台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力度较弱,所以基于对零工工作者的保护提出如下建议:
(一)建立除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之外单独用工关系——零工关系
零工关系专属于零工经济形态,能够明确反映出零工经济的用工形态,将劳动者称为“零工工作者”能够正确体现其身份。为了加强平台对零工工作者的管理和控制,可以对加入平台的零工工作者提供岗前培训,为了体现平台属性可定制平台工作服,要求工作者统一着装,体现身份属性。但平台不能随意开除工作者,建立考核机制是不错的选择,对工作者进行定期有效的评价,在保障工作者权益的同时也能保证平台的利益。
零工关系应当主要体现对弱势群体即零工工作者的保护。比如国家出台一最低时薪制,该时薪是指劳动者在完成工作后扣除平台费用每小时所能获得收入的最低限制。这一制度可以防止工作者在各平台之间因恶性竞争故意压低收入或平台利用自身优势收取不合理费用压榨零工工作者,造成利益受损。同时各平台不应对签约工作者施加工作时间或工作量的要求从而保证零工经济的灵活性和多重性。建立零工关系可以给共享经济平台提供一条合法可行的用工出路[4],同时应当明确零工关系的归属,若平台对于某一专职化劳动提供者存在明显的强力控制,其二者间关系归属于劳动关系,如平台招募的运营人员或客服等,以此来规范平台的用工行为,防止平台规避责任,有损工作者利益。
(二)提供社会保障的法律保护
首先,零工工作者较于平台处于劣势,为保障其权益,避免受到劳动损害,强化平台责任,应由平台为其制定相应的保险计划,强制投保或强制加入。平台可以作为投保人为零工工作者购买保险以减轻事故发生时平台所应负担的支出。平台还可以作为中介,代收保险费,要求零工工作者在平台注册时必须购买保险,费用与相关合同由平台代为办理,具有统一性,应遵守有关部门或保险公司的费用标准,不可借机损害工作者利益。同时,零工关系下,平台应充当保护者角色,对零工工作者负担安全保障义务。有学者认为法律应该通过税收体系而不是雇佣关系普遍地适用社会安全网来解决“零工经济”下社会保障不足的问题。根据我国国情,税收体系并不能对接社会保障体系,而可对比类似的劳动关系中的工伤保险制度来补充社会保障的不完备。由于我国基本的城乡的居民基本养老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已覆盖每个人,零工工作者还可通过这一体系来保护自身利益,再将其纳入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领域,从而建立一个完善的安全保护法网。
(三)互联网条件下工会模式创新
工会原意是指基于共同利益而自发组织的社会团体。这个共同利益团体诸如为同一雇主工作的员工,在某一产业领域的个人。工会组织成立的主要意图在于职工权益的保护,可以与雇主谈判工资薪水、工作时限和工作条件等等。互联网的发展为工会提供新的发展模式,零工平台的工作者可通过网络介质如网站、公众号的形式创办并加入工会,利用网络优势创新维权模式为平台工作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四、总结
零工经济是时代的产物,随着经济发展与变化零工工作及零工工作者必然会逐渐增加,我们应顺应其发展趋势,给与零工工作者应得的保护。但零工工作关系能否成立仍需讨论,既不能随意扩大劳动法保护范围,也不可阻碍新兴经济的成长,将零工工作者纳入法律及社会保障的范围或者先行采用互联网工会的形式不失为一种选择。
注 释
[1] 班小辉.“零工经济”下任务化用工的劳动法规制[J].法学评论,2019,37(03):106-118.
[2] 关怀、林嘉.劳动法(2006年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 史尚宽.劳动法原论(1934年版)[M].上海:上海正大印书馆.
[4] 于莹.共享经济用工关系的认定及其法律规制——以认识当前“共享经济”的语域为起点[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21(03):49-60
参考文献
[1] 班小辉.“零工经济”下任务化用工的劳动法规制[J].法学评论,2019,37(03):106-118.
[2] 孔德洲.论网约车主体之法律关系[J].法制与社会,2018(26):211-212.
[3] 薛萍萍.网约私家车模式下平台与司机法律关系分析[J].中外企业家,2019(12):229.
[4] 王全兴,王茜.我国“网约工”的劳动关系认定及权益保护[J].法学,2018(04):57-72.
[5] 郑祁,杨伟国.零工經济的研究视角——基于西方经典文献的述评[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9,36(01):129-137.
[6] 丁晓东.平台革命、零工经济与劳动法的新思维[J].环球法律评论,2018,40(04):87-98.
[7] 图南. 零工经济:自由职业者的新蓝图[N]. 财会信报,2017-12-18(C04).
作者简介:鲍洁莹(1995-),女,汉族,河北秦皇岛市人,天津工业大学2018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济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