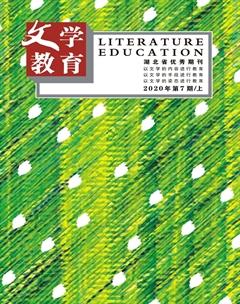《陋室铭》的文化解读
内容摘要:刘禹锡和他的《陋室铭》,千百年来为人们所称道。原因是什么呢?怀着这样的问题,本人“上下求索”,最终决定在文化中寻求解答。因为“人是文化的存在”,一切人的问题,都可能在文化中找到原因和依据。而“文学就是人学”,归根到底,文学的问题,也是文化的问题。本文尝试从个人遭际、陋室文化和文本内涵三个维度来观照《陋室铭》,以期有新的收获。
关键词:陋室 遭际 文化
高尔基曾说过:“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宗旨。”刘禹锡创作了流传千古的《陋室铭》,正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体现,给予后人源源不断的文化滋养,影响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道德情操和品格修养。
那么,我们不禁会问:刘禹锡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陋室铭》?为什么是“陋室”铭而不是其他铭?《陋室铭》又为什么会超越时代获得后人的共鸣?面对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不从文化的视域来观照刘禹锡及他的《陋室铭》,我们理解刘禹锡及其《陋室铭》的价值就会有所欠缺和不足。文化视域下的《陋室铭》,我认为应该至少包括以下三个维度:个人遭际、陋室文化和文本内涵。
一.个人遭际:意气风发的青年与屡遭弃置的中年
说到《陋室铭》,作者刘禹锡的个人遭际和时代背景是不能被忽略的。古代中国有一个重要的文学批评方法,即孟子所提倡的“知人论世”。孟子在《孟子·万章下》中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的意思是说:“吟咏他们的诗,读他们的书,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可以吗?所以要研究他们所处的社会时代。”[1]因此,要想理解《陋室铭》,得先了解刘禹锡的个人生平和当时的社会背景。
(一)青年:意气风发
在讲刘禹锡之前,有必要简单说一些唐代的科举考试。唐代科举考试的科目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明经、进士两科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可见唐代科举录取之难。然而,这样还不能直接做官。常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所以,唐代的科举考试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很多。
刘禹锡生于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其父、祖历任唐朝州县官员,“世以儒学称”。贞元六年(公元790年),刘禹锡游学洛阳、长安,在士林中获得很高声誉。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与柳宗元同榜擢进士及第,同年登博学鸿词科。两年后(公元795~796年)再登吏部取士科,释褐为太子校书。刘禹锡这样的科举过程与初次仕途经历在当时如何呢?我们可以拿刘禹锡和同时期的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比较一下。
韩愈生于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其祖辈都曾在朝或在地方为官,但韩愈年仅三岁时,其父逝世,由兄长韩会夫妇抚养成人;十二岁,兄长去世,由兄嫂郑氏抚养。韩愈于贞元三年至五年(787年-789年)在长安参加了三次科举考试,均失败。直到贞元八年(公元792年),他第四次参加科举考试才进士及第;其后参加了三次博学宏词科考试,到了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仍失败,只好离开长安,去幕府任属官。可见刘禹锡和他同时代的韩愈相比,他是比较幸运的。科举考试和仕途起步,都比韩愈要远远顺利,刘禹锡的青年时代应该称得上是意气风发。
刘禹锡青年的意气风发不仅表现在科举考试和仕途起步,还表现在仕途上“得遇”。刘禹锡仕途起步的官职是太子校书,由此认识了王叔文。当时王叔文担任太子侍读已经快十年,“常言民间疾苦”,深得太子恩宠和赏识。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唐德宗卒,太子李诵即位,是为唐顺宗。唐顺宗即位之后,任命王叔文进行政治改革,史称所谓的“永贞革新”。[2]而刘禹锡与王叔文相善,其才华志向尤受叔文器重,遂被任为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参与对国家财政的管理。他在这期间,刘禹锡政治热情极为高涨,成为王叔文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由此看来,刘禹锡在他的青年时代,真正称得上是意气风发。
(二)中年:屡遭弃置
刘禹锡参与的“永贞革新”,针对当时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政治改革,其主要内容是抑制藩镇势力、反对宦官专权与改革德宗朝各项弊政等,确实对当时的唐朝社会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取消了“宫市”,也就是白居易所写的《卖炭翁》中的那种情形,“百姓相聚,欢呼大喜”。[3]“同年的八月四日(公元805年),唐顺宗禅位,太子李纯即位,即唐宪宗。八月六日,王叔文被贬,“永贞革新”大势已去。九月中旬,刘禹锡与柳宗元等八人先被贬为远州刺史。后来朝廷觉得惩罚的太轻,又加贬他们中的八个人到更远的地方为司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八司马事件”。刘禹锡由青年的意气风发转入了中年的屡遭弃置,当时是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刘禹锡是年34歲。真可谓是“福祸相依”,由先前的青云直上,到发配边疆,令人唏嘘不已。
刘禹锡被贬谪了多长时间呢?初贬为连州(现今湖南常德)司马。元和九年十二月(公元815年2月),奉召回京。次年三月(公元816年),因作《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得罪执政,次贬连州(今广东连州市)刺史,又近五年。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因母丧离开连州。长庆元年(821年)冬,刘禹锡被任为夔州(今重庆奉节县)刺史。长庆四年(824年)夏,调任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在这期间,创作了《陋室铭》;直到宝历二年(公元826年),他才回到洛阳,任职于东都尚书省。
刘禹锡从初次被贬到最后回东都洛阳任职,前后共经历了二十三年。在这期间,他写给白居易的一首诗,也印证了他中年的屡遭贬谪,即著名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是刘禹锡被贬二十三年生活的如实写照和真实心情。在刘禹锡被贬谪期间,他的好友柳宗元于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卒于柳州刺史之任。虽然柳宗元的英年早逝与他自己的身体和心态有很大关系,但也足以侧面印证屡遭被贬对一个人的重要影响。刘禹锡与柳宗元相比,毕竟是幸运的,他在自己53岁的时候活着回到了东都洛阳。
刘禹锡的性格和信心是否会因为屡遭贬谪而改变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他的《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此诗深刻的讽刺了当时朝廷的新贵,显示了刘禹锡不与他们同流合污的高尚品格以及对朝廷新贵的蔑视。被贬还未结束时,刘禹锡创作了《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一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聽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又向我们表明了他豪迈的性格和对自己未来坚定的信心。长期而又艰苦的贬谪生活,磨练了刘禹锡更加豪迈的性格,更加坚定的信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逆境中的刘禹锡,正是自强不息文化的代表之一。
我想,了解和认识刘禹锡的个人遭际和时代背景,以及他身上的中国传统自强不息的文化因子,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理解《陋室铭》的文化内涵。
二.陋室文化:儒家的陋室传统与士人的道德追求
说到《陋室铭》,“陋室”肯定是绕不开的话题。那什么是“陋室”?或者“陋室”是怎样的处所?我想,这应该是我们理解“陋室”的前提与基础。众所周知,汉字是表意文字,它的音形义结合在一起。所以,它的每个字都有本义和引申义。我们理解“陋室”的含义,不仅要对其作本义的考据,也要重视其引申含义,而引申义往往又有传统文化的渗透,会赋予新的意义。那么,下面我们就对陋室进行一番“咬文嚼字”,看看陋室在传统文化视域中有怎样的内涵。
(一)儒家的陋室传统
“陋”字,在白话版的《说文解字》中是这样记载的:陋,交通不便的山隅,字形采用“左耳旁”(阜)作边旁,采用“”作声旁。从结构上来说,有部首“阜”和音旁“”构成。“阜”为石阶,代表荒山旷野。“”的左下部分为“匚”(半封闭的空间)+右上部分“”(内,疑为“穴”的误写),表示原始的穴居。当“”作为单纯字件后,强调远离市井城区。隶书“”将篆文字形中的“”写成左耳旁“”。所以,“陋”的造字本义为:偏远、封闭、狭隘的生活空间。那“室”的本义又是什么?
“室”字,在白话版的《说文解字》中是这样记载的:室,内室。字形采用“宀”、“至”会义。“至”,表示一天奔波后的停歇。“至”,既是声旁也是形旁,是“到”和“倒”的本字,表示倒卧、躺下。“室”,由“宀”(房屋)+“至”(躺下),表示倒卧睡觉的房屋。所以,“室”的造字本义是:正屋。在古代中国,妻住的屋子叫“室”,妾住的屋子叫“房”。因此,“陋”字和“室”字连在一起组成“陋室”,本义为偏远、封闭、狭隘的正屋,是家里主人居住的地方。那“陋室”的引申义又什么?
“陋室”一词,在儒家经典《论语》中至少出现过两次。在《论语·雍也》中,孔子评价他最认可的弟子颜回时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句话的意思是:“颜回多么有修养啊!一竹筐饭,一瓜瓢饮,住在小巷子里,别人都受不了那穷苦的忧愁,颜回却不改变他自有的快乐。颜回多么有修养呀!”这句话中的“陋室”在杨伯峻的翻译中解释为“小巷子”,[4]其实也可以解释为“狭窄的居住空间”。在孔子的眼中,“陋室”与个人道德修养联系在一起。“在陋巷”,其他人“不堪忧”,而颜回却“不改其乐”,孔子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应该是带着自豪和赞叹的语气!之所以这样判断,是因为孔子还在《论语·里仁》中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这就是著名的“见贤思齐”说。而颜回又是孔子眼中的“贤”。所以,在孔子的提倡下,以颜回为代表的陋室文化逐渐成为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实,不仅颜回“在陋巷”不改其乐,而且孔子本人也想要“居陋”,还为此而辩。在《论语·子罕》中,有这样的记载:“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此句话的意思是:孔子想要搬到九夷去住。有人说:“那地方非常简陋,怎么好住?”孔子道:“有君子去住,就不简陋了。”[5]由此可以看出,孔子不仅赞赏颜回的“在陋巷”,而且自己还身体力行,并赋予居住空间新的内涵——有“君子”而“何陋”,即有德不陋。此句话,也是《陋室铭》最后一句话“何陋之有”的出处。孔子对陋室及其陋室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也深刻的影响了后代的士人。在别人与孔子的对话中,“陋”也应该包括边远的地区,即古代常说的远离中原的蛮荒之地。在刘禹锡的个人遭际方面,我们已经提到他家“世以儒学称”,对陋室文化必然了若指掌,根植于他思想,并且在适当的时机(比如在边远之地和居陋室的时候)会表现出来。
(二)士人的道德追求
如果光有“陋室”这个外在因素,没有居住之人的德行,是不能形成陋室文化的。士人的道德追求,是一个具有复杂内涵的论题,这里不展开论述。在此文中,我们所说的士人道德追求,指的就是刘禹锡的道德追求。刘禹锡作为儒学世家的成员之一,其个人的道德追求也大致符合儒家的道德追求。纵观刘禹锡中年屡遭贬谪的经历以及一些相应的作品,我们也可以从中窥探到他的道德追求。
在刘禹锡被贬初期,他创作了《秋词二首》。其中的一首:“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为人们所称道。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在逆境中的豪情。还有在刘禹锡被贬辗转之际,他显得更为坚韧,又陆陆续续创作了《浪淘沙九首》,其中第八首为:“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刘禹锡的道德追求不但没有消退,反而显得更加成熟和理性。刘禹锡从古时夔州人民淘金的劳动生活场景中,生发出了唯物主义的哲理,即是金子就不怕被埋没,总有一天会发光发亮。在刘禹锡被贬谪的晚期,他在扬州遇见了白居易,写下了那首著名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更是生发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感慨,也蕴含着他对未来坚定的自信。
面对屡遭贬谪,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在支撑着刘禹锡?我想,还是应该从他所信奉的儒家文化中去寻找。《论语·里仁》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这句话的意思是:“君子没有吃完一餐饭的时间离开仁德,就是在仓促匆忙的时候一定和仁德同在,就是在颠沛流离的时候一定和仁德同在。”[6]刘禹锡长达二十三年的贬谪生活,有谁能说他不是“仓促匆忙”,有谁能说他不是“颠沛流离”。而他始终不违“仁”,也就是他不违反自己的道德追求。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刘禹锡在他的被贬谪期间,基本上是坚守他自己的思想道德追求。那么,在刘禹锡被贬结束之后,他会不会有所松懈呢?读刘禹锡的两首《游玄都观》,我们或许会找到心中的那个答案。
第一首《游玄都观》,写于刘禹锡第一次被贬回长安之时,也正是因为这首诗,他很快被贬到更远的地方去。《游玄都观》如下:“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全诗对当时朝廷趋炎附势之徒和当权新贵的讽刺是辛辣的,态度是蔑视的,一点也不会因为自己遇赦就与那些人妥协。第二首《再游玄都观》,更加表明了这一点,它写于刘禹锡被贬结束之后(公元828年)。这时候皇帝早已变成了唐文宗,玄都观也破败了。《再游玄都观》如下:“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此诗表面说的是花事变迁,实质暗寓当时朝廷当权者的消亡,而刘郎又“胜利”归来。再一次显示出刘禹锡不变的道德追求和豪放精神。刘禹锡逆境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道德追求,不禁使人想到孟子说过的一句话“此之谓大丈夫”。
我们经过梳理儒家的陋室传统和士人的道德追求,明白了刘禹锡写作《陋室铭》时的心理以及背后的文化支撑,也对《陋室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有了更近一步的认识。
三.文本内涵:兴比的艺术手法与隐喻的文化意象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7]其意思是:“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人的年龄寿夭有时间的限制,荣誉欢乐也只能终于一身,二者都终止于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样永久流传,没有穷期。”我想:《陋室铭》应该属于曹丕所说的那类文章,即能流传无穷。那么,《陋室铭》流传于后世的原因是什么?肯定与文本所表现的文化内涵有密切联系。实际上,《陋室铭》使用的兴比的艺术手法和隐喻的文化意象,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一)兴比的艺术手法
《陋室铭》中使用的艺术手法丰富多样,如对偶、比兴、互文等,但最为人称道的是兴比的藝术手法。《陋室铭》开头和结尾的句子分别用的是兴和比的手法。“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这些句子使用了“兴”和“比”的艺术手法,符合中国人认识事物的传统方式,也能获得广泛的共鸣。
“兴”和“比”的艺术手法,在《诗经》中运用的最为广泛。所谓的“兴”就是见物起兴,先见到一个外物,引发你内心的感想。从“心”与“物”的关系来看,这种表现方法是由“物”及心,也就是说,由形象过渡到情意。[8]如《关雎》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是典型的起兴艺术手法。先见到河边成双成对的关雎鸟,都有美好的伴侣,想到人也应该有美好的伴侣,即“君子”也应该寻找“淑女”。所谓的“比”就是以此例彼:用一件事情来比喻另一件事情。从形象和情意的关系来看,是先有情意,后有形象,二者的关系是由“心”及“物”的。[9]如《硕鼠》中“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就是典型的用“比”的艺术手法。因为从理性上讲,人不可能去服侍肥大的老鼠,所以硕鼠一定另有所指。在这里,作者显然用老鼠来比喻那些剥削者,表明当时的剥削者对普通民众的压榨和迫害之深。“兴”“比”的艺术手法,是中国古代诗歌及其他文学作品中常用的艺术手法,刘禹锡在《陋室铭》中将它们使用的很自然,易于被人们所接受。弄清楚了“兴”和“比”这两种艺术手法,我们接下来继续探讨《陋室铭》是如何分别使用“兴”和“比”的。
《陋室铭》开头三句话:“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由山引出仙,由水引出龙,由陋室引出德馨。有人就会产生疑问:那么多山和水,能让人起的的东西很多,为什么偏偏刘禹锡想到的就是仙和龙。其实,这是刘禹锡翻用刘义庆所著《世说新语·排调》中“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的结果。从山水起兴到陋室,刘禹锡的起兴可谓运用的恰到好处,更为巧妙的是从有仙山才出名和有龙水才神异的意义起兴到陋室有德才馨的结论,由外部世界过渡到内在境界,可谓是巧用典故,胜意迭出。所以,刘禹锡将陋室与品德紧密结合起来的做法和用意,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中国传统的陋室文化,是他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
《陋室铭》结尾也是三句话:“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刘禹锡用诸葛庐(诸葛亮隐居时所住的草庐)和子云亭(西汉大作家扬雄在未成名之前居住的简陋处所),比喻自己所居地方之陋,并借孔子之口,表明陋室不陋,是因为有君子(有德行的人,即诸葛亮和扬雄,他们二人是各自时期儒家文化的代表之一)居之。比较开头“兴”和结尾“比”的,我们会发现意象出现的顺序很有意思。开头的“兴”是由远及近;结尾的“比”,按照时代顺序排列,却是由唐到春秋,由近及远,两两相对,妙趣横生。结尾更妙的是借孔子之口说“何陋之有”,将刘禹锡“惟吾德馨”的主旨上升到儒家圣人——孔子所认同的高度,可谓是上下古今,融为一体,意味深长,带有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息。总之,刘禹锡在《陋室铭》中将“兴”和“比”的艺术手法使用的炉火纯青又水到渠成,值得后人在写作时进行模仿和借鉴。
(二)隐喻的文化意象
高超巧妙的艺术手法固然能使《陋室铭》的文化魅力增加不少,但它的文章内容更为至关重要,才是决定其长久流传的内在根本。《陋室铭》的文体是一种“铭”,以短小精练著称,言简而意远,必然要求在创作之时非常讲究意象的选取和安排。我们有理由相信:刘禹锡在写作本文的时候,肯定精心挑选和遣用了意象。事实也正是如此,人们只要读过这篇文章,就会轻易地发现这一点。
在探讨《陋室铭》所表现出的隐喻的文化意向,我要先补充两个文学理论观点,即孟子的“以意逆志”和荣格的“原型理论”。孟子在《孟子·万章上》中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所以解说诗的人,不要拘泥于文字而误解词句,也不要拘泥于词句而误解文意。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推测作者的本意,这就对了。”[10]因此,在理解《陋室铭》文意的时候,也要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推测刘禹锡在此文中所表达的本意。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重视意象本身的文化内涵。文学写作虽然是发生在作家个体心灵世界的事件,但是文学作品总是属于整个人类。荣格说:“每一个原型意象中都有着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都有着在我们祖先的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和悲哀的一点残余……一个用原始意象说话的人,是在同时用千万个人的声音说话。他吸引、压倒并且与此同时提升了他正在寻找表现的观念,使这些观念超出了偶然的暂时的意义,进入永恒的王国。”[11]从“原型理论”来说,关注《陋室铭》中出现的文本意象,是必要的,也是我们可以到达其文化内涵的可能途径。
接下来,我们就探讨一下《陋室铭》中都有哪些意象?开头三句和结尾三句都已在前文有所涉及,其中包含不少典故,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此就不再赘述。实际上,《陋室铭》中需要关注的文化意象遍布全文,使文章充满了隐喻或象征,营造了丰厚的文化空间。下面我就从陋室的景、人、趣和事四个方面,论述《陋室铭》文本意象背后隐喻的文化内涵。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这一句描绘了陋室景色的清幽雅致,充满自然之美。“苔痕”,就是苔藓生长留下的痕迹。“苔”这种植物常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而且看上去很不起眼,但它的生命力及其顽强,常在不经意间慢慢长成一大片,留下痕迹。这是“苔”的生物属性,也是它文化意蕴的基础。“苔”最早见于诗赋,是在《汉书·外戚传第六十·孝成班婕妤》的《自悼赋》中:“华殿尘兮玉阶苔,中庭萋兮绿草生。”在这句话中,能明显地看出“‘苔是冷宫幽清寂寥的体现,载负着女子的淡淡哀怨。”[12]由此可见,“苔”出现在古诗文中,就带有幽独自怜的隐喻色彩。等到了唐代,“苔”的文化内涵更加的丰富和多元化。刘禹锡在自己的诗歌中还写到过“苔”。他在苏州所作的《西山兰若试茶歌》中有这样一句:“阳崖阴岭各殊气,未若竹下莓苔地”。可见在刘禹锡的审美情趣中,“苔”是高雅清静的象征,也是他对“苔”偏爱的原因。回到《陋室铭》中的“苔”,我们会发现刘禹锡在描绘陋室环境时,他是有目的的选择了“苔”这种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意象,而且还有所创新。在刘禹锡的眼中,“苔”不是幽独自怜的,“苔”和后面的动词“上”字联系在一起,不禁让人想到“苔”不因环境恶劣而努力向上生长的状态,还让人想到刘禹锡身处逆境而力争上游的自信,实在是让人心生敬意!而且一個“绿”字,不仅表现了“苔”具有欣欣向荣的强大生命力,而且展现它多而密的特点,都让台阶显出了绿色。“苔”的意象,不仅暗喻了刘禹锡身处逆境的现实,“也展现了唐朝广阔的社会生活与诗人丰富细腻的情感世界”。[13]刘禹锡以微小之“苔”,带给读者不尽的文化想象和审美体验,确实使“苔”的意象进入了一个新的艺术境界。
“草色入帘青”中“草”的意象,也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草”在大自然中也是到处存在的,比起前面的“苔”,它可能更受到人们的关注。在中国的北方,草一般春生夏荣秋枯冬灭,人们从草的生长过程,很容易想到季节的交替和生命的周期,草就不仅仅是大自然中一种植物,而是与人乃至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一种特有意象。“草”这一文化意象,《诗经》中就已经有,“它只是起兴的媒介,或者描写当时的客观环境起‘赋的作用,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寄托意义”。[14]等到《楚辞》出现,“草”在屈原的笔下就被赋予了不少特定的文化内涵。比如屈原在《离骚》中用“香草美人”来指自喻,代指忠贞贤良之士。等到唐代,“草”的意象在诗文中就更司空见惯。刘禹锡的好友白居易,就曾写过著名的《钱塘湖春行》,其中“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就形象描绘了春天“草”刚刚生长的样子,清新而有无限生机。此外,白居易还写了家喻户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首诗不仅写出了草生命力的顽强,更蕴含着对草自强不息精神的高度赞颂。当然,刘禹锡笔下的“草”,与白居易笔下的“草”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且来看刘禹锡是怎么描绘《陋室铭》中的“草”。“草色入帘青”,就是说草色青青葱葱,快要映入陋室里面(入帘,我认为在这里解释为室内比较合理,而不是一般所理解的帘里)。一个“入”字,不仅写出草的生长态势,都快要生长到陋室内,还暗喻陋室前面人烟稀少。这时候就需要孟子的“以意逆志”了。试想一下,刘禹锡当时作为贬谪之人,谁又会来拜访和关注他呢?如果这时刘禹锡是飞黄腾达的,我想来来往往的人早把他的门槛踏破了,哪里还会有什么“苔痕”和“草色”?家里早就“寸草不生”了,迎来送往的脚步应该会把那些“苔草”“踩灭”掉。一个“青”字,也是在写草的繁茂,衬托陋室的幽静。“草”的意象,就这样在刘禹锡的笔下具有新的文化内涵。陋室之景的文化内涵,分析到这里先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继续分析陋室中的交往之人。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个句子其实很有意思。调换句子中“有鸿儒”和“无白丁”,句子就变成了“谈笑无白丁,往来有鸿儒”,句子意思大致一样,因为这两句使用了互文的修辞手法,意思是相辅相成的。“谈笑有鸿儒”中的“鸿儒”,就是一个典型的传统文化意象。“鸿儒”即大儒,是博学多识的代表,这是千百年人们的共识。“白丁”,这个意象可能需要进一步的辨析。“白丁”的解释,向来有两种:人教社旧版语文教材(八年级上)对其注释为:“平民”;而人教社最新版语文教材(七年级下)对“白丁”注释为:“平民,指没有功名的人”。无论哪一种解释,代入《陋室铭》的语境中,都显得与刘禹锡的人品和节操有些突兀。这种解释,有人就认为“这怎能体现其宣称的‘惟吾德馨'呢?这岂不与本文主题相悖?”[15]其实,“白丁”的文化内涵非常丰厚。“丁”,在这里解释为男子,没有疑意。关键是“白”的解释。我们可以把“白”还原到语境中去理解。我认为:在语境中,“白”与“鸿”的词性一样,意思相对。因为这是句式决定的,从互文的修辞手法也可以看出这一点。“鸿”在这里指博学多识,那“白”大概率也与学问有关系,根据前面的否定词“无”,可以得出结论:“白”可能是学问少的意思。“白丁”可能就是指学问少的男子,也就是没有学问的人。“无白丁”就是有学问的人。至此,我们可以把刘禹锡陋室中交往之人的特点概括出来:博学多识,这也符合传统文化的交友之道。也暗喻刘禹锡的学问之高和品行之高。
说了陋室的景和人,这两方面可以说是刘禹锡陋室生活的外在表现,那刘禹锡的内在生活又是怎样呢?我们继续探讨陋室的趣和事。下面先从“趣”开始说起。众所周知,琴棋书画是中国古代人的文房四宝,它们“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成为中国历代文人必备之修养”。[16]“可以调素琴”,“琴”作为文房四宝之首,文化内涵自古源远流长。春秋时伯牙与钟子期就是琴文化的典型代表。伯牙鼓琴,钟子期听其音便知其高山流水之意。等到钟子期死后,伯牙便不复鼓琴。这时,“琴”的意象,便是知音文化的代表。后世的文人,或用“琴”来比如夫妻和谐,如琴瑟和谐;或用“琴”来表示独处修身,如王维的《竹里馆》中“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总之,“琴”的意象出现在陋室中,多维度展现了刘禹锡的人生趣味,具有了文化的广度和深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符号和象征。“阅金经”向来解释不为统一,但不外乎两种:第一种是珍贵儒家经典;第二种是佛教的《金刚经》,即佛教经典。无论哪一种解释,但都指向中國传统的文化经典,隐喻刘禹锡自己的读书之高雅品味。在清幽雅致的环境里,来来往往的都是博学之士,或弹琴,或读书,是多么的逍遥自在,小“陋室”自有大文化。
最后,我们来探讨陋室之事。大多数的人将“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放在陋室之趣。但我认为这句更多的是在说陋室之事,因为从文化内涵上来讲,“丝竹”和“案牍“都是指”事”。这句话中的“丝”代指古代指弦乐器,“竹”代指古代管乐器,“丝竹”合起来就是音乐的总称。《吕氏春秋·侈乐》就说:“为金石之声则若霆,为丝竹歌舞之声则若噪。”[17]就是说“丝竹”之声自古显得的嘈杂。因为以“‘丝竹类乐器为中心的娱乐、燕享性乐队,主要用于私密的休闲、内室娱乐性宴会场所”,[18]以衬托宴会的热烈气氛,而显得嘈杂乱耳。我想,刘禹锡用“无丝竹之乱耳”,应该指的是陋室没有宴会欢乐之事。刘禹锡作为被贬谪之人,时人往往避之唯恐不及,哪里会有欧阳修所说的“众宾欢也”,这样下来,“耳朵”当然是清静的了。在宴会私事如此,在官府公事上也同样如此。“无案牍之劳形”,把自己无公事的纷扰说的一语中的。反过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想:没有官府公事的烦扰,会不会是儒家“无为而治”的一种体现,或者说这是刘禹锡的期待。刘禹锡在《陋室铭》中说“唯吾德馨”,是符合朱熹“无为而治者,圣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为也”。[19]这可能就是刘禹锡“德化式”“无为而治”。[20]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百姓,是古代大多数士人的志向和追求。刘禹锡在“无案牍之劳形”的境况下,虽然有点受冷遇而生落寞之感,但又尝不是他本人对儒家理想社会的一种期待和坚守。由此看来,刘禹锡在陋室之事上,也有着非常多的可解读的文化内涵。
《陋室铭》文本所表现的景、人、趣和事的意象,使其充满了隐喻色彩,展现了其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令后人在其中“寻幽探胜”,感受传统文化的洗礼与熏陶。
刘禹锡不因个人遭际而改变其高尚品行,已经使他成为陋室文化的代表。而《陋室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更是道不尽和说不完。“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们对《陋室铭》的文化解读,也应如是。见其为人,思其源头,感其文化,不仅能帮助我们穿越人生的逆境而保持自我,而且警醒当下“趋华屋而德不行”的社会现实。这或许就是刘禹锡和《陋室铭》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渗透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中,生生不息。
注 释
[1][10]杨伯峻.孟子译注(简体字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8:193,167.
[2]黄永年.唐诗十二讲[M].北京:中华书局,2007:133.
[3]康震.康震讲柳宗元[M].北京:中华书局,2018:9.
[4][5][6]杨伯峻.孔子译注(简体字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6:65,66,105,39.
[7]李壮鹰,李春青主编.中国古代文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31.
[8][9]叶嘉莹.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2008:19,20.
[11][瑞士]荣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J],心理学与文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121.
[12]吴紫熠.先唐苔意象之文化意蕴及其在唐诗中的流变[J].遂宁: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2018(1),58.
[13]李晓彤.唐诗苔藓意象研究[D].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2017,33.
[14]王小艳.唐宋诗词中草意象的丰富内蕴[J].延安:延安大学学报 ,2015(6),90.
[15]罗献中.《陋室铭》“白丁”释义辨疑[J].廊坊:语文教学之友,2019(4),31.
[16]陈辉,施一南.琴棋书画——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四朵奇葩[J].北京:艺术人生2011(6),150.
[17]杨坚点校.吕氏春秋·淮南子[M].长沙:岳麓书社,1989,31.
[18]伍国栋.“江南丝竹”概念及研究述评[J].南京:艺术百家,2008(1),167.
[1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162.
[20]王海成.儒家“无为而治”思想的理论特质和当代意义[J].哈尔滨:学术交流,2016(1),28.
(作者介绍:侯成岗,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6届硕士毕业生,现供教于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丰台实验学校初中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