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家书》:“赤子孤独了”
赵晓霞
自古及今,家书都是最能打动人心,也最为真实感人的文字。扬雄《法言》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家书就是真正的“心声”与“心画”。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说:“杼轴乎尺素,抑扬乎寸心”,意思是,组织辞采于尺素之上,字里行间荡漾着方寸之心。这也就是西方人所说的“最温柔的艺术”。
家书是最能表现亲人心灵的文字。抒写心灵的文字很多,不过,大都不是专门写给家人的,无论是“感天地,动鬼神”的诗文,还是“心事浩茫”却“不欲人知”的日记,多是如此。而真正能够和自己的亲人袒露心声、表现心灵的,自然就是家书了。
家书是最能寄托家人情感的文字。古人因为交通、交流的不便,家书便成了最为直接的情感承载。今天所见我国最早的家书,是1975年湖北云梦出土的两封战国晚期的家书,由名叫“黑夫”和“惊”的人,写给他的哥哥“衷”。我们看这两封信,所表达的就是对父母兄弟、妻儿老小的问候与牵挂,以及生活的琐碎与艰难。后来杜甫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张籍的“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等,也无非就是这样的情感罢了。
家书是最能体现家庭教育的文字。我国传统的家庭教育有多种形式,其中之一就是通过家书实现的。从刘邦的《手敕太子文》开始,就以家书来宣教垂训;此后,司马谈的《命子迁》、刘向的《诫子歆书》、马援的《诫兄子严、敦书》、曹操的《戒子植》、诸葛亮的《诫子书》、刘备的《遗太子敕》、司马光的《训俭示康》、苏轼的《与侄千之书》、朱熹的《与长子受之》,以及闻名遐迩的《曾国藩家书》《梁启超家书》《傅雷家书》等,都是独具情抱的家教、家训文字。
职是之故,我们特别选择了《曾国藩家书》《梁启超家书》《傅雷家书》以及龙应台母子的《亲爱的安德烈》,以期和读者共同从家书中体味隽永的人生挚情。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世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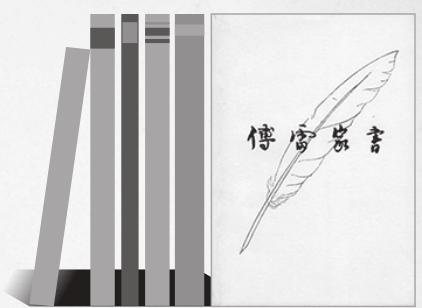
《傅雷家书》记录了从1954到1966年12年间,傅雷夫妇与其子傅聪和傅敏的书信往来。傅敏在2016年再版后记中讲道:
父母的家信不是为了发表而创作,只是普通的家信,写在纸上的家常话。1981年我将这些家信辑集成书,公之于众,是为了纪念自己的父母,寄托我们的哀思。
当打开这将近两百通家信,品读这些“家常话”,却令人惊叹:它为我们打开了一个赤子创造的世界。
为人:“先为人,次为艺术家”
“先为人,次为艺术家,再为音乐家,终为钢琴家。”(1960.12.31。傅雷,朱梅馥,傅聪著,傅敏编《傅雷家书》,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下同)。“为人”是根本,根本做到了,才能在艺术上开出最美的花朵。这是傅雷夫妇始终秉持的教育信条。
如何“为人”,用傅雷的话来讲,即不失“赤子之心”。
(一)“赤子之心”在生活中,是传统的“温良恭俭让”
一方面傅雷教导孩子对人要诚挚:“我一生做事,总是第一坦白,第二坦白,第三还是坦白……得拿出勇气来面对事实,用最正大光明的态度来应付。”(1955.5.11)在生活的细节上,有礼有节,同时秉持正直、刚强的道德规范。无论是对老师、朋友、乳母等,都能够不忘恩情。如傅聪离开波兰后,母亲始终提点他:“你们的结婚照片千万别忘了寄给杰老师……”(1961.1.5)
另一方面,傅雷自己则树立了榜样。1961年,物资紧张,度日艰难。从朱梅馥写给傅聪的信中可以看到傅雷的君子之風:“每次要你寄食物的单子,他都一再踌躇……他想到你为了多挣钱,势必要多开音乐会,以致疲于奔命,有伤身体,因此心里老是忐忑不安,说不出的内疚……此中痛苦,此中顾虑,你万万想不到。”(1961.4.20)生活困窘却不愿向孩子伸手,是傅雷凡事不麻烦别人的处事原则。而此时精神的苦闷也甘愿独自承受。1958-1961年间,傅雷被错误地化为“右派”,辛勤翻译的译著无法出版,不断受到批判……这一切都是事后才由朱梅馥告诉孩子的。即便身处困顿,傅雷仍保持君子的体面,还劝勉孩子“个人的荣辱得失事小,国家的荣辱得失事大”(1961.10.1),更是令人心生敬仰。
(二)“赤子之心”在事业上,是“士不可以不弘毅”
当傅聪远赴波兰深造时,他提醒道:“少年得志,更要想到‘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更要战战兢兢,不负国人对你期望。”(1954.3.24)当傅聪代表中国参加肖邦音乐大赛并获得大奖时,他劝勉他:“我始终是中国儒家的门徒,遇到极盛的事,必定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格外郑重、危惧、戒备的感觉。”(1955.3.20)傅雷始终引导孩子成为有社会担当的人,不汲汲于小我的满足。
在傅雷的眼里,始终有“大我”与“小我”之辨。所谓“大我”,即追求学问第一,艺术第一,真理第一。“无论男女,只有把兴趣集中在事业上、学问上、艺术上,尽量抛开渺小的自我,才有快活的可能,才觉得活的有意义。”(1960.8.29)因为有“大我”,即便是面对人生的苦闷和矛盾,“倘是忧时忧国,不是为小我打算而是为了社会福利、人类前途而感到苦闷,因为出发点是正义,是理想,是热爱,所以即有矛盾,对己对人都无害处,倒反能逼自己做出一些小小的贡献来。”(1961.2.7)
傅雷以儒家“仁以为己任”的价值观来教育孩子。他不赞同傅聪祖岳母只笼统地培养子女做“好人”的观念,认为没有弄清教育的目的。“在我看来,她所谓好人实在是非常狭小的,限于respectable(正派的)而从未想到更积极更扩大的天地和理想……她从未认识到人的伟大是在于帮助别人,受教育的目的只是培养和积聚更大的力量去帮助别人。”(1961.7.7)或许傅雷眼里的理想的“人”,当是《论语》中“士不可以不弘毅”的“士”,《孟子》所称道的“大丈夫”,抑或《学记》中“化民易俗”的“君子”。
(三)“赤子之心”在艺术中,是第一把金钥匙
在艺术上永葆赤子之心的人,才能走得更远。傅雷深刻地道出了二者的辩证关系:“大多数从事艺术的人,缺少真诚。因为不够真诚,一切都在嘴里随便说说,当作唬人的幌子,装自己的门面,实际只是拾人牙慧,并非真有所感。所以他们对作家决不能深入体会,先是对自己就没有深入分析过。”没有“情动于中”,何以有真正的艺术?因此,“真诚是第一把艺术的钥匙……有了真诚,才会有虚心,有了虚心,才肯丢开自己去了解别人,也才能放下虚伪的自尊心去了解自己。建筑在了解自己了解别人上面的爱,才不是盲目的爱。”(1956.2.29)《乐记》讲“惟乐不可以为伪”,在傅雷的世界里,不仅是音乐,诗歌、小说、戏剧、绘画、雕塑,都何尝不是以十二分的赤诚来面对。
傅聪则正是践行父亲庭训遨游在艺术的海洋。1955年,傅聪的音乐会在国外大获成功,一位曾获萧邦音乐会大奖的钢琴家盛赞傅聪的演奏:“这种天赋很难说来自何方,多半是来自心灵的纯洁;唯有这样纯洁到像明镜一般的心灵才会给艺术家这种情感,这种激情。”另一位教授则评价:“所有的波兰钢琴家都不懂萧邦,唯有你这个中国人感受到了萧邦。”(1955.1.26)这大概就是傅雷以“赤子之心”做人、做艺术的教育信条在傅聪身上发生了作用。
1965年傅聪写道:“我一天比一天体会到小时候爸爸说的‘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我在艺术上的成绩、缺点,和我做人的成绩、缺点是分不开的;也有的是做人的缺点,在艺术上倒是好处,譬如‘不失赤子之心。其实我自己认为尽管用到做人上面难些,常常上当,我也宁可如此。”(1965.5.18)闻思而行诸,艺术人生的合一,傅聪在而立之年就已经做到了。
为学:“听无音之音者聪”
“任何艺术品都有一部分含蓄的东西,在文学上叫作言有尽而意无穷,……真正的演奏家应当努力去体会这个潜在的境界(即淮南子所谓‘听无音之音者聪)。”(1965.2.20)“听无音之音者聪”,是艺术追求的大境界,是自称高格的境界。
(一)道器融通:从工匠到艺术家
任何艺术都离不开精湛的技巧。正如《学记》讲“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我们看到,这一时期的傅聪每日练琴少则8小时,多达12小时,非常之勤奋。当傅雷发现傅聪在演奏时身体有“摇动”,便反复探讨劝诫:“唯有肉体静止,精神的活动才最圆满,这是千古不变的定律。”(1955.3.15)关于弹琴“放松”的技巧,傅雷更是不厌其烦地予以关注和指点,探讨竟达十余处。如一开始讲技巧:“所谓放松,是一切力量都是自然的,不用外加的力。”(1954.8.13)到后来:“似乎你说的relax(放松)不是五六年以前谈的纯粹技巧上的relax,而主要是精神、感情、情绪、思想上的一种安详、闲适、淡泊、超逸的境界。”(1961.8.31)正是秉持这种严谨的为学精神,才能在艺术的探索中见“道”。
追求技巧,又不止于“器”。钢琴家李赫特与傅聪谈起:“音乐是主要的,技巧必须从音乐里去练。”(1954.11.14)傅雷得知后深表赞同:“技巧和音乐是宾主关系……艺术是目的,技巧是手段:老是只注意手段的人,必然会忘了他的目的。”(1954.11.23)绘画艺术也是如此,“倘若单从形与色方面去追求,未免舍本逐末,犯了形式主义的大毛病。”(1954.10.22)
音乐是道,技巧是器,要做到由器见道;这与傅雷先为人,次为艺术家的人生哲学息息相通。他多次提醒傅聪:太偏重以音乐本身去领会音乐……但与音乐以外的别的艺术,尤其是大自然,實际上接触太少……久而久之会减少艺术的新鲜气息。(1961.10.5)他多次建议傅聪去森林或上博物馆,以此丰富精神世界,并不辞辛苦为傅聪抄录《艺术哲学》“希腊的雕塑”的译文,以提升其艺术气度。
(二)诗乐融通:唐诗与古典音乐的互训
傅雷以中国诗解读西方古典音乐的部分,无疑是本书最为妙曼的艺术探索。
“上星期我替恩德讲《长恨歌》与《琵琶行》,觉得大有妙处。白居易对音节与情绪的关系悟得很深。凡是转到伤感的地方,必定改用仄声。《琵琶行》中‘大弦嘈嘈‘小弦切切一段,好比Staccato(断音),像琵琶的声音极切;而‘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几句,等于一个长的pause(休止);‘银瓶……水浆迸两句,又是突然的attack(明确起音),声势雄壮。”(1954.2.28)这里,傅雷另辟蹊径以音乐解读唐诗,不得不说非常精彩。中国古代诗歌自古即有很强的音乐性,傅雷则注意到古代诗、词唱法的逸失,对我们理解古诗提供了新的门径。
音乐可以解诗,诗同样可以解音乐,这就是诗与乐的互训。
傅聪说:“萧邦是非常真情的,他的音乐最富于情感,却又那样的精妙;他是真正的诗人”。(1956.1.10)傅雷回应道:“你提到萧邦的音乐有‘非人世的气息,想必你早体会到……我觉得这一点近于李白,李白尽管飘飘欲仙,却不是德彪西那一派纯粹造型与讲气氛的。”(1956.1.22)傅聪继续回应:“我想音乐家中诗人气息如萧邦那样的,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萧邦在音乐家中的独一无二,就像诗人中之李白……李白的那种境界尤其特殊,像他那样的浩气、才华、幻想的高远,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了。”(1956.2.1)后来傅聪又说:“除了音乐,我的精神上的养料就是诗了。还是那个李白,那个热情澎湃的李白,念他的诗,不能不被他的力量震撼。”(1958.1.8)
这一番艺术对话真可谓“致广大而尽精微”,跨越时间、地域和文化,李白和萧邦,诗与乐,竟然能够这样彼此照见、光华闪耀。
(三)中西合璧:淡泊超脱与热情深邃何以相遇
中西文化的差异如鸿沟。傅雷说:要真正达成东西融通的人不是没有,只是“稀如星凤”。而他和傅聪都努力尝试。傅雷这样形容东方人格:
比起近代的西方人来,我们中华民族更接近古代的希腊人,因此更自然、更健康……亲切、熨帖、温厚、惆怅、凄凉,而又对人生常带哲学意味极浓的深思默想;爱人生,恋念人生而又随时准备飘然远行,高蹈,洒脱,遗世独立,解脱一切等等的表现,岂不是我们汉晋六朝唐宋以来的文学中屡见不鲜的吗?(1961.2.6)
傅雷以其非凡的审美洞察力,提炼出中国人的文化品格,而这又源于中国人不滞于物,不为物役的人生哲学。这样的提炼,令我们心向往之。因为我们如何理解过去,实际上是帮助我们理解当下、面向未来。
傅聪则以音乐家的视野看到东西差异的“水平”和“垂直”之分:
西方人的整个人生观是对抗性的……我们的观点完全相反,我们是要化的,因为化了所以能忘我,忘我所以能合一,和音乐合一,和听众合一,音乐、音乐家、听众都合一。换句话说一切都是水平式的关系。听众好比孙悟空变出来的几千几万个自己的化身。”(1965.5.18)
现代西方哲学的“视域融合”“主体间性”等,似乎都可以在音乐家的这席妙语中得到共鸣。但这席话的文化根底,可以追溯到中国的老庄,追溯到魏晋汉唐的艺术品味。
由此可见,中西文化的融通之路,可能不是一味“向外走”,而是要同时“向内走”。傅雷讲:“对自己的文化遗产彻底消化的人,文化遗产决不会变成包袱,反而养成一种无所不包的胸襟,既明白本民族的长处短处,也明白别的民族的长处短处,进一步会取长补短,吸收新鲜的养料。任何孤独都不怕,只怕文化的孤独,精神思想的孤独。”(1963.11.3)
所以说,傅雷创造的这个世界里,从为人到为艺术,是道器融通的、是诗乐互训的、是中西合璧的!过去未曾孤独,现在和将来也不会孤独。
走进《傅雷家书》的读法
如何才能走进《傅雷家书》?很多人可能会选择“跳读”,毕竟家书是“家常话”,没有动人的情节,不注重文学化的表达。但倘若“跳读”,则难免断章取义。所以,倘若时间充足,还是应该仔细地、连贯地读,当作与朋友聊天和漫谈,“设身处地”地品读、思考。
首先,“知人”中阅读。《傅雷家书》围绕傅雷、傅聪和朱梅馥展开。尽管我们都已知傅雷夫妇的人生结局,但在他们人生的最后十年,有着怎样的状态和境界,却是含混模糊的。例如,读到1957年3月后,傅雷的书信戛然而止,多由朱梅馥代写,不禁令人生疑,这样一位关心孩子的父亲,怎么忍受没有书信的日子?又例如,1961年左右,傅雷夫妇如何度过生活的拮据?逆境之下的傅雷如何自处?带着“知人”的好奇心阅读,看似平淡的书信,却如同有了纪实小说般的魅力。
其次,在音乐、绘画、诗歌等多重对话中阅读。《傅雷家书》创造了一个跨越时空、文化的非凡的艺术世界,因此,我们還可以尝试在多重形式的呼应中作艺术的巡礼。例如,傅雷和傅聪对萧邦、巴赫、贝多芬等音乐家有着深入的探讨,我们可以听大师的音乐,对照书中的评价来印证和感受。又如,书中多次提到了中国诗,我们可以结合诵读白居易的《琵琶行》,以此感受书中谈到的音乐美;诵读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来体会萧邦音乐中的“诗仙”气质。再如,傅聪的结婚礼物是《敦煌壁画选》,结合敦煌壁画的欣赏,想必更能帮助我们走进傅雷所探讨的艺术问题。此外,书中还多次提到《约翰·克里斯多夫》,丹纳的《艺术哲学》,以及《世说新语》《人间词话》等,都可以作为参考文本,一起品读。
如此,当我们沿着傅雷父子的艺术探寻之路阅读,未尝不能曲径通幽,而见识别有洞天。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