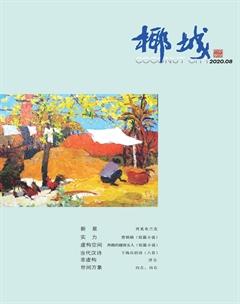向左,向右
作者简介:沐沐,江西人,客居厦门,厦门市作协会员,发表散文作品若干篇。
一
他在岔路口停下来,面前有两条路。左边,是巷弄,向前延伸20米即巷子口。在老城区,这样的巷子如河道密布,有的断了流,更多的汇入更大的河流;右边,是一个大铁门,门被卸了,只剩铁门架,铁门后是一幢灰黄的旧楼房,外墙驳杂。
他驻下脚步,不知作何选择,左右两个选项都似是而非。他低下头,竭力地回想,快速回忆,在脑子寻找蛛丝马迹,然而,记忆一片混沌,没有任何清晰的指向。他被这个二选一的选择题难住了,这不比外甥女考试,选错了,只是失分,顶多挨顿骂而已。他隐约感知到,这个题面,凶多吉少。更让他惶惑的是,记忆如鸟群一轰而散,他是鸟喙里掉落的谷粒,正乘着风坠落,来路杳杳,去处渺渺。
河水滔滔,云层漫卷。
记忆的浮冰不断被抽离,立锥之地岌岌可危,他有失重的眩晕,不敢作丝毫动弹,就那么仓皇地站着。
一旁有个人,坐在凳上,打量着他,那是个环卫工人。他其实早已洞悉,这日日下楼买菜和他打招呼的老头,异于常人。此时,他饶有兴趣地盯着老头,像个猎奇者,对于左右这种答案,守口如瓶。他的工作很闲,日日枯守着几个垃圾桶,在他的头顶,是楼房搭出的铁皮窗,银灰的铁皮窗,一层一层,逐层而上,直逼银灰色的天空。来来往往的人眼皮也不抬地从他身旁走过。他是个被遗忘的人。此刻,他打量着面前这个被记忆抛弃的人,看他额上汗水渗出,看他目光涣散……他的嘴角浮起了狭促的笑。
“这人怎么这么坏,就不能给你爸指一下路?”老妈转述给我听时,还很忿然。她说,她只是驻脚问了下西瓜的价钱,就耽搁了那么一下,老爸就一个人往前走了,在自家楼下做人生选择题,还好,她及时赶到了,老爸才没有作出发生方向性错误的选择。
每天走的路都有陷阱,对于老爸,家门口以外的每一寸地方,都布满了潜藏的凶险。这不是他的麦山垄,他闭着眼睛也能数出有几条沟沟壑壑的麦山垄。
他离开麦山垄,缘自女儿的求助。年过不惑的我被生活逼着做了第二职业,这个职业是教书育人,且教的是唬人的四大名著。对于一个并没有完全看完四大名著的人,要讲四大名著,且在两个小时不停歇地讲,太具挑战性。我道行不深,不能信口开河,我也不具备信口开河的能力,况且班上有个熟读三国的熊孩子,我一开口他就能滔滔不绝地接下去,如此,压力如泰山压顶。加之记性奇差,备好的课,转眼就能忘掉,所以做的功课要比想象的多得多。
早上六点多,从床上一骨碌起来,就猫一般伏在电脑面前,梳理的不是头发,而是各个情节和知识点。晚些时,女儿小叮起床了,被逮过来,听我试讲,如有卡壳或没讲透的,再查看资料,打通脉络。下午与学生们斗智斗勇两小时,课后写反馈、发反馈,与家长交流,紧接着备第二天的课。我像一个钟摆,被内部的巨大机制牵引着,规律、刻板地摆动,不能有片刻停顿和喘息。九岁的小叮确实能干,去买菜每次都买回一荤两素,加上冰箱的存菜,能凑合着吃一天,只是她再能干,也没办法煮出一家人的饭食。和小时候一样,放牛回到家,看着冷锅冷灶,就倚在门口,盼着我妈回来煮饭。是的,没得吃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他们——我也只能想到他们。我妈是个爽快人,她说玩就不去了,如忙不过来,需要帮忙,就去。打开天窗说亮话,我把窘状告诉了他们,他们如以往一样,义不容辞地来了,救我于水火中,给我带来了温暖的吃食。
可老爸离开了麦山垄,如同鱼儿离开了水,鸟儿离开了山林,步步惊心。每一步都是选择题,向左,向右,对他来说是最大的人生难题。哪怕是每晚从二楼到底楼扔个垃圾,老妈一再叮嘱后,终是不放心尾随而去。偌大的城市,是个巨大的迷宫,丛林密布,野花星散,鸟兽奔突,幽深又不乏凶险。老爸早已失去了探求的能力,从一开始的焦燥,转而无奈、哀怜,他早已收起了他的好胜之心。他像个乖孩子,从不独自出去涉险,除了和老妈去趟菜场,帮忙拎个菜。老妈这段时间腿不好,走不了路,去菜场短短的路,走上几步,就要坐着歇一会。而我们,都忙得脚不着地,没人领他出去,老爸只能困守在屋子里。
困守在屋里的人有多捣蛋。每天早上起床,我眯著惺忪的眼睛,找我的眼镜,四处搜寻,终于看到我亲爱的伙伴正两脚朝天,被放置于桌上。钢琴上及书桌上的,所有夜晚从鼻梁上功成身退、休养生息的眼镜都四仰八叉。不用说,是老爸干的,除了他,谁这么“好心”,这么操心。他孜孜不倦地纠正我们的“错误做法”。我告诉过他,不用翻过来,镜片搁桌面易磨损,他睁大眼睛,说:“这样啊,晓得了。”第二天照旧,镜面贴桌,镜腿朝天。
洗完澡出来,咦,穿的还是一身的脏衣服,带进去的干净衣物,已被他浸泡在水里了。老妈自然气极败坏。有时,我的衣服放衣篮里没及时拿出,他也不分青红皂白地套上,白T恤吊在身上,短了一截,把我们笑得前仰后合,他还很无辜地愣在那,不知道我们在笑什么。之后,每次洗澡,老妈都要中途冲进去,把脏衣服及时拿出来。老爸对此很抗拒,说,男人洗澡,女人家进来做什么。刚洗过澡,过一会,又去洗个澡。一天洗两次澡是常有的事,把一辈子的泥土味儿都洗没了,七十多岁的人儿,头发洗得发亮,香气沐人,照我二姐的话说,像个城市人。
这么多天了,还没学会开电饭煲。头天发生的事,他毫无印象。为了让他有点乐趣,我把女儿的一只溪鱼交给他养,这只溪鱼在水瓶里自在地生活一年多了,不料,他一接上手,隔天就翻肚皮了,肚子胀鼓着,是撑死的。鱼是傻瓜,喂的人没记性,一遍接一遍地扔下食物,它也不管不顾地一遍又一遍地吃,真是不自量力。更糟糕的是,老妈说他越来越爱撒谎,对没发生的事情振振有词,无中生有。一天,他又在找烟斗,找烟斗是几十年的历史了。我很小的时候,他就经常将烟斗遗落在田间地头。这次准备行李时,老爸掖了一卷烟丝。老妈说,你带烟丝不带烟斗,怎么抽?于是,老爸在包里塞了一根烟斗。现在,唯一的烟斗找不到了,老爸急得很,外面有烟买,可他说忒贵,烟丝才多少钱,骗骗嘴的东西,要抽那么好干嘛。他找来找去,翻箱倒柜,没找着烟斗。后来,他一拍脑袋,说,哎呀,差点忘了,刚掉进外面平台的坑里了,想捡来着,但坑里太脏了,又够不着,就算了。我们信以为真,就此作罢。第二天,打开抽屉,老爸的那根烟斗赫然在目。
这样的他,自然总挨我妈的训。他也不辩嘴,呆呆地站在窗前,眼睛空空荡荡的。窗外是一幢幢矗立的高楼。城市的天空属于高楼,不属于鸟儿和云朵。他有时会有所觉悟,很懊恼地拍拍自己的脑袋,埋怨道:“现在,这脑子都不知怎么了?不中用得很。”我安慰他说:“年纪大了,记性差些,很正常。”我妈在耐心用完了时,会冲他喊:“你怎么变成这样一个人啦!”喊声带着哭腔。喊得我心里直发抖。
二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我也问自己。我小时候明明是会包粽子的,可现在我妈来了,包了三次粽子,她包得很好、很快,我照样画虎,还是没办法把粽叶裹紧,米撒了出来。算了,不学了。我是越来越笨了,也越来越懒了。我不想费脑去钻研事。孩子喊,妈,看你这道题会不?然后她读出一串数字,我一听,立马捂住耳朵,连连告饶:“不会不会,别问我,我什么都不会。”
填报女儿的校服尺寸时,突然不确定女儿读哪个班。怎么也想不起坐我对面的同事姓什么。更别提经常性地忘带钥匙、忘记关火,在街上遇到个人,很面熟,却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是谁,诸如此类的糗事——未酿成大害的惊险只能付之一笑。记忆如此经不起推敲,仿佛一夜之间已化作齑粉,消融于时间那条无形的河流,打捞不起半点残渣。很熟悉的词语突然想不起来,敲字显得极为困难——这才是最具毁灭性的打击,在文字的道路上,我还没起步,就已经宣告夭折。记忆力就是想象力——我无比赞同这句话,没有记忆那根无形又精准的航线,想象的双翼何以划开天空?幸好,我未曾失去远期记忆,小时候的事情仍清晰如昨,那些画面仍存放在记忆的匣子里,被时间封存为琥珀,透明的质地里犹见飞虫的最后行迹。就如父亲,他在城市险象环生,然而在麦山垄,那个他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他对每条山垄,每座矮冈,每一个岔路,都了如指掌。在那里,他来回自若,除了每天把农具丢掉,没有向左向右的困扰。
我越来越像我爸,看得见是长相:嘴巴突出,牙齿外突且参差不齐,有一颗门牙,连歪斜着的角度都和他一模一样。还有看不见、潜藏于内的。比如,不爱说话。他不爱说话,干活回来,就独自待在房间里抽烟斗。我也是,我几乎不主动联系人。有时姐姐们发来微信,我都不回或者忘了回。并非真的不想回,而是有心无力,是懒,总觉得说话太费力,总觉得有些话,不需要说。除了必需,我经常失语般地沉默着。
对很多人和事无动于衷。缄默。不再锐痛。我越来越相信命运。心如裹了一层膜,不,是脑。脑子好像包裹了一层膜,让我对一切外在的感受不再那么清晰。是的,不那么痛了,也不那么乐了。很久没有大笑过,也没有大哭过。我像个迟缓的老人,连走路都步履缓慢。生命似乎进入了秋天,秋风吹着吹着,叶子就凋零了。
确凿无疑,父亲患了一种病——阿尔兹海默症,俗称老年痴呆症。而一切的指象都在预示着,我可能是下一位继任者。这种发生于老年前期和老年的中枢神经退行性病变,已经越来越年轻化了。报上曾登载过一个三十八岁的女人找不到回家的路。我呢,已露出种种迹像,向左向右那道选择题我也绕不过,怎么都得做。
我对老爸并没有老妈那么的不耐烦,因为照顾他的人是她,不是我;也因为他经历过的,我正在经历,感同身受,才能给予最好的了解和宽慰。就如外人无法理解我的困扰,他们总说记性差是很正常的,他们也记性越来越差。而且,他们说,你还讲课,在写东西,都在用脑,怎么可能会痴呆。于是,我缄口,不再诉说。是的,没人会认为,“记忆力不太好”,是什么要紧的疾病。
我对老爸的怜悯,更多是基于对自身的怜悯。
研究者说,老年痴呆症的症状是从舌头开始的,说话变慢,表情呆滞。确实,那个曾经对我们家的牛和猪破口大骂的老爸不见了,他轻易不再开口,难得开个口,也是慢慢斟酌,我很少再看到他疾言厉色的样子。
嗜睡也是症状之一,一切迷团得以解开。我以为,老爸来了,会禀承原来的好习惯,帮我干些家务活的。可我讶然发现,村里第一勤人,变成了一个懒人。每天上午,老爸和老妈去一趟菜市场。然后老妈整菜、择菜,我坐在电脑面前备课,孩子做作业,而老爸呢,戴着眼镜,捧着女儿的《三国演義》看。静谧又详和的气息,在屋子里弥散开来。看书挺好的,老爸一直爱看,我一直记得小时候,晚上,干完一天的农活,或难得的大雨天歇在家,他就读书,是真的读出声的,拖着调念,像吟哦,吟得窗外瓢泼的大雨都静下来听。小伙伴来家,惊问,你爸在唱歌吗?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缄了口,不再吟书。他戴着黑框眼镜,坐在窗前,默默地看书,像个老学究。一会,窗前的人不见了,再一看,他已躺上了床,打着呵欠说困。
我给孩子讲课时,他好奇地坐在一旁,眼睛睁得大大的。突然一阵呼噜声,像波涛一样起伏。我和孩子们面面相觑,只见老爸正倚靠在沙发上,嘴巴有节奏地一张一合。每日中午吃罢饭,睡午觉至三四点,晚上看两集电视,又上床了。他的觉越睡越多,越睡越没精神。像关在笼子的一只鸟,总是恹恹的。偶尔张望着外面的世界,久而久之,外面的任何动静便激不起他的兴致了。
三
阿尔兹海默症,我一点也不陌生。先生的外婆就是患此症者,她是一个好人,一个人独居在山上,山脚的农人到山上摘油茶、砍菜、种地,甚至躲计划生育……到了她土屋,她都留人家喝茶吃饭。粮食紧张的时候,她宁愿自己不吃,也会给那些冒昧上门的人一碗热饭吃。可有一天,她发现自己种的一地番薯被偷了,而偷番薯的人,是和她贴心贴肺好着的女人。那个女人住在另一山坳里,是外婆在山里唯一的近邻。这件事颠覆了她原有的认知,她的认知是那么朴素,那就是人应该礼尚往来、好来好去。她没有去找女人讨要番薯,也没对任何人声张,而是将此事闷在心里,然后,像大病了一场,她开始神情恍惚,记忆锐降。
勉强在山上撑了几年,实在没办法独自生活时,外婆被在城里上班的儿子接回了山脚的老房子,让一个本家给她管饭,可她一天到晚不着家,饿了,到处翻垃圾吃。原来受过她恩惠的人遇着她,会装碗饭给她。最后,一辈子体面,领口那个盘扣都扣得紧紧的外婆,把衣服撕掉,敞着身子,在外游荡。有一天,在外面摔坏了骨头,再也不能走动,躺在床上,咽气的时候,半边身子都烂了。